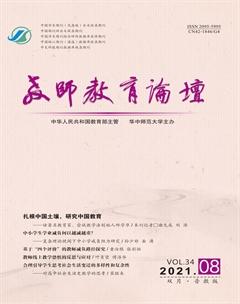生態系統理論視角下課堂“邊緣人”的生成機理及轉化路徑
摘 要 課堂“邊緣人”處于課堂教學的邊緣地帶,是教學過程中的“沉默者”、班級活動中的“隱形人”、情感支持中的“孤獨者”,這不符合微觀層面教育公平的內在訴求,急需關注和轉化。基于生態系統理論,課堂“邊緣人”的形成受到微系統、中系統、外系統、宏系統等多重環境的影響。因此,從“邊緣人”可接觸的環境系統出發,教師、學校和家長要發揮家校期望的正面效應,搭建家校合作平臺,打造溝通融合的文化生態,促成“邊緣人”的轉化。
關鍵詞 邊緣人;課堂教學;生態系統理論
中圖分類號 G45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5995(2021)08-0067-04
課堂是每一個學生健康成長的原野,教學是促進每一個學生全面、充分發展的基本途徑。然而,在現實教學過程中總有一些學生“處于課堂教學的邊緣地帶,無法得到良好的發展”[1],這類學生個體或群體被稱為課堂“邊緣人”。課堂“邊緣人”往往在課堂教學中受到極少的關注,他們既沒有優等生備受關注的光環,又不像后進生“惹是生非”,引起教師注意。他們往往被教師遺忘或忽視,成為默默無聞的群體,這不符合微觀層面教育公平的要求,急需關注和轉化。生態系統理論把環境看成一個相互聯系、不斷變化的“動力變化系統”,認為個體發展是自身與其周圍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課堂“邊緣人”的形成,受到了家庭、學校、社會等多重環境的影響。因此,透過課堂“邊緣人”存在的問題,探尋其在生態系統中的生成機理,對于該群體的轉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現實關照:課堂“邊緣人”問題凸顯及其價值考量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出了一個“差序格局”的概念,認為社會系統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被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社會聯系,而圈子的大小和強弱與血緣、地緣、經濟水平、政治地位、知識文化水平密切相關。由于“差序格局”的存在,那一圈圈波紋如果沒有和其他事物產生任何聯系,就會出現邊緣化傾向,這就類似于課堂的“邊緣人”。他們像被推出去的“水波”一樣,除非有明確的互動規定,否則就很少與人溝通,久而久之在課堂教學中就處于邊緣地帶。有研究指出,所謂課堂“邊緣人”,是指“在日常課堂教學情境中被教師和其他同學排斥或遺忘,或者因自身原因(生理、性格、身體狀況等)拒絕參與教學、主動游離到教學活動邊緣的學生個體或群體”[2]。這類學生很少參與課堂教學的互動過程,有意無意地逃離與教師和同學的溝通,是教學過程中的“沉默者”、班級活動中的“隱形人”、情感支持中的“孤獨者”。
(一)教學過程中的“沉默者”
在新課程改革教學理念的引領下,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課堂教學是師生良性互動以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過程。然而,課堂“邊緣人”群體卻始終以沉默的姿態面對教學過程,他們或是默不作聲、低頭沉思,或是心不在焉、拒絕溝通,是教學過程中的“沉默者”。通常,“邊緣人”課堂參與度低,知識吸收困難,教師無法全面了解他們對知識的理解程度,進而無法做出有效的教學調整,從而導致其教學效率降低,教師逐漸將這類群體拋棄。長此以往,“邊緣人”自身形成消極的學習體驗,自我效能感較低,可能會產生自卑或自暴自棄的消極心理。但有另一類“邊緣人”群體把自身邊緣化的處境視為一種理性選擇,猶如“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狀態,享受沉默帶來的深刻思考。這類學生認為教學只是獲取知識的媒介,而不是自我展示的平臺,他們不熱衷于在課堂討論中展示自己的才華,也不滿足于通過精彩的問答博取教師的歡心。對他們而言,課堂沉默絕非“缺場”的代名詞,而是他們在課堂中的一種理想狀態,這種“無聲勝有聲”的沉默正是他們“從自己、從其他人、從這個世界的最深處呈現出來的表達”[3]。
(二)班級活動中的“隱形人”
班級是幫助學生實現成長和社會化發展的重要場所。換言之,班級是一個微型社會,班級中存在的組織結構、人際互動等都是社會關系的縮影,會直接影響學生社會化的發展。正如杜威所說:“學校環境的職責在于平衡社會環境中的各種成分,使學生能夠和更廣闊的環境建立充滿生氣的聯系。”[4]毋庸置疑,學生必須要在學校環境中學會與他人溝通,培養自身的社會責任感、人際交往能力和溝通合作能力。課堂“邊緣人”性格較為孤僻,喜歡安靜獨處,人際交往能力較弱,很難融入班級活動的小圈子,對自身在班集體中的身份也缺乏認同感。他們由于成績平平、性格內向,在課堂教學中常常容易被教師遺忘,同時,這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其他學生對“邊緣人”的態度。他們既淡出教師的視野,又遠離學生人際交往的圈子,往往被整個班級群體所排斥,其班級話語權逐漸減少,慢慢成為班級活動中的“隱形人”。他們的存在缺乏教師和同學的認可,在班級中無法獲得歸屬感,無法體驗班級文化帶來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人際交往帶來的幸福感和成就感。這種在身體和心理上的排斥和遺忘,使得“邊緣人”體驗著顛沛流離的身體流放,逐漸遠離班級群體。
(三)情感支持中的“孤獨者”
情感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強連帶關系,是一個人是否能與人溝通并獲得關懷的表現。在學校場域中,學生通過群體活動可以培養自身的責任感和合作精神等優良品質,從而實現個體心理向社會群體心理轉變。然而,課堂“邊緣人”由于自身性格的原因或者成長環境的差異,存在明顯的自卑心理,他們覺得自己處處不如人或認為自己的存在無關緊要,當自身需要幫助的時候,很少開口求助,與教師和同學的交往也小心翼翼,甚至避免接觸以求得心安。因而,他們無法與同學建立良好的情感關系,這會導致缺少必要的情感支持和情感體驗,在班級中慢慢變得孤立無援,從而成為情感支持中的“孤獨者”。同時,教師的情感支持可以提高學生的成就動機、自我效能感、學習興趣和學業信心,對學生的不良情緒或行為具有緩解作用。“邊緣人”往往對自己的學習能力喪失信心,在學習活動中處于被動或退縮狀態,自我效能感較低。因此,他們逃避與教師的溝通交流,盡量掩飾自己在學業上的無助,以維持自我價值感,也很少體驗到教師給予的情感支持。
二、生成機理:基于生態系統理論的存在原因透析
人與環境是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整體。心理學家布郎芬布倫納深入分析環境對個體的影響,將人生活于其中并與之相互作用、不斷變化的環境稱為行為系統,并提出生態系統理論。該理論關注兒童所處的多重系統及多重系統關聯的重要性,在布朗芬布倫納看來,兒童世界是由一組從近到遠、相互嵌套的系統或環境因素組合而成,即:微系統、中系統、外系統和宏系統。從微系統到宏系統,對兒童的直接影響逐漸減弱[5]。
(一)微系統:家庭關懷與教師期望的異化
微系統是課堂“邊緣人”生活的最里層環境,是其直接接觸的環境系統,該系統對其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就學生而言,家庭和學校是對其影響最大的微系統。家庭是學生成長的重要場所,家庭成員之間的關懷對學生的健康成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父母的教育方式會對學生性格的養成產生深遠的影響。在內爾·諾丁斯看來,“沒有什么比一種穩定、充滿愛的關心更重要的了”[6]。課堂“邊緣人”的家長往往忙于工作,無暇顧及子女的教育問題及心理健康狀況,特別是那些從小家庭出現變故的兒童,他們可能缺乏父母的關心,由此產生自卑心理,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逐漸喪失自信,久而久之,性格變得孤僻。家庭關懷的缺失在課堂中的表現即兒童淪落為課堂“邊緣人”。
從學校系統來看,目前大多學校教育指向精英教育,教學被視為促進社會發展的工具和手段,而學生個體的生命價值卻受到漠視。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會對學生有一種預先的經驗性期望。如果教師對學生表現為正向的期望,就會對學生的學習和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反之,則會對學生的課堂參與產生負面影響,這就是教師期望的負效應。受學生性格、家庭情況、已有成績等刻板印象的影響,教師一旦給學生貼上某種標簽,就很難改變,甚至將學生推向課堂的邊緣地帶。[7]
(二)中系統:家校合作的形式化
中系統是指各微系統之間的相互聯系。布朗芬布倫納認為,如果微系統之間有較強的積極的聯系,個體的發展可能實現最優化。相反,如果微系統間關系疏遠可能會阻礙個體的成長。家庭和學校是對學生影響最大的微系統,因此,家校合作是教育發展的必由之路,是構建良好中系統環境的堅固基石。根據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喬伊斯·愛普斯坦教授提出的交疊影響域理論,家長、學校和社區三方是合作伙伴關系,三者通過彼此之間的交集領域的教育疊加作用,共同影響兒童的健康成長,幫助兒童在學校和未來生活中取得成功[8]。然而,我國家校合作存在主體責任模棱兩可,家校合作形式化等偏差。[9]從家長方面來看,隨著學校教育專業化的進展,子女教育的主導權由家庭讓渡給了學校,家庭教育的功能逐漸弱化。一些家長處于“合法的邊緣性參與”狀態,他們忽視自身的主體責任,把子女的教育歸為學校的責任,對家校合作敷衍了事,對子女的在校情況置若罔聞。家長的這種“低關注度”使其子女在班級中缺少家庭支撐,進而導致其班級話語權減少,逐漸走向邊緣化。從學校方面來看,一些學校將自身視為絕對的權威,期待家長的“配合”而非“合作”,忽視家校“主體間”的平等協商,這導致家校合作流于形式,沒有實效。學生的在校表現仍是教師“一言堂”的評價,學生逐漸演變為課堂“邊緣人”。
(三)宏系統:文化發展的差異性
宏系統指的是滲透于學生發展的各個層面,存在于以上三個系統中的文化、亞文化和社會環境。學校文化是全校師生經過長期積淀形成的具有本校獨立精神的文化傳統,是區別于其他學校的內在標識,其核心是精神層面中的價值觀念、教育理念,擔負著“以文化人、以文養人”的重要使命。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人們的價值取向逐漸偏向功利化和工具化。教育的消費化、學習的功利性日漸突出,學校教育真正的“育人”功能減弱,僅僅局限于提高學生的考試成績,提高學校的升學率等硬性指標。在功利性的學校文化影響下,那些學習能力較弱,競爭力不強的學生就被排斥在主流的學校文化之外,難以獲得教師積極的關注,逐漸淪為課堂“邊緣人”。從文化社會學視角來看,課堂“邊緣人”是文化沖突的產物。在不同文化的影響下,個人會形成不同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在交往過程中可能出現價值意識的沖突和思維習慣的碰撞。而一些具有異質文化的學生缺乏文化適應能力,與班級環境擬合不良,對陌生的文化符號認同感較低,因而無法融入班級主流文化。
三、“去邊緣化”:基于生態系統理論的轉化路徑
課堂“邊緣人”的存在,不僅與微觀層面教育公平的內在訴求相違,而且阻礙了全體學生全面發展的教育目標的實現。基于生態體統理論的歷時系統,通過系統間的相互配合,課堂“邊緣人”會隨著時間和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因而,我們可以借助系統科學的整體涌現性來說明各系統有序參與的重要性。整體涌現性指整體具有的,但其組成部分以及部分之和不具有的特性,一旦把整體還原為它的組成部分,這些特性便不復存在。“非平庸的涌現論帶來的不是物質數量的增減,而是異質的涌現——信息的創生與消除。”[10]在教育系統中,我們可以運用系統思維,按照涌現論識物想事,厘清整體與局部的辯證關系,從微系統、中系統、宏系統等方面探尋課堂“邊緣人”的轉化路徑。
(一)“摘除標簽”:發揮家校期望的正效應
教師的期望決定其對待學生的態度,間接影響學生的行為和自我認知。因此,教師對待所有的學生應一視同仁,避免出現“消極標簽”。當教學活動結束后,教師要及時反思,給予每一位學生尊重和關懷,特別是對于在課堂中處于邊緣狀態的學生,教師要慎之又慎,尋找適合該群體改變的方式。同時,教師要發揮期望的正面效應,適當運用鼓勵式教學,促進學生的正向發展,也要善于發現每個學生區別于其他學生的獨特優勢,捕捉學生的閃光點,并將之遷移至學習過程中,幫助學生樹立學習的主人翁意識。特別是在小組合作學習中,“邊緣人”往往以隱形的狀態存在,這時教師可以通過鼓勵,給予“邊緣人”更多的話語權,促進其思想的轉化。
“邊緣人”問題的轉化僅僅依靠教師轉變教學還遠遠不夠,還需要家庭無微不至的關懷。首先,家長應對子女的學業成績抱有合理的期待。“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思想在中國父母的心中根深蒂固,家長總是期望子女成為學生群體里的佼佼者,但是這種期望對于子女來說可能是“生命無法承受之痛”。這導致一些學生通過逃避學習來躲避父母的期望,從而逐漸邊緣化。因此,家長要根據子女的性格特點對之建立合理的期望值,樹立賞識教育理念,尊重子女個體發展的差異,充分接納子女的教育訴求。家長也應與子女進行“零距離”溝通,以朋友的身份關心子女的在校情況,做子女無話不談的“知心人”,營造溫馨和諧的家庭氛圍。
(二)“積極性溝通”:搭建家校合作平臺
家庭和學校是對學生影響最大的微系統。每個學生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不同。因此,為了促進不同學生的發展,搭建良好的家校合作平臺至關重要。哈貝馬斯認為現實社會中的人際交往行為是一種“主體間性”的行為,主體間通過理性交往和平等協作,以達到共贏的目標[11]。因此,家庭和學校要明確自身在合作中的地位,平等合作,避免合作異化。一方面,教師要樹立伙伴型家校合作理念,發揮主導作用,但不能以權威者的身份向家長發號施令。另一方面,家長要正視自身的主體地位,不過于自卑,視教師為絕對的權威,也不過于強制,隨意干涉學校事務。
根據列維納斯的他者性倫理思想,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是一種為“他者”負責的關系[12]。家校應明確自身在合作中的責任,以學生為共同的“他者”,尊重“他者”的特殊性,明確家校共同的“利他”目標,避免家校合作流于形式。家長要避免以工作忙、教育能力低為理由將教育責任全盤推給學校,要明確自身在家校合作中的主體責任,自覺更新教育理念,共同搭建家校合作平臺。學校和教師要豐富家校合作的形式,除了傳統的家長會,還可以通過對邊緣學生進行家訪,邀請家長定期訪校等方式,充分了解學生的家庭環境,使家長了解學生的在校情況及學校的教育情況,與家長達成有效共識。
(三)“共生共榮”:打造溝通融合的文化生態
我們處于共生共榮、命運與共的新時代,任何個體都不能因自身差異而成為自我隔絕的孤島,我們理應與課堂“邊緣人”群體積極溝通,幫助其轉化。基于社會多元文化的格局,當學生自身的異質性文化與班級文化發生沖突時,我們應對學生進行多元文化教育,促使其發現多元文化的獨特魅力,突破情感與地域帶來的局限,認識多元文化底蘊。學校和教師要通過選擇、傳承、創造文化,實現文化與人的雙向建構,進而幫助課堂“邊緣人”回歸課堂文化中心。從文化生態的視角來看,班級文化是塑造學生共同價值觀、培養學生品格、激發學生集體榮譽感的重要因素,也是促進課堂“邊緣人”回歸課堂中心的重要環境系統。因此,我們要打造和諧、民主、自由、積極溝通的班級文化氛圍,通過學習互助小組、師生互動、學習討論等方式,以情感為紐帶,提高“邊緣人”的課堂參與度,讓“邊緣人”逐漸回歸課堂中心。正如杜威所說:“個人參與某種共同活動到什么程度,社會環境就有多少真正的教育效果。”[13]我們應鼓勵“邊緣人”不斷參與班級活動,與班級同學形成共同的愿景,增加其自主實踐的機會,使之成為班級環境的塑造者。
(蔡婉怡,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院,西安 710062)
參考文獻:
[1] 李森,杜尚榮.論課堂教學中的“邊緣人”及其轉化策略[J].教育研究,2014(7):115-122.
[2] 亓玉慧.課堂教學中的“邊緣人”現象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14:32.
[3] [美]帕克·帕爾默.教學勇氣:漫步教師心靈[M].吳國珍,余巍,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79.
[4][13] [美]約翰·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旭,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27,28.
[5] 劉杰,孟會敏.關于布郎芬布倫納發展心理學生態系統理論[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09(2):250-252.
[6] [美]內爾·諾丁斯.學會關心:教育的另一種模式[M].于天龍,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4:125.
[7] 亓玉慧,李森.論課堂教學中邊緣人的形成過程及應對策略[J].教育科學,2014(2):32-37.
[8] EPSTEIN J.School,family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preparing educators and improving schools[M].Boulder:Westview Press,2001:156-158.
[9] 汪敏.家校合作的主體邊界與實踐范式[J].教育科學研究,2018(12):66-72.
[10] 苗東升.論系統思維(六):重在把握系統的整體涌現性[J].系統科學學報,2006(1):1-5,81.
[11] [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M].童世駿,譯.北京:三聯出版社,2003:88.
[12] 劉要悟,柴楠.從主體性、主體間性到他者性——教學交往的范式轉型[J].教育研究,2015(2):102-109.
實習編輯:劉 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