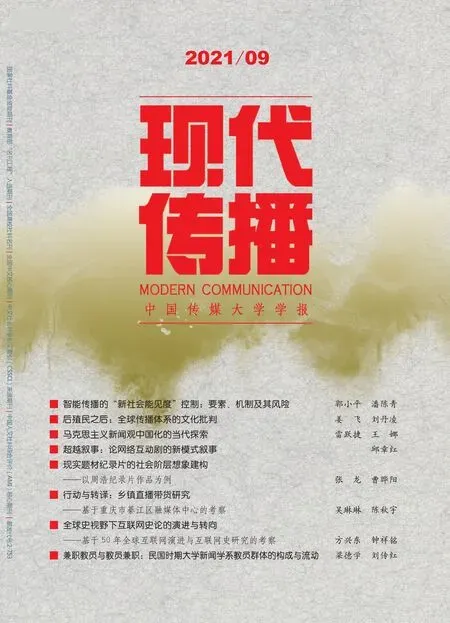現實題材紀錄片的社會階層想象建構
——以周浩紀錄片作品為例
■ 張 龍 曹曄陽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從認識論的角度而言,當今社會中的很多矛盾沖突其實與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誤解密切相關——由于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群在信息獲取的方式、數量和質量上有顯著差異,其認知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便也囿于所接觸的社會環境而逐漸分化。每當社會沖突事件發生后,媒體的爆炸式傳播與大眾的狂歡式輿論更會使社會中的“二元對立”情緒迅速高漲,進一步加深不同階層之間的理解鴻溝。
由此,在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的當下,媒體應當怎樣扮演起社會調和者的角色?大眾傳媒應當如何促使公眾對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形成全面的認知,從而建立起對其他社會階層人群的理解與信任?能否通過社會階層想象的構建,從認知層面促進社會階層之間的理解,進而改變公眾的行動,保障社會的有機流動與穩定發展?
本文認為,在眾多類型的媒體產品中,現實題材紀錄片顯得尤為特殊。現實題材紀錄片是對社會進行真實記錄的一種影像文本,它不但能通過非虛構敘事真切地反映社會問題,還可以對具體人物、具體社會環境進行生動的刻畫,從而推動公眾對社會問題的理解和反思。目前,中國已經有大量現實題材紀錄片的創作者和代表作。本文所關注的導演周浩,從21世紀初就開始扎根中國社會進行現實題材紀錄片創作,以寫實的拍攝手法與獨特的敘事視角呈現了中國多階層的社會面貌,在國內外獲得多項紀錄片大獎。本文采取影像文本分析方法,對周浩導演在2002—2018年間創作的13部社會現實題材紀錄片作品進行研究,旨在探討其建構社會階層想象的方法,以期為同類型的紀錄片創作提供借鑒,并對現實題材紀錄片的社會角色進行深入思考。
二、從認知差異到社會穩定:社會階層想象的建構
(一)社會階層的概念內涵
學界對于社會階層(social stratum)一直有著不同角度的理解。馬克思最早對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論述,認為社會階級起源于社會分工,生產資料和勞動的占有關系是階級階層劃分的標準,而共同的生活方式、階級利益和教育程度是劃分階級階層的必要條件。①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則強調多元的社會階層理論,將階級(class)、等級(status)和政黨(party)三者相綜合,作為階層劃分的依據。與二者的思想不同,涂爾干(émile Durkheim)從功能主義視角出發,將社會分工視為社會團結的本質條件;在此基礎上,以金斯利·戴維斯(Kinsley Davis)和威爾伯特·摩爾(Wilbert E.Moore)為代表的功能論學者開始將職業結構作為階層劃分的主要依據,強調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和社會整合。而與之相對立的是,以梅爾文·圖明(Melvin M.Tumin)為代表的沖突論學者則將權力關系視作社會階層的劃分依據,并且認為社會分層是社會沖突的根源,它造成了社會成員不平等的身份感受,應當消滅社會分層。②
本文認為,功能論學者的觀點更加契合社會分層在中國當下的現實意義。在當代社會中,區分人們社會地位的主要因素是職業,正是在職業的基礎上才產生了不同社會成員在收入、聲望等方面的差異。正如美國社會學家彼得·M·布勞(Peter Michael Blau)與奧蒂斯·達德利·鄧肯(Otis Dudley Duncan)的觀點:“階級雖然可以根據經濟資源與利益來定義,但是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決定這些的首要因素是其職業地位。”③職業地位高的人群在專業技術、收入、社會影響力等方面具有更顯著的優勢,因而其社會階層地位就越高;反之,職業地位越低的人群,工作崗位對其能力要求相對更低,其收入、社會影響力相對較差,因而社會階層地位也就越低。
社會階層的劃分與社會的不平等密切相關,但這種不平等在功能主義學者看來,反倒是一種確保社會穩定的機制。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指出,分工建立起的道德價值秩序能夠促使個人意識到自身對社會的依賴關系,社會也能夠由此對個人形成約束,從而促進社會團結。④美國社會學家金斯利·戴維斯則認為:“社會不平等是一種無意之中發展起來的手段,有了它,社會可以確保最重要的職位由最具資格的人來盡職盡責地承擔。”⑤社會分層一方面推動有能力的人去追求難度更高的工作崗位,另一方面,又激勵處在這些位置的人承擔起他們的職責。⑥換言之,社會分層在督促各個階層各司其職的同時,還能夠激勵處于社會較低階層的人向社會上層流動,在大融合、大發展的時代背景下,這種分層機制帶來的社會流動跨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宏大,社會各階層能夠在良性的競爭中維系著社會各項功能的穩步運行。
總結社會階層的概念內涵,本文認為:由于天賦條件、受教育程度、個人興趣和家庭資源等多方面的差異,社會成員占據著不同的職業結構位置,擁有著不同的經濟能力、政治資源和社會地位,從而使社會結構出現群體性的層級化。這些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層級位置就是相應的社會階層。認識社會階層的差距,有助于媒體工作者尋找社會問題的根源,通過紀錄片等媒介產品為觀眾呈現更加全面的社會現實,促進不同社會階層間信息鴻溝的彌合,增進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理解,從而促進社會流動,保障社會發展的活力與和諧穩定。
現如今中國的社會階層劃分已較為詳細。中國社會學家陸學藝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以職業結構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情況為標準,將當前中國社會結構劃分為十大社會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⑦
陸學藝表示,社會階層劃分的目的不是強調各階層之間的對抗關系、敵我關系,而是促進各階層之間的相互妥協、協商和廣泛合作,走“聯盟”、共贏的道路。研究中國各社會階層的變化、地位、特點,有助于協調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團結和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來實現經濟發展,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⑧而站在紀錄片的角度而言,理解社會階層的劃分有助于把握階層的特性,觀察階層之間的互動,從而建構準確的社會階層想象——這對于促進社會階層之間的理解、協商、合作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社會階層的想象
在社會學中,“想象”(imagination)具有深層的社會意義。現實中人們由于長期處于自己的生活情境,形成了自己的社會交往圈層,其社會認知水平往往會受到家庭、工作等具體背景的限制。在看待問題時,人們難以從自己的視角轉換至他人的視角;在面臨困擾時,人們的思維往往局限于有限的視野、經歷和境遇,而不能將自身與社會、與時代聯系在一起。人們需要的,是一種社會學的想象力——根據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C.Wright Mills)的闡述,社會學的想象力是一種觀察個人與社會之間所存在關系的能力,它幫助人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將自己置身于時代之中來看待個人的生活機遇,從而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自己的社會地位、看清世事的全貌⑨,甚至能夠“與那些遙遠而冰冷的世界發生關聯”⑩。
不同社會階層在社會認知傾向上的巨大差異,呼喚著社會學想象力的作用。美國心理學家邁克爾·W.克勞斯(Michael W.Kraus)等人在2012年的研究中表示,低社會階層者由于其追求的目標受到自身較少的經濟資源和較低的社會地位的限制,長期生活在該社會情境中,便會形成一種情境主義(contextualism)的社會認知傾向。他們的心理和行為往往受情境因素的影響,包括真實的、結構性的影響(例如社會不公、社會服務不足),以及外部力量對行為影響的預期(例如對低社會階層歧視的預期)。而對于高社會階層者來說,充裕的社會資源和相對較少的社會限制是其面對的主要社會情境,長此以往便形成了唯我主義(solipsism)的社會認知傾向。他們的心理和行為多由目標、情緒等個體內部因素激發,而忽略和抵制情境因素對行為的影響。
不同的社會認知傾向容易帶來社會沖突,它亟需社會學的想象力來調和。唯有建構準確、立體的社會階層想象,促進相互理解與尊重,才能保證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現實題材紀錄片來源于創作者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真實觀察記錄,在此基礎上,創作者可以充分調用社會學的想象力,為觀眾建構準確、立體的社會階層想象。運用社會學的想象力,紀錄片創作者能夠通過視聽元素的組合、敘事符號的意義串聯呈現社會問題,將具體的社會成員、社會差異與社會矛盾置于更廣闊的社會環境和歷史脈絡中加以審視,從而提升“感官”的維度;而透過紀錄片這一“感官”,社會成員也能夠更加近距離地觀察社會階層的樣貌,深入了解社會各階層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與社會的關聯性以及歷史的必然性,從而建構更加全面的社會階層想象,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三、從“墻上蒼蠅”到影像民族志:周浩紀錄片中的社會階層
中國紀錄片導演周浩曾作為攝影記者供職于《貴州日報》、新華社、《南方周末》等媒體,后于2001年開始轉行做紀錄片并獲得多項大獎,其作品《厚街》獲2003年“云之南人類學影像展”黑陶獎,《高三》獲2006年第30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人道獎”,《龍哥》獲2009年第15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社會類紀錄片銀獎,《棉花》獲2014年第51屆臺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2014年中國紀錄片學院獎評委會大獎、最佳攝影獎,《大同》獲2015年第52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等等。
對于紀錄片創作,周浩并不認同“墻上蒼蠅”(fly on the wall)這類所謂客觀、真實的創作方式。“墻上蒼蠅”是由美國紀錄片導演梅索斯兄弟提出的拍攝概念,即紀錄片創作者要像墻上的蒼蠅一樣,僅僅觀察人物的生活,而不是介入其中,影響故事的發展。但在周浩看來,創作者所帶來的這種影響是無法避免的,“墻上蒼蠅”只是一個“偽命題”;他主張紀錄片創作者走進被拍攝對象的生活中,深入地觀察被拍攝對象,并與被拍攝對象之間真誠地交流。周浩認為,紀錄片呈現的不僅是被拍攝者的生活狀態,還有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關系,它能在深入的觀察與交流過程中展現出人性復雜的層次感。
眾所周知,當今社會不同階層的人群之間由于生活圈子狹隘、集體無意識等原因造成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容易對其他階層的人群產生不理解和不信任的心態,而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對一些諸如警察毆打民眾之類的社會事件集中火力的報道,使得這種不理解和不信任進一步激化。人們對特定社會人群的污名化、標簽化幾乎已成為網絡輿論的常態,而紀錄片是一種能夠幫助人與人之間搭建起溝通橋梁的影像媒介產品。正如周浩所言,紀錄片能夠“增加人們思維的維度”,讓人們“知道這個世界原來還可能有另外一種解讀方式”。不同于當下各類新聞快訊“觀光游覽”式地呈現社會動態,現實題材紀錄片的特點更偏向于“實地調研”,通過長時間的影像民族志呈現人們的私人困擾與所遭遇的具體情境,以社會學的想象力幫助觀眾理性地看待社會的焦慮與淡漠,思考社會問題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讓觀眾腦海中已經固化的認知變得模糊而多元起來。
本文將周浩導演在2002—2018年間創作的主要紀錄片作品信息列為表1,并將作品中所表現的社會階層與陸學藝劃分的中國社會十大階層進行了對應。其中,由于學生群體尚未進入社會,我們將其單獨列為一個關注的對象。

表1 周浩紀錄片作品中的社會階層
周浩作品表現的社會階層非常廣泛,且頻數分布相當,其中對產業工人階層的關注最多,先后用了四部紀錄片對其進行記錄和呈現——《厚街》主要講述了東莞市厚街鎮的某出租房內,外來農民工在日常生活中的爭吵、斗毆、戀愛、非法接生等一系列真實發生的故事,反映了本世紀初農民工艱難的生活狀況;《差館》主要講述了廣州火車站旁的一間派出所內,民警每天接待各種社會人士上門求助的故事,著重反映了春運期間農民工過年回家難的問題;《棉花》和《異鄉的父母》則更加關注農民工遠赴他鄉的工作狀況,講述了農民工父母與孩子之間難以言喻的愛與苦楚。
周浩作品對于專業技術人員階層也較為關注,先后通過三部紀錄片作品,以三種職業人群為視角闡釋了當代社會的三個問題。其中,紀錄片《高三》以教師為視角,展現了班主任王錦春帶領高三學生奮戰高考的艱苦歷程,期間老師對早戀、逃課等校園問題的處理,更是反映了老師和學生之間“關愛”與“不理解關愛”之間的矛盾;《急診》以醫生為視角,以急診室和救護車為窗口來觀察社會眾生百態,如因懼怕抓捕而逃亡的墜樓者、裝病的行騙者、被勸酒而飲酒過度身亡的人等,在展現社會痛點的同時,深度闡釋當下的醫患關系問題;《7%》則以人工智能程序開發師和職業圍棋手為視角,探討AI技術發展對圍棋、乃至對人類社會帶來的顛覆性影響。
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階層等人群也是周浩作品中常見的表現對象。例如《大同》以時任山西省大同市市長耿彥波為主角,講述其在任期間為了振興大同的經濟及文化產業,大力改建古城并遷移數萬居民過程中遭遇的重重挑戰。這一方面是關于城市房屋拆遷問題的深刻探討,另一方面也是對當地政府與百姓之間信任危機的真實寫照。此外,周浩也曾沉至社會最底層,關注活動在社會邊緣的毒販群體——紀錄片《龍哥》中,毒販觸目驚心的生存場景與一段耐人尋味的愛情故事相互纏繞,深刻地震撼了觀眾的想象。
值得一提的是,周浩的大多數紀錄片作品都并非局限于表現某個單一的社會階層,而是在影像民族志中注重展現該階層與其他階層的互動——紀錄片《急診》展現了專業技術人員階層(醫生)與其他階層(患者)的互動,如醫生與癲癇患者的對話、與農民工患者溝通醫藥費、與一名假病行騙者的糾纏等;紀錄片《差館》展現了辦事人員階層(民警)與其他階層(市民)的互動,如民警協調農民工的欠薪問題、自掏腰包幫流浪漢打車、批評“騙吃騙喝”的社會人員等;紀錄片《書記》展現了社會管理階層(縣委書記)與其他階層(商員、百姓)的互動,如書記為市民解決欠薪問題、幫外國企業家慶生、在酒席上酩酊大醉等。周浩紀錄片通過不同階層間的互動來刻畫各個階層,在展現人物特性的同時啟發觀眾對社會問題進行深入思考。這有助于激發公眾的社會學想象力,幫助人們從結構性的視角審視問題、增強理性,從而建構起更加全面的社會階層想象。
四、現實題材紀錄片對社會階層想象的建構方式
(一)社會關聯:差異與共性兩種信息的交叉呈現
現實題材紀錄片通過將差異信息與共性信息交叉呈現,能夠生動地揭示社會階層群體的生活狀態與社會環境,從而以社會學的想象力將社會群體的個人困擾與公共議題相互關聯,幫助觀眾建構準確的社會階層想象。
具體而言,通過展現不同階層的社會認知傾向,紀錄片能夠生動地反映階層間的差異,從而為觀眾補充認知,調動其對社會問題的理性思考。例如,紀錄片《厚街》從農民工所屬的階層視角闡述了在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農民工艱難的生活狀態及其遭遇的重重挑戰。片中一位農民工在斗毆中被打得頭破血流,劉大爺急忙將他送往鎮上的小診所,而診所卻對他的傷勢無能為力,建議劉大爺將其送至“大醫院”就醫。傷者絕望地說:“大醫院,我來不起啊。”短短的一句話,不僅暴露了當時看病貴、看病難的社會問題,也道出了自己對于當下生活狀況的無奈。這一差異化信息,充分表現了低社會階層情境主義的社會認知傾向,展現了其受社會結構影響而產生的主觀判斷。該片段也呈現了米爾斯所指出的公眾理性與社會合理化之間的矛盾,即當下個體的理性意志與能力愈發被科層的合理性所阻礙,人們“‘有’合理性,卻沒有理性;越來越自我合理化,卻也越來越焦慮不安”。這些差異化信息與理性的思辨視角,均能透過紀錄片納入到觀眾的社會階層想象當中,促進社會階層之間的理解。
除此之外,紀錄片中一些具有人情味的片段也能通過共性社會情境的展示,在階層形象的刻畫中增添共性信息,并使其與差異信息互補來幫助觀眾建構更為立體的社會階層想象。例如,《厚街》中的舞女王莉以少女口吻和男朋友說著情話、在出租屋內經歷接生的產婦祝兒抱著自己的嬰兒與民工街坊們打招呼等片段,都通過觀眾熟悉的社會情境營造了人情味;又如紀錄片《大同》中,耿彥波即將離任大同市市長,在滿街群眾不舍的呼喊聲中,一向不茍言笑的“鐵面市長”流下了感動的淚水。這些片段通過發掘愛情、親情、社會人情等人性當中的共同點,激發觀眾的情感共鳴,在更為立體、更加“有血有肉”的社會階層想象之中促進不同階層之間的相互理解。
總結而言,紀錄片通過將差異信息與共性信息交叉呈現,能夠有效地幫觀眾建構社會階層想象。一方面,差異性的信息能夠與觀眾的認知形成補充,吸引觀眾的注意力,豐富觀眾的社會階層想象;另一方面,共性的信息則推動觀眾產生認知共鳴,在某種程度上達成對該社會階層的認同,同時促使觀眾跳脫“獵奇”和“圍觀”的心理,在情感共鳴的引領下走進故事中去。兩種信息交叉呈現,能夠幫助觀眾在認知中建立起自我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私人困擾與公共議題之間的關聯,從而更立體地理解不同社會階層的生活狀態與價值取向,加強社會階層想象的準確性。
(二)社會參與:旁觀與互動兩種講述的融合運用
現實題材紀錄片將旁觀與互動兩種講述融合運用,能夠通過創作者的社會參與營造更豐富的敘事場景,展現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物特征、生存環境和價值觀念,從而提升觀眾社會階層想象的全面性。在全知視角下,紀錄片主要以旁觀的形式來講述故事。這種視角下觀眾幾乎感受不到拍攝者的存在,而是將自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去凝視紀錄片中人物的生存空間,見證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站在時代的角度對社會進行思考。例如在紀錄片《差館》中,民警與各種社會人士之間互動的呈現就采用了全知視角。此時觀眾不會意識到攝像機的存在,而是跟隨敘述者的引領,專心地觀察作品中民警與百姓角色的性格特征與生存環境,去思考他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審視其價值觀念的差異,從紀錄片講述和觀眾自我解讀兩重維度的交織彌合中建構社會階層想象。
在鏡頭外的限知視角下,紀錄片主要以互動的形式來講故事。此時敘述者雖然不出現在畫面中,但是觀眾卻能夠明顯地感受到其存在,這是因為敘述者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故事的發展。限知視角下的互動講述,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建構社會階層想象:
首先,這類敘事視角能夠打破畫面與觀眾之間的藩籬,實現敘事的場景化。例如在紀錄片《龍哥》中,導演將攝像機放置在毒販阿龍所住的出租屋內,營造了封閉式的敘事場景和空間;在導演的引領下,觀眾時而聽阿龍室友對著鏡頭講述偷盜經歷的“斗智斗勇”,時而近距離觀察眾人吸毒的“醉生夢死”,時而又在鏡頭外與阿龍互動,以“朋友”的身份監督阿龍戒毒。如此一來,畫面與觀眾之間的藩籬被打破——在觀看影片時,觀眾仿佛就置身于出租屋場景內,成為主人公阿龍的一名室友,而那些震撼的故事就如同發生在眼前一般。場景傳播不僅能通過互動來提升觀眾閱片的臨場感,還能促使觀眾以想象的身份進入具象的場景符號中,完成不同階層之間社會情境的“想象性”縫合。
其次,限知視角下人物的自我表述有助于展現人物特點,建構細致入微的人物形象。例如在紀錄片《書記》的片尾,時任河南省固始縣縣委書記的郭永昌在車上說道:“所謂縣太爺,有那個‘爺’的感覺,再大個廳長,連個‘爹’都不是。”如此一言,簡直令人大跌眼鏡。郭永昌的話不僅體現出了前文提及的高社會階層“唯我主義”社會認知傾向,也將該縣委書記的官僚主義思想表現得淋漓盡致。影片的片尾字幕列出郭永昌因貪污受賄被依法懲處的信息,也是在向觀眾展示,郭永昌的這種思想和言論與社會大眾相背離,最終只能自食惡果。總之,隨著限知視角下的敘述者與故事中其他人物之間建立起越來越密切的關系,紀錄片也就更有可能捕捉到一些由敘述者自我表述出來的重要信息,這些信息是敘述者在與其他人物的互動中不經意間的真實流露,而不是在導演或記者的提問下經過自身語言組織后形成的表達。因此,與解說詞和新聞采訪相比,這種敘事方式對核心信息的呈現更加流暢自然,對人物形象的刻畫以及社會階層想象的建構也更具沖擊力。
最后,限知敘事視角有助于呈現鏡頭內外的人物關系,增加故事的維度,引發觀眾的深刻思考。在周浩紀錄片中,觀眾經常能夠察覺到導演與被拍攝對象之間的互動,甚至導演有時在故事中可能會被拍攝對象當成自己的“朋友”。例如在紀錄片《龍哥》中,毒販阿龍想要利用與導演周浩的關系,向周浩借錢生存;而周浩為了能夠繼續拍攝阿龍,也選擇自掏腰包對其進行援助。片中有一幕,阿龍對著鏡頭說道:“我現在唯一的朋友就是周浩了。”該幕也成為了整部紀錄片的點睛之筆——正如《龍哥》的英文片名“Using”一樣,周浩導演通過互動式講述暗喻了人與人之間相互利用的關系,以此激發觀眾的社會學想象力,使其得以置身自我命運之外來對其他社會階層、乃至整個社會結構進行審視,從而填補觀眾對社會階層之間的互動以及龐大社會體系的縱向想象。
米爾斯曾指出,社會科學家有三種角色類型——“哲人王”“國王的顧問”和“自我控制團體的理性成員”——前兩者分別具有鮮明的貴族立場和政治立場,體現出與公眾的對立;第三種研究者則以更加獨立、理性的身份參與到社會當中,從個人的經驗出發觀察社會,找到自己在所處時代的思想生活和社會歷史結構中的身居之處,而非將自己視為“外在于社會”的存在。實際上,現實題材紀錄片的創作也同樣如此。具有社會學想象力的紀錄片創作者通常能將自身置于具體的社會情境中,以自己的親身參與作為標尺,呈現社會情境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同時又能適時地從中抽離,通過更廣闊的視野為觀眾呈現社會的本真面貌。在旁觀與互動融合、影像民族志式的講述中,觀眾對社會階層的想象無疑將更加全面。
(三)社會隱喻:對比與承接兩種語義的巧妙傳遞
在社會關聯與社會參與的基礎上,現實題材紀錄片還能通過敘事符號的語義組合,將創作者觀察到的社會問題以隱喻的方式進行書寫和傳達,幫助觀眾建構更加深刻的社會階層想象。具體而言,周浩紀錄片作品中的社會隱喻表達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畫面構圖、蒙太奇和同期聲。
在畫面構圖方面,周浩能夠充分調用現實中已有的元素,向觀眾傳達特殊的意義,建構社會階層的想象。例如紀錄片《棉花》中,一位女工在火車上對著鏡頭唱起了豫劇《誰說女子不如男》,此時的畫面構圖具有極強的沖擊力:畫面的背景是擠滿了整個車廂的婦女,而唱歌的女工作為畫面的主體處于黃金分割線的位置上,暗喻她是這些從河南奔赴新疆打工的婦女們的代表。再配上女工的唱詞——“這女子們哪一點兒不如男”,將畫面構圖與同期聲的語義巧妙地承接,充分展現了民工階層堅韌頑強的品質,豐富了人們的社會階層想象。
在蒙太奇運用方面,周浩創作的紀錄片注重通過表現特定場景下人物的心理來塑造人物形象,建構鮮活的社會階層想象。紀錄片《差館》中,一位市民來派出所里認罪,聲稱自己冤枉了朋友,而且說了“粗口”,對別人造成了傷害。此時導演巧妙地運用了心理蒙太奇的手段,以特寫鏡頭抓取被拍攝對象面部和手部的細節,與同期聲相承接,將其內心的糾結、悔恨表達得既細致又鮮活。周浩在該作品中還多次運用了心理蒙太奇,并列呈現了各色各樣的人物形象,給人以“大千世界,無奇不有”的想象;而在民警頻繁地與這些人物形象進行跨階層互動的過程中,觀眾也自然會對民警所屬的社會階層產生理解與認同。
在同期聲方面,周浩作品十分注重引用人物原聲來渲染情緒,以解構、拼貼的表征方式參與敘事,從而調動觀眾的社會階層想象。在紀錄片《大同》中,市區改建過程中路面及地下管道設計的不合理,致使雨后道路排水不暢,于是就有了一段市民在積水中騎車前行的畫面。導演為其配上了一段大同市民街頭齊唱《紅星照我去戰斗》的同期聲。其中,唱詞“小小竹排江中游”與畫面內容巧妙地承接,將市民與這座城市的處境進行了戲謔性的關聯,從而引發觀眾對市民和政府所處不同階層之間關系的想象。
除承接語義外,周浩紀錄片中也常常運用對比性的視聽語言來建構社會階層的想象。在紀錄片《小彪和狗》中,班主任老師嚴肅地強調:“假期要注意安全,不準去爬什么高山。”在下一個鏡頭里,主人公梁忠彪就和其他留守兒童一起爬上了高山。此處對比蒙太奇的運用,不僅在敘事過程中提升了紀錄片的趣味性,也將孩子叛逆、頑皮的性格特征巧妙地表達了出來,在觀眾腦海中留下了“記憶點”,這無疑能夠幫助觀眾對學生群體進行生動、細致的想象建構。
如果說充滿想象力的文段是社會科學家對社會問題的闡發手段,那么包含社會隱喻的視聽語言就是現實題材紀錄片創作者建構社會階層想象的工具。一方面,紀錄片的視聽語言具有隱喻的修辭功能,能夠賦予畫面或聲音新的意義,直接觸及觀眾的心靈;另一方面,視聽語言還具有強調的修辭功能,能夠通過對視聽語言符號的充分調用,以一種“話外之音”的方式向觀眾傳達觀點,刻畫人物形象,在觀眾腦海中形成記憶點,從而加強觀眾對于社會階層想象的深刻性。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現實題材紀錄片對社會現實有著“天然”的批判性,其視聽語言的運用也往往蘊含著深刻的解構主義思想;其對于事物發展隱蔽細節的揭示和對于社會整體結構的剖析,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起公眾社會學的想象力,建構超越自我階層的社會全局想象,從而推動人們對時代命運、社會發展作出理性的認知和把握,促進社會的穩定發展。
注釋:
① 楊國斌:《社會階層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9頁。
② 周怡、朱靜、王平等:《社會分層的理論邏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2頁。
③ Blau,P.M.,& Duncan,O.D.TheAmericanOccupationalStructure.New Jersey:John Wiley & Sons Inc.1967.p.6.
④ [法]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358-359頁。
⑤ Kingsley Davis,Wilbert E.Moore.SomePrinciplesofStratification.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10,no.2,1945.pp.242-249.
⑥ [美]格爾哈特·倫斯基:《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關信平、陳宗顯、謝晉宇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頁。
⑦⑧ 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8、7-108頁。
⑩ [美]理查德·謝弗:《社會學與生活》(插圖修訂第9版),劉鶴群、房智慧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