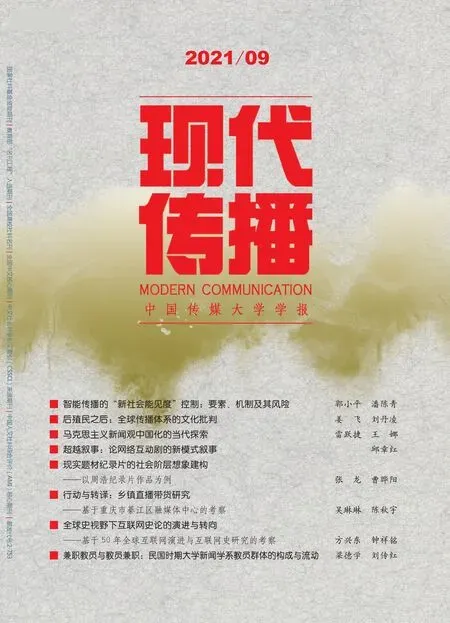兼職教員與教員兼職:民國時期大學新聞學系教員群體的構成與流動*
■ 梁德學 劉傳紅
1921年,中國首個大學新聞學系——上海圣約翰大學新聞學系正式創辦①,中國大學新聞學系中的教員群體自此出現。此后至1949年的近三十年間,大學新聞學系教員隨著中國大學新聞教育發展而逐漸專業化、群體化。然而,因民國時期中國高等新聞教育整體發育度不高,以及新聞學科天然的重實踐屬性,大學新聞學系教員群體呈現出與其他大學系科教員不同的結構特征。
大學新聞教育以培養高層次新聞專業人才為目的,對教員各方面素養要求較高。與此同時,民國高等教育主管部門及各大學當局,對教員準入資格亦有明確限定。這些限定條件,對新興的、強調實踐的新聞學科而言顯得較為“苛刻”,使其在延聘教員方面困難重重。此一問題終民國時期未得到根本性解決。
在專職教員準入門檻較高的情況下,大學新聞學系的籌辦與運作采用了較為靈活的策略,即大量聘請具有一定名望的新聞業界人士到系兼課,導致兼職教員占比畸高。與此同時,為數不多的專任教員因開展新聞實踐、緩解經濟壓力等需要,往往跨校兼課或到報館兼差。由此導致民國時期的大學新聞學系始終無法穩定發展,其受制于師資難題,或旋生旋滅,或淪為文法科的附庸。與之密切關聯的另一問題,是民國時期大學新聞學系教員較之于其他系科教員具有更大的流動性,這種流動在政治和戰爭等因素的作用下進一步加劇。
目前,有關民國高等新聞教育史的研究已有深厚積累,但仍有諸多可議之處,新聞學系教員群體之構成及流動問題即未得到應有關注和系統研究。其實,這是影響民國時期大學新聞學科發育、新聞學系創建與發展、新聞專業人才培養的關鍵問題。本次研究共涉及民國時期先后出現的13個大學新聞學系(表1中標有“※”號者),通過檔案、年鑒、民國報紙書刊、回憶錄、地方文史資料等史料,整理出專兼職教員108人,在此基礎上展開研究。
本文所討論的問題主要包括:師資問題何以成為困擾民國時期大學新聞學系發展的根本性難題?大學新聞學系教員群體基本構成情況如何,對兼職教員占比畸高問題,民國政府有何約束,時人又有何爭論?專職教員外出兼職的原因及具體方式為何,積極與消極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多重因素驅動下的專兼職教員大范圍、高頻度流動,對改變民國高等新聞教育總體格局及新聞學系教員群體結構有何影響?
一、師資:困擾大學新聞學系發展的根本難題
民國時期各類新聞教育機構總數近60家②,包括大學新聞學系和專修科、新聞專科學校、新聞函授學校等多種類型。但嚴格意義上的大學新聞學系卻數量不多,僅十三四家,且大多旋生旋滅或有名無實,甚至是否真正開辦過都存疑。辦學規模較大、持續時間較長的大學新聞學系,僅燕京、復旦、中央政校等少數幾家。另有一些雖冠以“新聞(學)系”或“新聞學院”之名,本質上卻是新聞干部訓練班或培訓班,如重慶新聞學院、華北聯合大學新聞系等。
民國時期,新聞界已較普遍地認為,較之于其他類型新聞教育,“大學新聞(學)系的新聞教育較為適合社會與新聞事業之需要”③。但如表1所示,終民國時期,辦學穩定且有影響力的大學新聞學系數量甚少。這與當時新聞學科自身發育程度、新聞行業需求及時局變化等因素有關,也與大學辦學經費、師資、設備等緊密關聯,其中尤以師資問題為切要。

表1 有史料可考的民國時期大學新聞學系
對于延師之難及總體師資質量不高的問題,當時大學新聞學系師生有相當真切的體認。1936年,燕大新聞學系主任梁士純指出,新聞教育師資“從量到質的兩方面看來,都確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④。1939年,復旦新聞學系畢業、時任《戰時記者》月刊主編的杜紹文感嘆:“試放眼一觀……掌教新聞教育者,有多少學有專長?又有多少人濫竽充數?”⑤1943年,主持中央政校新聞學系多年的馬星野將辦系“經驗到的一切困難”歸結為五點,其中,“延聘教授是最大問題”⑥。迨至1944年,時任燕大新聞學系主任的蔣蔭恩仍為尋覓不到合適教員而苦惱:“談到中國新聞教育,尚有一個嚴重問題亟須補救,即師資十分缺乏。……大家均有同樣困難,即找不到合適教員。”⑦1948年,時為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學系學生的鐘華俎(晚方漢奇先生一屆)⑧在《報學雜志》上發文稱:“師資缺乏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即新聞界先進亦莫不為此呼吁。⑨”同年,在新聞業界和新聞教育界均甚活躍的儲玉坤在《教育雜志》撰文:“不論是燕大、復旦、暨南甚至政大,都有著教授缺乏的現象。”⑩
揆諸民國時期各新聞學系辦學實際,師資不敷使用的情形比比皆是。最早創辦新聞學系的上海圣約翰大學,初由《密勒氏評論報》主筆柏德遜主持,3年后由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碩士武道接任。武道任系主任累計近二十年,“不過系內長期也就只有他這一位老師”。國人自辦最早的大學新聞系科——廈門大學新聞學部(后改為“新聞科”“新聞學系”),“沒有專門新聞學課程,也沒有新聞專科老師”。1923年創辦的北京平民大學新聞學系,系主任為當時在北京大學任職的徐寶璜,平大新聞學系主任僅是他的“兼差”。1924年,燕大新聞學系創辦,最初兩年有專職教員4人,但僅兩三年后,即出現師資嚴重短缺的情況。1927年,燕大文學院(新聞學系隸屬該院)院長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最可惜者,此時新聞學系乃竟無一教員。……殊愿新聞學系將來有充足之捐款,能聘用二三教員以供給本校課程之重要需求。”
延師之難不獨與學科專業人才自身儲備有關,亦與民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有關。北京政府時期,對大學教員準入資格并無明確限制,大學延師設系靈活性較大。但南京政府成立后,教育行政委員會于1927年6月頒布《大學教員資格條例》,正式規定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為大學教員的四種等級,對各等資格提出明確要求(見表2)。
表2 《大學教員資格條例》有關大學教員職稱及準入資格的規定

表2 《大學教員資格條例》有關大學教員職稱及準入資格的規定
助教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而有相當成績者;于國學上有研究者。講師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碩士學位,而有相當成績者;助教完滿一年以上之教務,而有特別成績者;于國學上有貢獻者。副教授外國大學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學位,而有相當成績者;講師滿一年以上之教務,而有特別成績者。教授副教授完滿二年以上之教務,而有特別成績者。
《大學教員資格條例》的頒行,使大學辦理新聞學系在原先師資難題未得紓解之際,又面臨教員資格審定的新問題。由此造成的結果是,1927年6月以后大學新聞系創辦數量明顯減少。自此至1949年的22年間,新創辦的、可查考確證的大學新聞學系,僅復旦大學新聞學系(1929)、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系(1935)、廣東國民大學新聞學系(1942)、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學系(1945)和上海暨南大學新聞學系(1946)等少數幾家。此前1921—1927年短短7年間,則有9家。在大學新聞教育愈加受到社會和行業認可的情況下,這樣的數字對比不能不歸因于《條例》所產生的“制約效應”。該《條例》頒布20多年后,名報人、新聞教育家儲玉坤仍對之“耿耿于懷”:
“依照大學教授聘請的條例,必須經過教育部的審查合格,才能充任教授。因此,在新聞(學)系,就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師資問題。……現在各報總編輯總主筆的人,雖有豐富的就業經驗,為學生所歡迎,但其學歷未必能合教授的資格。若聘為副教授或講師,則又為他們不愿接受。所以在各大學新聞系,最不容易聘到優良的教授。”
《大學教員資格條例》此后雖經修訂,但其所設置的教員準入門檻并未調低。客觀而言,《條例》對提升民國時期大學師資總體質量有積極作用。回望1927年《條例》頒布前創辦的新聞學系,彼時雖可拉來一班學歷不高甚至無學歷的兼職人員草草成系,卻大多無法穩定辦學。這一時期的大學新聞學系,僅燕大新聞學系日后得到長足發展。
當然,民國時期各大學對政府相關法令會作靈活處理。據曾在復旦、政校和社會教育學院等校新聞學系任教的曹聚仁自述:“在資格審查項目下,(教授)首先要算到留學歐美各國,在大學研究院獲得博士、碩士學位,或者是工程師學位的,其次才是國內大學畢業獲得學位的,又其次,才是專門研究有著作的。我呢,當然什么都不是,最多也只能算是寫稿賣文的人。然而,我居然做了大學的教授。”
由曹聚仁的自述可見,南京國民政府對大學教員準入資格之限制,有很大通融余地。1929年秋,復旦大學新聞學系正式創辦,這是《大學教員資格條例》頒行后出現的首個大學新聞學系,但專任教員僅系主任謝六逸1人。次年,留日歸國的黃天鵬加盟,但其任專職教員的時間不足半年,旋即進入《時事新報》工作,在復旦新聞學系之職務改為兼任。此后至全面抗戰爆發,復旦新聞學系基本保持依靠兼職教員維持辦學的局面。中央政治學校是國民黨最高學府,其在1935年創辦新聞學系,最初一年僅馬星野1人支撐,1937年前后,教務處主任劉振東兼系主任,馬星野1人為專任講師,沈頌芳、錢倬2人為兼任講師。至1939年,有馬星野及新加盟的俞頌華2位專任教員。同年,該系暫停招生。這與抗戰時局艱難有關,更與師資吃緊有關。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學系1945年秋創辦于四川璧山(今屬重慶),因屬國立大學,經費相對充裕。1948年,已遷至蘇州辦學的該系有教授4人,副教授、講師及助教各1人,共7人。于1946年創辦的同為國立性質的暨南大學新聞學系,教員人數略少于社教學院新聞學系,專兼職合計約在5人左右。至于燕京大學新聞學系,據曾任該系教員的盧祺新、葛魯甫回憶,平均每年有專任教師5位,兼任及客座講師1位。另查多份民國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員名冊》,全國在冊“新聞學門”教員人數處于墊底之列。如1942年度共6人(謝六逸、馬星野、朱應鵬、程滄波、儲安平、儲玉坤),1944年度共2人(張琴南、蔣蔭恩),1945年度也只2人(張琴南、蔣蔭恩)。
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大學新聞學系已走過近三十年的發展歷程,但所面臨的師資難題仍未得到根本性解決。為維持辦學,各大學新聞學系除聘請數量極為有限的有留學背景、有學歷的“高層次人才”外,大多向報館“拉夫”“敦請報界人士為教師”,卻由此造成兼職教員占比畸高的現象。
二、兼職教員占比畸高現象及其利弊之辨
在滿足《大學教員資格條例》要求的教員寥寥無幾的情況下,各大學新聞學系為維持專業課程教學,采取的主要策略是大量延聘新聞業界人士做兼職教員。不惟私立大學如此,國立大學亦然。
據現有史料,較早創辦的一批大學新聞學系,除教會學校燕京與圣約翰以外,平民、光華、南方、國民等校新聞學系的師資幾乎全由報館報人兼任。事實上,這些新聞學系本就是由報館報人創辦或主持的,如光華和南方兩校報學系由《申報》汪英賓籌辦并任系主任,國民大學報學系由《時報》戈公振為系主任,平民大學新聞學系則由《京報》邵飄萍創辦。其有史料可考的教員也均為兼職,如國民大學報學系授課教師為戈公振、潘公展、潘公弼、陳布雷,光華大學報學系授課教師為汪英賓、鮑威爾,平民大學新聞學系授課教師為徐凌霄、孫幾依、王小隱等,他們都是來自報館的兼課者。
燕京、復旦及政校新聞學系是民國時期辦學最為正規的三個大學新聞學系。但統觀三系師資結構演變,同樣是報館來的兼職者占絕大比例。就燕京而言,1924—1925年未見兼職教員相關記錄,這與當時該系可以便利地使用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供給的師資有關,也與彼時該系辦學經費相對充裕有關。但1927年時,該系來自美國贊助的經費告罄,專職師資隊伍亦無法維持,只能停辦。1929年重獲資金支持后,再次搭建起4人專職教員隊伍。至遲從1930年起,該系教職員名錄中出現兼職教員,當年為專職4人、兼職1人。此后兼職教員數量逐年增加,至1937年,共有教員9人,但專職者僅有3人。經歷抗日烽煙,至1947年,僅余教員5人,其中兼職者3人。
復旦新聞學系是民國時期國人自主創辦最負盛名的大學新聞學系。1929年9月正式創辦時,僅系主任謝六逸1人為專職。此后幾年,依靠來自上海報界、出版界的兼職教員維持。至1937年春,教員共計5人,但只1人為專職。1941年末,抗戰中內遷重慶的復旦改為國立,辦學經費支絀的局面大為改善,新聞學系兼職教員占據絕大比例的情況因之略有變化。至1947年春復員回滬時,有教員14人,其中專職9人、兼職5人,已是空前壯大。但在本文所能統計到的1929—1949年間該系總計44名專兼職教員中,專職者僅13人。
民國時期與燕大、復旦并駕齊驅的是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系。該系由國民黨于1935年推動創辦,是中國國立大學中首個新聞學系,馬星野是其實際主持者并長期任系主任。該系創辦后,“積極與國內完善之報館合作,教師之中,多兼任滬上大報之要職者”。1937年,有教員4人,其中專職1人,為專任講師馬星野;兼職3人,為教務主任兼系主任劉振東、兼任講師沈頌芳和錢倬。1939年因戰爭等因素瀕臨停辦之際,僅有馬星野、俞頌華2位專職教員。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國民黨決議將中央政校與中央干校合并,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為其三院九系之一。在該年度校方的一份《教職員姓名錄》中,僅馬星野、盧翼野、孫如陵3人可確認為專職教員。但此時,馬星野的主要身份已是中央日報股份有限公司常務理事、南京中央日報社社長。至于其他在該系充任兼職教員的“報業先進”,1947年的《中央日報》約略述及,為程滄波、董顯光、潘公展、詹文滸、趙敏恒、顧執中、武道、陶希圣、盧翼野、趙漠野。
1945年后創辦的大學新聞學系,主要為暨南大學新聞學系和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學系。社教學院新聞學系創辦于1945年9月,初由俞頌華主持,1947年俞頌華去世后由馬蔭良主持。專職教員除俞頌華、馬蔭良外,先后有葛思恩、許杰、載敦復、謝東平、方秋葦等,兼任教師有甘導伯、吳奔星、張少微、張格偉、許幸之、程錫康、劉靜淵、戴公亮、陶次如、王偉鼎、嚴欣淇、李稚甫、李凌飛、熊世方、張云谷等。到1948年時,共有教員7人,其中至少4人可確認為專職(馬蔭良、葛魯恩、曹聚仁、謝東平)。因當年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全校140名教員中兼職教員僅11人,可大致推測新聞學系兼任教員數量應不多,這與該校辦學經費相對充裕有相當關系。暨南大學新聞學系創辦于1946年,聘馮列山為系主任,一年后由著名報人詹文滸接任。為強化師資,詹氏也是廣納“業界良師”,包括“大美晚報總編輯兼采訪主任吳嘉棠先生及邵鴻香先生等”。此外,上海《大公報》編輯主任許君遠也曾受邀在該系兼課。但上述人包括系主任詹文滸在內,均為兼職。
民國時期校外人士到大學兼任教員的情況不獨存于新聞學系,在其他系科尤其偏實踐性系科也普遍存在。但兼職教員比重過高,必然影響教育教學質量,也不利于學科的成熟與發展。南京政府1929年7月頒布《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得聘兼任教員,但其總數不得超過全體教員三分之一。”1940年,《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聘任待遇暫行規程》再次明確:“教員以專任為原則,應于學校辦公時間在校服務。教授、副教授、講師授課時間每周以九小時至十二小時為率,不滿九小時者照兼任待遇。”此外,民國教育主管部門要求大學對兼任教員最多給以“講師”的名分,不得稱“教授”或“副教授”。如此規定,透露出政府方面并不十分支持校外人員進入大學兼課,如到校兼課,只能以“無名分”的方式進行。在本次研究所查閱的民國時期各相關大學教職員名單中,確對“兼任講師”與“專任講師”作出明顯的區分,如在1937年《北平私立燕京大學一覽》“教職員一覽表”所列新聞學系教員名單中,當時已大名鼎鼎的“報王”成舍我只記作“兼任講師”。
對于大學新聞學系大量聘請業界人士充當兼任教員的利弊,當時已有較多公開討論和爭辯。前文提及的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學系學生、日后曾任《四川日報》副總編輯的鐘華俎1948年撰文指出,在業界活動的報人,是大學新聞教育可資利用的“一個寶貴的資源”,因“他們了解中國的環境,他們知道中國目前的所需,他們洞悉中國過去教育的缺陷”。一些新聞學系的負責人也歡迎新聞界人士到系兼課。1937年,時任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系主任的馬星野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大學中設新聞學系者,雖極普遍,然師資教材,往往甚感缺乏,且是學在經驗方面之重要,較理論且有過之。故新聞學系,當充分利用實際在報館服務之專才,擔任教課。”
然而,從可資查閱的史料看,當時贊同大學新聞學系聘用兼任教員的聲音并不多。更多人認為,盡管新聞專業有較強的實踐屬性,但高等新聞教育并非職業教育,過多、過濫聘請兼任教員不是長久之計。1944年,時任燕大新聞學系主任蔣蔭恩直言:“不否認新聞界前輩,以其數十年廣博精深之事業經驗與道德修養,出為人師,足以使受教青年獲益匪淺。但在新聞界服務之現役記者,即令具有相當經驗,并不一定俱能教書。如果大學新聞學系講師教授僅能傳授一點工作經驗,則與普通職業學校教員何異?又何貴乎大學新聞學系?”次年,燕大新聞學系學生張如彥在學位論文中寫道:“目前中國的報界顯然仍甚落后,在報館工作的,平均起來,受過高深教育的還不太多,而且職業品德的修養,缺欠的地方也不少。一個好的新聞記者尚不容易做到,遑論為人師表?”1948年,時在中國新聞專科學校任職的施志剛發文指出:“新聞記者則憑其極少數的理論書籍的根據,用個人經驗現身說法,作某種新聞工作技能的傳習。……良好的新聞記者卻并非一定是良好的老師。在這種情形之下,新聞教育已落入次要地位,新聞教育卻變成了普通文法科的附庸了。”
然而,無論支持抑或反對,都不得不直面為數眾多的報界人士走進大學新聞學系兼課的事實。報界人士自身對到大學兼課,亦有不同初衷,有為利祿計,有為聲名計,有的礙于情面不得已勉強為之,有的則主要出于公心。如汪英賓、戈公振等報界名流均主動與大學合作,親力親為地籌辦新聞學系并擔任系主任。這些人當時已有相當社會聲望,經濟亦較殷實,他們參與創辦或主持大學新聞學系,有為整個新聞行業培養和儲備高水平專業人才的初衷。趙敏恒、張琴南等名記者甚至義務兼課,不支薪水。至于報人兼課所得薪水,往往十分低廉。據暨南大學新聞學系兼職教員許君遠回憶:“(詹文滸)主持暨大新聞(學)系時,計劃把當時上海各大報負責人拉到系內教課……我擔任‘新聞編輯’,每周上課二次。薪水甚薄,幾個月發一次。”正因如此,“往往一個富有實際經驗的報人,不肯,不愿,或不能教書,也是常有的事兒。”
報人工作本就日夜顛倒,若還在大學兼課,則更為辛苦。對此,抗戰時期在重慶主持《掃蕩報》編務工作,同時在北碚復旦新聞學系兼課的舒宗僑有一段十分生動的回憶。他是1941年冬應邀到母校兼課的:“說來這真是一份苦差事。報館編輯工作,每晚弄到早晨四五點睡覺,七點鐘就要站在李子壩馬路邊恭候校車的大駕,兩三個鐘頭的睡眠,談不到疲勞的恢復,就是能夠早睡也睡不著,所以一大清(早)起來怪不是味兒,眼睛里血絲發紅,不斷地打著哈欠。經過一路擁擠和顛簸,到達北碚夏壩的復旦已是下午一點左右。五六個鐘頭的汽車勞頓,四個小時的講課之后,還得拉得你報告新聞,講時事,參加晚會,做評論,總要弄得十二點鐘才能放手。”新聞職業本身的艱苦,使得大多數兼職教員無法保證足夠的精力投入。
客觀而言,來自新聞業界的兼職教員可更好地指導新聞學系學生的新聞實踐,與新聞專業屬性相互吻合,還可使大學新聞學系低成本運行。對大學主辦者而言,何樂而不為?更為重要的是,來自中國本土的、熟悉中國文化傳統和新聞實踐特征的兼職教員,使中國大學移植自美國的新聞教育模式逐漸本土化、中國化。只不過,整個民國時期,大學新聞系科兼職教員的占比過高,遠遠超過合適的尺度。
三、新聞學系專職教員的普遍性兼職
教員兼職,主要指在本校之外兼任各類工作,既包括教育領域內的兼課活動,也包括非教育機關的與教學無關的活動。較之于其他學科專業,民國時期大學新聞學系專職教員在本校之外兼職的現象更為突出。在專職教員本已不敷使用、師資結構中兼職者占比畸高的情況下,一些新聞學系甚至出現專職教員全員外出兼職、兼課的現象。
新聞學系專職教員兼職從事新聞實踐工作有一定合理性,甚至必要性,“若只有理論上的學識,而無實際的經驗,亦不能成為盡善盡美的新聞學教授”。基于此種認識,民國時期大學新聞學系的專職教員有邊教課邊從事新聞實踐活動的積極意愿,各新聞學系也希望借此與業界有更多勾連和互動。然而,民國教育部對大學教員的校外兼職行為并不支持。北京政府時期,大學教職員校外兼差或兼課被明令禁止。這一時期,辦有新聞學系的大學主要為私立,如圣約翰、平民、燕京、光華、南方、大夏等,尚無國立大學辦理新聞學系,教育部相關“禁令”的約束力較弱。從現有史料看,未見燕大新聞學系專職教員在外兼職情況,這與該系辦學經費相對充裕、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為其提供有力師資支持有關。但圣約翰大學新聞學系僅有的專職教員武道,卻在執教之余兼任美國、加拿大等多家報刊的駐華記者。在北京政府時期國人自辦的新聞學系中,平民大學新聞學系的規模相對較大,持續時間也較長(1923—1937),是首個國人自辦四年制大學新聞學系,但該系專職教員始終處于較低比例,甚至長期無專職教員。1923—1928年任該系主任的徐寶璜因其“人事關系”在北大,所以平大新聞學系主任就是兼職。兼平大新聞學系主任期間,徐氏還曾出任北大經濟系主任、京華美術專門學校校長、朝陽大學與中國大學教授等職,可謂“兼職達人”。由此可見,盡管北京政府對大學教員的兼職行為明令禁止,但相關“禁令”無法真正落實,新聞學系教員外出兼職蔚然成風。
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教育部對大學教員的校外兼職、兼課行為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規范化管理,由簡單“禁止”轉變為“限制”。自此,新聞學系教員到其他學校兼課或到報館兼差,甚至自辦新聞機構,成為更加普遍的現象,以致出現內遷以前的復旦新聞學系“專任教師幾乎全部去報社兼職”的情況,譬如,系主任謝六逸曾兼編《立報》副刊《言林》、生活書店《國民》周刊等,同時在申報新聞函授學校兼授“實用新聞學”“國外新聞事業”“通信練習”等課程。曹亨聞則自辦時事新聞類雙周刊《現實》,自任發行人兼總編輯。
不獨復旦新聞學系專職教員“四處”兼職,南京政府時期其他大學新聞學系的情況也大抵如此。俞頌華在任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學系主任,同時兼《國訊》周刊主編;馮列山在內遷至成都的燕京大學新聞學系任教時,一度主持《成都周報》編務,后又創辦《自由周報》,同時在四川大學夜校兼授新聞學課程。一些新聞學系教員名為專職,實則把主要精力放在兼職工作之上。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學系在俞頌華去世后,聘馬蔭良接任系主任一職。1947年,他因“滬上事務繁忙不可分身”,竟向院方請假一學期。馬星野曾長期擔任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系及此后的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主任,校方各類教職員名錄也將其列入“專職教員”一欄,但在任后期,他兼任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南京《中央日報》社長、中央日報股份有限公司常委及董事等要職。
至于新聞學系專任教員“熱衷”兼職的原因,一則是學科屬性使然,再者,與民國時期大學教員薪酬太薄,不足衣食之用不無關系。民國時期,大學新聞學系主要分布在私立大學,這些學校大多無政府經費支持,長期面臨辦學經費緊張問題,教員工資比國立大學低很多。1929年時,國立大學教授月工資在350—500元之間,而私立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月工資僅200元,別無任何津貼。謝六逸等專任教授的月工資亦為200元,但一年只發11個月。在復旦行政會議記錄中,可見多處當時學校經費緊張的記錄,如1930年6月的一次校務會議上,新聞學系所在的文學院院長余楠秋鑒于學校財務狀況,提議各系預算“不能增加”。此間,復旦正遭遇“校內良好的教授因待遇不佳有脫離本校的危險”。此境況下,一些新聞學系教員無法僅靠工資養活多口之家,只能四處穿梭兼職。再以復旦新聞系主任謝六逸為例,1945年他病逝時,茅盾在悼念文章中寫道:“六逸是不喜歡多事的人,然而也弄到不得不四處兼職,還不是為了家累太重了嗎?聽說他有子女六人,不說別的,光是喂飽這幾張嘴,也不容易吧?”
總體而言,進入南京政府時期以后,大學教員工資標準有所上調,但國立、私立大學間的差異仍然較大。此外,南京政府時常拖欠教育經費,“教職員之薪俸既有拖欠,教師兼課之惡習,亦將無法制止”。全面抗戰爆發后,物價飛漲,包括新聞學系教員在內的大學教員群體更加陷入前所未有的生活困境。謝六逸因貧病交迫壯年早逝時,竟至無棺槨入殮,由貴陽文通書局負責人捐贈棺木一副才入土為安。
由謝六逸的例子可見,如同其他學系教員一樣,新聞學系教員到校外兼職多有緩解經濟壓力方面的考慮,兼課所得的“鐘點費”成為不辭辛勞的誘因。有民國教育史研究者推論,“20世紀20年代直至全面抗戰前,一般大學教授的兼課月收入應該在50—120元之間,相當于一個大學助教的月薪收入”。抗戰勝利后,教員兼課的收入也較可觀。1948年,上海復旦、交大、同濟、暨南等八所國立院校聯名呈請教育部追加辦學經費。對其中提高教員兼課“鐘點費”一項,教育部復函回絕:“教職兼課鐘點費,照十分之一指數支給,系比照舊案辦理,并不為低,所請提高一節,礙難照準。”在辦學經費相對充裕的新聞學系中,如燕京與社教學院,專職教員外出兼職的情況相對較少,間接說明經濟因素是新聞學系教員外出兼課、兼差的重要誘因。
與其他學系教員不同,新聞學系教員的兼職活動并不以到其他學校兼課為主。他們兼職的主要去向是報館等各類社會性新聞機構,甚至如馮列山、曹亨聞等直接由自己創辦社會性報刊。通過在新聞機構兼職或自辦報刊,他們與新聞業界建立起十分密切的聯系,有利于更好地開展新聞業務教學。一些新聞學系教員兼職或自己創辦的報刊,往往成為新聞學系學生實習、實踐的重要基地。
當然,本就數量奇缺的專職教員普遍外出兼職的弊端也很明顯。在各類學校和新聞業界的兼職活動,使大學新聞學系本就數量有限的專職教員難以全身心投入教學與研究活動:“精神既不能專注,教學自無效率可言,即單就講演以貫(灌)輸智識猶嫌不足,遑論訓練人才與研究學問乎?”
四、多重因素驅動下的專兼職教員流動
兼職教員與專職教員的畸形比例關系,是民國時期大學新聞學系教員群體顯著的結構性特征之一,其內含的不穩定性,衍生出該群體的大規模流動問題。對兼職教員而言,其“人事關系”在報館而不在大學,從而有相當大的流動自主性;至于專職教員,因新聞學專業自身的重實踐屬性、民國大學的短聘制度及變幻無常的政治環境,同樣流動頻繁。
民國時期大學新聞學系辦學時間大多較短,無法給專職教員提供穩定的工作環境。尤其在大學新聞教育創辦早期,受學潮等因素影響,常出現整系跨校、跨地域流動的情況。譬如,1923年,廈門大學發生學潮,新聞學科“教師9人及全科學生離開廈門到上海創辦大夏大學報學科”;1925年,南方大學的學生因抗議校長江亢虎參與復辟,報學系學生憤而出走至國民大學,另建報學系;同是1925年,圣約翰大學發生反對校長風潮,部分師生出走另組光華大學,設立報學科。
一些大學的新聞學系,有明顯因人而設、因人而毀的特征。1923—1925年間,汪英賓、戈公振曾在大夏、光華、南方、國民等校創辦或主持報學系,但均甚為短暫。隨著他們的離去,其新聞教育隨之停滯。中央大學還曾打著戈公振旗號在滬上報刊大登“報學系”招生廣告,最終卻不了了之。又如,暨南大學曾在1928—1929年聘請《申報》編輯馬崇淦開設新聞學課程,但隨著馬崇淦另有他聘,新聞教育遽爾停止。“這種事隨人定、因人而毀的新聞教育現象,在中國新聞教育興起過程中不是個例。”
上述戈公振、汪英賓、馬崇淦等人均來自新聞業界,不受一校一系之約束,可在不同新聞教育機構間頻繁“自由”流動,可謂名利雙收。此類兼職教員,還可列出一串長長名單:邵飄萍、潘公展、潘公弼、陳布雷、郭步陶、張竹平、趙君豪、章先梅、錢伯涵、黃天鵬、成舍我、馬蔭良、趙敏恒、顧執中、曹聚仁……他們大多在報界聲名赫赫,是各新聞學系熱情追逐的兼職教員人選。這些人中,黃天鵬、馬蔭良、曹聚仁等少數人曾短暫地在大學新聞學系專任教職,但大部分時間是以兼職教員身份在不同新聞教育機構間穿梭。
較之于兼職教員,專職教員的流動頻率和規模又如何?試枚舉幾位民國時期知名新聞教育家的“流動軌跡”:梁士純先后在滬江、燕京、圣約翰等校任教;黃憲昭曾在燕京、上海商學院、滬江等校任教,后又一度重返燕京;馮列山的任教足跡遍及復旦、滬江、燕京、暨南等校。這些實例已部分說明,專職新聞學系教員的流動頻率和流動規模并不遜于那些來自報館的兼職者。
除政學沖突、人事紛爭、經濟收入等因素以外,新聞學系專職教員的頻繁流動與民國時期大學教員聘期普遍較短不無關系。短聘制度使其職業穩定性較弱,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流動與兼職成為一種無奈選擇。1931年的國際教育聯盟教育考察團報告揭示,中國國立大學教員聘期“平常均為一年,罕有超過兩年者”。1948年,《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聘任待遇暫行規程》規定,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之聘任,第一次試聘一年,第二次續聘一年,以后每次只續聘二年。這從暨南大學聘請馮列山為新聞學系主任的聘書中可見一斑。1946年,該校聘請馮氏為文學院新聞學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任期自1946年8月1日起至1947年7月31日止,僅一年。一年后,馮列山期滿去職,改由詹文滸接任,但后者聘期也僅一年。
專職教員除在不同新聞教育機構間流動以外,還常從大學向新聞業界或政界流動。這反映出,民國時期大部分新聞學系教員的職志是成為新聞記者或從政。馬星野從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成回國后,從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系教員做起,之后任系主任多年,但自1942年開啟從政和辦報之路,成為國民黨中宣部要員和《中央日報》負責人。作為為數不多留日研習新聞學的學生,黃天鵬回國后只于1930年短暫任教復旦新聞學系,僅半年,即進入《時事新報》工作,后任該報總經理、總編輯等職,又創辦《微言》《南報》等小報,重慶時期曾主持《重慶各報聯合版》。黃氏在民國時期新聞學研究領域知名度甚高,亦曾在復旦、政校等校任教,但就其當時職業身份而言,仍主要是一名報人。燕大新聞學系學生盧祺新畢業后曾留校任助教,1930年赴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深造,但學成后只短暫回燕大新聞系繼續執教,隨后進入英文《大陸報》和國民黨中央社工作。與盧祺新同一時期的燕大新聞學系助教徐兆鏞,最終也選擇到國民黨中央社工作。至于那些本就從新聞業界而來的專職教員,大多只在大學新聞學系作短暫停留,然后匆匆回歸報界,蕭乾、詹文滸如此,黃憲昭、梁士純等人亦如此。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受大學停辦或內遷影響,新聞學系教員出現更大規模的跨校、跨地域流動。復旦新聞學系1937年底內遷至重慶,系主任謝六逸因家庭負擔較重,未隨內遷隊伍一同前往,而是攜家眷乘船赴香港,后經廣西返回老家貴陽。至1938年春,謝六逸才入川,重回復旦新聞學系任教一個學期。但是同年8月,因病再次返回貴陽,任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復旦新聞學系主任由程滄波接任。1941年程滄波到香港擔任《星島日報》總主筆,改由陳望道任系主任。同年,復旦由私立一躍而為國立,實力大為提升,加之程滄波和陳望道廣為搜羅,新聞學系教員隊伍空前壯大。除程滄波和陳望道外,專任教員有曹亨聞、祝秀俠、李光詒、楊思曾、林淑英、王研石、沈有秩等人,兼職教員則有端木蕻良、趙敏恒、儲安平、陳欽仁、郭斌佳、劉光炎、胡健中、周欽岳、傅襄謨、姚蓬子、馮列山、舒宗僑、袁倫仁、周伯吹等人。對比1937年春時,專任教員只有謝六逸、郭步陶、章先梅、沈頌芳和陸詒5人。殘酷的戰爭使復旦新聞學系教員完成了一次艱難的輾轉流徙,但也正因為戰爭,實現了師資隊伍的全面更新和空前壯大,一躍為中國辦學實力最為雄厚的新聞學系。
燕大新聞學系在日本全面侵華之初困守北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已不能茍安,遷往成都。在困守北京期間,學校臨時邀請曾任天津《益世報》總經理、總編輯的劉豁軒代理系主任,另有孫瑞芹、羅文達、張景明、白序之、胡道維等任專、兼職教員。但當1942年10月成都復課時,北平時期原有教員全部流散,“沒有一人來到成都參與復校”。幸由燕大新聞學系校友、時任桂林《大公報》編輯主任的蔣蔭恩臨危受命,接任系主任一職并重新網羅師資,使燕大新聞學系得以在抗戰烽火中延續和發展。
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系內遷重慶后,系主任仍為馬星野,專職教員有俞頌華等少數幾人,但此前的沈頌芳、錢倬等人已不在教職員名單之中。不久,新聞學系停辦,改辦新聞學訓練班和干部培訓性質的重慶新聞學院,原有師資繼續參與教學工作。圣約翰大學新聞學系于1941年被迫停辦,此前已在國民黨宣傳部任顧問的武道轉赴重慶,在繼續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顧問的同時,也到中央政校新聞學系兼課。
抗戰勝利后,在大后方的新聞學系陸續回遷,造成教員群體的又一次大規模流動。1946年6月,復旦新聞學系復員返滬。次年春復旦公布的教職員名錄顯示,此時復旦新聞學系的專兼職教員共14人,其中,專職9人(陳望道、曹亨聞、蕭乾、王研石、杜紹文、沈有秩、李光詒、楊思曾、林淑英),兼職6人(趙君豪、趙敏恒、舒宗僑、卜少夫、唐亞偉、林淑英)。燕大新聞學系復員后的教員為蔣蔭恩、張隆棟、張琴南、吳范寰、李炳泰、張馨保、張明煒、孫瑞芹,當年流散的教員如孫瑞芹又重新“歸隊”。中央政治學校1945年回遷南京,次年與中央干校合并成“國立政治大學”并保留新聞學系,教員包括馬星野、孫如陵、盧翼野等,與重慶時期略有變化。除復旦、燕京、中央政校新聞學系回遷以外,1945年9月在四川璧山創辦的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學系也面臨東遷問題。1946年,該校擬遷南京,但因基建未竣,改遷蘇州,俞頌華、曹聚仁、馬蔭良、葛思恩等任教員。
上述新聞學系教員之流動,總體上可分為自由流動和被動流動兩種形態。前者是一種正常的、動態的、雙向選擇式的流動,有利于大學新聞教育的健康發育;后者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消極作用,特別是戰爭及政治干預因素所造成的流動,對中國大學新聞教育產生較大的阻滯和破壞。1948年后,大陸形勢逐步明朗,一些經歷了各種戰爭和政治動蕩的新聞界人士或前新聞學系教員,重又回到大學新聞學系的教學崗位。直至1952年院系調整,才出現新一次較大規模流動。
五、結語
對于民國時期高等新聞教育而言,新聞學系中的教員群體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能動性主體,是考察中國近現代新聞教育不可忽視的對象。本文通過對各類史料的爬梳,甄別出一份百余人的民國時期大學新聞學系教員名單。這份名單尚無法做到全面、嚴謹、精確,但從中可窺見民國時期大學新聞學系教員群體的基本樣貌。其最大特征是兼職教員占比過高,本就不敷使用的專職教員又普遍到校外兼職。這種內含不穩定因子的結構性特征與民國動蕩的政局相作用,又造成專兼職教員的高頻度流動的現象。
試驗所用土樣取自陜西省延安市吳起縣。所取試樣為砂質黃土,土樣呈灰黃色。現場取樣采用刻槽法,取回試樣后應立即進行室內的制樣與養護工作,并測定土的基本物理參數,土樣的基本物理力學指標如表1所示。制備好的試樣如圖1所示。
無論是專、兼職問題,還是群體流動問題,均非民國大學新聞學系面臨的獨有情況。這兩種情形,在整個民國時期的大學中普遍存在,但因新聞學科的強實踐屬性,以及學科自身發育程度較低,兼職教員占比畸高和專職教員外出兼職現象較其他學科更顯嚴重,群體流動性也更強。進入南京政府時期以后,大學教員的職業化和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絕大多數學科逐漸改變早期那種大量聘請兼職教員的做法,代之以培育經過專業訓練的職業化師資。遺憾的是,各新聞學系未跟上這一步伐。
對上述現象與問題,不應作二元對立式的理解。應看到,主要來自新聞業界的龐大兼職教員群體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學新聞學系師資緊張問題,降低了辦學成本,維持了專業課程教學的正常開展,尤其是“中和”了民國新聞教育濃厚的美式色彩。至于專職教員到業界兼職或自辦報刊,本就具有一定的社會服務性質,有助于他們將學理與實踐相結合,從而為學生提供貼近實際的專業新聞教育。至于他們以兼職所得收入來維持動蕩時局中個人及大家族之溫飽,也無可厚非。
但毋庸置疑,各色報館報人充斥于大學新聞學系兼任教職,以及專職教員的四處兼職,極大地阻滯了民國時期大學新聞教育的良性發展。畢竟,大學新聞教育不能僅以傳授新聞實踐經驗為主,亦應在學理層面潛心開拓和鉆研,破除“有術無學”的成見,建構起新聞學自身的學術、學科和話語體系。否則,便只能淪為文法科的附庸了。
注釋:
① 關于圣約翰大學新聞學系創立的具體年份,不同歷史及學術文獻記載不同,有1920年和1921年兩種說法。本文比較相關記述后,認為“1921年”說較為確切。
② 方漢奇:《新聞史的奇情壯彩》,華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頁。
③ 王公亮:《進步的新聞教育》,《報學雜志》,1948年第6期,第11-12頁。
⑤ 杜紹文:《中國報人之路》,浙江省戰時新聞學會1939年版,第60頁。
⑥ 《渝蓉記者聯歡——記燕大新聞學系座談會》,《中央日報》,1943年4月28日,第5版。
⑧ 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編:《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概況》,1948年版,第1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