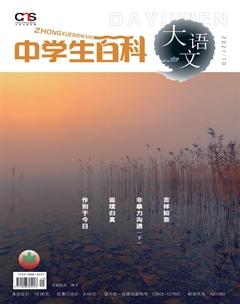“文以載道”與“獨抒性靈”
林天宇
古來為人津津樂道的文選中,北宋范仲淹所寫《岳陽樓記》是很突出的一篇,那超越了世俗或喜或悲的覽物之情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圣人境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博大胸懷,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慨,斯文承載著國人的修身處世之道。
同樣寫岳陽樓的還有另一篇美文,相映成趣卻鮮為人所知——晚明袁中道的《游岳陽樓記》,標題只一字之差,似乎是故意與先賢相互激賞;作為性靈文學有代表性的人物,所寫的這篇文章,內涵上又有什么講究呢?
《游岳陽樓記》這篇文章為什么會出現,可以先捋一捋中國文章的兩個源流:“文以載道”和“獨抒性靈”。
中國自古推崇“道德文章”,從讀書求學到文藝創作,都注重對人立身處世的指引。最老的古籍《尚書·堯典》有言“詩言志”,所以當最早的一部文學作品《詩經》被用作官方教材后,對它的解釋也是盡力往道德志向上來說,如敲動著每一個輾轉反側的有情人之心的“關關雎鳩”的鳴唱,在《詩大序》中,定性為講“后妃之德”,是為“風天下而正夫婦”來“教以化之”——這也是“教化”一詞的由來。具體講,道德教化和政治、人倫密切相關: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當然,人性有理性道德的一面,自也有感性抒情的一面,哪怕《詩大序》也無法否定詩歌的源頭是“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晚明湯顯祖在《牡丹亭》中,就借著杜麗娘聽老塾師用德行講《關雎》而覺得莫名其妙的反應,來調侃違情的弊病。當詩人一路傳唱著人生千姿百態的悲歡離合,抒寫著喜怒哀樂來到魏晉,陸機明確提出和“詩言志”相對的另一派理論:“詩緣情”。到南朝劉勰編寫中國第一部系統的文學理論著作《文心雕龍》時,提出了“情者文之經”,把言情看作一切文學的特征。對性情的重視與肯定,成為后世文人的共識。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況下,為了不同的目的,會有不同的觀點。文學是為道德教化服務,還是只為抒寫自我的性情,歷來多有爭論,潮起潮落,此起彼伏而各有高峰。唐時韓愈有感于聲色之文的流弊,發起古文運動,舉起“文以明道”的大旗,得到了正統文學家的支持,從此有了“道統”;而在文人習慣說道德之后,又衍生了太多“假道學”的偽作,當明朝正統文人追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境界之后,出現了一個逆流——以袁宏道為代表人物,和其兄袁宗道、其弟袁中道共同組成的“公安派”,公安派的核心宗旨,出自袁宏道對弟弟袁中道詩文的評價:“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于是,“獨抒性靈”和“文以載道”相并立,成為文心的兩座高峰,區分、統領著千古文脈的源流。
而今學子在讀書生涯中,所學古文以道統為主,如初中必背的諸多先秦諸子文,那振聾發聵的“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的教誨,讀過的人不會忘記品嘗“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滋味。到高中一系列的正統文章:講學習重要性的《勸學》,講圣賢發憤之所為的《報任安書》,以史諫今的《過秦論》《阿房宮賦》《六國論》,講孝道的《陳情表》……是為教化,起人格塑造之用。表達真性情的文章自然也有,如《歸去來兮辭》《蘭亭集序》等,更多的存在于詩歌選篇中。
道統文章的高峰在唐宋,《岳陽樓記》可為典范。
在《岳陽樓記》中,范仲淹所樹立的“古仁人之心”,將儒家所尊崇的任重道遠的家國情懷推到了極致。在面向自我的層面,強調對個人性情的超越,滿目蕭然不必感極而悲,把酒臨風不必其喜洋洋,所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面向家國的層面,“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強調個人對蒼生百姓、朝堂國君擔當責任,以至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而被袁宏道評為寫文“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袁中道,筆下的《游岳陽樓記》,相較之下,多有異同參照之趣。
在開篇,介紹岳陽樓的環境格局:“峙于江湖交會之間,朝朝暮暮,以窮其吞吐之變態。”讓人以為是在重復范仲淹所寫的“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但袁中道不會讓人乏味,立馬在范仲淹的基礎上,對岳陽樓的山水做進一步的品味:如果岳陽樓前只有洞庭湖水而沒有君山,如果“無一山以屯蓄之,莽莽洪流,亦復何致”,可見袁中道的用心處比范仲淹的壯闊更顯細致,從而總結出“故樓之觀,得水而壯,得山而妍也”的結論,提醒讀者來這里不僅要登樓、看水,也要看山,而且要看山與水的配合,這很有小品文的風格。
然后作者開始具體寫自己的此次游歷,先是白天“風日清和”,在小船上取酒共酌,感覺“亦甚雄快”——呼應范仲淹寫“春和景明”游洞庭會有的“心曠神怡”的積極情感體驗;然后到日暮,湖上“猛風大起,湖浪奔騰,雪山洶涌,震撼城郭”,讓人“四望慘淡,投箸而起,愀然以悲,泫然不能自已也”——呼應范仲淹寫“淫雨霏霏”游洞庭會“憂讒畏譏”“感極而悲”的消極情感體驗。
如果按范仲淹的邏輯,接下來就要進入寫自己超越世俗小我的悲喜,追求博大的心志;袁中道真正區別于范仲淹的,集中在下文。
袁中道想起了滕子京當時的遭遇:“昔滕子京以慶帥左遷此地,郁郁不得志,增城樓為岳陽樓。既成,賓僚請大合樂落之,子京曰:‘直須憑欄大哭一番乃快!范公‘先憂后樂之語,蓋亦有為而發。”讀到這里,我們更清楚地明白范仲淹所說的情懷所指,是為了開導滕子京懷才不遇、被貶岳陽而哭,希望他能超越一己之得失榮辱。但袁中道并不贊同范仲淹的意見,下面開始了他的反駁:
“夫定州之役,子京增堞籍兵,慰死犒生,邊垂以安,而文法吏以耗國議其后。朝廷用人如此,誠不能無慨于心。第以束發登朝,入為名諫議,出為名將帥,已稍稍展布其才;而又有范公為知己,不久報政最矣,有何可哭?”
簡言之,滕子京已經在定州建功立業,雖然后來遭人構陷彈劾,但年紀輕輕就入朝做官,在朝廷是有名的文臣,出朝廷外出統領軍隊是知名的武將,年輕時就展示了自己的才華,又有范仲淹這樣的名士做知心好友,貶官不久又政績卓著,有什么值得哭的呢?
可見袁中道認為,滕子京其實沒有什么好憂傷的,甚至是值得羨慕的,這與范仲淹要朋友超越一己為天下不相同。我們不由得要懷疑,是不是袁中道胸無大志、格局小了呢?對于自身,袁中道想表達什么呢?這要看文章的收尾:
“至若予者,為毛錐子所窘,一往四十余年,不得備國家一亭一障之用。玄鬢已皤,壯心日灰。近來又遭知己骨肉之變,寒雁一影,飄零天末,是則真可哭也,真可哭也!”
真相大白,好壞都是在對比中體現出來的,袁中道列舉了自己的四個情況來證明自己才是那個最應該哭的人:未得功業;年已半老;骨肉(指二兄袁宏道)病故;飄零在外。——本文從游洞庭湖入手寫起,思前人,不為表達對道德教化的感想和追求,只想吐一吐自己心中的苦水,慨嘆人生不得志的艱難困頓。
袁中道并不想把自己端起來塑造成為一個偉岸的圣賢,不渴望讀者從他這篇文章中找到修身養性、為人處世的法門,只想坦白一個平凡小人物的內心世界。他16歲中秀才,科舉考場上幾經落第,至34歲時才中舉,而考進士又多次名落孫山。“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對諸多像他一樣的不得意文人來說,其實很遠。
所謂“獨抒性靈”,就是面向自己的個性,表達小我的真性情。一個“獨”字當先,表明他們的文字不求外界他人的簇擁,他們的宗旨也不需要集體觀念的認可。公安三袁用他們真實、細膩的文字,給個人的性情做了解放;讀他們的文章,一花一水,一山一木,常妙不可言。上文提到的《牡丹亭》(和三袁基本處于同一時代),則是用戲曲的形式,讓飽受禮教禁錮的青春女子杜麗娘,在游園驚夢中吟唱著情之不可阻礙。又如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并序》中所說的“違己交病”,很多事情、很多觀念是世俗安排給我們的,使得“心為形役”。道德成為教化的規章時就有了枷鎖,人性如果敢于求真又何嘗不是美的?
讀懂范仲淹與袁中道兩篇寫岳陽樓的文章,且能辨別它們情感內涵的不同,以此為參照的方法,就可以對古往今來的文選進行源流的區分,并深入了解其主旨。
要注意的是,也有很多詩文的思想情感內涵是包含了“情”與“志”的,既有真實小我的抒發,也有道德志向的表達,二者相互交融。比如曹操的《短歌行》,從自己飲酒消愁寫起:“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頹廢的感覺溢于言表。但轉而去渴慕賢才,從對“青青子衿”的設想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又將詩意導向正統的抱負,詩境雄偉。
所以,“文以載道”和“獨抒性靈”,并不是勢不兩立的雙方,不過是各有偏向;文以載道不該成為虛言妄作,獨抒性靈自也不是道德敗壞之流。人的理性與感性兩面,又何曾可以偏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