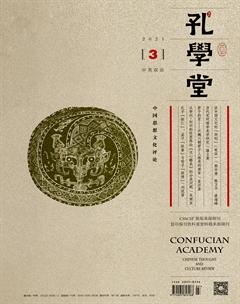中國文化的“兩創”
郭齊勇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課題。面對時代的挑戰,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需要我們虛心學習東西方各國、各民族、各族群的經驗,博采眾長,援外于中,又調動自身的文化資源,做推陳出新、返本開新的努力。
歌德的《浮士德》有一句名言:“理論全是灰色的,只有生命的金樹常青。”理論固然非常重要,但任何理論都一樣,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東西,只能大體上概括實際生活中的一般情況。但生活之樹是常青的,有許多復雜的、活生生的問題及其中蘊含的新的發明創造。所以說,一步實際行動勝過一打綱領。
今天,中國文化的發展面臨復雜的情況。從時間軸來看,文化綿延,有傳統與現代,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歷程;從空間軸來看,文化廣闊,有東方與西方,中心與邊緣,上層與下層、精英與民俗的張力。從時間與空間的交互網絡來看,有時代性與民族性、世俗生活與宗教信仰,日用倫常與終極關懷的矛盾。
因此,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只能立足現實,繼往開來,在現實性的基礎上調動傳統,面向未來,不能迷戀過去,也不能迷信將來。我們對中國傳統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價值觀念文化的內涵、樣態與表達,予以改造,賦予時代性,激活生命力。
中國文化不斷發展,不同時期的上層文化有其特色,如人們常說的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等,雖不免以偏概全,但也說明了不同時代文化風尚的區別。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漢唐盛世雍容博大,宋代市井多樣豐饒,留下了寶貴的文化基因。南宋以降,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簡略地說即是儒釋道文化。三教通過簡易化、普及化,不斷深入人心。民間老百姓不一定讀過四書、五經、老莊、佛經等,但通過唱戲的、說書的,通過蒙學讀物、民間諺語等,耳濡目染的是飽含著我們這個民族的價值觀的話語,如:“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諸如此類,筆者個人在童年時代常聽父輩、祖輩的親人念叨,接受過這種教化的啟蒙。筆者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這種體驗。
應全面地體認、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的屬性與特質。筆者曾把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特質歸納為六點:“和而不同,厚德載物;剛健自強,生生不息;仁義至上,人格獨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整體把握,辯證思維;經世務實,戒奢以儉”;把中國哲學的精神與特點概括為七點:“存有連續與生機自然,整體和諧與天人合一,自強不息與創造革新,德性修養與內在超越,秩序建構與正義訴求,具體理性與象數思維,知行合一與簡易精神。”這當然是對上層精英文化的概括。好在中國文化中精英文化與民俗文化并非對立的兩橛,而是相貫通的。
要“揚棄”中國傳統文化。“揚棄”這個詞包含著兩層意思,即既克服又保留,也即我們常說的“批判地繼承”。因此,在理解文化傳統的優長與價值時,又必須深具自我批判的精神,正視并檢討中國文化自身的內在缺失、缺弱與缺陷,這恰好是中國文化“兩創”課題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有本有源,開放包容 [見英文版第6頁,下同]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現實中的中國文化,是馬中西相融合的文化。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雖然與古代的社會理想不可同日而語,但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百多年來,在中國的土地上,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傳統文化、西方近現代文化不斷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土壤,兩者有契合之處。我們的馬中西相融合的現代文化是主體性的文化,是淵源有自的,有本有源的,其根源在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這一傳統開放包容,因此接納了外來的西方文化,尤其是與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相結合。馬中西相融合的新傳統也有了百多年的歷史,這是中國文化“兩創”的結晶,也是中國文化進一步“兩創”的基礎。
應當指出,當代馬中西相融合的新型文化的建構,包括了對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改造,既非全盤接受,也非全然拋棄。對傳統文化最成功的繼承和保護,就是不斷創新,把外來的、多樣的、現代性的內涵融入民族文化的內容與形式中來。對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的最成功的引進、吸收和消化,也是與時俱進地發展、創新,把現代性的因素結合到中國文化中來,進而改造現實與傳統,重塑當代中國精神。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頗多內在契合之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在5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形成了“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傳統,倡導“天下為公”,注重“知行合一”,論證“相反相成”,彰顯實踐的思維方式和大同的社會理想。馬克思主義思維方法和價值理念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為傳播并得到具體發展的基礎。應該看到,這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帶有兩者的優點與缺點。
近兩年來,人類面臨新冠疫情的肆虐,據相關數據統計,至2021年8月初,全球累計確診病例超2億例,死亡逾425萬人。新冠病毒對人類的挑戰,促使我們反思許多問題。不僅如此,2021年7月河南鄭州等地暴雨成災,暴露了地鐵與隧道設計及修建的若干缺失,對現代化城市建設與市民生活提出新的挑戰。瘟疫、水旱等災害的出現與反復,對我國的發展提出了諸多深層次的問題。自然災害的挑戰與應戰,本是人類社會長久、普遍的問題,但在現代化的今天,自然與人為、科技與人文的矛盾更凸顯,災害對現代社會、現代人的負面影響日益加劇,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加脆弱。
我們需要在大的背景,即“天、地、人、物、我”共生的背景下討論人類與世界文化的生存與發展,以及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生存與發展問題。中國文化中有豐富的珍寶,古人的“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生存經驗與生存智慧并沒有過時,對現代人依然啟發良多。
關鍵在于深度認識我們的傳統。很多學者還停留在“五四”時期粗淺的文化批判的水平。中國文化有自身內在的理路,有自身的優長與缺失。我們的新文化有主體性,但不盲目自大與盲目排他。對傳統,我們應當守先待后,理性批導;對現實,我們應當擴大社會空間,鼓勵更多社會組織的生成發展與積極參與,努力實現大社會小政府。從我們的實踐來看,還應當防止烏托邦主義與極“左”思潮的干擾,警惕并批判民粹主義與民族沙文主義。
二、重視科學邏輯,變革思維方式 [7]
我們的傳統文化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如知識論與邏輯學的傳統,科學的精神,邏輯的分析與細密的論證方法等,是我們的短板。我們沒有“為知識而知識”“為學術而學術”的傳統,尤其是儒家“重政輕技”“重道輕器”的傾向,抑制了有科學研究訴求的墨家等流派,包括儒家自身的某些派別與人物。近代以來,通過引進西方文化并學習西方文化的優長,補充了這方面的不足,但還很不充分。
從一般思維方式的分類來看,有線性思維與非線性思維,形式邏輯屬前者,辯證邏輯屬后者。思維方式又可分為直覺與分析、輻散與聚合、習慣性與創造性的不同。分析與輻散思維有助于思維的周密性。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應強調形式邏輯、線性思維的基礎教育,重視思維的確定性、程序、步驟與周密性,防止不確定性與思維滑轉。直覺思維與創造性思維有一定聯系,但我們還是應多強調分析性思維的基礎。
當下,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飛速發展。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帶來新的契機與可能。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應用,已經顛覆了傳統。大數據、海量存儲、便捷搜索等,帶來新的學術生長點。在現代,我們要進一步重視、擁抱科技革命,借此改革我們的模糊籠統的、大而化之的思維方式。
新冠疫情發生之后,通過運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成果,我國公共衛生、公共秩序的建構成就斐然。在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中,科學、邏輯思維的前景十分廣闊。同時,我們又要避免科學主義與技術主義的偏頗,以人文精神相補充與協調。
三、建樹獨立品格與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8]
馬克思主義倡導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理想社會。建構與完善民主、自由的價值與制度,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近代以來,數代中國知識人為爭取自由意志和獨立精神,做了不懈的努力。我們鼓勵個體人有心靈的自由和獨立的個性,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在精神層面保持獨立性,有獨立的品格、獨特的見解與自主的行為,不依傍他人,不依傍權威。我們反對奴隸性、依附性的人身關系,主張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達、自由地發展,有懷疑、批判的勇氣。如果沒有自由的思想,也就不會有獨立的人格。
正如馮契先生所說,我們要有知、意、情等本質力量的全面發展,進而達到真、善、美的統一,這就是自由的德性。而有了自由的德性,就意識到我具有一種“足乎己無待于外”的真誠的充實感,“我”就在相對、有限之中體認到了絕對、無限的東西,即達到了本體的理境。一般地說,這是通過實踐即在人的自由自覺活動中達至智慧之境。馮契先生由知識到智慧之境的飛躍,是通過自由勞動即自由的感性活動來辯證統合自然原則與人道原則的,又通過認識與實踐的辯證過程,包括理性直覺、德性自證的過程,發展人的理性與非理性,統合自由個性與集體精神,奔向個性解放和大同境界的理想目標的。因此,馮先生超名言之域的達成過程同時又是生活實踐中人的全面發展與平民化的理想人格的實現過程。其理性直覺、思辨綜合、德性自證都是社會實踐、文化創造和人性全面自由發展的諸環節。
四、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在民間,重點還是做人做事之道 [8]
從文化的傳氶來看,民間生活的多樣化促進了各地書院的勃興。這些書院繼承傳統書院而新創,一般是政商學界相結合,有的作后盾,有的出錢、出力、出師資,和合而成,對今天民間傳統文化的教化與傳承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據個人管見所及,北京中國文化書院、三智書院、四海孔子書院、山東尼山圣源書院、曲阜洙泗書院、湖南長沙岳麓書院、汨羅屈子書院、貴陽孔學堂、湖北經心書院、武漢問津書院、鄭州本源社區書院、山東嘉祥曾子研究院等,非常活躍,接地氣,聚人氣,創造了各自成功的經驗,讓老百姓了解中國文化的歷史與現實,在民間社會的基層推動著傳統文化精神與價值的繼承與發展。
中國文化不是過去,而是現在,還要面向未來。時代背景在變化,文化也要變化。不管我們現在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等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我們的現實關懷還在于中國人。中國文化其實也沒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它講的是平實的做人做事之道。儒釋道三教,其實還是講做人做事。中國傳統文化在現當代的創造性轉化,關鍵還是在于我們如何做一個現代的中國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這樣一個新時代的人的精神人格、精神風貌、安身立命提供一些思想背景、根源性的東西。在中國文化“兩創”的過程中,我們既反對復古主義,又反對崇洋媚外。
時代變了,我們的精神追求也在變化。但是,變中還有不變的東西,比方說我們曾經倡導很多常識,做人的常識是不會變的。我們做人的底線,至少要遵守底線倫理;然后我們還有基本的人格健全的要求,還有對理想的追求、境界的追求。在人格健全的過程中,可以從傳統的文化資源,儒釋道、諸子百家、宋明理學中找到一些精神養分、精神根據。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這樣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在大家都在求富、國家在求強,即求富求強的大背景下,又有日新月異的科技革命、機器人、人工智能等給我們提出的挑戰。但是不管怎樣變化,有一條還是不變的,就是人要與時俱進地發展,人要有真善美的追求和健全的人格養成才能很好地建設現代化的中國。孫中山先生當年就提出以人格建國,立國立人,我們要培養一代一代的人。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古今中西都是相通的,根本的就是做人做事之道。
中國文化的知識系統、價值系統、信仰系統是合在一起的,但也是可以分疏的。在知識系統上要有一個建構,要打基礎。所以馬中西的基礎的知識都要有,然后再分別看知識系統中蘊涵著哪些價值系統,在價值系統中還有一些屬于信仰系統。
要走出書齋、深入群眾,還要了解群眾在想什么。群眾首先關注的是自己怎么生活,自己的衣食住行,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現在的群眾也有精神世界的訴求,這個精神訴求不是講一些假大空的話,而是講西方的、中國的、馬克思的對自身做人做事有益的格言、有益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在哪里?我認為就是真善美的統一,追求全面、自由的發展的人格,這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東西。這也是前面我說到的它和西方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共通性的一面。因此,既要懂得理論,又要能夠用群眾的語言把它宣講出來,這需要一點本領,還要有一個實踐過程。
中國文化的“兩創”發展本身并不是目的,仍是過程,活生生的“人”的養育與成長才是目的。我們的目的就是現代中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是目的”,政績不是目的。尊重人的生命,尊重自由意志,一切為了人民的自由與創造。在這里,我們要吸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結合馬克思主義與西方近現代文化,予以重建。對老百姓仍有一個提升、教化的過程,當然更多的是人民的自我教育。現代書院就是人民自我教育的很好的形式。現代書院是提高人們的科學、人文與道德素養,安身立命,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的新的學校。
- 孔學堂的其它文章
- How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 The Fundamental Policy of Preserving and Develop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 Transforming and Boos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a Creative Way
- On the Creativ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 論南宋道學之黨的政黨特質
- 蘇軾的“平生功業”與“憂困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