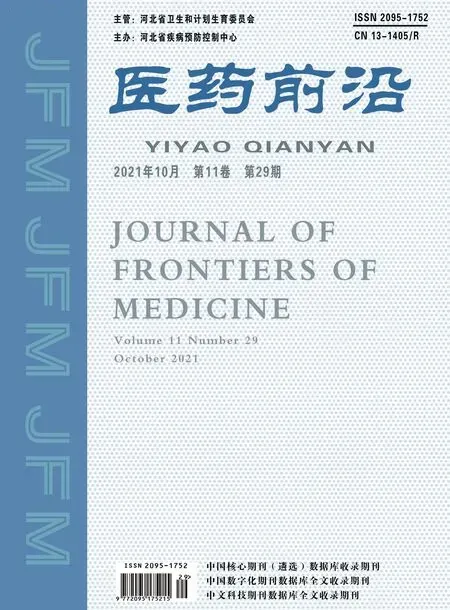可調節式人類位支架與蛙式石膏在小兒發育性髖關節脫位中的應用效果比較
唐詩鵬
(樂山市人民醫院血管小兒外科 四川 樂山 614000)
發育性髖關節脫位(DDH)是臨床發病頻次普遍較高的兒科髖部畸形疾病之一,是致使嬰幼兒落得終身殘疾的危險因素。對于18 個月以內的DDH 患兒來說,其軟組織攣縮情況還未發展至嚴重地步,同時由于其肌肉纖維密度較低,因此肌肉強度不高,同時關節柔順度較強,可采取手法復位或外固定等方法予以糾正,其中外固定方法是糾正小兒DDH 的主要方式,以蛙式石膏和人類位支架外固定兩種方法最為常用,兩種方法均有固定髖關節的技術優勢,前者受損部位的聯銜和穩固功能較強,后者的透氣性和操作靈活性較強[1]。現研究結果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 取 我 院2019 年1 月—2020 年1 月 收 治 的70 例DDH 患兒,隨機數字法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35 例,兩組基線數據差異無統計意義(P>0.05),可比較,見表1。

表1 兩組基線數據
納入標準:①患者及家屬知情同意,愿意參與研究;②符合小兒DDH 的診斷標準[2];③手術前拍攝兩側髖關節3 個位置的DR 片,完成三維CT 重建。
排除標準:①凝血功能障礙;②嚴重心血管系統疾病;③明顯誘因或外傷引起的DDH;④其他類型的病理脫位。
1.2 方法
觀察組患兒給予蛙式石膏:處于全麻閉合條件下給予復位處理,采取石膏繃帶彎曲雙膝90 度,采用合適長度的木棒固定患兒的兩條小腿,(1)如患兒為單側脫位,則需要以木棒再坐固定大腿,避免產生滑脫,如雙側脫位,則固定兩側;(2)如患兒的內收肌群因應激性緊張無法伸展至90 度,需根據實際情況行內收肌切斷術,避免內收肌裂傷或股骨頭損傷過重,引發缺血性壞死;(3)內收肌群應激性緊張且脫位較高者,應切斷內收肌牽引患肢到髖臼水平的股骨頭位后,采取復位固定。(4)每2 個月更換一次石膏繃帶,定期拍片復查,密切觀察髖臼發育情況,通常需要4 ~8 個月左右。(5)記錄髖臼指數,如指數正常則改為外展內旋固定法固定2 ~3 個月,然后拆除,開展功能鍛煉[3]。
對照組患兒給予可調式人類位支架,于全麻下,實施手法復位后,切斷皮下內收肌,以人類位支架外固定5 ~6 個月后,以貝氏石膏固定3 個月。具體方法:(1)取仰臥位,屈曲90 度髖,外展60 度,佩戴人類位支架固定,固定期間可囑咐取蹲位行走,以此促進股骨頭與髖臼的摩擦刺激,幫助骨骼發育塑形。(2)六個月后去除人類位支架,實施雙下肢伸直位骨盆X 線檢查,如頭臼包容性良好,關節穩定,則更換外展支架,固定3 個月。(3)頭臼包容性差,關節缺乏穩定或有半脫位現象,需延期佩戴人類位支架三個月,再更換外展支架,固定3 個月。(4)如患兒在接受支架治療后仍有頭臼包容不良者,可墊高健康側鞋2 cm 繼續治療,堅持治療3 ~6 個月[4-5]。
1.3 觀察指標
比較兩組患者的臨床效果(以X 射線檢查評價髖臼和股骨頭發育情況,分數越高說明恢復和發育情況越好)、足底壓力變化(采取FOOTscan 型平板式足底壓力測量儀測量足底壓力,壓力感受板200×40 cm,配置4 個傳感器,取樣頻率為126 Hz,需要測量5 次平均值確保準確性)和殘余畸形發生率(股骨頭壞死、再脫位和髖臼發育不良)。
1.4 統計學方法
2.結果
2.1 兩組患兒的臨床效果對比
治療后,觀察組(94.29%)的治療優可率與對照組(91.43%)相比差異不顯著(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兒的臨床效果比較(例)
2.2 兩組患兒治療前后的足底壓力變化對比
治療前,兩組足底壓力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觀察組各項足底壓力均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兒治療前后的足底壓力變化比較( ± s)

表3 兩組患兒治療前后的足底壓力變化比較( ± s)
最大壓強(N.cm-2)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觀察組 35 32.55±3.44 18.36±0.74 3.57±0.25 1.43±0.25對照組 35 32.47±3.16 27.24±0.15 3.55±0.27 2.34±0.32 t 0.101 69.578 0.322 13.258 P 0.920 0.000 0.759 0.000組別 例數最大壓力/N沖量(N.s)治療前 治療后觀察組 35 8.25±0.24 4.27±0.14對照組 35 8.34±0.34 7.22±0.25 t 1.279 60.909 P 0.205 0.000組別 例數
2.3 兩組患兒的殘余畸形發生率對比
治療后,觀察組(5.71%)的殘余畸形發生率與對照組(8.57%)相比差異不顯著(P>0.05),見表4。

表4 兩組患兒的殘余畸形發生率比較(例)
3.討論
在臨床治療小兒DDH 時,需根據不同患兒的年齡階段和脫位程度做出系統判斷,同時早發現早治療尤為重要,是治療DDH 的重要前提,臨床治療DDH 普遍多采取早期復位療法和外固定療法,可有效減輕局部神經血液供應,且不良反應較少,甚至在長期堅持治療下,可大大降低未來開展骨盆截骨術的風險[6]。其中,外固定療法又可細分為蛙式石膏和可調節式人類位支架,前者以閉合復位后蛙式體位為基礎開展的蛙式固定,具有較強的髖部穩定性而被臨床上持續采用至今,而后者通過吸收人體力學原理,制造出符合人類位線條的支架護具,該支架護具能夠有效地維持復位后的頭臼同心的解剖關系,有利于促進股骨頭和髖臼相互摩擦,可充分促進骨骼生長。
在本研究中,觀察組的殘余畸形發生率與對照組差異不大,具體分析如下:可調節式人類位支架的透氣性較好,可有效減少皮膚瘙癢和局部皮膚不適的情況,同時支具在固定的時候,由于重量較輕,可充分放松肢體和固定位置,可合理減少肌肉勞損,避免其他組織部位出現勞損和損傷情況,另外支具還具有靈活的操作性,如患者自覺不適,可由醫師幫助解除;合理減少股骨頭壞死等并發癥,降低殘余畸形發病率[7]。而蛙式石膏雖然缺乏靈活性、透氣性,但石膏在固定后,能夠充分且牢固地維持骨折斷端、韌帶受損位置,可合理避免骨折斷端移位以及軟組織和韌帶拉傷,對于臨床治療小兒DDH 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同時,為驗證患兒的關節恢復效果,本組研究還采取步態分析作為測試指標,通過測量足底壓力來判斷小兒DDH 的恢復情況,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各項足底壓力均顯著低于對照組,究其原因在于:DDH 發病后會導致患肢縮短,臀中肌功能受損等多種病理改變,而蛙式石膏可以穩固地銜接骨折斷端、韌帶損傷和肌肉損傷區域,能夠盡快將損傷組織聯銜成較為穩固的狀態,可促進關節功能快速恢復,同時配合復健鍛煉,增強運動能力,提升預后水平。
綜上所述,在DDH 患兒治療中,無論是采取蛙式石膏還是可調節式人類位支架,均能取得同樣的效果。但在減輕足底壓力方面,蛙式石膏更具有優勢。而可調式人類位支架透氣性好、可操作性強、靈活度高。因此,具體選擇哪一種固定方式,需根據具體情況和醫生建議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