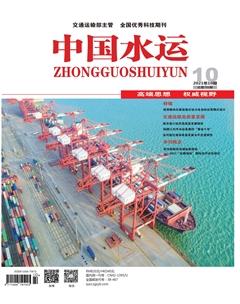長江航道濱岸帶水生植被修復試驗
李楊 周學文 楊順益 閔奮力 潘文杰 羅宏偉 王勖 王茜茜



摘 要:為探索長江航道濱岸帶水生植被修復技術,我們在長江中游宜昌至昌門溪河段航道整治二期工程護灘區開展了水生植被原位修復試驗。依據修復試驗經驗、修復監測結果,本文研究了影響水生植被修復的主要因素,同時對原位試驗過程中相關技術進行總結優化,為長江生態航道建設提供工程經驗、基礎數據和技術支持。
關鍵詞:生態航道;濱岸帶;生態修復
中圖分類號:X171.4?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文章編號:1006—7973(2021)10-0129-03
1前言
河流濱岸帶在水文調節、水質改善、物質輸入調控、生物多樣性維持等方面對河流生態系統有明顯的影響[1]。濱岸帶水生植被的生長使水體生態系統食物鏈不斷完善,對水體生物多樣性的提升具有明顯的貢獻[2]。航道整治工程廣泛應用鋼絲網籠技術、生態護坡磚等生態型結構和技術在濱岸帶開展護坡護灘[3-4],其在有效防止水流對岸坡攤地沖刷的同時也有一定的促淤功能,為陸生植被的生長提供了良好的生長基質,但并未考慮濱岸帶水生植被的生長恢復。目前,長江部分江段濱岸帶水生植物群落嚴重退化,濱岸帶水生態系統結構嚴重失衡,生態功能嚴重缺失,不利于長江的健康發展。因此,在航道整治工程同時進行濱岸帶水生植被的修復技術研究可以為生態航道建設提供基礎資料和科學依據。
本文針對長江航道濱岸帶水生態系統存在的問題,開展小規模的水生植被原位修復試驗和修復效果監測。研究旨在通過科學試驗,采用不同技術方法恢復各種水生植物,比較不同技術方法條件下各種植物的恢復效果,結合長江濱岸帶特征和航道整治工程工藝,分析得出適合長江生態航道建設中最佳的種植技術方法,同時對原位試驗過程中相關技術參數進行總結優化,為長江生態航道建設提供技術支持。
2水生植被修復試驗
2.1 試驗地點和材料
選擇宜昌昌門溪航道整治二期工程中沙咀邊灘守護工程區域作為實驗地點。根據實地考察,發現一號和二號護灘帶間豐水期水位較低,枯水期有若干大小水潭且存在零星草本植物,且兩護灘帶間水流速度相對較緩,為開展濱岸帶水生植被修復提供了可能。
根據現場調查和查閱資料[5-7]確定枯草、菹草和千屈菜作為試驗物種。苦草群落具有較強的抗沖擊能力;菹草抗逆性強;千屈菜根系發達、生命力強。
2.2 修復方案及實施
整個試驗區分總面積為600m2(15m*40m),分別按照如圖1所示的種植物種和種植方式開展試驗。近岸側向水中延伸5m的范圍種植千屈菜,按照底質改造后種植幼株和原位沙土種植幼株2種種植方式進行實驗,試驗區靠外側10m的范圍進行苦草和菹草的恢復,植物主要采用種子和植株,采用底質改造和無紡布包種2種方式進行恢復。
根據修復方案,2019年3月開展了水生植被修復試驗,相關試驗參數見表1。苦草和菹草的植株種植密度相同;因苦草和菹草種子萌發率差異,苦草的種子種植密度更高;千屈菜修復區均以幼株為種植體,種植面積和種植密度相同。
3修復效果
在試驗區域各布設1個樣方(2m×2m)進行植被蓋度監測。2019年3月對修復工程完工后進行了植被蓋度的初次監測評估,之后在2019年4月至12月共進行了3次監測,2020年12月監測一次。
3.1苦草恢復情況
修復工程完成后2019年3月第一次監測發現,兩個植株修復區域苦草蓋度均為15%,但2019年4月以后的監測均不能觀測到苦草。兩個種子修復區域,2019年3月第一次監測均未發現苦草種子萌發,隨后的監測中也沒有觀測到苦草。
苦草植株只能短暫的存活,苦草種子未能萌發,表明種植區域的環境不適合苦草的定殖。即使采用了底質改造和無紡布包種技術,苦草也不能存活和萌發,表明試驗中影響苦草生存的主要因素不是土壤環境和種植方式。
3.2菹草恢復情況
修復工程完成后2019年3月第一次監測發現,在兩個植株修復區域中菹草蓋度均為10%。2019年4月監測發現,“底質改造+植株”區域菹草蓋度增加至15%,而“無紡布包種+植株”區域菹草蓋度降低至5%,表明底質改造有利于菹草植株的存活和定殖。經過2019年汛期后,2019年11月和2019年12月的監測發現,“底質改造+植株”區域菹草蓋度降低至1%,“無紡布包種+植株”區域菹草蓋度降低至2%,洪水對菹草的定殖產生了重大影響。經過2020年汛期后,2020年12月未監測到菹草,第二次洪水的沖擊使得菹草難以生存。
修復工程完成后第一次監測發現,兩個種子修復區域中菹草種子暫未萌發。2019年4月監測發現,“底質改造+種子”區域菹的草種子萌發形成植株蓋度為15%,“無紡布包種+種子”區域的,菹草種子萌發形成植株蓋度為10%,表明菹草種子能在此萌發生長且底質改造技術更有利于種子的萌發。與植株修復區相似,經過2019年汛期后,種子修復區菹草蓋度都有所下降,經過2020年汛期后未監測到菹草,第二次洪水的沖擊使得菹草難以生存。
3.3千屈菜恢復情況
修復工程完成后2019年3月第一次監測發現,兩區域千屈菜的蓋度均為5%,但2019年4月以后的監測均不能觀察到千屈菜。千屈菜幼株只能短暫的存活,表明種植區域環境不適合枯草的定殖。即使采用了底質改造技術,千屈菜幼株也不能存活,表明試驗中影響千屈菜定殖的主要因素不是土壤環境。
4結論
通過開展水生植被修復試驗和效果監測發現,三種水生植物中只有菹草觀測到萌發和定殖。苦草和千屈菜在利用底質改造技術手段、種子和植株包種方式修復后,也未能觀測到萌發或定殖。菹草在未進行維護和補種的情況下,難以抵御第二次洪水的影響。由此推斷,水文因子應是影響長江航道濱岸帶水生植被修復的關鍵因素。
無論以植株或種子作為修復材料,底質改造區域的菹草都在未受洪水侵擾前表現出更高的蓋度,證明底質改造技術能有效地加強水生植被生長。菹草在蓋度為10%上時能夠抵御第一洪水的侵擾,當蓋度低于5%后,第二次洪水侵擾使得菹草消失,這表明可以通過補種等工程維護手段提高水生植被抵御洪水的能力。菹草的存活和抵御第一次洪水表明在航道整治護灘帶進行水生植物修復是可行的。
結合本次修復試驗工程經驗以及效果監測結果,長江航道濱岸帶水生植被修復需要重點關注水生植物的篩選、種植密度、底質改造方式以及維護管理,修復區域的水文條件是水生植被修復成功的決定因素。我們建議:
(1)水生植被篩選時可以優先考慮菹草,其他物種可根據修復區域的植被調查結合工程實際考慮,可以先做小規模篩選實驗確定修復物種后再大面積種植;
(2)合理提高種植密度,適時補種提高水生植被抗洪水侵蝕能力;
(3)進行底質改造,提高修復效果。
參考文獻:
[1]王斐.濱岸帶生態工程技術研究與應用綜述[J].水道港口,2017,38(06):632-638.
[2]王超,尹煒,賈海燕,等.濱岸帶對河流生態系統的影響機制研究進展[J].生態科學,2018,37(03):222-232.
[3]趙航,方佳敏,付旭輝,等.河道生態護坡技術綜述[J].中國水運,2020,4(11):113-116.
[4]李慶,張濤.新型生態護灘技術在航道整治工程中的應用[J].中國水運(下半月),2018,18(07):127-128.
[5]陳開寧,蘭策介,史龍新,等.苦草繁殖生態學研究[J].植物生態學報,2006,30(3):487-495.
[6]陳洪達.菹草的生活史、生物量和斷枝的無性繁殖[J].水生生物學報,1985,4(01):32-39.
[7]沈偉,黃先全,羅霞,等.千屈菜生態浮床與鳳眼蓮對養殖水體凈化的比較研究[J].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17,32(02): 77-81.
基金項目:長江航務管理局科技項目(20191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