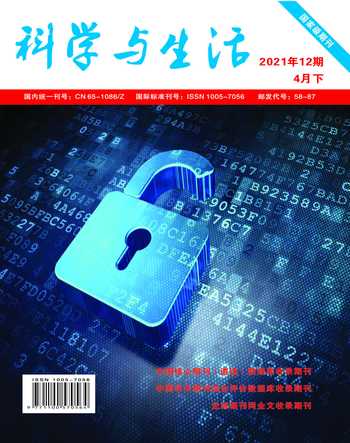中世紀英國村莊共同體與農民個體的關系
孟瑞瑞
摘要:村莊共同體是日耳曼馬爾克村社制度的延續和發展,也是中世紀英國鄉村基層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英國封建制度不斷發展的歷史環境下顯示著共同體自身的強大力量以及對農民個體的管理與保護,不斷推動農民個體向前發展。雖然這種保護力量并沒有改變農民個體的社會地位,也沒有改變封建領主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并且隨著社會經濟以及農民個體力量的發展,村莊共同體對農民個體由保護逐漸轉變為束縛,但是這種村莊共同體體現的民主、互助、協作、協商等精神和理念在英國社會始終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中世紀村莊共同體;個體發展;英國鄉村
村莊共同體是中世紀英國鄉村基層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來源于馬爾克村社制度的村莊共同體在很多方面顯示出其強大力量與自治性。由來已久的村莊共同體在英國鄉村社會有著深厚的根基,隨著英國封建制的發展,英國鄉村基層組織呈現出村莊和莊園的雙重結構,在二者的關系上,侯建新教授在《交融與共生:西歐文明的三個來源》一文中指出,“莊園和村莊同等重要,莊園始終沒有完全取代村莊,即使在殘酷的農奴制下,村莊共同體仍然具有抵抗手段和行動的空間。……村社從沒有喪失集體行為,而且得到廣泛認同。”[1]可以說,鄉村共同體在農民個體力量微弱的情況下為個體提供了保護,使得農民個體免于受到領主的過度盤剝,這是中世紀英國農民能夠積累財富的重要原因。村莊共同體在保護個體的同時也限制了個體的發展,當個體力量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努力沖破共同體的束縛,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力量。但是鄉村共同體所具有的協作、協商精神得到了保留和傳承,這對英國社會整體發展十分有利。
中世紀英國村莊共同體既是英國最為重要的鄉村基層組織,也是敞田制下的基本經濟組織。“村莊作為基層行政共同體和合作經濟共同體而存在。”[2]村莊共同體的主要作用是協調管理村莊內部的日常生活與生產活動。英國中世紀早期的村莊共同體就構成了是村民有序處理村莊事務的基層組織,通過村民大會對共同體各項事務進行管理,在與封建莊園制融合之后,村莊共同體依然不斷發揮作用,且共同體理念也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得以延續。它源自于日耳曼傳統,最為典型的就是馬爾克村社制度,這種具有部落傳統的制度保留了傳統的民主成分,因此在共同體發揮自身作用時,往往是通過全體村民的集體參與來體現。“中世紀早期的英格蘭,村莊共同體事務統一管理者是村民們通過比較民主的方式共同選舉出來的。”[3]這種共同體觀念及其實際運作顯示了村莊共同體的自治性和農民個體的自我管理意識,為英國歷史發展留下了寶貴的財富。隨著封建制的發展,一些地區莊園興起,村莊共同體在管理上與莊園有所融合,“莊官制度”逐漸產生并發展起來。莊官的任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但從整體上看,盡管莊園與村莊在鄉村管理上實現了某種程度的融合,但是村莊共同體依然發揮著更為核心的作用,并且村莊共同體在封建制領主的統治下也保持這很大程度的自主性,二者既交融又合作。
敞田制是英國歷史上最主要、最普遍的土地管理和運作方式,也是鄉村共同體力量的重要體現。從敞田制的管理進而運作方式上看,這是一種保留了部落傳統,同時又很繁雜的土地制度。條田是敞田制的重要特征,耕地和草地成條狀交錯分布,個人所占有的條田分布也十分分散,且這種個體占有權只是在作物生長和收獲過程中享有,在收獲之后,條田需要向所有的土地占有者開放。并且由鄉村共同體管理敞田制的運行,包括公共放牧權的維護、條田的重新分配、作物的種植和收獲等都需要鄉村共同體做出統一的安排。可以說,敞田制在中世紀英國鄉村經濟生活層面最大程度地顯示了村莊共同體和農民個體之間的關系。在敞田制運行過程中,要進行土地的重組、分配等工作,這是一件復雜而繁瑣的事情,要求村莊共同體擁有很強的自我管理和組織能力。另外,敞田制在共有權利的管理上也顯示了共同體對個體的保護,“共用權的存在和實施體現了一定的慈善與救濟功能。”[4]可以說,敞田制下的農民個體在共同體的保護下能夠獲得基本的生存,也能夠擁有對封建領主勢力斗爭的力量,同時有了積累個人財富的基本條件。盡管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個體尋求更大程度的發展,敞田制不再適宜社會發展的需要,但是村莊共同體的奠基性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中世紀英國村莊共同體對村莊內部事務進行管理時,如管理者的選擇、田制的運行、糾紛的處理等都依賴古老的習慣和長期形成的村規民約。這些村規包含村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同時具有法律效力。“村規檔案的記錄一方面是為了規范村莊的法令并指控犯罪,對違反村規的人進行懲罰;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證村民利用村規來反抗領主的過度盤剝。”[5]這些村規民約依托于古老的慣例,并且是莊園法庭審判時最為重要的依據。因此,從整體上說,莊園法庭既是封建領主維護自身權益手段,又是村民處理日常糾紛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村社共同體以集體力量反對領主濫用權利的工具。村莊共同體的村規以及封建化后的莊園法庭,都不同程度地顯示了村莊共同體對農民個體的管理與保護,雖然這種保護力量并沒有改變村民的社會地位,也沒有改變封建領主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但是這種村莊共同體體現的民主、互助、協作、協商等精神和理念在英國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封建制莊園和封建領主被歷史遺棄之后,村莊共同體精神依舊在英國社會各個方面發揮這重要影響。
正如侯建新教授所說,“鄉村共同體理念是理解西歐中世紀鄉村社會的鑰匙,作為精神遺產則穿越了時空,影響深遠。”[6]村莊共同體在封建制的發展過程中,在封建領主居于統治地位的社會歷史背景下,發揮著保護農民個體權利的重要作用,盡管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農民個人力量強大之后,農民個體在謀求自身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會不斷突破共同體的約束,但無論在什么歷史時期,英國村莊共同體理念和精神都在持續發展,并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參考文獻
[1]侯建新:《交融與共生:西歐文明的三個來源》,《世界歷史》,2011年第4期.
[2]徐浩:《中世紀英國鄉村體制構架補論》,《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總第113期).
[3]趙楊:《莊官、村規和莊園法庭——中世紀村莊共同體的民眾參與性》,《黑龍江史志》,2015年第3期.
[4]孫立田:《中古英國敞田制的運作及經濟社會效應》,《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總第214期).
[5]陳立軍:《英國中世紀村規檔案的歷史解讀》,《蘭臺世界》,2012年第8期.
[6]侯建新:《西歐中世紀鄉村組織雙重結構論》,《歷史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