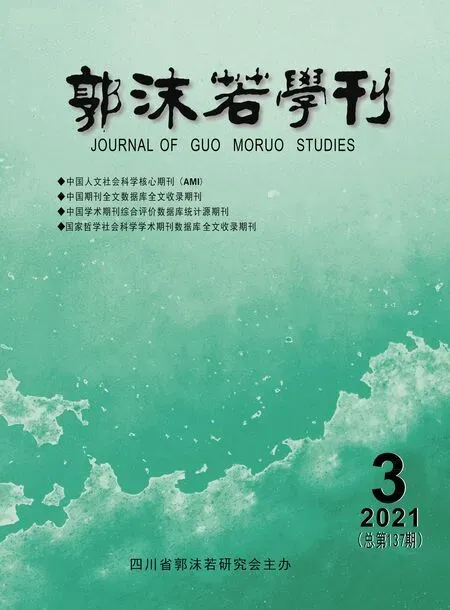郭沫若詩話(二)
蔡 震
(中國社會科學院 郭沫若紀念館,北京 100009)
大轟炸的記憶
抗日戰爭期間,從1938 年起,日本侵略軍對重慶進行了持續五年的轟炸,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也留下了慘痛的歷史記憶,這是中華民族的集體歷史記憶。郭沫若在那時為此創作了若干篇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作品,他們就是這一集體歷史記憶的一部分。其中有幾首詩的相關創作史跡,仍然需要說一說。
《罪惡的金字塔》是一首自由體詩歌,發表于桂林《詩創作》1941 年9 月第3、4 期合刊,后收入《蜩螗集》,現收錄于《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2卷。但保存下來的郭沫若手稿中有一篇抄錄清晰的該詩手稿,透露了一些我們所不知道的歷史信息。
這篇抄錄清晰的手稿,顯然是一份謄錄稿,因為一同保存的還有幾頁手稿,是這首詩的創作草稿。那么這份謄錄清晰整齊的手稿,應該是為發表所用。而這篇謄錄的手稿署名作“河芷”。也即是說詩人擬用“河芷”的筆名,發表這篇詩作。“河芷”之名,大概與《離騷》有關。屈原《離騷》中有“扈江離與辟芷兮”句,芷是香草名,“河芷”當是生長在江河中的香草之意。但該詩發表時的文本有一些改動,且沒有使用“河芷”的署名。
在這篇手稿之外,沒有見郭沫若以“河芷”為筆名的其他文章作品,這與前篇寫到的“老丘八”不大一樣,或者只能稱之為擬用筆名吧,但不妨也做個立此存證。
這篇手稿值得注意的另一則信息,是關于該詩創作時間的問題。作者于手稿文末所署的創作時間為“6 月8 日晨”,沒署哪一年。幾頁草稿是沒署時間的。
在收入《郭沫若全集》的該詩文末,所署創作時間為“1940,6,17”。該篇題注亦寫明“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桂林《詩創作》三、四期合刊”。那么“1940,6,17”這個日期從何而來?何以一篇即時性非常強的時事題材的詩作,寫成一年多之后才發表出來?這起碼不符合郭沫若作品創作發表的常態。
查看《詩創作》原刊,《罪惡的金字塔》發表時文末署“(六月七日)”。《郭沫若全集》是按照詩集來輯錄詩歌作品的,《罪惡的金字塔》輯錄在《蜩螗集》名下,再查看1948 年群益出版社初版本《蜩螗集》,該詩文末署創作時間為“(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七日)”。也就是說“1940,6,17”出自《蜩螗集》。就三處文本均署為“6 月”,但日期的不同而言,并非多大的問題,甚至稱得上為尋常事,從創作到定稿發表會有個過程的。但署“一九四〇年”是怎么一回事呢?
《蜩螗集》是郭沫若自己編的,其實作者將發表時未署年份的該詩創作時間,即使署為1940年,雖會讓人疑惑,但也難強說有誤。不過在《蜩螗集》輯錄的《罪惡的金字塔》文末,作者附寫了這樣一段話:“這首詩是為大隧道慘禍而寫的。日寇飛機僅三架,夜襲重慶,在大隧道中閉死了萬人以上。當局只報道為三百余人。”這段話是該詩在《詩創作》發表時沒有的文字(當然手稿、草稿上亦沒有)。《詩創作》于該詩文末附有一則“編者按”,道:“郭先生來信說:‘……最近很少寫詩,尤其是新詩,……x 月x 日大隧道慘事發生,曾親往洞口看運尸,寫了這首印象的東西,……恕我不加解釋吧。……’”
看來郭沫若是在1948 年輯錄《蜩螗集》時,想到了將創作該詩的緣由以文字附于文末,事由就是該詩發表時他給《詩創作》信函中所說的重慶“大隧道慘事”。
抗戰期間日寇對重慶長達數年持續轟炸的史實,現在已經有了清晰的歷史記述。雖未必能記錄下每一次轟炸的情況,但是有幾次轟炸,人們是有刻骨銘心的歷史記憶的,譬如:1939 年的五三、五四大轟炸。而造成大隧道慘案的那次轟炸,發生在1941 年6 月5 日。也就是在這次轟炸之后,作者方可能“親往洞口看運尸,寫了這首印象的東西”。這個日期與《罪惡的金字塔》發表時署創作月、日為“六月七日”,或謄錄手稿所署的“六月八日”,是可以吻合的。詩成后,于9 月發表在《詩創作》(該期刊物出版于1941 年9 月18 日),考慮到這是《詩創作》兩期的合刊,于郭沫若而言,應屬正常情況的創作發表周期。
看來該詩創作時間的問題,應該是郭沫若在輯錄《蜩螗集》時記憶有誤,把時間搞錯了。特別是把大隧道慘案發生的年代記錯了。其實還有一例亦是這種情形。在一篇未完稿《防空洞里人》中,郭沫若也寫到制造了大隧道慘案的那次轟炸,卻把時間寫作“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這種記憶上的錯誤,大概與日軍轟炸重慶的次數太多了有關,曾身臨其境的人會記得那些慘痛的史實,卻未必記得清每一次轟炸的具體日期。那么確切的創作時間,按照最初發表時所署月、日,加上年份,即:1941 年6 月7 日為好。
《慘目吟》、《轟炸后》是郭沫若創作的另外兩首大轟炸題材的詩,均已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2 卷。他還有幾首大轟炸題材的詩未曾收入單行本集子,所以也就未收入《郭沫若全集》,是為集外作品:《五用寺字韻》《母愛》《警報》等篇。
《五用寺字韻》是郭沫若在1939 年間所創作的十幾首寺字韻詩中的一首,約作于10 月間。這首詩是舊體詩的形式,但是用了敘事的方式。“無邊浩劫及祠寺,機陣橫空作雁字。由來倭寇恣暴殘,非我族類其心異。”詩句寫的是1939 年5 月3日、4 日敵機連續兩天轟炸重慶市中心的情形,羅漢寺、長安寺就是在轟炸時毀于大火之中。事實上,詩人所寫的十幾首寺字韻詩,基本上都是在對1939 年間發生的一系列時事作歷史敘事。
《母愛》發表于桂林《文藝生活》1941 年10 月15 日第1 卷第2 期,抒寫的是詩人在一次敵機轟炸后所見:
走上觀音崖的坡道上,
有兩位防護專員
扛著一架焦結著的尸體。
一位是年青的母親,
身體雖然全部都焦了,
但青春依然透露著。
右側的乳畔
焦結著一個嬰兒,
怕僅僅五六個月的光景?
左側的腹部
又焦結著一個,
也怕還不到兩歲吧?
母親的兩只手
——那多么有力的手呦!
各各和幼兒焦結成一片。
這是新的三位一體,
比文藝復興時期的圣母畫,
不是更要莊嚴嗎?
后來詩人又以這首詩為本,改作成散文《芍藥及其他》的一則,仍以“母愛”為題。
看來這種針對時事,具有鮮明紀實性的題材,更適于創作自由體詩歌。
《警報》是郭沫若在1941 年創作的另一首以大轟炸為題材的自由體詩。詩中沒有寫悲傷、沉痛,而以非常樂觀的情緒,描寫了人們在敵機來襲,警報拉響后從容應對的情景。
此外,郭沫若還有一些詩作間接寫到與大轟炸有關的史實、史事,如:《敬吊寒冰先生》《游縉云寺和田漢詩》等。
郭沫若當年創作這些詩作,實為“書所見如此,以志不忘”。它們或許如詩人自謙的所說,“作為詩并沒有什么價值,權且作為不完整的時代紀錄而已”,但這是歷史敘述的文本所難以見到的紀錄。
送西北攝影隊
《迎西北攝影隊凱旋》是《蜩塘集》中收錄的一首自由體詩歌,作于1940 年12 月。這是郭沫若在中國電影制片廠為歡迎往西北拍攝電影《塞上風云》外景歸來的攝影隊而舉行的歡迎宴上所作。
其實差不多一年前,1939 年歲末那一天,郭沫若為這支將赴西北拍攝《塞上風云》外景的攝影隊,還曾題贈了兩首送行詩:《疊用寺字韻贈別西北攝影隊》。這是未收入任何集子,甚至不為人知的兩首舊體詩。詩寫道:
(一)
純陽洞外喇嘛寺,
一塔嶙峋列梵字。
電影制片廠其鄰,
精神時代全相異。
初由武漢遷入岷,
斬山刊崖生訚訚。
防空洞深營三窟,
敵機雖暴如鴉馴。
慘淡經營幾二載,
辛勤換得巍峨在。
列宿明迷光麗天,
方人聚集江湖海。
感心最是夢蓮卿,
寄子遠舉俗塵驚。
欲把風塵寫塞上,
藝功當與佛齊名。
(二)
遠征將訪百靈寺,
幟題西北影隊字。
于時凜冽屆隆冬,
雪地冰天風俗異。
藝界勇者辭涪岷,
抗戰建藝氣殊訚。
不入虎穴焉得子,
豈得甘心羊兔馴?
此去凌寒將半載,
不教耳鼻徒健在。
若無偉績震寰區,
撫抱堅冰眠瀚海。
眾情慷慨邁蘇卿,
我亦瞠然自嘆驚。
三唱諸君萬萬歲,
千秋青史垂芳名。
中國電影制片廠前身為國民黨“南昌行營政訓處”下轄的漢口攝影場,成立于1935 年。1938年,中國電影制片廠在武漢成立,隸屬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郭沫若是時任三廳廳長。隨著抗戰局勢的變化,制片廠于1938 年9 月西遷入蜀,至重慶觀音巖純陽洞。這就是郭沫若詩開篇寫到的地方。
《塞上風云》原是陽翰笙1937 年創作的一部話劇作品。1938 年至1940 年間,該劇先后在漢口、上海、香港、昆明、桂林、重慶、廣州等地上演,頗受好評。1940 年初改編為同名電影,由應云衛導演,黎莉莉、舒秀文、周伯勳等出演。影片故事是發生在內蒙古大草原上,以抗戰為時代背景,制片廠特別組織了西北攝影隊去大草原拍攝外景。
外景地即詩中寫到的“百靈寺”,應該指“百靈廟”,詩為寺字韻,故用寺字,寺廟之謂。百靈廟作為地名,指百靈廟鎮,因廟得名,位于內蒙古包頭市境內,是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政府的駐地。1936年,在這里曾爆發過百靈廟武裝抗日暴動和百靈廟戰役。或許正是因此,這里被選為外景地。
時屆隆冬,天寒地凍,往西北地區拍攝,工作條件的艱苦可想而知。郭沫若高度贊揚攝影隊隊員們為藝術獻身的大無畏精神,稱贊其慷慨豪邁之氣勝過古代歷史上在北海持節牧羊十九載的蘇武。
影片全部制作歷時兩年,于1942 年2 月首映于重慶。
1939 年間,重慶文化界盛行作寺字韻詩,郭沫若在這一年內寫了十余首,這兩首大概稱得上是他當年寺字韻詩的收官之作了。
“老郭不算老”
“老郭不算老,詩多好的少”。這兩句叫打油詩也好,叫順口溜也罷,很多人聽到過,但都是口口相傳,查郭沫若的詩歌作品集或整理他的佚詩,并不得見,所以也有人疑其為調侃戲說的文字。也有誤傳為“文革”期間題寫給紅衛兵的,或說是在一次科技大會上發言所講。事實上這是一首詩中的兩句,確實為郭沫若所作。詩先是隨手寫在一封信函上,后錄入一篇短文。文章雖發表了,但后來并未收入《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所以隨時間流逝,詩句有人記得,且口口相傳,詩文的創作及出處卻鮮有人知了。
那是1958 年末的事情。12 月18 日,郭沫若收到《文藝報》文學組編輯的一封約稿信,信中說:“今天《人民日報》第8 版上有一組《孩子的詩》,我們看了覺得很好,有一位小詩人還寫道:‘快馬加鞭趕郭老。’編后小語里也提到:‘后生可愛,他們是會超過我們這一代詩人的。不知郭老和其他詩人們以為如何?’因此,我們想請您寫千多字的小評論談談這些詩。”郭沫若接讀約稿信后讀了《孩子的詩》,隨即草擬了一篇評論短文。文中寫道:
《人民日報》(1958 年12 月18 日)第八版有一組《孩子的詩》,我讀了。我同意編者的話,真是“后生可愛”。十二首里面有一首叫“小作者”特別提到了我,那詩是:
“別看作者小,
詩歌可不少,
一心超過杜甫詩,
快馬加鞭趕郭老”。
是工農中學一年級劉玉花作的,特別是第三句,氣魄可真不小。編者認為這些小作者是會“超過我們這一代的詩人的”,問我“以為如何”?我要老老實實地回答:我完全同意,他們一定會超過我們,特別是超過我。因此,我作了一詩來答復那位小作者。
撰寫這篇短文的同時,郭沫若先在約稿信上用紅筆寫下幾句詩:“老郭并不老/詩歌實在少/少還不要緊/既少又不好/快馬再加鞭/老小同賽跑……”詩未寫完,斟酌一番,最后改成五言四句,寫在信的頁眉上,并錄入短文中:
“老郭不算老,
詩多好的少;
老少齊努力,
學習毛主席!”
郭沫若于18 日夜作成短文《讀了〈孩子的詩〉》,19 日晨即送出稿子。大概因為《孩子的詩》是《人民日報》第八版編發的,所以郭沫若把自己的評論文章先送到《人民日報》第八版編輯那里,并在手稿上附言,告以:“這是《文藝報》要我寫的,請您們看了,即轉《文藝報》。”不過,《人民日報》編輯看后卻留下了郭沫若的短文,20 日發表在自家報紙上。
詩的末句“學習毛主席”,指學習毛澤東的詩詞創作,倒并非套話或虛應之詞。1957 年《詩刊》創刊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18 首詩詞。郭沫若看到后由衷的欣賞,即作《試和毛主席韻》詞三首:《念奴嬌(小湯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調歌頭(歸途)》,和毛澤東所作《念奴嬌·昆侖》《浪淘沙·北戴河》與《水調歌頭·游泳》。不久,又撰寫了《一唱雄雞天下白》一文,稱贊毛澤東詩詞“是有高度的創造性的,意境開闊,聲調宏朗”。
郭沫若這四句口語體的詩,看似是為呼應“孩子的詩”而作,其實反映了他此時正大力提倡新詩創作要學習、吸收民歌、民謠創作的優秀傳統。他與周揚合編了一本《紅旗歌謠》,認為“新民歌對新詩的發展會產生愈來愈大的影響”。他稱今天的民歌、民謠是“今天的新‘國風’”,相信“新時代將會有從新‘國風’的基礎上創化出來的新‘楚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