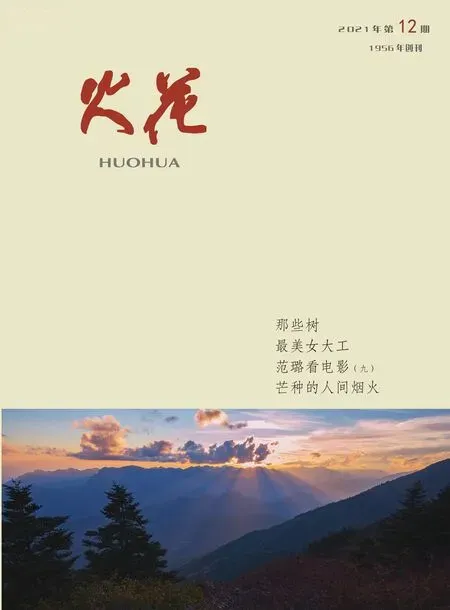蔡潤田:后樂先憂古士風
楊占平
2013年的最后一天,作家韓石山先生讀過蔡潤田作品集《南華雜俎》后,致函蔡潤田先生,稱其“既見學識,又見文彩”,并手書一聯相贈:“老安少懷平生志,后樂先憂古士風”。這兩句話應當說是對蔡潤田一生為人為文相當準確到位的評價。作為山西文學界當今資深的編審、評論家、散文家,蔡潤田是伴隨著新時期山西文學的發展一路走過來的。他沒有大起大落的官場經歷,沒有轟轟烈烈的文壇焦點,也沒有讓人經常議論的人生風雨,總是兢兢業業干事、認認真真寫作、老老實實做人,工作任職期間業績圓滿,作品雖然不夠多卻沒有劣質,跟人們相處一貫謙謙君子,傳承了古往今來文人士子的風節,口碑很好。
蔡潤田的祖上原本居住在山西省平定縣石門口村,祖父在天津一戶商鋪做賬房先生,收入尚可維持全家生計;可惜英年早逝,家境很快陷入困厄。迫于生計,奶奶攜幼小父親改嫁到本縣朝陽堡村白姓人家。奶奶明事理,讓父親幼年即進入私塾,接受孔孟蒙學教育,把《三字經》《論語》《孟子》之類四書五經都讀爛了,課余還要下地做農活。長大之后,結婚生子,繼續祖父之業,外出行商,足跡遍及晉冀多個縣份。
1943年陰歷六月十五日,蔡潤田出生。有父親經商供養,全家生活能夠保障。然而,那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年代,平定縣作為敵我“拉鋸”地帶,經常有戰事,人心惶惶。他剛剛四歲時候,為避兵燹,一家人離開老家,跟隨父親到了省城太原,仍然是戰亂不安。當時鐵路已經中斷,父親多方努力弄到機票,帶領全家人乘坐慈航班機,飛到天津,又轉至唐山,伙同先期到達的親友,從事印染業買賣。四歲的蔡潤田,坐飛機的奇妙印象并不深刻,只記得顛沛流離,幼小的心靈對大千世界產生的是恐懼心理。
蔡潤田一家在唐山安頓下之后,十來年光景,依靠父親自任掌柜,先后輾轉唐山郊區、灤縣、灤南縣的多個鄉鎮開染坊,做實業,付出很多辛苦,收入也不錯,雖然是國家新舊交替時候,卻讓全家的生活過得還是比較順暢。父親喜歡他,帶他跟隨各地,給他留下美好的記憶,這在他的散文集《獨語集》里有極其鮮活的表現,至今他都能講出當時去過的小新莊、甸子等地的許多故事。平原的廣袤遼闊、鄉民的淳樸友善、生活的優游無慮,正是這些自然與人文環境,鑄就了他幼年率真樂天的性格。
但是,到了蔡潤田七八歲時,他的母親患上癆病,不及三十歲就去世了。這個變故對他的打擊非常大,感覺未來的生活一片茫然,快樂的日子再也沒有了。雖然不久父親再婚,繼母也能滿足他生活的基本要求,畢竟感到隔膜,難以給他精神上的慰藉;同時,父親看他到了讀書年齡,為了他長大后能成才,管教也嚴格有加,這樣,年幼的蔡潤田越來越拘謹,不敢在大庭廣眾下多講話,做事總是小心翼翼。
1956年,國家對各類企業實行大規模的公私合營政策,蔡潤田父親經營的染坊被合并到公有制企業,父親不再參加管理,收入也大不如前。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次年他們一家遷回山西平定老家。起初在鎮上開裁縫鋪,不久停業,就回到本村。家境、環境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吃飯居住條件更是下降很多。在村里,他們家是唯一的蔡姓外來戶,當時,宗法意識很濃的農村,都是以家族為伙伴來往,他們家本來就是外來戶,再加上新回到村里,自然要受到排擠打擊,人際關系比較緊張。新的生存環境讓蔡潤田非常不適應,進而使他已經少言拘謹的性情更為加重。那時,他尚未讀完高小,轉到鎖簧鎮學校讀了幾個月畢業了,憑著優異成績考入平定中學。
中學生規定住校,能夠暫時脫離家庭的煩惱,讓蔡潤田似乎找到了新的凈土,一切都向順暢愜意目標進展。他靠著出色的學習成績,當上學校大隊委、語文課代表等等,除了認真完成各門功課,還積極參加課外活動。然而,席卷全國的反右運動迅猛到來,就在他們學校里,同樣進行得轟轟烈烈,他眼見一些平素所尊敬的老師驟然成了右派,被批斗的場面讓他這個好學生無法接受,他感到惶惑甚至悚懼,想到自己將來想靠好成績謀前途是多么不容易。
如果說反右運動中蔡潤田還只是一名觀看者,那么,轉年又掀起的反右傾運動,他就沒那么幸運了。這場運動有所謂“拔白旗、插紅旗”內容,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成了運動的對象。當時,十四歲的蔡潤田是初一第二學期學生,初露文學寫作才華,在老師的指令下,為學校的墻報寫了一篇稿件,題目為:《汪洋一幼魚》,大體內容是抒寫了一個熱情上進卻感到迷茫無助的少年,期望得到黨的引導,以便走出迷茫,走向光明。不料,稿子被團支書認為是傾向不正確,拿去交給了一位由輕工局派到學校的專職“紅旗”班主任。這位政治至上的班主任如獲至寶,多次找蔡潤田談話,要他交代寫作動機是什么,這讓他惶惶然不知所措。接著,班主任召集全班同學以及科任老師開他的批判會,說他稿件中的“黨”,是國民黨,說他是小右派、反革命,等等。一個初一學生,哪里經歷過如此屈辱,本來就脆弱的心靈受到了嚴重挫傷,極大地改變了他的思想性情和生活態度,只能以消沉畏縮的心態觀察社會,與人交往也因為壓抑而變得沉靜甚至于冷漠;于是,中學生蔡潤田不再參加任何課外活動,除了上課,就是尋找各種書籍閱讀,好學勤思的習性悄然形成,他感覺到,只有讀書和思考才是最適合自己的,在書海里,他可以暢快游動,獲取豐富多彩的知識。
經歷了那次“運動”,蔡潤田與讀書結下了不解之緣,讀書也成為他終身不棄的愛好。整個中學時期,他以近乎狂熱的狀態披覽所能得到的益智悅性的書籍,尤其是魯迅著作,盡管似懂非懂,囫圇吞棗式閱讀,卻能領略到魯迅作品中那種不屈辱的品格,讓他受用一生。喜歡上讀書,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購書、藏書的嗜好,李國濤先生說“他對藏書頗有興趣”,興趣在當時就開始培養起來了。他把家里給的不多的生活費精打細算,伙食標準降到最低,節省出一點錢來跑書店,遇到喜愛的或者覺得稀奇的書,毫不猶豫地買下,一些書至今還珍藏著。讀書多了,就有想自己寫的想法,于是,開始了讀書筆記的寫作,記述自己的思考與煩惱,也成為他后來文學寫作道路的開始。
1960年中考,蔡潤田以出色的成績,考入陽泉二中,進入高中學習階段。他已經十七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卻遇到國內大饑荒年代。家里同樣遭受不測,繼母與慈愛的祖母都于當年去世,父親雖堅韌、勤苦,也無補于事,他的生活和學習條件也難免窘迫,經常處在饑餓狀態。好在換了學校,政治上對他的壓迫不再明顯,他喜歡讀書的特性得到充分發揚,客觀上,也是由于讀書可以減少饑餓感。高中階段,接受能力有了提高,他把興趣從現當代文學轉向古典文學,不少名篇佳句當時都曾熟背,并和二三有相同嗜好的同學學著寫詩唱和;同時,把古詩文選本放在身邊,隨時翻閱;讓他最喜愛的是由中華書局剛創刊、裝幀簡樸、價格便宜、旨在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中華活頁文選》,幾乎期期都買。假期住到北京表姐家,表侄帶他跑書店,到東安市場古舊書店買下《三蘇文萃》《經史百家文鈔》《李長吉集》等線裝書,回來半懂不懂地閱讀瀏覽。應當說,他對古詩文的興趣與修習,是從那時培植起來的。蔡潤田喜歡讀書,讓許多同學和老師贊賞有加,畢業時,一位因病不能高考的同學送給他一套范文瀾注的《文心雕龍》,語文老師送給他一本《何其芳散文選》。或許這位同學和那位老師想不到,研究古典文論與寫散文,真的成了他畢生的喜好,尤其關于《文心雕龍》的研究,使他進入了國內“龍學”研究的學者行列。
充實的高中生活,讓蔡潤田收益良多,從一個青澀少年進入有思維有理想的青年時代。1963年高考,他的成績自然是優秀的,出于對文學和教育事業的愛好和尊重,報志愿時,他報了中文系與教育系,理想是要做一個文學家或教育家,到校后才知道,教育系招收名額不夠,便從報教育系的考生中把他錄入了。二者不可兼得,他也只能接受。
接收錄取通知書還出現了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插曲。當年夏末,得知錄取通知書已經下達,蔡潤田興沖沖地從平定縣的家里騎了自行車趕到陽泉二中去查看,結果同班四位考上的同學都收到了錄取通知書,就是沒有他的。他覺得自己不幸落榜,特別沮喪和失望,但也只能喪魂失魄地往回返,老天也發難,剛出市區,就遇到瓢潑大雨,一路上坡,行進維艱,苦苦行至平定縣城。他鬼使神差地到了縣教育局,向一位領導講述自己高考情況,表達想當一名教師的心愿。那位領導知道他成績優秀,動了惻隱心,要幫助他,讓他去一所鄉完小當臨時教員。這個結果在當時,真可謂是根救命稻草了,他深表感激,欣然從命,當即到了那所學校,履職任教。一星期后,他回家看望老父親,竟在大隊辦公室看到了自己的錄取通知書,原來是陰差陽錯,通知錯發到昔陽縣,又輾轉回到他的村里。這個插曲,還是讓他感受到了人間有溫暖。
1963年秋天,二十歲的蔡潤田帶著對未來美好的憧憬,進入山西省最高學府山西大學就讀。盡管不是中文系,但教育系所設立的科目,諸如生理學、心理學、教育學、教育史、邏輯學、習作、古代漢語等等,新穎而雜多,都是他比較有興趣的。大學生活不像中學管理嚴格,課業也不重,課余他就去讀那些愛好的文學書籍。圖書館的閱覽室,晚上,那長長的栗子色書桌上,綠油油的玻璃燈罩下灑出一片清輝,清幽、靜謐的氛圍令青年學子蔡潤田特別陶醉。在那里,他如饑似渴地讀鄭振鐸編的《世界文庫》,讀趙家壁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讀蒙田的散文,讀尼采《蘇魯支語錄》,讀世界名著《美狄亞》《死魂靈》《簡愛》,讀古典詩文《唐傳奇》《花間集》,讀魯迅、冰心、朱自清……時日既久,竟招來系主任老師的注意,在其學生花名冊上,給蔡潤田名字下注明“跑圖,不鞏”的字樣,意思是愛泡圖書館,專業思想不鞏固。但他并沒有太在意。可惜這樣安心讀書的日子不長久,1965年就斷斷續續走出校門參加“社教”“四清”運動了。
1966年夏天,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山西大學是全省的運動中心之一,三年級學生更是主力,蔡潤田不可避免地被裹挾到運動中。1968年10月,中央下達命令,全國所有大學生到部隊農場接受再教育。于是,他跟同學們奉命到了河北獲鹿的解放軍農場,在解放軍官兵的帶領下,每天或勞動,或軍訓,或政治學習。
1969年底,各地大學生結束勞動教育,分配工作,按照當初離校前的校方分配方案,絕大多數下到基層的工廠、學校、鄉鎮,而蔡潤田是比較幸運的,被分配到陽泉市文化系統,并且就留在文化系統革委會機關業務組,這讓他感覺到命運的垂青。他的工作主要是編輯刊物《文化戰線》,組織全市文藝匯演,還有其它日常具體工作。由于他年輕肯干,樂于出力,盡管事務很多,卻也深得領導和老同志們的關愛。三年后,文化系統革委會撤銷,恢復文化局,他也隨之成為文化局工作人員,主要工作仍然是組織業余創作,經常下廠礦、農村開會或者審看各類稿子。不久,局領導讓他創辦《陽泉文藝》,集中刊發本市作者的文學作品。這項工作基本上是他一個人做,但這正是他喜愛的,自然干得非常上勁,把刊物辦得有聲有色,推出了不少后來成名的作家。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蔡潤田感覺到自己也應當創作,用作品證明自己的實力。他先后寫出表現一位煤礦工人為了集體利益而犧牲崇高精神的長詩《張啟林之歌》,寫出反映抗日戰爭時期礦工斗爭生活的多幕劇本《礦山怒火》,還在一些省內外報刊發表文藝評論文章。這些作品初步展露出他的文學創作才華,也受到省里文化部門領導的注意,曾經被抽調到省文化局觀摩各地市戲劇匯演,撰寫相關評論文章,并且參加過幾次省里召開的創作、評論會議。
1975年10月,山西省文藝工作室(也就是后來的省文聯、省作協)在太原召開創作會,為《汾水》雜志創刊組織稿件,蔡潤田應約與會。工作室負責人馬烽、西戎等進一步考察了他的寫作水平、工作情況,對他的知識積累、為人處事都滿意,這樣,會后就被留在文藝工作室,隨后辦理了調動手續,正式成為《汾水》雜志的一名編輯,參與創刊選稿、編稿、撰稿事宜,重點負責詩歌欄目。工作單位的變化,讓他從市級進到省級,環境隨之改變,與過去仰慕的老作家馬烽、西戎、胡正,與前后調來的有成就的作家、評論家、編輯家段杏綿、郁波、李國濤、顧全芳、馮池、周宗奇、張石山、王東滿等成為同事,讓他既高興,也有壓力,決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也要在寫作上有成果,做一名名副其實的稱職的文學編輯。
蔡潤田在《汾水》以及后來改名為《山西文學》編輯部,做了整整十年編輯,主要是編輯詩歌和評論。他特別敬業,一方面向老編輯虛心求教,把握當編輯的基本功,另一方面自己潛心琢磨、研究,幾年過來,就成為一名非常熟練的詩歌和評論編輯,能夠從大量的來稿中發現最好的作品,發現有培養前途的作者。那個時期山西活躍的詩人文武斌、梁志宏、馬晉乾、張不代、陳建祖、秦嶺、周所同、李建華、趙國增、華丹、郭志勇等,都因為詩歌稿件跟他成為很好的朋友;而評論家鄭波光、張仁健、張厚余、程繼田、高捷、武毓章等,同樣跟他成為終身來往的學術研究同道。
作為一名文學編輯,工作之外,一定要用創作來證明自己,蔡潤田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在完成編輯工作之外,他努力寫作,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配合編輯部編稿需要,以“編者”或者筆名茹辛、茹歆、金梓等,撰寫編輯手記、評論,或者配合文學活動撰寫述評,配合形勢和刊物需要寫些新詩;另一方面,伴隨思想解放大潮,適應文藝事業發展,對文學創作、理論研究領域的問題進行反思,寫出了一些辯駁與解析文章,代表作有:在《光明日報》發表的《略論典型化》,在《山西大學學報》發表的《文學與人性》,在《山西師范學院學報》發表的《朦朧詩風格特點及其形成原因淺探》,在《汾水》發表的《試論“寫中間人物”》等。這些文章既有理論深度,又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在學術界和文學界都產生過積極影響,其中《文學與人性》一文被選入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人性、人道主義問題討論集》一書中。《試論“寫中間人物”》獲首屆趙樹理文學獎。此外,按照他自己的研究興趣,純粹出于學術研究,認真研讀中國古代文論中最經典著作劉勰的《文心雕龍》以及其相關的“風格”問題,寫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文章,在國內研究《文心雕龍》領域,自成一家,得到眾多學者的首肯,不少篇目被權威的《文心雕龍》研究文獻著錄,被《新華文摘》《文藝理論研究》《當代作家評論》等雜志摘介。評論家李國濤在給他的文集《泥絮集》序中說:“潤田浸漬《文心雕龍》十年,又是為了繼承古代文論的傳統,對當代文學進行評論。潤田的評論文章,字斟句酌,簡約清麗,在文體上也很受了劉勰的影響。”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山西一批青年作家憑借豐厚的生活積累、充足的知識準備,創作出一大批優秀作品,在全國文壇闖出一片天地,被稱為“晉軍崛起”。但是,作為與創作同為兩翼的山西文學評論,卻不能跟創作同步發展,并且比較滯后。這個問題成為制約山西文學發展的瓶頸之一,也引起山西省宣傳文藝部門領導的重視,順應廣大作家和評論家的呼聲,決定由省作家協會主辦一份文藝評論雜志。
省作協黨組研究,決定由董大中做主編、蔡潤田為副主編,具體創辦。他們經過深思熟慮并征求意見后,把刊物定名為《批評家》,得到領導的認可,得到廣大作家和評論家的贊同。他們從最基礎工作做起,找辦公室,落實經費,跑印刷廠和郵局、書店,選調編輯,外出約稿,于1985年4月,出版了《批評家》創刊號,打造了山西文學史上第一份專門的評論雜志,對于推動山西文學創作發展、培養青年評論人才、及時評介作家作品,起到了特殊作用,在全國文壇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由于他編輯工作的一貫認真負責,同年五月,獲得首屆“山西省優秀文學編輯獎”。
在做好《批評家》編輯工作的同時,蔡潤田寫了不少關于山西作家作品的評論;同時,他注意到在新時期文學的蓬勃發展中,漸漸地顯露出一些不好的苗頭,有感而發,寫了一組力圖糾偏的文章,如《新潮求疵錄》《文學的成熟、人類的悲哀》等。后者以封面標題形式全文選入1988年11月《新華文摘》,并獲“雙塔”全國征文獎一等獎。這些文章都是扎根于現實,有時代特征。
1989年底,《批評家》雜志因故停刊。一份有過很大影響、培養出一批中青年評論家、刊發過許多優秀文章的雜志,留下諸多遺憾,留下諸多話題,結束了使命,也結束了蔡潤田在省作協長達十五年的編輯生涯。三四十歲的大好年華,都貢獻給了編輯事業,他有欣慰,也有感慨。在出版《泥絮集》的自序中,他引用清人王蘋詩句“身如上水船難進,身似沾泥絮不飛”,取“逆水行舟”“沾泥之絮”的意思做書名,自謙之余,寄托了編輯與寫作難以兼擅的感慨。同年,還出版了他與山西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恒合作搜集、譯注的《中國歷代諧趣詩》,此書出版后,頗受歡迎,很快銷售一空。此外,編輯之余,還應約參與了《中國新詩鑒賞大辭典》《唐宋元小令鑒賞辭典》的詞條撰稿、《山西民歌》的評點等項撰述。
《批評家》停刊,他轉到省作協文學理論研究室任主任。楊占平、閻晶明、謝泳同時轉入。這個理論研究室在作協是工作職能部門,不是研究機構,主要是配合作協的行政和業務工作起草相關文字材料,重點關注本省各項文學種類創作動態,研討創作成果,包括評介作家作品、組織研討會等。
在理論研究室任職,不用按時編輯出版刊物,工作量少了不少,就相對多了自己讀書寫作的時間。蔡潤田出于興趣,同時,也因為大學期間有過心理學的知識儲備,集中精力推出了長篇文章《文學氣質論稿》,受到了相關研究人員的高度評價,有學者說:“蔡潤田在《文學氣質論》中,從生理和心理的角度研究了古今中外對氣質的探究和這種氣質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有碩士論文引用蔡潤田的理論觀點分析賈平凹的創作。在這期間,他還寫出較有分量的闡述散文發展及特征的《散文散論》,應約參與了《中外文學名著人物辭典》《唐詩精品》等書籍的撰稿。
1996年,蔡潤田意識到自己年事已高,應當抓緊時間創作,不太適合繼續擔負部門負責人,于是,向作協黨組提出請求,辭去理研室主任,到文學院從事專業創作。黨組尊重他的意愿,批準了他的請求。不過,兩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他雖然不是上級提名的候選人卻破例被選為省作協副主席,充分反映了全省文學界人士對他工作和成績的認可。當了副主席,就得完成一些主席團交給的工作,但畢竟不占用他太多精力。
有了比較寬裕的時間,蔡潤田投入到讀書寫作中。他感覺到自己的性格和興趣多半在古典文學上,因此,集中研讀古代文學史上魏晉之際嵇康、阮籍等人的書籍,撰寫出了一批相關論文,比如《難以評說的嵇、山之交》《婞直之風與龍蛇之道》《嵇康論敵與摯友》等;同時,在《太原日報》《太原晚報》《合肥晚報》等報刊開專欄,寫散文與學術隨筆之類的文章,數年后結集出版了散文隨筆集《獨語集》。評論家孫釗說:“書名獨語,其實非也。書中的文字都是在同讀者進行和平的交流,屬于那種溫文爾雅的性情中語。所謂獨語,我覺那無疑是作者的自謙,不只是有意規避炫耀之嫌,更透著一種儒雅的矜持。這和一些文人輕狂、矯情乃至自我炒作顯然成一反觀。從頭至尾讀一遍《獨語集》,讓我們想到中國文人慎獨的傳統品質——它所蘊含的審慎、平和、謙謹,獨善其身,大體和我們今日的道德自律意思一樣。因為它的久違,這些流利而質樸的文字里讀出了自覺的人格意識,我們被感動著。”作家韓石山說:“書名《獨語集》,想來是說,這一切不過是心靈寧靜的回眸,繁華落盡的獨白,不妨說是抖落了世俗的桎梏,顯出了本真的心性。這一抖落,顯現出來的不光是心性,就是文字,也變得清純自然,充溢著妙曼的生機。別說那些記述少年憨直、青春戀性的文字了,就是抨擊世態的文字,也同樣顯示著一種內在的活力,感人的深情。”
此外,為紀念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省作協交由他主編全面展現山西文學五十年進展歷程文學史著作《山西文學五十年縱橫論》。他和大家首先梳理了這一時期山西文學史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制定出詳細而有專題性特點的提綱,然后依章節先后,由杜學文、傅書華、蘇春生、蔡潤田、閻晶明、楊占平、段崇軒、謝泳、孫釗、王春林、楊矗等評論家分頭撰稿,這些人都是省內年富力強、學術有成的一時之選,為著作質量提供了可靠保證。蔡潤田參與撰寫并逐篇審定,傾注了大量心血。這部書出版后,受到省內外廣大文學界人士和讀者的好評,成為最具權威性的山西當代文學史著作之一。
2003年,蔡潤田年滿六十周歲,按政策規定,辦理了退休手續。不過,這個退休對于像他這樣的作家、評論家來說,只是一種體制身份的轉化,研究和寫作并不受任何影響。他仍然跟過去一樣,有規律地讀書、寫作、生活,有選擇性地參加一些文學活動。十年時間,繼續進行自己的選題,先后出版了《三邊論集》《南華雜俎》《縱橫且說宋之問》等作品集和專著,后者還是國內少有的有關宋之問研究的專著。這些作品和專著更為成熟、老到,文學界諸多人給予很高評論。詩人、作家寓真2015年元月賦詩說:“雅才成雜俎,酌古復斟今。談藝詮人性,論儒辨道心。熔裁文若錦,惜墨字如金。健筆勤無輟,新年耕愈深。”熱情贊揚了他的學問根底和文字功力。
總結蔡潤田走過的七十多年人生與文學道路,可以說,他是個富有深厚學養與藝術追求的評論家、散文家、編輯家,是個認認真真為人處事的文化之士,是個有情懷、愛憎分明的學者型人物。2014年春節,他寫了一首《馬年自嘲》的詩:“桑榆有馬難著鞭,獨行踽踽且安然。閉門哪知風頭勁,嚼蠟不覺世味艱。煮字但求七成熟,應物倒要十分憨。情知寸金不多讓,卻道曉岸近客船。”這首詩雖說有些自嘲意味,卻也折射出他立身處世的行為,是對自己很好的評價和寫照。蔡潤田用嚴謹的為文態度和坦蕩的為人品格,書寫了自己的平凡而不平淡的人生與文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