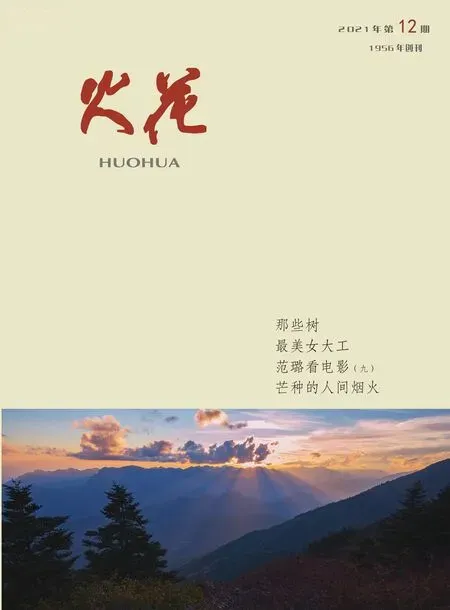那些樹
方華
苦楝
那棵樹就在外婆的屋前,粗壯的枝干上滿是紋裂,像外婆那張滄桑的臉。
樹在春夏之交開花,滿樹淡紫色細碎的花瓣散發著淡淡的清香。花開過后,結出青色的小果,櫻桃般大小,只是非常苦澀,不能食。到了秋冬,果子變黃,一串串掛在樹葉落盡的枝頭,特別的顯眼。
青黃的小果子成為我和小伙伴們手中的玩物。攀爬到樹上,一個個裝了滿衣袋的小果,然后在村舍和鄉野間發動一場場“子彈”飛舞的戰斗。
小時候尿床,每每在床墊上“畫了地圖”,外婆就將被絮晾曬在拴在那棵樹干和窗檔上的一根麻繩上。這時候,我會苦守在樹邊,想著法子引走小伙伴,不讓他們走近,怕那“絕密地圖”被發現。
守在樹下最多的時光,是在夏夜。一張涼床,一把竹椅,在樹隙中篩下的星光月色里,聽外婆說西游記,講今古傳奇。
記得某個夏日,身上生了癬,奇癢難耐。外婆就從那棵樹上剝了幾片樹皮,又摘了一把樹葉,在鍋中熬湯給我涂抹,沒幾日,便癬消癢失。剩下的藥水,外婆將它灑在屋角,說是可以驅蟲殺蟲。
外婆是一位民間醫生,懂得許多草木的奇效。比如我的表妹冬天手上生凍瘡,外婆就是將那棵樹上的小黃果子搗爛,包敷在那紅腫的小手上。
父母終于調到一個城市工作,結束兩地分居,我也從鄉村轉到城里上學。母親接我離開外婆那天,外婆就站在那棵樹下向我揮手。那時,正是滿樹花開的日子,一樹的紫色映襯著外婆瘦削的身影。誰知,這竟是外婆留在我心中最后的形象。
生活在都市,很難見到外婆屋前那棵開著淡紫色小碎花、結滿小果的樹。偶爾遇到一棵,趕緊詢問附近人家,卻一直沒有得知這種樹的名稱。就像我現在一直無法得知外婆的名字,或許,外婆那樣年代的人根本就沒有什么大名,她嫁到了我母親的王家,或許就是一個“王氏”之名。
那天,看到一位網友拍攝的圖片,那熟悉的細碎的花朵滿畫面地紫著。畫面的下方有幾個字:苦楝花。原來,那棵樹就是苦楝樹啊。
記得夏夜的苦楝樹下,外婆給我說的西游記里,唐僧師徒過通天河,答應負他們渡水的神龜,問一下如來它能活多少歲。可是唐僧取經歸來,卻忘了此事。神龜一氣之下,把四人甩進河里,經文全濕。唐僧師徒撈起經書,晾曬于樹上。這棵晾經的樹就是苦楝。真是曾經相識不相知,只是我幼時晾曬的是尿濕的被絮。
也記得古籍《花鏡》上有句:“江南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為首,楝花為終。”意思是說,到苦楝花盛開的時候,春天也就結束了。又找到一首宋詩人溫庭筠以《苦楝花》為題的詩:“院里鶯歌歇,墻頭蝶舞孤。天香薰羽葆,宮紫暈流蘇。晻曖迷青瑣,氤氳向畫圖。只應春惜別,留與博山爐。”
原來,苦楝花開就是一場人生的惜別,就是一份留在生命中的美好懷念。
苦楝——苦念,如此的諧音,那棵苦楝就是為了我心中的那一份情感而來嗎?“楝花飄砌,簌簌清香細。”愿那縷縷細香,把我這份苦澀的思念渲染浸透。
泡桐
泡桐花開了,像一團紫色的夢,渲染在鄉村大地。
在我生活的這個長江北岸的平原地帶,那些或依山傍水或靜臥平川的村落,隨處可見泡桐的身影。而每個村莊里,也總有一兩棵粗壯的泡桐高過錯落有致的村舍。花開的日子,這些水墨的村莊被泡桐的淡紫點染著,像一幅幅清新秀麗的畫卷。
如果你走近一棵泡桐,你會看到那懸掛著的花朵,像一串串玉瓷兒般的風鈴,在風中搖曳,著實玲瓏可愛。如果你有一顆敏感的心,似乎可聽到它們相互碰擊的清音。
在我的故鄉,沒有人刻意地去栽種泡桐,完全是自生。有的是老樹邊上的叉生,更多的是風把泡桐果子帶到了一個地方,就此生根、發芽、成長。泡桐樹長得很快,幾年的功夫,小苗兒就變成了參天大樹。這多么像我那生活在鄉間的小伙伴們,分別多年以后回去相見,竟一個個已是難尋那當年的青蔥稚嫩。
剛從鄉下搬到縣城時,小城里也常能見到泡桐的身影,三三兩兩地生長在松散的巷陌樓舍間,有點像小城的生活狀態,自然、純樸、隨意。
記得我居住的,是一個有著幽深庭院的明清式兩層青磚木樓。一個春天,院墻根處突然冒出一棵小樹苗兒,起先并不在意。等至春末,小苗兒已迅速長成一棵小樹,這才發覺,原是一棵泡桐樹兒。這棵自生的泡桐硬生生地在墻磚的縫隙之間扎住腳,到第二個年頭,已是一棵茁壯的樹兒,并開出滿枝的花朵。
閉塞在陳舊的樓舍間的庭院,到了夏天濕熱難當。自從有了這棵斜生的泡桐,平添了幾許陰涼。早早晚晚,母親會將一張小餐桌搬到樹蔭下,一家人圍坐進餐,其樂融融。而伸到我窗口的寬大泡桐葉片兒,又給了我多少詩意與遐思。記憶里特別深刻的,是泡桐花綻放日子里的那一個個月朗星稀之夜。晚風過處,花兒飄零,一地的紫色花朵臥在月光上,給那懷春的少年增添了幾多甜蜜的煩惱與纏綿的憂愁。
隨著時代的發展,城市不斷改造。我親眼看著那棵已是花冠如蓋的泡桐,在傾倒的磚土瓦礫間被兩名工人鋸斷,訇然倒地。變得越來越高、越來越大的城市,馬路寬了,綠地多了,可是,卻很難見到泡桐樹的影子了。城市里多的是樟樹、冬青之類四季常青的植物,營造著單調的綠意。
又是泡桐花開時。在這樣的一個日子里想起那抹魂牽的紫色,不是對舊時光的留戀,而是對一種悠然恬靜生活的回味。于是決定,趁著泡桐正開,到鄉間去走走,看一看那夢繞的身影,探一探那氤氳的鄉情。
香椿
去菜市場買菜,見一農人面前的竹筐里擺放著許多嫩芽頭,散發著誘人的香馨———知道鄉下的椿樹又發芽了。買下一把香椿頭,心里卻在感慨,久居城市,豈止是對季節的變幻麻木,就是那濃濃的鄉情,也在喧囂的生活里淡遠了。
對香椿有著一份特別的情感。
即便是在鄉下,香椿樹也是不多見的。記得小時,村前屋后,多的是一種不能吃的椿樹,俗稱“臭椿”,樹上爬著一些扁扁的小蟲,身上散發著一股騷臭味。能吃的“香椿”,村中只有兩棵,一棵在一遠房堂叔的院子里,一棵就在我家的屋前。
香椿樹那時在鄉下沒人特地去栽,完全是自生。因堂叔院子里的那棵看得緊,每當桃花凋謝、香椿發芽、嫩黃的芽葉生滿枝頭的時候,就有村人到我家的屋前采摘,嘗個新鮮。與和善的母親打聲招呼,或攀爬、或勾拽,就將一把青嫩嫩的椿芽兒采了去。有客氣的,來時還會帶上三兩個雞蛋什么的。
香椿頭可以涼拌著吃,也可以腌了曬干后存放。最常見的吃法是炒雞蛋。那時候鄉下都燒柴草,灶臺上的鍋很大,每當母親用香椿頭炒雞蛋時,一屋子都飄蕩著馨人的芳香。直到現在,每當吃到香椿頭炒蛋這道菜,眼前總浮現出母親在灶臺前那片氤氳里揮動鍋鏟的身影。
遠離故鄉,在城里生活了幾十年。椿樹發芽的日子,偶遇鄉鄰進城帶來幾把香香的葉兒,總感覺比菜市場、超市里買的香郁,是那葉芽兒里飽含著濃濃的鄉情吧?
一個春日去鄉下,親戚家的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香椿樹,下面的葉芽采光了,上面卻是一片嫩綠。問怎么不摘了,說是太高了,再說現在吃的東西太多,也不稀罕了。我立即脫了外套,用小時候鍛煉出來還沒忘卻的爬樹本領攀了上去。不一會兒,小院子里便落滿了香椿芽兒。回家后,我依照母親的做法,用鹽腌了,卻不曬,用大玻璃瓶裝了放在冰箱里。那個春天的芳香,陪我淺酌慢飲了漫長的時光。
記憶最深的是在外地流浪的那個春天。在深深體味了打拼的艱難及生活的困苦、心歷了人世的冷暖和人情的淡漠后,一個中午,我疲憊地落腳在路邊的一家小飯館。香椿頭炒蛋——貼在墻上的菜譜一下子就勾住了我的眼睛。等一盤熱氣騰騰的香椿頭炒蛋擺在我的面前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我想起了灶臺前那片氤氳里母親的身影,想到了故鄉……
年年春天,年年香椿發芽,讓我把那份特別的芳香一直品嘗。最香最溫馨的,還是故鄉的那樹香椿。
槐花
油菜結莢、麥子抽穗的時節,槐花開了。當那一串串潔白的花兒綴滿枝頭時,空氣中便彌漫著一縷素雅的清香。
“槐林五月漾瓊花,郁郁芬芳醉萬家,春水碧波飄落處,浮香一路到天涯。”四五月的鄉村大地,到處可見槐花的身影,那潔白的花朵一叢叢一簇簇點綴在滿山遍野的綠色中,遠遠地望去,宛如團團朵朵的白云漂浮在林叢,給人清新飄逸的感覺,讓人心怡。
槐花碎小而淡雅,不似別的花朵艷麗而招搖,它靜靜地垂掛在枝葉間,無聲地開,默默地謝。真宛如身邊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們,平靜而淡泊地生存繁衍在這個春來秋往的世界。
想起謝軍的一首《槐花香》:“又是一年槐花飄香,勾起了童年純真的向往,兒時的玩伴杳無音信,讓人不由得心傷。又是一年槐花飄香,心上的人兒不知在何方,在這個槐花飄香的季節,又想起那個溫情的夜……”
歌聲里,與槐花有關的記憶,便浮現在眼前。
只要在鄉下生活過的童年,恐怕都有過摘槐花的經歷。像一只小猴子一般地攀上樹,也顧不得枝條上的刺兒扎人,一邊將甜滋滋的花骨朵兒捋下往嘴里送,一邊將串串槐花扔給樹下急切張望著的小伙伴。有時也采上滿滿一篾籃帶回家,讓母親蒸上一鍋槐花飯,或是做成槐花粑粑,解饞兒。
槐花年年開。但仔細想想,這么多年來,再也沒有采嘗過槐花的滋味,也有很多年沒有回到我那童年的故鄉了。
面對若雪槐花,在我心中涌起的,不只是甜美的回憶,還有一段惆悵的記憶。
年少時的事了。一位女孩,從遙遠的地方來我生活的小城看我。領著她在城中的公園散步,走到一片槐樹林,坐在落滿槐花的草坡上休息。因為飲了一點酒,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兒時,自己竟睡著了。一覺醒來,女孩正斜靠一棵槐樹看我。后來,接到女孩的來信,大意是:那樣一個美好的時刻,你竟在我的面前沉沉睡去,于是,那個渾身落滿槐花瓣兒的夢里男孩,就此成了我最美的也是最終的回憶。
時光如流水。在這槐花又飄香的季節想起那個女孩,已不知生活在何方?由此想起生命里那些匆匆走過的身影,真如槐花的開開落落。
“滿地槐花,盡日蟬聲亂。獨倚闌干暮山遠,一場寂寞無人見。”面對槐花,在古今心同的寂寞里,生起的思念與回味雖是淡淡的,卻是清香襲人,如一縷槐香縈繞、飄蕩。
槐花香飄又一年,那潔白的花朵當是一次心靈的相約,在歲月的山坡上等那有緣的人兒。遙看那片春天的守候,我已準備好綻放的心情,“即應來日去,九陌踏槐花”。
梔子
唐詩人王建有首《雨過山村》:“雨里雞鳴一兩家,竹溪村路板橋斜。婦姑相喚浴蠶去,閑看中庭梔子花。”那天去鄉下,未進農家院,便已嗅到一縷綿濃的芳香——是熟悉的梔子花的香味。果然,院中正有一棵梔子蓬勃開放,滿枝頭的白花炫目耀人。
朋友見我久在梔子前盤桓,便摘了十幾朵潔白的花兒送我。滿心歡喜地帶回家,養在水中,滿屋飄散著梔子的香氣,令人神清氣爽。
在鄉下,有兩種花,人們喜歡佩戴在身上。一種是木蘭,一種即是梔子。因為這兩種花的香氣十分濃郁。很久以來,我一直認為木蘭花的香氣有點嬌貴的成分,而梔子的香味才是平民的味道。
初夏,梔子花開的季節,若你正行走在南方的鄉村山野,村陌巷舍間,可時常遇見那些佩戴梔子的女子。上年齡的,喜歡將梔子別在對襟褂的前胸,小媳婦大姑娘歡喜將梔子斜插鬢角烏發,而小女孩則愛將梔子扎在麻花辮梢。
小時候在鄉下,未見過哪戶人家養花草。是覺得矯情,還是在解決溫飽之外難以顧及逸致閑情?但大多數人家還是喜歡在房前院后養一兩株梔子。
過去,農家屋前都有一個壘砌的土臺,用來曬醬晾菜。記得我家的梔子樹就栽在土臺邊,郁蔥茁壯的一棵。春末夏初,梔子花開,母親每日摘下一些,或是夾在床頭的蚊帳上,或是放置案頭,三間簡陋的農舍便盈滿香氣。
妹妹的辮梢上,往往是含苞欲放的兩朵。一跑動起來,兩條辮子擺動跳躍,仿佛兩只小蝴蝶在腦后飛舞。母親也喜歡將一兩朵碩大的梔子別在發間或胸口,她忙忙碌碌地走過我們的身邊時,總是拂過那縷特別的香味。這縷香味是梔子又有別于梔子,幾十年來一直存儲在我的記憶里。
現在想來,為什么這么喜歡梔子的香味?怕是這香氣對于我來說,就是鄉情的味道、親情的味道、母親的味道吧。
杜甫的《梔子》詩云:“梔子比眾木,人間誠未多。于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對于我來說,是沒有什么花朵能替代梔子在我童年里的記憶了。
鄉間普通的梔子,其實也有過顯貴的歲月。因為梔子可以提取黃色的顏料,在古代,皇家衣著的富貴黃,就是用它浸染。只是后來有了替代,才回到民間。所以杜甫詩中言“于身色有用”。
豈止是香有味、色有用,梔子花還可入肴。幼時,就吃過母親用梔子花炒韭菜、涼拌梔子花、梔子蛋花湯。只是現在已回味不出當初的味道,就像離我愈來愈遠的故鄉的模樣。
很多年前,何炅曾演唱過一首《梔子花開》,雖然歌是唱給即將分手離開校園的同學們,但其中的歌詞令我難以忘懷:“梔子花開,如此可愛,揮揮手告別歡樂和無奈。光陰好像流水飛快,日日夜夜將我們的青春灌溉。梔子花開呀開,像晶瑩的浪花盛開在我的心海;梔子花開呀開,是淡淡的青春純純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