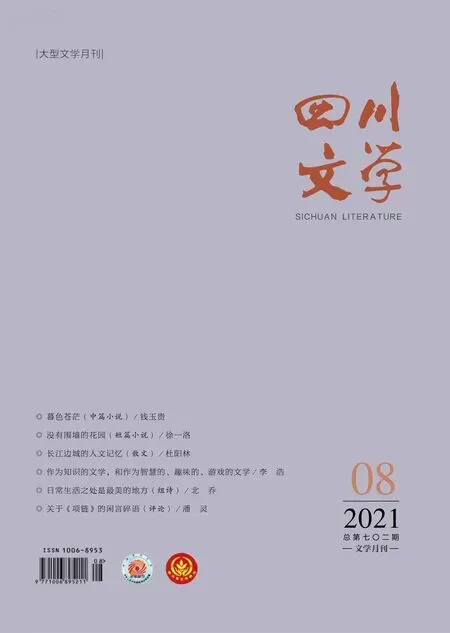作為知識的文學,和作為智慧的、趣味的、游戲的文學
□ 文/李浩
作為作家,在進入大學以來,我發現一個特別的、具有固化感的現象,就是在文學院,真正閱讀文學作品的人很少很少,但大家——無論是學生還是教師——都在忙文學的事兒,他們在忙著梳理和背誦文學史中每篇作品、每位作家的文學定位;在發現或人云亦云地發現文學流變對于作家的影響,時代對于作家的影響,而作家的作品和它可憐的書名則“恰好”適應和驗證了這一社會學影響,它證明著社會的線性進步和歷史推動;他們在忙著記住概念,某某作家屬于現實主義還是浪漫主義,未來主義還是荒誕派,他筆下的這個人物屬于先進的還是滯后的,是可歸屬于哪個階層階級,他們的表現又“恰好”表現了某一族群和階層的共通特征……從某種意味上講,他們在忙于建立知識化的、部分可忽略作家和作品的“文藝史學”,在他們那里,文學似乎只是由文學史知識所構成的,掌握了概念和文學史定位即掌握了文學。我從不輕視文學的知識性,更不會輕視文學史梳理對于“未來文學”的某種照亮:事實上,大凡有影響和建樹的作家,他們對于文學知識性的掌握和對于文學史潮流的演變與可能都是極為敏銳的,或清楚的,因為每一個野心勃勃的作家都不希望自己是“渺小的后來者”,不希望把別人早已發明的自行車再發明一遍,他一定希望自己寫下的新作能夠容納“前人經驗的某些綜合”,并在這一基礎上再向前一步,為“前所未有”提供個人的補充。我從不輕視文學的知識性,還因為我有一個大約偏執些的觀點:我認為自20世紀以來,作家僅依借自己的“天分”和“才氣”而縱任自己知識匱乏就能達到卓越的機會越來越微小。隨著人類知識的共享、共有和溝通的便捷,文學其實不斷地朝向知識化、科學化、綜合化提升。在對20世紀以來文學經典的閱讀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這一點,這也是文學史梳理所提供給我的啟示和教益。但是,我想只把文學簡化為文學知識或文學史知識本質上是片面的、匱乏的,甚至是有害的,我想我們無法漠視米蘭·昆德拉曾發出的警告:簡單化的白蟻正在吞噬著人類,而小說或一切文學則永遠要用它的方式告知我們:事情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同樣,我們也無法漠視來自蘇珊·桑塔格的同類警告,她認為我們的文學闡釋部分地“像汽車和重工業的廢氣污染城市空氣一樣,藝術闡釋的散發物也在毒害我們的感受力。就一種業已陷入以活力和感覺力為代價的智力過度膨脹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闡釋是智力對藝術的報復,同時也是對世界本身的報復。”
藝術闡釋的散發物也在毒害我們的感受力。在我進入大學之前我從未如此真切而有些痛心疾首地意識到這一點,而現在,我對它的感受則是越來越強烈。有時我真的想追問或者自問一下:將文學簡化為文學知識和文學史知識,簡化為社會學知識,進而簡化為低端、滯后的社會學知識,是出于對文學的愛還是文學知識的愛?或者,我們兩者都不愛,我們只是恰巧從老師那里學到了這門已有知識,而它又恰巧能保證我們的教職和成果,讓我們得以有個沾沾自喜的位置?藝術闡釋的散發物毒害著我們的感受力,在時下,這一現象似乎日趨嚴重——在我們的大學里,老師們“假裝”在教授文學,學生們“假裝”在學習文學,但我們始終輕視文學最最需要的感受力,始終輕視著作品的藝術之美甚至它貯含其中的真切表達。即使,我們不輕易地斷語說出“大學不是培養作家的”這樣的話的楊晦先生是錯誤的、輕率的,但它的偏頗之處也日漸明顯。大學不培養作家,那大學又培養了怎樣的文學學者?他們對文學的認知有多少過人之處,有著多少啟蒙和提升文學品質的價值?退而,我們大學的文學院,不會寫詩不會寫小說,甚至連散文和公文也寫不好,是不是我們應當反思這個問題出在哪里?
蘇珊·桑塔格的許多看法我并不認可,但我認可并愿意借用她的這句話來重審:相對于文學的闡釋學,我們也許更應當建立文學的色情學——她的原話是:“為取代藝術闡釋學,我們需要一門藝術色情學。”我愿意將中文詞意中的“色情”分開:色,是顏色、色彩,是文學所帶出的直覺性質感,在這里我們需要運用我們的直覺感受力,而它是我們在閱讀文學作品時最最美妙的感受之源;情,是情緒情感,是我們在閱讀文學作品時的自我投入,是文學作品可以作用于我們情感的部分,是我和我們在“感同身受”之后引發的思忖:生活如此嗎?非如此不可嗎?有沒有更好的可能?我們是不是可以完成在好和更好之間的選擇?
是故,我愿意在承認文學具有知識性的同時,更愿意用更大的力氣認知它的“智慧性”“趣味性”和“游戲性”。它們的這些側面,在我看來遠比我們目前教授的所謂知識性重要得多。我們的創意寫作教育,也許可以更多地從這些點上展開。它不僅僅是出于對傳統教育的區別,而是更有效的補充、更本質的補充。
列夫·托爾斯泰曾反復地說過,在談論莎士比亞的戲劇和談論莫泊桑的小說時說過,文學越對生活生命有意義,文學的價值則越高,越屬于高格——這一點兒我覺得應當得到強調,但,這個意義不只是我們從中抽出了社會學知識,看到了道義、階級和淫欲問題,而是看到人物的行為、心理和這樣的可能,進而看到我們自己和我們的選擇。有時,談及“智慧性”我們可能不自覺地會和“知識性”混淆,將二者看成是同一的,但在我看來它們之間有著極為嚴格的、寬闊的區別。知識是共有的,而智慧則作用于個人,是對“我”的提升和啟示,在這里“我”是接受的主體而不是他者。在這里我也想自問:我在文學閱讀中是想自己從中取得智慧嗎?我認可文學所提供給我的智慧和影響嗎?我嘗試在閱讀和分享中,給予過我的學生我所體會到的智慧和影響嗎?多年之前有一次學術會議上,李敬澤談到,我們批評家掌握著哲學的理、社會學的理,以一種堅固的、真理在握的樣子出現,但我們是不是相信,文學家們也掌握著他們的理?我們是否信任過這種理呢?現在,我也想問一問我自己,在進入學院體制后,我是否還相信文學家們掌握著他們的理?我和我們是否相信,文學中有種人類之光,是在別的科學和學科里所找尋不到的?
另外,我想我們也應看到,文學的理大約不同于其他的理,它不是以譜系的、邏輯的、完全正確的方式講出來的,而是不斷地提示:對我們的習焉不察進行提示,對我們的習以為常進行提示,對我們先于理解之前的愚蠢判斷進行提示,對我們的聰明和幽暗處的隱藏進行提示,對我們的固執偏見和對他人的不理解進行提示……米蘭·昆德拉將它命名為“智慧之聲”,它不具有絕對性,它里面貯含的多是糾結、掙扎、反問和自我審視:我們是否愿意在我們的文學教育中,與同學們一起聆聽這樣的智慧之聲,并將自己也放置進去?我們在嘲笑阿Q、孔乙己的荒謬愚蠢和可笑的時候,是否愿意從他們的DNA中,找見自己的影子并嘗試抵御?
“文學,真正的文學,是不能囫圇吞棗地對待的,它就像是對心臟或者大腦有好處的藥劑——大腦是人類靈魂的消化器官。享用文學時必須先把它敲成小塊,粉碎、搗爛——然后就能在掌心里聞到文學的芳香,可以津津有味地咀嚼,用舌頭細細品嘗;然后,也只有在這時,文學的珍稀風味,其真正的價值所在,才能被欣賞,那些被碾碎的部分會在你腦中重新拼合到一起,展現出一種整體的美——而你則已經為這種美貢獻了你自己的血液。”這是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說過的話,在我看來它包含著真誠和真情,幾乎具備了真理的性質。文學,當然是不能囫圇吞棗地對待的,可我們的文學教育卻似乎又致力將它們壓縮成一枚枚囫圇的棗,或者將它們簡化為某種流行思想影響下的簡單反映。在我們時下的文學教育中,那種屬于文學的藝術之美、語詞之美和表達之美幾乎盡然地排除在了視野之外,我們很少就藝術的審美和它在文本中的達到進行分析,在我看來它也是值得甚至特別值得商榷的。如果將一首詩簡化為詩歌所表達的意思,它等于直接地取消了詩歌,而正是那些不太容易翻譯的部分構成詩歌的美,它會將詩歌中所貯有的神經末梢完全地剪斷,趣味盡失。沒有了趣味,沒有了作用于閱讀者情感和共鳴的部分,文學的獨有價值也就遭到了巨大減損。詩人奧登提到,閱讀即翻譯,因為沒有兩個人的經驗徹底一致。糟糕的讀者即糟糕的譯者:應該意譯的時候直譯,應該直譯的時候又意譯。學習完美的閱讀,學識固然具有價值,卻不及直覺重要;有些偉大的學者是低劣的譯者。作為一個作家,我當然不希望將自己的作品交給低劣的譯者,而另外許多作家,我想同樣也不希望。
文學的游戲性,我不準備再次枚舉博爾赫斯的話、納博科夫的話、君特·格拉斯的話、略薩的話或米蘭·昆德拉的話為我佐證,我想到的是,我在一節文學課上的“游戲”:有學生提及《百年孤獨》的最后,奧雷里亞諾·巴比倫在解讀完羊皮卷上的文字,接受其命運的“那種平靜”。她自問:這種平靜接受,是心死,是反正也抗爭不過的絕望,還是一種世事不過如此的安然?然后,我們開始游戲:如果是我們,拍一部《百年孤獨》的電影,如何處理這個鏡頭,這種所謂的平靜?我提供的設計有兩個:一,近景,奧雷里亞諾·巴比倫將雙手攥緊。他將羊皮卷用力地攥在手里,然后,將它丟進自己點燃的火焰中。然后盯著火焰,看著羊皮卷變成灰燼,和別的另外的灰燼成為同一顏色。他的臉上,似乎有淚水的出現——平靜,也是可以用激烈來表達的。二,中景和遠景。奧雷里亞諾·巴比倫緩緩推開羊皮卷。這里,房間里原來用作煉金術的一個圓形器皿突然掉了下來,滾動著,滾動著。它一直滾到奧雷里亞諾腳下。奧雷里亞諾伸出腳去。這個圓形的、已經變得不那么規則的器皿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響,然后滑向……之后,我的學生孫靜的設計是:奧雷里亞諾將羊皮卷隨手扔掉,任其被一陣颶風隨便刮到了什么地方。他的神情是那么淡漠,他的心從未像現在這樣安寧,他向后徑直躺在了被毯子裹著的阿瑪蘭塔·烏蘇拉的身旁,享受著這份獨有的陪伴與孤獨感。這時,飯廳仿佛傳來了一陣遙遠的鋼琴聲,奧雷里亞諾的目光透過頹敗沒落的飯廳看到了一場盛大的舞會:優美而充滿活力的人們,在一架自動鋼琴下翩翩起舞。人們臉上熱情洋溢的笑容與他們身上散發出的孤獨與衰頹的氣息將隨著這架自動鋼琴歡快的樂曲一直循環著,永不停歇。另一位學生梁靜雯的設計則是:一,奧雷里亞諾·巴比倫劃破手指,在自己的額頭畫下代表家族血脈的血色十字刺青,從遙遠的記憶中搜尋到上校曾用過的手槍,里面那一顆不曾要了上校性命的子彈在槍膛中保存完好。奧雷里亞諾·巴比倫沒有絲毫猶豫地對著自己的太陽穴開槍,可是并沒有子彈飛出。他的雙眼通紅而濕潤,他再次對著羊皮卷扣下扳機,歷史在多次的眷顧后,終于在羊皮卷上留下了一個彈孔的痕跡。奧雷里亞諾抬頭,看到橘紅色的球狀物體迅速飛過,他緩緩地放下了拿槍的手臂。二,奧雷里亞諾·巴比倫把手放在羊皮卷上,他感到沸騰的文字和微微發熱的羊皮卷正在快速地冷卻、凝固、變硬。他閉上眼,神圣而不可抗拒的感覺正如書中所記載的,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初次見到并觸摸冰塊的那個下午。他拿起那已經無比堅硬的羊皮卷,懷著對冰塊崇高的敬畏睜開眼時,發現,手指尖那冰涼的觸感并非是冰塊,羊皮卷已經變成了刻有透明字跡的玻璃鏡子,反射著令人戰栗的光……
我想我的這兩位學生體味著文學的游戲性和這種游戲性所帶給她們的快樂,她們讓一個靜止的情節變得生動多樣,甚至有意識地“模仿”了馬爾克斯的語言方式,盡可能與《百年孤獨》中的敘述風格相“貼近”。而這,難道不是文學學習的一種本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