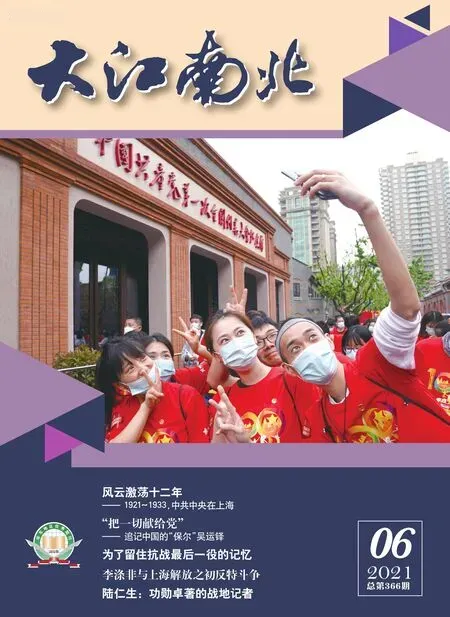風云激蕩十二年——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
□ 史為鑒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1921年7月黨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被迫遷往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除了有幾次為時很短暫地遷離上海外,一直都設在上海。
一
上海之所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自然是黨的創始人選擇的,而他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則是與上海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地位,以及獨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分不開的;是與工人階級的集中、工人運動的發展、革命力量的匯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等重要的因素分不開的。最早醞釀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與李大釗。李大釗是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陳獨秀則最早在上海開始了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活動。
正當中國的先進分子積極籌備建黨的時候,經過共產國際的同意,1920年3月,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派出全權代表維經斯基等人,來中國了解五四運動后中國革命發展的情況,以及組建共產黨組織的條件是否成熟。維經斯基一行抵達北京,結識了李大釗,表示要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李大釗介紹他們到上海找陳獨秀。雙方通過交流中國革命情況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國革命情況,商討發起在中國創建共產黨。
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中國最早建立的共產黨組織。
1920年6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五人在上海環龍路(今南昌路)老漁陽里(后改稱裕德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即陳獨秀的寓所)開會,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積極地指導各地建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的工作;有組織有計劃地研究和更廣泛深入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繼續促進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經過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積極努力,正式成立全國性的集中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逐漸成熟了,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宣布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了。1921年6月3日,經列寧推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馬林作為共產國際代表抵達上海。同時,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尼科爾斯基為接替維經斯基的工作也到達上海。他們與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李漢俊、李達取得聯系,經商討并同陳獨秀、李大釗聯系后,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隨即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以及日本留學生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或黨員,通知他們派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7月23日晚上8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開幕。國內各地的黨組織和旅日的黨組織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會,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陳獨秀派遣的包惠僧。他們代表了全國的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也出席了大會。由于會場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國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會議改在浙江嘉興南湖的游船上舉行。
中共一大不僅宣告了黨的正式成立,而且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明確提出“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規定“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而且堅持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積極投身到實際的革命活動中去,并在斗爭中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觀察與分析中國革命面臨的實際問題,包括社會的各類矛盾和處理矛盾、解決問題的方法,正如1922年1月,黨的機關刊物《先驅》的發刊詞所指出的,必須把“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實際情況,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實際解決中國的方案”當作“第一任務”。
為了大力開展工人運動,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公開做職工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書記部在武漢、北京、濟南、廣州、長沙設立了5個分部,上海由書記部直接領導開展工作。1922年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從上海遷到北京,上海另設立分部。自成立之日起直到1925年5月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書記部一直是中共領導職工運動的公開合法的領導機關,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
1922年6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通過對中國政治、經濟狀況的分析,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第一次提出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還指出:為了實現反帝反封建的目標,必須組成“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同時又強調“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斗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革命團體’”。二大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章。通過決議案,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二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完成。
二大召開后不久,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舉行會議(史稱西湖會議),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在會議上提出了“共產黨員、青年團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把國民黨改造成為各革命階級的聯盟”的建議。1923年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據此作出了《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同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國共合作的方針和辦法做出了正式的決定,雖然規定“在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時,黨員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但沒有提出工人階級應當努力爭取民主革命領導權的問題。
三大后,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成功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國共合作實現后,促進了工農運動的發展,很快開創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
隨著革命的發展,國民黨內部的左右派進一步分化,國共關系也日趨復雜化,中國革命面對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給以回答。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的問題;同時,還強調黨的“組織問題為吾黨生存和發展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二
如同中共在上海誕生不是偶然的一樣,將早年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設在上海也不是偶然的。
從1921年 到1928年 中 國共產黨召開的6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有3次即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中共四大是在上海召開的。黨的三大與五大分別在廣州和武漢召開,會后不久,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便又遷回上海。中共六大是在蘇聯的莫斯科召開的,會議期間,上海仍有留守中央,負責處理黨的日常工作。六大后,中央機關仍在上海。位于云南中路與福州路交匯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就是中共六大后設置的,駐扎了三年多,是目前所知黨中央在滬期間,使用時間最長的一處機關。中央政治局在那里舉行過很多次會議,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等經常在此秘密辦公。
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這個時期,是黨的幼年時期,也是艱辛地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時期。黨在上海領導了一系列重大的斗爭,也包括領導全國各地的革命斗爭。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黨的隊伍自身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得到了發展壯大。
中共四大召開后不久,1925年5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領導發起的五卅運動,揭開了全國范圍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全國各地約有1700萬人參加了運動。運動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促進了黨的隊伍進一步發展。在國共兩黨的通力合作下,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進行北伐準備了后方基地。
在沿途群眾的支持下,北伐軍勢如破竹。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各地工農運動迅速高漲。五卅運動后處于低潮的上海工人運動,在中共領導下,也重新高漲起來。1926年秋到1927年春,上海工人在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的領導下連續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
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階級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占領了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成功,并建立了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也稱市民政府)。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新右派的代表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隨后,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地,也相繼以“清黨”的名義大肆捕殺共產黨員與革命群眾。在緊要關頭,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于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未能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為黨指明方向,未能制止局勢的繼續惡化。7月15日,汪精衛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分共”會議,宣布同共產黨決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夭折了。
為了糾正大革命后期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決定新的路線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并選出了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由于受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左”傾思想及黨內“左”傾情緒的影響,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時沒有注意防止和糾正“左”傾錯誤。
三
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10月從武漢遷回上海。直至1933年初遷往江西中央蘇區,中央領導機關一直設在上海。在敵情嚴重、社情復雜的上海,黨中央領導全黨為復興革命而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和探索。中國共產黨人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以不屈不撓的抗爭回應國民黨的屠殺。中共中央派出許多干部到各地恢復黨的組織、領導武裝起義。
盡管黨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革命形勢仍然處于低潮。但是中共中央沒能正確判斷革命形勢。1927年1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計劃,“左”傾盲動主義在全黨取得支配地位。慘痛失敗的教訓,使得這次錯誤至1928年4月,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停止。
為總結大革命失敗后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確定革命斗爭的路線和任務,1928年6月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對中國革命的一系列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確定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
經歷了大革命失敗后的“左”傾盲動錯誤后,新一屆黨中央貫徹六大爭取群眾的總路線,強調深入群眾,領導日常斗爭,加強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開始重視對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領導,革命局勢出現了新的生機。
黨中央加強對宣傳文化工作的領導,在上海先后創辦了《布爾塞維克》 《紅旗》 《斗爭》《黨的建設》等黨報黨刊,團結左翼文化人士,成立左聯、社聯等革命文化團體,研究和傳播馬列主義理論,反對國民黨文化“圍剿”,推動革命文化運動的發展。
隱蔽戰線上,中央特科在保衛黨中央機關的安全、營救被捕同志、嚴懲叛徒、搜集情報、支持與配合紅軍和根據地的斗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0年6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錯誤又一次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9月下旬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左”傾錯誤在中央的領導,3個月后的六屆四中全會又開始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長達4年的統治,給中國革命事業造成極大危害。
1931年6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的向忠發被捕叛變。9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由博古負總責。九一八事變后,臨時中央高舉抗日旗幟,號召全國人民一致奮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領導抗日救亡運動,但由于繼續貫徹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嚴重地影響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同時,也使黨的組織和工作遭到嚴重破壞。臨時中央已難以在上海繼續立足,于1933年1月遷往江西,中國革命開始了更加艱苦與艱巨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