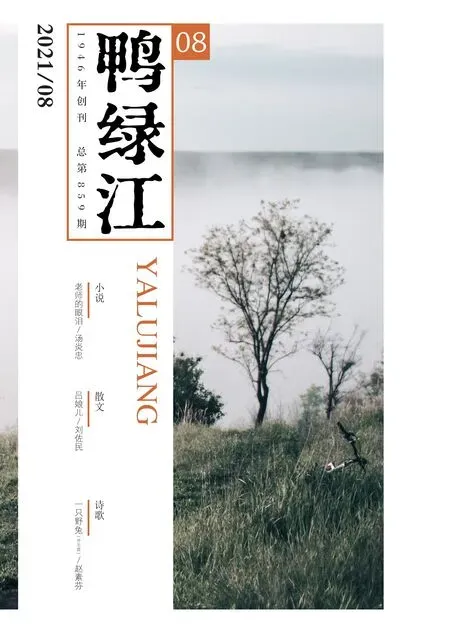我于夕陽下看見
邢璐璐
季節出乎意料地多情,秋日的溫度仍掛在略顯干燥的柳樹的長發上,纏綿而不愿退卻。氣溫也顯得那么仁慈,似乎還在留戀妙齡女子們俏麗鮮艷的秋裝而并不注目于婦人們華貴的狐裘。空氣如同被反復漂洗過一般,純凈得一如彼時青澀的初戀。
還是那條通往家的筆直的路,還是一包書本和一包換洗衣物,還是喜歡走路時驅逐一顆可憐的小石子以尋找樂趣,還是有一只干凈溫暖的手牽著我,手的主人還時不時會為我踢石子的笨拙動作而發笑。在我們的身后,夕陽像一只剛從樹上采摘下來的新鮮橙子,看起來美味而又多汁,它就那樣典雅安詳地端詳著,光輝就如同黃油一樣厚厚地涂抹在道路上,將我倆的身影頑皮地拉扯得好長好長。
我腳下的石子滾出了一段距離,也將我倆的目光帶走。然而,迎面而來的景象卻讓我們再也無法將眼睛移走。頭發斑白的老婦裹著厚重的棉衣,推著一輛簡易的木箱式的輪椅,小小的輪子忙不迭地轉動,歪歪斜斜,發出細微的吱吱聲。輪椅上坐著的是個怎樣的人啊——他的臉上鐫刻的也許是數年都不曾變換的表情,皺紋似已深嵌多年。一邊的嘴角向后微微咧著,另一邊的嘴角則緊緊地抿著,露出的牙齒像古城慘遭侵略之后的殘垣斷壁,又像曬干的老玉米一樣籽粒疏松。他的左手像龍爪槐落光了葉子的枝干一樣痙攣,而蜷曲的右手則像一團揉皺的報紙,毫無生機地搭在腿上。他頭戴一頂樸素的灰布帽子,穿著黑色棉布面的小襖、洗褪了色的板褲和一雙千層底的黑布鞋。
我不自在地看了看男友,不知輪椅上的老人的境況是否使他想起了他的爺爺。他就那樣一直看著輪椅上的老人,我拉了拉他的手,他微微側了側頭,但仍沒能拉回自己的思緒和眼神。我嘆了口氣,看向推車的老婦,不知我們的目光有沒有驚擾到他倆的平靜。老婦的眼睛因為向著太陽而微瞇著,并沒有看向我們這里。她額角依稀有汗水,濡濕的鬢角躍金似的閃爍著光芒,我不禁為她的辛苦而嗟嘆,而她帶著笑意的臉龐卻似乎對我的同情進行了委婉的拒絕。
離我們更近一些時,老奶奶騰出一只手臂向前指著,我們也不禁向身后張望。她附身在老爺爺耳邊說:“你看今兒的太陽,又紅又大的不?”就那么一瞬間,那么一句話,讓我動容。我深吸一口氣,看向輪椅上的老人,他緩慢地消化著妻子的話,吃力地轉動著眼珠,終于定格在了她食指所指的方向。接著,他就像是一臺生了銹的機器一樣艱難地點了一下頭,并且咧開嘴角,嗯的一聲在他空蕩蕩的口腔里回蕩著。老奶奶開心地看著他,笑著,簡單平實的喜悅就像聽到丈夫贊美她種出的果實一般溢于言表。
這時,一滴口水從老翁向下撇著的嘴角流了出來,老翁用力地吸著氣。妻子見了,繞到他身前,低頭從口袋里摸出一塊手絹,折出一角,靠近那滴口水,她慢慢彎下身子的時候很自然地發出嗨的一聲,那聲音就像是一位母親擦拭地板上小兒子的鞋印時一樣無奈卻又寬宏。
我想起了史鐵生的妻子陳希米多年的堅強與辛勞。如果說一個人的不幸在母親那里總是要翻倍的,那么在妻子這里就被分擔掉了一半。而我至今仍無緣向史鐵生的妻子致以敬意,不料卻得在這里見到了她的翻版,也見識到了這樣的夫妻是多么堅強隱忍。他們在人生接近黃昏的時段仍能如此瀟灑地觀賞著像他們的生命和愛情一樣壯麗的夕陽,算來真的是一種幸福。
我不再怕我們過于直白的目光會使這對可敬的夫妻覺得魯莽,因此目送他們走遠,身后拖曳著被夕陽溫柔的拉長的影子。
我碰碰男友的胳膊,不知他是否也有同樣的感動與欽佩,看著他的頭發上浮動著夕陽橙紅色的反光,不知歲月將我倆的頭發漂白時,我們能否像他們一般長久地相守,而他似乎是回答我的疑問似的沖我笑著,用手指小心地靠近我的眼睛,就像那個老奶奶擦拭老爺爺嘴角的口水似的蘸走我眼睛下方的濕潤。
通過被他擦干之后的視線,我于夕陽下清楚地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