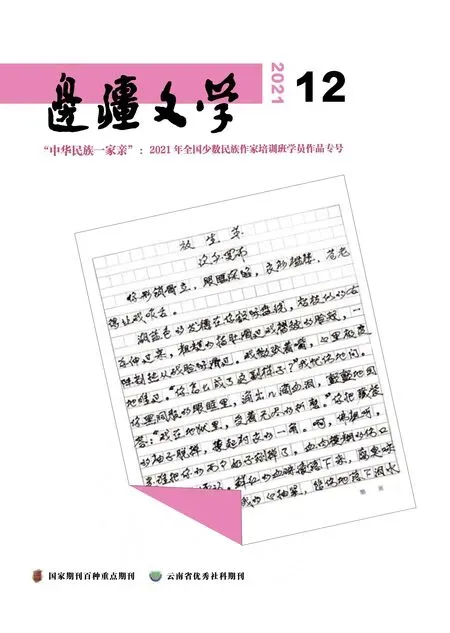薩家的月亮
帕蒂古麗(維吾爾族)
福州朱紫坊22 號(hào)薩家大院里,有月亮的晚上,非常適宜聽(tīng)薩家人說(shuō)故事。從先祖薩拉不花,說(shuō)到元朝著名詩(shī)人薩都剌這個(gè)在福州做官,將雁門(mén)認(rèn)作故鄉(xiāng),在他的《雁門(mén)集》里無(wú)處不提西域的詩(shī)人。尤其是薩琦這個(gè)一生多變的人,他內(nèi)心世界經(jīng)歷過(guò)的變化讓我著迷。出于好奇,在福州見(jiàn)到每個(gè)薩家后人時(shí),我不斷地把話(huà)題引向薩琦。
“看歷史如同照鏡子”,薩琦為這句話(huà)做了一個(gè)很有意味的注腳,自從了解了薩琦,找到了一面可以照亮自己一生的鏡子。看歷史不是單純地看過(guò)去,是以歷史對(duì)應(yīng)現(xiàn)在。對(duì)于我來(lái)說(shuō),看歷史就是看未來(lái),看一個(gè)家族的未來(lái)、一個(gè)民族的未來(lái)。
說(shuō)到薩琦就應(yīng)該說(shuō)說(shuō)他的大夢(mèng)山。這座山過(guò)去被稱(chēng)為薩家山,那時(shí)西門(mén)住著看管著薩氏宗祠的人,薩家人每到清明,都到大夢(mèng)山掃墓祭拜祖宗。
薩都剌的侄子薩仲禮是入閩第一代,從元代算起,薩氏入閩至今已有七百多年。一個(gè)民族遷徙到另一個(gè)地方,住所、飲食、衣著、出行都得變,依照一般規(guī)律一般三代以?xún)?nèi),語(yǔ)言、節(jié)日習(xí)俗基本不變,薩琦恰巧是入閩第三代,薩家俗變從薩琦開(kāi)始,他晚年尊崇了朱子家禮。
薩琦色目習(xí)俗未變時(shí),捐資重修過(guò)清真寺,在朱紫坊薩家大院斜對(duì)面的清真寺里,有一面薩琦為重修清真寺捐資的碑,上面清清楚楚地刻著捐助者是“薩琦公”。清真寺原來(lái)很小,薩琦捐錢(qián)重修后的清真寺變大了。
晚年薩琦一改色目人的習(xí)俗,在皇帝賜他的墳塋旁修造薩家祠堂,變成了熱心于重修《薩氏族譜》的人。也有返祖的,清朝康熙年間,薩家還有人信伊斯蘭,這里也可以看出歷史上的薩家人在習(xí)俗上的搖擺不定。
晨霧中尋夢(mèng)大夢(mèng)山
去看薩琦大夢(mèng)山墓瑩,是一個(gè)大夢(mèng)初醒的清早,我拽著藤條爬上山丘,好不容易尋到薩琦撰寫(xiě)的摩崖石刻,與其合影留念。我唯恐不趕緊拍下它們,一眨眼它們就如大夢(mèng)一般散去。好在散去的只是山腰的晨霧,我窺見(jiàn)大夢(mèng)山仿佛沉睡了一夜的男子,醒來(lái)后正要換掉昨夜的睡衣。
晨光送我拾級(jí)攀上山頂?shù)耐ぷ樱晃荒凶颖硨?duì)著晨練者們?cè)诶√崆伲仁侨A爾茲,后是一支新疆舞曲,有個(gè)大學(xué)生模樣的新疆女孩忍不住甩開(kāi)裙子隨音樂(lè)跳了支維吾爾舞,托花帽,飛旋,下腰,移頸,再飛旋,曲終,她的舞步戛然而止。世界之大,無(wú)巧不有,不料想竟在這大夢(mèng)山的亭子里,看到妙齡少女被一支新疆曲子感染踏樂(lè)起舞,給睡在這方福地幾百年前的故鄉(xiāng)人舞一曲胡旋,薩琦應(yīng)不會(huì)怪罪她不敬吧。
家族中唯一有跡可循的唯有薩琦做過(guò)確認(rèn)身份的夢(mèng),對(duì)確認(rèn)身份家族恐有各種爭(zhēng)議。皇帝贈(zèng)大夢(mèng)山為薩氏墓塋,薩琦隨了漢俗,建造祠堂,祭拜祖宗,身份之夢(mèng)隨之被隱藏于大夢(mèng)山,埋葬于大夢(mèng)山,薩家這一場(chǎng)歷史大夢(mèng)幾百年不覺(jué)。
明朝與前清薩家人埋葬都在大夢(mèng)山,宗祠修在大夢(mèng)山下。1946年抗戰(zhàn)勝利時(shí),因痛恨福州漢奸薩福疇,薩家祠堂被學(xué)生燒毀。薩家出名人,盡是堂堂正正的,唯獨(dú)出了個(gè)薩福疇,敗壞了祖宗的風(fēng)水。
如今大夢(mèng)山薩氏宗祠已不見(jiàn)蹤跡,皇帝賜的墳塋亦消失得無(wú)跡可尋,唯有我拍下來(lái)的山間摩崖石刻,是薩琦留下的印痕,注解著大夢(mèng)山曾經(jīng)是薩家山的歷史。與薩家墳塋舊址遙相對(duì)應(yīng)的,是亭子里華爾茲與西域舞曲,七百年,一種文化又一種文化交疊而來(lái)。沒(méi)有什么是停滯不變的,歷史的車(chē)輪輾過(guò)來(lái),天可翻,地可覆,哪有不覺(jué)之夢(mèng)?亂夢(mèng)三千,終有醒時(shí)。醒來(lái),已換了人間,薩家人開(kāi)始進(jìn)入另一場(chǎng)夢(mèng)。
在故事里慢慢變老
薩本珪住在一處老舊的小區(qū)里,他曾任福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zhǎng),離休后在小區(qū)里開(kāi)起了圖書(shū)室,帶學(xué)生寫(xiě)寫(xiě)書(shū)法,彈彈鋼琴。老人性格開(kāi)朗,順手拿起省藝術(shù)學(xué)院教授薩本瓊作詞作曲的《海軍世家之歌》樂(lè)譜,彈唱了一曲。
他從書(shū)柜里抽出《薩氏族譜》,一邊翻著,一邊埋怨紙張那么快就變黃、變舊、變老了,似乎心有不甘。這個(gè)飽受漢文化浸染的薩姓老先生,剛剛為北門(mén)外“萬(wàn)壽園”石碑寫(xiě)完第一百個(gè)“壽”字回來(lái)。其實(shí),無(wú)論他在墓園里寫(xiě)下多少個(gè)壽字,無(wú)論壽字寫(xiě)得多么巨大,多么蒼勁,人也擋不住他和那些壽字一起慢慢變老,最后老得跟石碑一樣。
薩家有那么多人名字刻在了石碑上,走進(jìn)博物館、紀(jì)念館,故事都在發(fā)黃、變老。希望變老的故事能一直流傳下去,這才是薩本珪追求的那個(gè)精神意義上的家族壽命吧。就精神來(lái)說(shuō),人類(lèi)的創(chuàng)造中總有一些東西是永恒的,比如薩都剌的詩(shī)歌,被人們記了千年,也就足以佐證他精神的長(zhǎng)壽了。
人不管浸染在什么樣的文化里,鄉(xiāng)情是貫穿一生的。2017年與子女一起去雁門(mén)關(guān)尋根,薩本珪帶回了一捧祖籍地的泥土,現(xiàn)在就在朱紫坊薩家大院第三進(jìn),伯父薩君豫遺像前供奉著。他相信雁門(mén)的泥土能滋養(yǎng)祖上的精魂,也能讓薩家不忘初心。雖然史料有記載,薩家真正的遠(yuǎn)祖是西域色目人,薩家還是認(rèn)了雁門(mén)這個(gè)時(shí)間和空間距離都相對(duì)離他們近一點(diǎn)的地方,作為自己的故地。
當(dāng)我問(wèn)他,為何不去新疆取一把泥土祭祖的時(shí)候,他的表情變得凝重。他相信自己的祖上是色目人,卻不知道去到新疆哪里尋根問(wèn)祖,他根本就沒(méi)有去過(guò)新疆,他對(duì)新疆這個(gè)最早的祖籍地,一直停留在諸如沙漠狂風(fēng)、草原游牧的想象中。那種想象長(zhǎng)滿(mǎn)了他的一生,那是像荒草戈壁一樣遼闊的想象。去一次新疆原本不難,難的是讓想象鋪滿(mǎn)一生,讓沙漠覆蓋一生,或者干脆讓自己的腦海變成無(wú)垠的沙海戈壁,日日夜夜隨想象在上面馳騁。不近鄉(xiāng),也不情怯,這么難的事情,他這一生幾乎做到了。
我理解了這位老人,長(zhǎng)達(dá)近七百年二十幾代人的想象,已經(jīng)讓那個(gè)遙遠(yuǎn)的故鄉(xiāng)懸置在生命的高位和頂端,成了永遠(yuǎn)不敢攀爬涉足的圣頂。西域,色目人,這樣的字眼,只留在夢(mèng)里,存于心間,祖先的一切,那是用來(lái)膜拜的。他們讓回不去的故鄉(xiāng)成為圣境,生怕到達(dá)和踏入都會(huì)褻瀆了它,這個(gè)靈魂的遠(yuǎn)方,他們不再妄想接近,只適合留在夢(mèng)中作為一份念想。
橫豎講不清楚
薩兆溈完全贊同陳垣先生1923年在《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文中科學(xué)的論斷,薩都剌先世為“回回教世家”,即西域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shù)民族后裔。
有史料記載,薩都剌先世為蒙古人開(kāi)始西進(jìn)時(shí)占領(lǐng)的哈剌魯王朝內(nèi)的“答失蠻氏”。答失蠻氏,是哈剌魯王朝由貴族組成的氏族支系。在蒙古人繼續(xù)西征時(shí),“自其祖思蘭不花,父阿魯赤,世以膂為起家,累著勛伐,受知于世祖,英宗名仗節(jié)鉞,留鎮(zhèn)云、代。君生于雁門(mén),故以為雁門(mén)人”(干文傳《雁門(mén)集·序》。
薩本珪對(duì)先祖的一切選擇非常體恤,“入閔第三代薩琦時(shí),有薩氏信伊斯蘭,后來(lái)血統(tǒng)交叉混雜。漢族人居住固定,一定居就是幾百年以上,姓薩的游牧民族住蒙古包,跟著風(fēng)沙跑,大風(fēng)刮來(lái),行囊一裹架在駝背上就跑。跑到有水的地方,蒙古包一扎,再住下來(lái)”。
薩氏先祖薩拉不花娶了第一個(gè)妻子后,就拋妻別子隨成吉思汗西征,至于他的子女們與何族何人成婚,如今恐已難考證,不過(guò),后代混血是確認(rèn)的,且品種之優(yōu),薩本珪言語(yǔ)中也很肯定。
薩本敦上初中時(shí)接到通知,薩姓改漢族身份為蒙古族。父親吃驚地解釋?zhuān)_氏是色目人。那應(yīng)該是1961年的事,他至今記得。
有語(yǔ)言學(xué)專(zhuān)家認(rèn)為,薩都剌這個(gè)名字是信阿拉伯話(huà)借來(lái)的,這個(gè)名字維吾爾族現(xiàn)在仍在用。薩家對(duì)祖先的認(rèn)識(shí)停留在色目人,一個(gè)離開(kāi)西域在內(nèi)地繁衍了六七百多年的家族。他們認(rèn)為,能夠牢牢記得祖先是色目人,這一點(diǎn)已經(jīng)足夠了。
2016年有劇組在朱紫坊薩家大院拍攝紀(jì)錄片時(shí),發(fā)現(xiàn)屋頂?shù)睦菆D騰,瓦脊上還有個(gè)元寶,廚房里還嵌有佛龕。尤其是狼圖騰這稀奇的寶貝,整個(gè)福州僅朱紫坊22 號(hào)有,可薩家人一直以為那是祖先用來(lái)鎮(zhèn)宅的。
紀(jì)錄片《大海邊的蒙古人》里拍了薩家蒙古化的祭祖,獻(xiàn)的是綠色哈達(dá)。這是蒙古禮儀。鏡頭從草原習(xí)俗過(guò)渡到海邊,十分有跨度,從草原文明跨越到海洋文明,這也是薩氏祖先實(shí)現(xiàn)的從北到南的文化大跨越。
狼圖騰也好,元寶也好,佛龕也好,哈達(dá)及其他都好,對(duì)于薩氏家族,文化就這么交疊混雜,時(shí)而一種覆蓋了另一種,時(shí)而一種淹沒(méi)了另一種,時(shí)而一種沉落。另一種浮出歷史水面,任何時(shí)候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種文化在薩家,自古就互倚共存。
“西北的民族問(wèn)題研究專(zhuān)家來(lái)過(guò),上海研究薩都剌的專(zhuān)家來(lái)過(guò),內(nèi)蒙古大學(xué)教授也來(lái)過(guò),清史稿兩處寫(xiě)清薩氏‘是回回’,又寫(xiě)‘實(shí)蒙古人也’。只有薩氏是色目人,這一點(diǎn)毫無(wú)疑問(wèn),更確切地說(shuō),是蒙古化了的色目人后裔,我們也講不清楚,真的講不清,沒(méi)辦法,橫豎是講不清楚。”薩本珪也為難地?fù)u頭。
薩本敦說(shuō):“我們是薩氏后人,不是民族屬性專(zhuān)家。上世紀(jì)60年代初認(rèn)定我們是蒙古人。薩家大院的建筑上發(fā)現(xiàn)蒙古族的狼圖騰后,民族屬性的架從50年代吵起吵到了現(xiàn)在,他們吵歸他們,我們沒(méi)有多少發(fā)言權(quán)。”
從這些跡象可以看出,薩氏后人對(duì)祖先認(rèn)識(shí)模糊,或者說(shuō),對(duì)民族這個(gè)概念不怎么去窮根究底。其實(shí),無(wú)論究與不究,根底就在色目人那里。追蹤來(lái)追蹤去幾百年了,薩家似乎也累了,最終也放棄了追個(gè)究竟。近七百年的歷史長(zhǎng)河洗刷,薩氏的血管里流著各種民族的血液,薩家是什么民族變得不再重要,反正都已經(jīng)成為中華民族之中的一員,重要的是這個(gè)家族的成員為國(guó)家、為社會(huì)做過(guò)的那些貢獻(xiàn)。
漢民族修家譜這個(gè)習(xí)慣真好!《薩氏族譜》清朝修過(guò),30年代薩鎮(zhèn)冰編過(guò)一次,1987年再編過(guò),2007年新編之后,又不斷增補(bǔ)、續(xù)譜,只要薩家有人出世,他們就想方設(shè)法找到,中國(guó)臺(tái)灣及香港,還有新加坡、馬來(lái)西亞、加拿大、美國(guó)的薩氏悉數(shù)被納入族譜。薩本鐵夫婦去世后,六個(gè)子女到現(xiàn)在聯(lián)系不上,薩家從未放棄尋找。薩家在這方面固執(zhí)地持守著,薩家人一個(gè)都不能丟。
月光里的朱紫坊
薩家大院門(mén)前的安泰河,是福州城內(nèi)的護(hù)城河,上世紀(jì)70年代還船來(lái)船往。建薩家大院的材料全從河運(yùn)過(guò)來(lái)。安泰橋下,護(hù)城河畔,朱紫坊老巷子里,薩家的月亮從古到今,圓了又缺,缺了又圓,陽(yáng)晴變換。津泰路護(hù)城河兩岸的高院深巷里探出月亮的臉,也是冰冷的,一如深冷的歷史,靠現(xiàn)世活人的血微溫著。
也許是因?yàn)橐股苍S是因?yàn)樵鹿猓耙沟脑?huà)題,放下了薩門(mén)英烈,祖上榮耀,回到薩家大院里,變得離生活很近。劉新法講述時(shí)的表情變得很柔和,他妻子在茶桌邊忙碌的身影變得很輕快,笑容也時(shí)不時(shí)閃現(xiàn)在院子里。小孫子在桌子周?chē)D(zhuǎn)著,不肯回房做作業(yè),嚷著要聽(tīng)薩家先輩的故事。這么近的傳奇,這個(gè)敏感的孩子怕是用了整個(gè)童年在聽(tīng),只是家族的冷暖,歷史的興衰,到了孫子這輩,也只是爺爺口里講述的故事罷了。
劉新法母親的爺爺薩子安是一個(gè)大鹽商,明末清初買(mǎi)了這一處房子,薩家大院從他30 歲時(shí)修建整整修了18年。薩子安從這里送薩鎮(zhèn)冰去馬尾船政念書(shū)。薩鎮(zhèn)冰與薩子安小兒子薩君豫又是忘年交,薩鎮(zhèn)冰與朱紫坊的關(guān)系就有好幾重,可謂有不解之緣。
劉新法認(rèn)為,“薩家家訓(xùn)是寫(xiě)在紙上的,有的東西是在基因里的”。薩家人不與人爭(zhēng)名利,懂得謙讓禮讓?zhuān)匀虨樯希辉跔?zhēng)搶費(fèi)心思。人的一生精力有限,某些方面做到不爭(zhēng),在有些方面才能做出貢獻(xiàn)。退讓虛的,反而有實(shí)在的所得歷代有成就的人輩出。薩家人個(gè)個(gè)沉靜儒雅,做事有原則,也許薩家產(chǎn)生那么多人精英的原因,就是能頑強(qiáng)隱忍下來(lái),這似乎已經(jīng)成為他們骨子里的基因。劉新法的母親就是薩家的女兒,他的記憶中母親生活樂(lè)觀(guān),即使特殊年代慘遭迫害導(dǎo)致雙目失明后,還織毛衣、學(xué)英語(yǔ),甚至讓人制作了框架書(shū)寫(xiě)書(shū)信。
劉新法懂家族源流,是深諳薩家的人。在劉新法的記憶里,大院落家教很?chē)?yán),不說(shuō)粗話(huà),冬天烤火、夏天乘涼,大人都講故事。誰(shuí)買(mǎi)了吃的,都會(huì)分給大院里住的人。小時(shí)候,左右鄰居都是親戚,無(wú)論誰(shuí)家的小孩都會(huì)被照顧,一碗飯可以從一進(jìn)吃到三進(jìn),吃好幾家的,每一進(jìn)的大廳里都擺著飯桌,來(lái)客人大家?guī)兔φ写?/p>
劉新法退休后,常與發(fā)小、早年同事在這里聊天,中秋節(jié)薩家一大家人吃飯,朋友看到這場(chǎng)面十分感慨,真希望薩家不要散去。這樣四世同堂的大宅院,如今在福州也不多見(jiàn)了。
薩家大院大門(mén)上貼著“私人住宅,謝絕參觀(guān)”,但游人還是常常探了進(jìn)來(lái),多是為著這里掛了抗日英烈“薩師俊故居”的牌子而來(lái)的。
第三進(jìn)里供奉祖先牌位和遺像桌前,擺著一個(gè)紅色鐵漆盒子,上面白底黑字寫(xiě)著“雁門(mén)關(guān)泥土”,我猜測(cè)那是薩本珪去雁門(mén)尋根帶來(lái)的那一抔泥土。
薩家大院是閩變最早的議事點(diǎn)之一,福州迎解放的三份安民告示,也是從這里由薩鎮(zhèn)冰手書(shū)后送出去的。以前這里花廳也曾是個(gè)達(dá)官貴人聚會(huì)的要地。薩家大院里最多時(shí)住150 人,每進(jìn)一個(gè)廚房,解放前,都是薩家人住,剛解放時(shí)出租,部分被收為公房。2013年,公房部分的住戶(hù)搬走了,剩下的薩家的人繼續(xù)守著祖先留下的房產(chǎn)。現(xiàn)在一個(gè)大院子住著三戶(hù)人,幾十間屋里,只有十來(lái)個(gè)人,沒(méi)以前熱鬧了,顯得很冷清,空寂。
薩家未保留先祖任何民族的風(fēng)俗,完全浸潤(rùn)漢文化傳統(tǒng)里的薩家,早已習(xí)慣了在祠堂里祭拜祖宗。已經(jīng)沒(méi)有祠堂的薩家節(jié)日沒(méi)地方聚會(huì),薩家聯(lián)誼會(huì)商議定薩家大院第三進(jìn)作為祠堂。現(xiàn)在福州的薩姓,每逢正月初五都會(huì)來(lái)此祭祖。每年五大節(jié)日祭祖都在此,五遍響鼓敲過(guò)之后,薩家的祭祖儀式就開(kāi)始了。擺上祖宗香位、貢品桌,藍(lán)色花瓶插上正月十五的白黃紅三色菊花,多少年來(lái),只有花瓶的大小和顏色在變,自劉新法記事起,這三色菊花是從來(lái)也沒(méi)有變過(guò)的。
大院第三進(jìn)的大廳背面,原建有公婆庵(先祖檀香木牌位,高40 厘米,寬15 厘米),刻先祖名字、輩分,可惜1966年被毀。自那時(shí)起,怕愧對(duì)祖先,再也沒(méi)人敢打開(kāi)過(guò)公婆庵,但誰(shuí)都知道那里面早已是空的。
將劉新法先生的介紹當(dāng)成畫(huà)外音,閉上眼睛想象那些薩家大院里過(guò)去的生活畫(huà)面:頭進(jìn)墻頭泥塑是西游,花廳是三國(guó),二進(jìn)是西廂,墻上是彩色泥塑,墻圍一圈是黑墨壁畫(huà)故事。那薩家大院的墻頭壁畫(huà)、墻頭泥塑,“破四舊”的火燒了一周,現(xiàn)在殘留的痕跡依稀可見(jiàn)。
薩家大院里的光景
朱紫坊薩家大院里,劉新法每日面南而坐,一張八仙桌上擺著茶具,官宦宅邸,迎來(lái)送往,行的還是大戶(hù)人家的禮,只要主人在,三重門(mén)常開(kāi)著,來(lái)了人請(qǐng)茶,客走送到院門(mén)外,作揖,眉恭目虔。劉新法舉手投足,也浸潤(rùn)和傳承了薩家人的儒雅。
也許因著劉新法被薩家大院那種悠遠(yuǎn)刻骨的愛(ài)感染,我對(duì)這東南老宅由衷地心生愛(ài)戀。清早和晚夕都偷偷跑去探望,走走老巷子,坐在安泰河畔,聽(tīng)榕樹(shù)上的鳥(niǎo)鳴,呼吸薩家門(mén)口的空氣。雖是榕城異地,這薩家大院里的人,最早卻是來(lái)自西域的色目人的骨血。幾百年歷史更迭,如今他們已是福州薩姓了。或許歷史的襯底本是冷硬的,只因了人類(lèi)熱血的灌注,才變得溫軟和暖了許多。
劉新法一直活在對(duì)薩家的回憶里,他的生命跟薩家的一切密不可分,他母親是薩子安六子的小女兒。劉新法原配妻子過(guò)世后,他娶了自己的表妹薩玲,薩玲的祖父薩君豫(第十子)和劉新法的外公(老六)是親兄弟。劉新法把自己的后半生與薩家緊緊地綁在一起,兒時(shí)表妹跟在他屁股后面長(zhǎng)大,其間,一個(gè)很微妙的心理恐怕是夫妻倆共同擁有關(guān)于薩家的記憶。
緣由這婚姻,沉淀在他生命最深層的記憶又被從根底打撈起來(lái),這些回憶成為他們作為薩家人共同的基因延續(xù)著,即使有一天他們搬離世居的朱紫坊薩家大院,也會(huì)被他刻進(jìn)骨子里,并在他們耳濡目染的兒子、孫子身上延續(xù)下去,這是祖先賦予的精神遺產(chǎn)。
劉新法牢記母親臨終囑托,“薩家待我們不薄,要看好家,守好業(yè),讓遠(yuǎn)居美國(guó)的親人回來(lái)時(shí)能找到家。”
現(xiàn)在劉新法跟兒子兒媳孫子一家三代,還住在那一間廂房里,他與這里總有種割舍不斷的情思。
劉新法的外婆楊鶴齡(冰心母親的同胞妹妹)晚年,靠商務(wù)印書(shū)館給薩本棟(廈門(mén)大學(xué)第一任校長(zhǎng))按月送來(lái)的稿費(fèi)版稅生活。她至死都不知道兒子英年早逝,以為兒子從美國(guó)寄錢(qián)來(lái)了;她到死都住在薩家大院,似乎大院在,兒子就會(huì)回來(lái)。
薩本棟的妻子黃淑慎1979年回來(lái),婉拒政府邀請(qǐng)和大學(xué)的安排,一定要住在薩家大院。薩本鐵在世時(shí)總每次寫(xiě)信來(lái),都說(shuō)他很想回到朱紫坊。薩本祥(女)——?jiǎng)⑿路赣H的姐姐從北京帶著壽衣回來(lái),在朱紫坊住了兩年,執(zhí)拗地要在這里度過(guò)人生最后一段時(shí)光,最后被兒女接回北京。漂泊在外,他們把這里當(dāng)作了故里,能回朱紫坊看看,在這里住住,是薩家人的期望。
夕陽(yáng)下的仁壽堂
福州名人太多,2004年修三坊七巷,福州有十一處國(guó)家級(jí)文物保護(hù)單位,薩家大院是其中一處。福州的三山陵園有薩師俊衣冠冢,廈門(mén)大學(xué)有薩本棟公園,他和夫人的墓就在公園里。福州薩鎮(zhèn)冰公園有薩鎮(zhèn)冰雕像,冶山公園有薩鎮(zhèn)冰晚年故居仁壽堂。薩氏名人在湖北的、山東的甲午海戰(zhàn)博物館,清華大學(xué)的校史館,福州中山艦博物館、馬尾船政博物館均有陳列。劉新法建議我去看看。說(shuō)起薩家的名人,劉新法如數(shù)家珍,平靜的臉上禁不住涌上驕傲的激情,他全然把自己當(dāng)成薩家人了,并且以此為榮,他很珍視薩家祖上的榮耀。
閩侯縣南通鎮(zhèn)上世紀(jì)二三十年代遭受水災(zāi),薩鎮(zhèn)冰救災(zāi),都叫他薩菩薩。后來(lái)為了紀(jì)念他建了薩公橋、薩公長(zhǎng)壽亭,鎮(zhèn)里開(kāi)了很多飯館,好多以薩鎮(zhèn)冰命名。羅源、霞浦和太姥山、閩江出海口等處還有薩公堤、薩公嶺和他的題詞石刻,央視播出的《百年中國(guó)》《船政風(fēng)云》《北洋水師》《東方有大海》《大海邊的蒙古人》等電視片和電視劇都有講到薩鎮(zhèn)冰的。
薩本珪回憶:“我叔公薩鎮(zhèn)冰30 歲夫人去世,獨(dú)身一人,清廉無(wú)房。抗戰(zhàn)時(shí)他在重慶,抗戰(zhàn)結(jié)束,叔公回朱紫坊住。1948年福建鄉(xiāng)紳集資修了仁壽堂,作為90 周歲壽禮贈(zèng)送給薩鎮(zhèn)冰。叔公與馬夫和薩姓窮親一起住,叔伯姐姐本康,哥哥本昆,還有我們?nèi)? 口人,祖母、父母還有我和弟弟都一起住在里面。我父親抄抄寫(xiě)寫(xiě),當(dāng)薩鎮(zhèn)冰的私人秘書(shū)。我在福州一中念書(shū)時(shí),弟弟去廈門(mén)修水堤。我住仁壽堂到薩鎮(zhèn)冰去世為止,才搬到姑母那里。我去浙大土木系工程系測(cè)量專(zhuān)業(yè)上大學(xué),跟薩鎮(zhèn)冰拍照了最后一張照,這張像我現(xiàn)在還珍藏著。”
夕陽(yáng)西下的時(shí)候,適合去冶山春秋園看薩鎮(zhèn)冰先生晚年的居所,通過(guò)省文物局修復(fù),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成冶山公園的一處景點(diǎn)。這棟木結(jié)構(gòu)亭子式建筑,像一個(gè)懸屋,一座孤島,更像一艘船艦。為了給這座房屋找一個(gè)切合它形象的比喻,我連去了三次,都是在黃昏,最后一次,在草坪上坐到天黑,感覺(jué)薩先生隨時(shí)都會(huì)從樓梯上走下來(lái)。最終等到一位修自行車(chē)的老人,瘦瘦的,談吐淡泊,黑暗里我想象照片上薩老先生騎馬的樣子,無(wú)論如何與眼前修自行車(chē)的老人聯(lián)系不到一起。
這艘船艦型的建筑,兩層木樓在艦頭位置,木樓前留有陽(yáng)臺(tái),像船甲板,艦首位置是一個(gè)防空洞,洞口突出來(lái),洞頂龜背紋的石頭砌成一個(gè)烏龜?shù)男螤睿瑥那懊婵矗褚恢痪扌秃}旕W起整座艦艇。
木樓背后,是一叢石山,山體上多有摩崖石刻,后人修復(fù)時(shí),書(shū)法用紅漆刷過(guò),異常醒目。這叢山像是船艦上滿(mǎn)載寶藏,使得船頭的木樓和船尾的石山,在重量感上實(shí)現(xiàn)了一種視覺(jué)平衡,讓危巖上的建筑有了一種平穩(wěn)感,仿佛這艘瀚海穩(wěn)進(jìn)的船,由于海龜?shù)鸟W舉不至于沉沒(méi)。船舷右側(cè)是上樓的石階,靠外側(cè)以綠漆石欄桿護(hù)圍,像是船舷,石階外一塊綠草坪,草坪邊是銀白沙石,從上往下看,給人一種碧海沙灘的錯(cuò)覺(jué)。薩鎮(zhèn)冰,這個(gè)中山艦的艦長(zhǎng),航海人家的后裔,以販鹽發(fā)達(dá)的鹽商后人,住在這樣的房子里,恐怕晚年一直都沉浸在他最光彩奪目的航海生涯中。
兩棵古榕像兩只結(jié)實(shí)的錨,將這艘“中山艦”牢牢地拴住,固定在了這一片福州人海,恐怕薩鎮(zhèn)冰的心應(yīng)該至死都在航行。
薩本溁的黃巷
黃巷薩家大院入口遇見(jiàn)薩本溁,雖一介市民,卻斯文不減,一看他就是薩家人的模樣。空出的房子里,有人在出售花燈。他守住院門(mén)入口,不讓東張西望的游客和路人進(jìn)到里面。他坐在門(mén)口守住的架勢(shì)很熟悉,有點(diǎn)像終日坐在薩家大院里的劉新法,我忽然明白,那是一種守的姿勢(shì),似乎他們要守住的不僅僅一個(gè)入口,似乎他們的肉身坐在這里,就能阻止世界上的一切震蕩和變動(dòng),擋住街市上洶涌而來(lái)的潮熱氣流。
薩本溁的黃巷是薩家第二支的居住地。薩家十八世薩本溁,就出生在這里。院子里的住戶(hù),非姓薩的前幾年都已搬走。他帶我看民未清初到現(xiàn)在三百多年的薩家老房子,那些木雕已然保護(hù)得很完好:
“我祖宗的房子,薩鎮(zhèn)冰13 歲以前還住這里。1952年以前我在福州火柴廠(chǎng)童工,1953年收為國(guó)有。妻子也在廠(chǎng)里,雙職工,那時(shí)候搬出去,廠(chǎng)里給我們分了宿舍。后來(lái)又讓我們搬進(jìn)來(lái)了。1998年,房子木頭爛了,快倒了,我把房子部分墻面改成磚墻。住了20年,現(xiàn)在我們也要搬出去了。”
盡管薩家院落在黃巷是第一家,隔了一堵墻,便是兩重天,把市場(chǎng)喧囂的氣息擋在了外面。空空的舊院里,屋子的頂、墻面,地都在整修,三間屋子,住在過(guò)去書(shū)宅的位置,從這里看出去,古舊的韻味從照壁每一塊磚上透出來(lái),從天井的雜草和青苔里滲出來(lái)。
從幽靜的黃巷薩家大院出來(lái),便是喧鬧的三坊七巷。出門(mén)的時(shí)候,看到那個(gè)賣(mài)花燈的,生意極好,薩本溁說(shuō):“一個(gè)過(guò)去的住戶(hù)在這里賣(mài)花燈,初一賣(mài)到十五,今天元宵節(jié),晚上有燈會(huì),福州風(fēng)俗。”
薩本溁送我出了大門(mén),站在黃巷46 號(hào)的大門(mén)前向我揮揮手,他未知覺(jué)自己正站在薩家的一個(gè)故事里,像一張發(fā)黃的老照片。
他送客的姿勢(shì)也像守在朱紫坊薩家大院的劉新法。
夜里,推開(kāi)朱紫坊薩家大院沉重的老木門(mén),劉新法端坐在空無(wú)一人的院子正中一把太師椅上,面前八仙桌上擺著茶壺、茶杯,他似乎一直在等誰(shuí)。他似乎能這樣坐到地老天荒,雁門(mén)舊地早已老去,祖上西域的天也已荒遠(yuǎn),雁門(mén)薩氏的故事,也隨劉新法一起,在朱紫坊薩家大院里慢慢變老。
薩家的月亮躲在榕樹(shù)背后,獨(dú)獨(dú)地亮著。讓人想到薩都剌的《登石頭城》里,那一輪元朝的月亮:
寂寞避暑離宮,
東風(fēng)輦路,芳草年年發(fā)。
落日無(wú)人松徑里,鬼火高低明滅。
歌舞尊前,繁華鏡里,暗換青青發(fā)
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這個(gè)月亮一直追趕著遷徙的薩家,從西域追到雁門(mén),從雁門(mén)追到閩土。元宵夜的月亮,照著薩家的過(guò)去,也照著薩家的今朝。歷史上的月亮,與今晚薩家的月亮一樣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