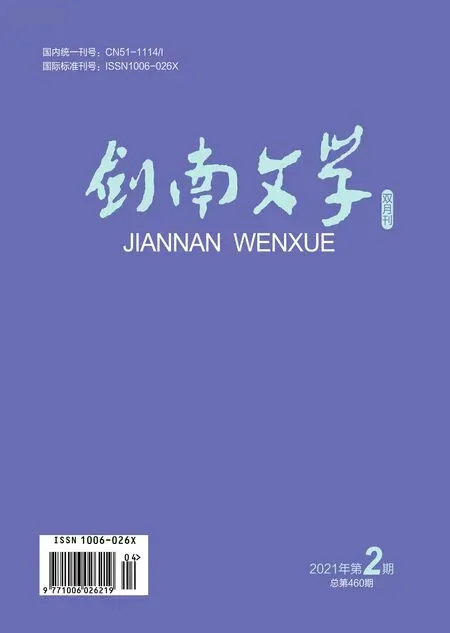時光深處(外一題)
□王曉華
塵歸塵
核桃熟了,鵝蛋大小,裹著青殼墜在枝葉間。男主人敏捷地爬上高大的核桃樹,叉開雙腿站在樹杈上,手中一根長竹竿在枝丫間飛來舞去,核桃紛紛落下,砸在地上,滾進草叢。最后一個核桃落地時,背著背篼、拿著鐮刀、站在不遠處觀望的女主人走到樹下,低頭彎腰,仔細搜撿核桃……
打了核桃,核桃樹一下子就老了,殘枝間的綠葉沒了水分,像皺巴巴的老人的臉。風夾著涼意吹過來刮過去,核桃樹葉一夜之間就枯了。枯葉大多呈焦糖色,火一點就能著。偶有一片亮眼的明黃,卻布滿焦糖色的斑塊,稀稀拉拉地掛在秋風里,搖搖欲墜。與其他依舊翠綠的樹葉相比,核桃樹葉最先把秋寫滿大地。
集市上,裝著鮮核桃的蛇皮口袋排成長龍,每根口袋前都圍滿了人,蹲著的,站著的,弓著腰的,挑挑選選后提著鼓鼓的袋子滿意而歸。
每年核桃成熟時,父親一大早就打來電話:給你帶的鮮核桃,司機到了給你打電話,你去拿一下。我愛吃鮮核桃,提回家,撿一盤,砸開雞蛋大小的核桃,剝掉硬殼和皮,露出雪白的果仁兒,入口滋潤,清香。碎核桃殼被我和進泥里,用來栽蘭草。吃不完的鮮核桃曬干,裝進蛇皮口袋,閑時剝了蒸花卷,炸核桃酥。干核桃仁的皮剝不掉,有點淡淡的澀味,去掉澀味最理想的吃法是小時候那樣:沿著火塘邊放一圈干核桃,我們姐妹圍著火塘而坐,火苗紅紅的,映著我們的笑臉。我們搶火鉗,翻烤核桃,核桃外殼烤成焦黃色,核桃仁就熟了,那香味兒,饞得人直流口水。拿一個烤好的核桃,滾燙,不停地在兩手間倒騰,再使勁往地上一甩,核桃殼裂開,剝出核桃仁,丟進嘴里,唇齒留香。剝掉的核桃殼和隔心木堆積起來,丟進地里當肥料。就這樣,年復一年,核桃葉、核桃殼、隔心木……源于自然又回歸自然。
八九十年代,村民的娃們讀書,家中零用的錢,除了養蠶、養豬,就指望著賣核桃。每到核桃成熟時,家家戶戶都會上山到玉米地里把核桃打下樹,背回家,在屋角堆成一座小山。晚上,借著昏黃的燈光,全家總動員,一人一根小板凳,圍著“核桃山”而坐,用鐮刀剝離包裹著核桃的青殼,核桃裝滿一個又一個籮筐。第二天一大早就有販子上門收購。村子里,男女老少的雙手都被核桃青殼的汁水浸染得漆黑,指甲縫隙都是黑的。那時,沒聽說過有誰打核桃掉下了樹。三年五載,偶有一人從核桃樹上落下來,趴在地上不能動彈,干脆在地上多趴一會兒,再吃力地站起來,佝僂著身子,慢慢走回家,靜養兩三月,人又活蹦亂跳的了。
現在,外出打工的村民越來越多,核桃的價格越來越低,加上打核桃不時有人掉下樹,有人摔死,有人摔殘,有人摔傷,一到核桃成熟時我就打電話,再三叮囑父母:千萬莫上樹,實在覺得可惜,就站在樹下用長竹竿敲幾下,能打幾個是幾個,打不到的就算了。回家我拿兩百塊錢買成核桃,你們倆吃不完。
父親嫌我嘮叨,不耐煩地說,曉得了,曉得了。父親七十多歲的年齡,六十歲的面容和身板,說話像敲鑼,精神抖擻。
去年秋天,七十六歲的父親趁母親背著核桃回家的空檔,悄悄爬上樹。母親把一背篼核桃倒在院墻邊,轉身剛走到屋后田邊,就看見父親像一枚熟透的核桃,從一丈多高的地埂上的核桃樹上落了下來,掉進了田里。母親飛跑過去,稻子被父親打倒一大片,父親仰面朝天,睡在稻子上,四肢叉開,像個大字。母親跪在田里,雙手拼命按壓父親的胸脯,直到父親吐出一口氣來。蘇醒過來的父親仿佛走遠路走累了,吐出的那口氣變成一聲長長的呻吟。接到母親的電話,聽見母親顫抖的聲音變了調,我的頭轟地一下就大了。匆匆趕回去,和母親把父親扶了起來。父親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沒動。我和母親站在父親兩邊,挽著父親的胳膊,也立著沒動。藍天下的稻田中間,分明還留著一個父親:父親像一塊印章,將自己的整個身軀印在了稻田里。我抬頭,瞟了一眼石頭砌成的一丈多高的地埂,還有地埂上那棵一丈多高的核桃樹,心里塞滿茅草似的,堵得慌,鼻子一酸,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父親想走,卻邁不開步子,整個身子像秋風中的核桃葉,顫顫巍巍的。他的雙手不停地抖動,兩腿打著閃。我焦急地問他,頭疼不疼?能走不?手桿能動不?父親是恍惚的,一個字也沒回答,他雙眼無神,沒了靈魂一般,木然地、艱難地抬起一只腳,又無力地放下……
父親被我們送進了縣醫院,他的肋骨斷了九根,左腳、左邊的鎖骨、左手臂骨折……在縣醫院同一病區,住著五個老太爺,他們都是打核桃時從樹上落下來的。同病房一位老大爺不停地呻吟,他兒子望望我們,又看看老大爺,自言自語:喊你莫打核桃莫打核桃,你不聽,這下打成金核桃了!疼痛不是背背子,我不能替換你。我曉得你疼,你也要小點聲,莫影響別人休息……
出院后,父親走路一拐一拐的,什么農活都干不了,成天泡在藥罐子里也不能減輕身體的疼痛。父親掉下核桃樹時,把他的健康也掉在了那塊稻田里。我能做的就是牽著他的手,領他不停地進醫院,帶回大包小包的藥。我找出兩個干核桃,讓父親捏在手上不停地轉動,希望他多動手,少一點木訥與疼痛。
父親像一棵掉光了葉子的老核桃樹,愿意或者不愿意,終究要和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樣——塵歸塵,土歸土。
時光深處
吱呀一聲,理發店的四扇實木折疊大門向兩邊緩緩打開。時光在敞開的大門前飛逝,恍如黑白電影,帶我飛向三十年前的武都。
武都的理發店是一間寬大的屋子。屋子徑深很長,中間一道墻隔開,墻上開一扇小門。里間左邊一張木床,單人的。我仿佛看見張師傅躺在床上,用瘦骨嶙峋的左手笨拙地揩著眼淚。右邊屋角一個雞窩灶,灶上兩口黑色大鐵鍋。灶上方兩匹亮瓦,陽光射進來,塵埃亂舞。外間是理發店,右邊墻上一張大鏡子。我從沒見過那么大的幾乎和墻一樣寬的鏡子。鏡子前的木柜上擺著發膠、肥皂、火吹風、手動推子等。四把大木椅,深紅色,靜靜地立在木柜前。張師傅站在一把椅子邊,對一個十七八歲身材豐滿皮膚白凈的女孩說話。教女孩洗頭,教女孩練手——如何熟練地使用手動推子而不會夾住顧客的頭發;教女孩修面,打好肥皂泡沫,剃頭刀子如何將胡子刮得干干凈凈,露出青色光滑的皮膚;教女孩用鋒利的剃頭刀子洗眼睛:刀子中間凹陷處放一滴清水,左手下按壓緊下眼皮,下眼瞼翻了出來,刀片輕輕地從眼角刮向眼尾,刮了下眼瞼再翻刮上眼瞼。來洗眼睛的都是老人,洗一次,眼睛可以明亮一兩個月。張師傅是末代國營理發店的理發匠,帶了很多徒弟。洗眼睛、洗耳朵、舒筋活絡之類的絕學,只有這個體態豐滿、皮膚白凈的女孩學會了。這個女孩就是我的大姐。
理發店外面是街道,街是老街,約三米寬。街兩邊盡是青瓦房,穿斗式,篾編墻壁,涂上黃泥、抹上石灰,全做店鋪。店鋪里賣衣服的、賣百貨的、開館子的……應有盡有。街道上,背背篼的、挑挑子的、挎籃子的、扛糖葫蘆的、甩著兩手閑逛的……人來人往,熱鬧非凡。
我到達理發店時,店左邊挨墻的三條長板凳上已經坐滿了人。板凳原木的,沒上漆,破舊。墻角,一人坐在面盆前,一位師傅正在給他洗頭。張師傅和另外兩位師傅在木椅邊忙碌。張師傅中等個子,身材偏胖,花白的頭發,圓臉、圓腦袋,紅光滿面,穿著藍布褂子,黑色長褲。張師傅一邊彎腰將通紅的炭火放進火吹風的大肚子,一邊對大姐說:“你妹妹難得來一趟,你們出去逛街,好生耍一會兒。”大姐面露喜色,禮貌地告別師傅,拉著我的手,從街中逛到街北,從街北走到街南。逛完一條街再逛另一條街。武都鎮有許多條街,不像我的故鄉,一條七彎八拐的老街,三兩分鐘就走到盡頭。武都鎮街上偶爾矗立一幢樓房,三四層高,在青瓦房群里略顯突兀。目光越過遠處街的盡頭,竇圌山靜靜地站在那兒。竇圌山的下半截遍布石頭,大大小小,一律黑色,仿佛一群伏在地上的癩蛤蟆。上半截亭臺樓閣掩映在綠樹叢中,兩座峭壁高聳入云。竇圌山我去過一次。第一次到武都看大姐時,張師傅帶我們過小橋,走山路去的,目睹了華夏一絕——“鐵索飛渡”。至今,膽怯地、試探性地移動腳步到懸崖邊,那種汗毛豎立、仿佛會一個跟斗栽下山崖的眩暈感還在。“鐵索飛渡”更是讓心提到了嗓子眼兒,耳邊驚叫聲不斷。張師傅邊走邊給我們講竇圌山的歷史,講竇圌山的海燈法師和他的一指禪功。
街邊飯館里飄出的香味一個勁兒往鼻孔里鉆,肚子餓得咕嚕響。大姐當學徒,沒錢請我吃飯。我是一個窮學生,沒錢請大姐吃飯。我們回到理發店,店里空蕩蕩的,只有一個顧客在剪頭。張師傅說:“走,帶上你妹妹,我們去吃午飯。”大姐臉微紅,沒說話,順從地拉著我,跟在張師傅后面,我看見張師傅眼角一抹慈祥的微笑。
走到理發店斜對面一個飯店坐下,張師傅叫了六個菜,有魚肉,有牛肉,有鴨子,有豬肉,有素菜。仿佛張師傅是徒弟,我和大姐才是他的師傅!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館子,吃得過癮,直接吃撐了,脹得坐著發憨,不想起身。與之前在小食店吃一碗面,或者一碗抄手是無法相提并論的。飯后,張師傅在飯店隔壁買了兩個空心餅子,餅子的肚子里塞得滿滿當當的,鼓得老高。我想,肯定是干餅子夾涼面。兩個餅子從張師傅手里遞到大姐手里,又從大姐手里到了我的手里。大姐說:“師傅讓你回學校再吃,當晚飯。”
回到江油師范校,我取出餅子,一口咬下去,餅子咧開大嘴,露出大片的鹵牛肉。原來夾的不是涼面啊!一口氣吃掉兩個干餅子夾鹵牛肉。好香的鹵牛肉!或許是平生第一次吃鹵牛肉,我永遠也忘不了它的味道。那年,我正讀江油師范一年級。一個月三十多塊錢的生活補助,足夠我一日三餐。偶有結余,就去學校小賣部,用飯票買點魚皮花生、瓜子之類的零食。或者把飯票賣給飯量大、飯票不夠的本班同學,拿著那些零錢,周末去學校附近的市場逛逛,做夢都沒想過下館子。至于干餅子夾鹵牛肉,那是夢里都吃不上的美食。
兩年后,大姐回高村開了一間小小的理發店。張師傅在路上顛簸一整天,親自到我的故鄉耍了四天,為大姐的店開張坐鎮。大姐的生意一直很火爆,過硬的手藝讓她一度霸占了高村鄉百分之九十的理發生意,小日子過得甜甜蜜蜜。不幸的是那年寒假,大姐含著眼淚對我說:“師傅癱瘓了。”大姐去了一趟武都,照顧了張師傅一周。回家后,大姐說她師傅孤零零地躺在理發店后面那張小床上,好可憐。大姐說張師傅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但是,兒女嫌他脾氣古怪,斷了聯系很多年。大姐眼里閃動著淚花,對我說:“開學你有空就去看看師傅吧。”
我常想起那間理發店,想起理發店斜對面飯館里可口的飯菜,想起塞滿鹵牛肉的干餅子。張師傅癱瘓了,兒女不在身邊,誰在照顧他呢?照顧得好嗎?姐姐說得對,我應該去看看張師傅。一個周末,我用賣飯票的錢坐車去了武都。推開理發店里那扇小木門,我的眼睛濕潤了。只見昏暗的屋子里,一張單人小木床靠著墻,床頭堆滿衣服等雜物,床邊一個尿桶,裝著半桶水,尿垢斑駁,散發著一股臭味兒。尿桶后面,用木板把床和過道隔開。過道盡頭,冰鍋冷灶。張師傅躺在床上,安靜地躺在床上,與空氣為伴。張師傅瘦了一大圈,臉上皮膚松弛,白得沒有一點顏色。他看見我,眼睛突然一亮,有了幾分生機。我和他擺條,他像個孩子,嘴里吚吚嗚嗚說著什么,我一個字也沒聽清楚。我心里涌起一陣悲傷,自我安慰地說:“您一定會好起來的!您這么好的人,一定會好起來的!”小屋里短暫的寂靜讓我更加難受,想走,又覺不妥。我坐在床邊說:“我給您講個故事吧。”
我忘了故事的名字,只記得是一個童話故事,很長的童話故事。我努力微笑著,靜靜地坐在床前木凳上,慢慢地講,想用這個故事讓他開心。但是,我失敗了。張師傅沒有笑,他的眼睛里盡是淚水。為了不讓寂靜將我們淹沒,一個接一個的故事從我嘴里淌了出來,時光被我拉長,空氣里凝結的無奈也被我拉得老長。時至下午兩點,我站起來,告訴張師傅,我要回學校了,下次再來看他。淚水順著張師傅的眼角流淌。他掙扎著,用僅可以動的左手抖抖索索地伸到枕頭下面,摸了好一陣,摸出一張二十元的紙幣。他吃力地示意我收下。“不,您現在掙不到錢了,留著自己用吧。本來,應該我給您買點東西,或者拿點錢才對。可是……”說著,我歉意地從他手里抓過錢,壓到他的枕頭底下。他用那只僅能動的左手,瘦得皮包骨的左手,笨拙地揩著眼淚。淚水像小河,默默地淌過我的臉頰,我喉嚨哽咽呼吸困難,快步走出了理發店。
我再也沒去看過張師傅。后來,聽武都的一個朋友說,國營理發店請了一個老太婆,專門照顧張師傅飲食起居。張師傅癱瘓著,說不出話。老太婆沒有在理發店的廚房里給張師傅煮飯,而是回了家,一天給張師傅送兩次飯。后來,又變成一天給張師傅送一次飯。漸漸地,張師傅身上的票子一張一張地沒了。張師傅存了一輩子的存折,也一張一張地沒了。一年后,張師傅死在了理發店后面那張小小的木床上,沒有一個人為他送終。單位將他火化,遵照遺愿,骨灰撒在竇圌山山腳下清澈的小河里。
三十年后,我開著轎車飛馳在柏油馬路上,帶著父母去竇圌山游玩。車子路過武都鎮的小街,青瓦房的老街已蕩然無存,替代它的是高樓大廈。在那穿梭往來的人流中,我再也看不見那個熟悉的身影,一如當年的火吹風,一如當年的手動推子,一如當年洗眼睛的絕活……全部消失在歲月的風塵中。竇圌山下癩蛤蟆一樣的黑石頭被蔥蘢的樹木掩蓋,唯見小河清清,一如黑白電影,流向時光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