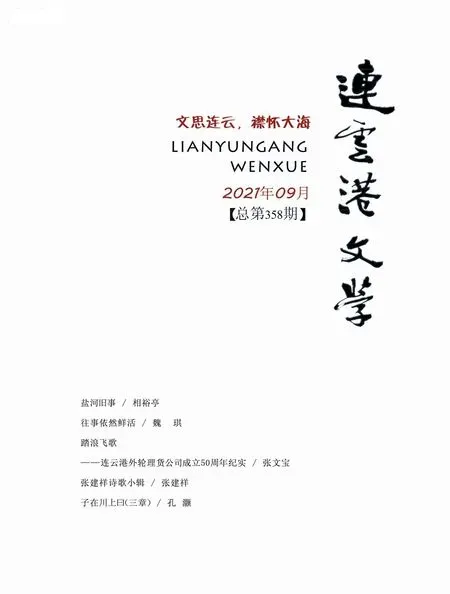子在川上曰(三章)
孔灝
子曰……
關于《論語》,宋代宰相趙普曾向宋太宗趙匡義稟報說:“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趙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大意是:微臣我平生的一點小知小見,真的全都是來源于這部書。過去,我以半部《論語》輔佐太祖皇帝平定天下,今后,我想再以半部《論語》輔佐陛下您治理出一個太平盛世。有學者研究說:此典出于宋代羅大經之《鶴林玉露》卷七。《鶴林玉露》其書,系文言軼事小說文體,所記之事,恐怕當不得真吧?好吧,此處且不討論。那么,《宋史·趙普傳》的真實性如何?“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宋史·趙普傳》記載:趙普同志年輕時熟悉政務工作,學問卻不大,等到了身居于宰相之高位,宋太祖就常常勸他多多讀書。晚年之后,他已經做到了勤奮讀書而手不釋卷,特別是每次退朝回家后,更是立刻關門閉戶,取出書箱里的書來讀上一整天。等到第二天處理政務時,總是剛毅果決、高質高效。他去世以后,家里人打開他那神秘的書箱一看,原來他每天所看之書,不過只是一部《論語》!
一部《論語》,按北宋五子之一、程朱理學的開山祖師小程子伊川先生所言,“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圣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于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那意思是:學習《論語》的人,需要把孔門諸弟子所問的問題,都當成是自己在求教,孔圣人他老人家回答的內容也正是我此刻當面親耳所聽,這樣讀書自然會有收獲。須知:即使是孔子、孟子這兩位圣人復活,也不過是以這些內容來教導他人。如果能在《論語》、《孟子》兩本書中深深探求、多多品味,那將來必定能涵養成多么了不起的氣質啊!當代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則講:“《論語》自西漢以來,為中國識字人一部人人必讀書。”身為中國人而不讀《論語》者,估計,他是不認識字吧?在錢穆他老人家看來:“我認為:今天的中國讀書人,應負兩大責任。一是自己讀《論語》,一是勸人讀《論語》。”
諸子之書中,《論語》相對平易、通俗,但卻并不易懂。實際上,如果沒有經過語言的訓練或者對《論語》有過專門的學習,恐怕一上來連《論語》這本書的書名都會讀錯!打開《新華字典》,一個“論”字,有兩種讀音:正常讀,發四聲即“議論”之“論”音,毫無疑義。但是,偏就只有另一種讀音,而且只用于一種語境,讀作二聲,是為“人倫”之“倫”音,那就是《論語》!《新華字典》在這個字條下的解釋是:“《論語》,書名,主要記載孔子及其門人的言行。”為什么是這樣?東漢大學者劉熙《釋名》說:“《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言也”。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論語》之“論”字讀作“倫”,是因為此書講倫理也。何為“倫理”?其意有二:一,為事物之條理。如《禮記·樂記》:“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東漢經學家鄭玄先生注:“倫,猶類也。理,分也。”二,為從人出發所產生的各種關系。如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社會家國的關系,及至人與天地鬼神之間的關系也!在這些關系中,人應當如何自處?這就是《論語》一書所要告訴你的。而“語”字,就是敘述之意,敘述孔子他老人家及其門人弟子的語。宋代經學家邢昺的《論語注疏》則詳解《論語》曰:
鄭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賢集定,故曰撰也。鄭玄《周禮》注云“答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后載之,以示非妄謬也。
《論語》之“論”字,其意有五: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即經綸世務,圓轉無窮,蘊含萬理,篇章有序,群賢集定,有此五意,故其音讀作“倫”也。同時,以經學家鄭玄的觀點,《論語》之“語”字,也與劉熙所謂“敘也,敘己所欲言也”不同,是“答述曰語”意。此說,與許慎《說文解字》之“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相同。
實際上,讀《論語》之“論”而作“議論”之“論”音的人,很多。比如說,我。四十多年前我念初中時在書上看到過孔子《論語》之句,在心中就是讀“議論”之“論”音。當然,以彼時淺陋之我讀錯,那當然也不算啥!但是以我現在之淺陋而觀,估計歷史上還真有個大學問家可能讀《論語》時,也作“議論”之“論”音。此人,即漢朝與司馬遷并稱“班馬”的歷史學家、文學家班固,他老人家在《漢書·藝文志》里寫: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相與輯而論纂”者,指弟子們把各自所記錄、編輯的孔子語錄會集起來編纂也。這個語境中,“論纂”之“論”字,確實當讀作“議論”之“論”音。
無論“論”字何音、“語”字何解,一部《論語》,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語錄體散文集,重點保存了大成至圣先師孔子他老人家的言論,這,是不爭的事實。從第一篇《學而》之首句“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到第二十篇《堯曰》之末句“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從某種角度來看,一部《論語》,簡直可以說就是孔子他老人家從頭說到了尾。
你看,講治國理政時,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說以德行來治理國家,就會像北極星那樣,自己安居于所當處的方位,而群星都會環繞在它的周圍。講如何盡孝時,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說侍奉父母時總是保持和悅的臉色,最難!遇到事情時,由年輕人去做;有好吃好喝的,讓年長者先吃喝,難道這樣就可以算是孝嗎?講人之誠信時,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說一個人沒有誠信,那可就真不知道他應該怎么辦了。就像大車的橫木兩頭沒有活鍵,小車的橫木兩頭少了關扣一樣,這樣的車怎么能行駛呢?講人的價值觀時,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說發大財,當大官,這是每個人都向往的。但是,如果不是以正當的手段得到它們,那么君子并不接受。貧困和卑賤,是人們所厭惡的,但是,如果不以正當的途徑來擺脫它們,君子是不會逃避的。一個君子如果背離了仁德,他又能憑借什么來成就自己的名聲呢?真正的君子不會有吃一頓飯的時間離開仁德,即使在匆忙緊迫的情況下也一定會堅守仁德,在顛沛流離的時候也同樣會堅守仁德。講安貧樂道時,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說吃粗糧,喝冷水,彎起胳膊當枕頭,這樣的生活中也有樂趣呢。如果是通過干不正當的事得來的富貴,對于我來說那就像浮云一般。你看,孔子他老人家說話,就是這么讓人如坐春風!或有人問:孔子他老人家就不生氣嗎?當然也有生氣的時候!有一次,宰我向孔子請教三年之喪問題。孔子問:“父母喪期不到三年,子女就吃好的,穿好的,對你來說心安嗎?”宰我說:“心安。”宰我出后,孔子說:“孩子生下來三年后,才能完全脫離父母的懷抱。三年喪期,是天下通行的喪禮。宰我難道沒有從他父母那里得到過三年懷抱之愛嗎?”可以想見,孔子他老人家說這話時,那種生氣、失望而又落寞的樣子。
在各民族的源頭文化中,語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載體。佛教經典中有“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句,并以“威音王”為太古時期佛的佛號。基督教的《圣經》《創世紀》篇中,從“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開始,世界完全是被神用“說話”創造出來的。有學者統計,現存《論語》20 篇,共492 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 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 章。讀《論語》,聽孔子他老人家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情景下、對著不同的人,講了那么多的話,于我而言,不過是在同一個場合、同一個情景下、對著自己,講了同一句話: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是的,孔子在大河之上對著自己喟然而嘆:那消逝的一切,都像這河水一樣呀!日夜不停,日夜不停地流去了。他的話,說給自己聽的同時,也說給大河聽、說給流水聽、說給每一朵浪花聽,也說給現在聽、說給將來聽、說給現在和將來的人們聽,他老人家說著說著,就不見了。要么,是他老人家走著走著,終于,走得太遠、太遠了;要么,就是他老人家,走著走著,終于,走到我們的心里了……
讀圣賢書 所學何事
公元1283 年1 月的一天,元世祖忽必烈親自招降抗元兵敗被俘已經關押了四年之久的南宋狀元公、宰相文天祥。文天祥再次斷然拒絕,并大義凜然地說:“文天祥深受宋朝恩德,身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賜我一死,我就心滿意足!”臨刑之際,文天祥從容不迫,告訴獄卒:“一生之事,終于完成。”在向南方跪拜后,從容就義。他的妻子歐陽氏收拾他的尸體時,見他面色安詳。其衣帶間,有絕命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
據《中國狀元全傳》載,中國歷史上總計可考的文武狀元共777 人,其中生卒年可考者51 人。文天祥以二十歲弱冠之年高中狀元,其一生的學問最后如何呈現?他的自我評價是:“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書至此,最令人想起《論語》之首句: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論語》這前三句,說是家喻戶曉、耳熟能詳,恐怕絕非夸張之語。但是,正如朱熹朱夫子他老人家之《論語集注》所說:“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此首篇既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到底當如何理解才得圣人之真意?按楊伯峻先生所說:“古往今來關于《論語》的書很多,總計三千多種。”僅以一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現代譯本為例,各家各派就各執其理,其翻譯出來的內容也各擅勝場、精彩紛呈,此處特舉三例:
學了,然后按一定的時間去實習它,不也高興嗎?——楊伯峻《論語譯注》
隨著不斷地學習,并把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到現實生活中,的確是一件很快樂的事。——辜鴻銘《辜鴻銘講論語》
學了為人處世的道理,并在適當的時候印證練習,不也覺得高興嗎?——傅佩榮《傅佩榮譯解論語》
三種譯法,細心品味可知內容截然不同。或者,一個“學”字、一個“時”字、一個“習”字,是把握這三句話精神的關鍵所在。
何者為“學”?按《說文解字》釋:“覺悟也。從教,從冂。冂,尚蒙也。”此“學”字,為“覺悟”意。那么,這種“覺悟”如何實現呢?朱夫子他老人家說:“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后。后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其善而復其初也。”“學”者,也可理解為“效仿”之意也。這“效仿”,卻不是單單指老師拿試管做實驗,學生再照模照樣重復做一次,從而掌握化學反應與物理反應區別之類的知識。而是說:人的生命,本來都應該達到一個光輝、至善的境界。但是,因為每個人對這境界的覺悟有先有后,所以,那后覺悟的人,就要向先覺悟的人“學”,亦即后覺悟的人來“效仿”先覺悟的人,最終,也達到那個所有人的生命本來都應該達到的光輝、至善的境界。這話,說得多好啊!而且,是不是有點似曾相識之感?當然!因為孟子他老人家曾經講過:“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說的是要論“學問”之道,亦無甚可談,也就是,把自己的那一顆放逸、走失的初心,找回來。或者說,也就是,把生命本來都應該達到的光輝、至善的境界,找回來。所以說,這個“學”字,既為“效仿”意,則其本身就包含著知識的獲得和行動的落實意,是知行合一也。所以,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孔門十哲之一的子夏同學認為:對妻子,能以注重賢德的心來代替喜愛美貌的心;侍奉父母,能竭盡全力;服侍君主,能獻出生命;同朋友交往,說話誠實、恪守信用。這樣的人,即使他自己說沒有學過什么,我也一定要說他已經學習過了。也所以,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那一回,魯哀公問孔子:“你的學生中誰最愛好學習?”孔子回答說:“有個叫顏回的,最好學。他從不遷怒于別人,也不犯同樣的過錯。只可惜,不幸短命死了。現在沒有這樣的人了,再也沒聽到有誰好學的了。”孔圣人他老人家講顏回其人“好學”,不過是舉例其“不遷怒,不貳過”而已。因為:不遷怒,是德行;不貳過,是智慧。也因如此,南老懷瑾先生在《論語別裁》中講“學而時習之”時說:“至于學問,哪怕不認識一個字,也可能有學問——做人好,做事對,絕對的好,絕對的對,這就是學問。這不是我個人別出心裁的解釋,我們把整部《論語》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講究做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個人。”
那么,如此之“學”,又應當從哪些方面入手呢?在孟子他老人家看來,一句話而已,叫作:學堯舜,做圣賢。按《周禮·保氏》所說,是“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孔子他老人家的私家課,和當時培養國家人才的教育課程完全相同。且說這“禮”,重點是養成做人的規矩;這“樂”,重點是陶冶人的性情;此兩者,主要是豐富和提升人的生命境界,這是人對自我的生命擔當。這“射”和“馭”,雖僅指“射箭”和“駕車”,但在古代,卻是一個成年男子保家衛國、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職業技能。至于“書”和“數”,那是認識世界、適應社會的知識和能力,這,倒是與當今有些人所注重的應試教育之內容頗相類似了。
何者為“時”?楊伯峻先生之《論語譯注》說:周秦時代,“時”字做副詞用,如《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時入山林”的“以時”,即“在一定時候”或者“在適當的時候”意。南朝時經學家皇侃的《論語義疏》釋“時”也說:“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為時,二就年中為時,三就日中為時也。”即學習有三個關鍵的時間節點,第一,是人在一定的年齡段,就要學習那個年齡段所需要學習的內容;第二,要根據一年四季的特點,合理安排不同的學習內容;第三,每天都要在一定的時間段里來學習。但是,朱夫子他老人家《論語集注》引心學的奠基人、創立了上蔡學派同時也是湖湘學派鼻祖的程門四先生謝良佐之言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謝先生以為:“時”者,“時時”也。他老人家還舉例說:無論是坐時還是立時,都要有參加齋戒或祭祀活動時的那種端正和莊重即是“時習”也。以“學”當作“成己、成人、成圣”或“生命的成長和完成”解,那當然“學”在“時時”!這是我個人的理解。不過,對學生來說,以考試得分論,自當以課本上的標準答案為準也!
何者為“習”?朱夫子他老人家之《論語集注》說:“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習”之本義,就是鳥兒多次練習飛翔。小鳥從不停息地練習飛翔是其本能,而作為一個人的“習”,則是通過持之以恒的實踐,在生命中的每個階段都豐富自己、提升自己,最終實現自己,這,也是生命的意義之所在。
另,“說”(悅)與“樂”之別,值得一說:“說”(悅),是個人內心的快樂,不一定需要為外人所知。而“樂”,有所不同,朋友來了,當喜形于色,這是發自內心的情誼所致,也是形動于外的禮貌所在也!并且,此二字經李澤厚先生專為拈出,以證明“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與西方以《圣經》為代表的“罪感文化”相比,這《論語》開篇前三句,即讓中國人的世間充滿了喜樂光明。
這樣看來,各家之說,當以楊伯峻先生所譯為佳!好在哪里?好在他不翻譯“學”!為什么?他老人家深諳學問之道,乃舉重若輕也!這也好比在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佛教之經典有所謂“五不翻”之說。即:有秘密含義的不翻,比如所謂真言、咒語;含義特別多的不翻,比如“自在”、“熾盛”、“吉祥”等詞匯;本國這里沒有的東西不翻,比如我們沒有所謂閻浮樹等,就沿用原名;按照過去習慣的不翻,比如“阿縟菩提”這樣的詞,可以翻譯其義,但東漢的法師已經以其梵音音譯了;容易讓人感受到敬意的不翻,比如“般若”這個詞就顯得厚重,若譯為“智慧”則不夠準確,且不容易讓人產生敬意,所以不翻。
具體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句,當然可以翻譯!或者我做不到做不好,但是若由我究其內涵實質而言,必譯為:時時覺悟自己的生命意識、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不斷擴展認識世界的眼界和強化擔當社會責任的能力,成己、成人、成圣,不是讓人打心眼里高興嗎?
“讀圣賢書,所學何事?”狀元公的話,令人深思!考狀元這種事之于我輩,且不去想了。一來年齡老大,二來資質有限。不過,真正在做人做事上,能有個忠臣孝子的樣兒,那也就是圣賢之行!而每個人行圣賢之行的那一時刻,自然,即是圣賢之人。那,也就是所學之事!實際上,只要我們真心想做圣賢,那真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當年錢穆錢賓四先生曾說:“天地只生了這人,卻不是生他作圣人,圣人要人自己做。自己做了圣人,天地會點頭,說你做得實合我心。”
10) quadrophonic [,kw?dr?'f?nik] adj.四聲道的11) underlay ['?nd?le?] n.襯墊物
是啊!天地會點頭,說:你做得,實合我心!我們自己,也會點頭,說:“生命本該如是!何況,我們本來,就是此等樣人”!
君子務本
明張岱《陶庵夢憶》之《鐘山》一文有記:
高皇帝與劉誠意、徐中山、湯東甌定寢穴,各志其處,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門左有孫權墓,請徙。太祖曰:“孫權亦是好漢子,留他守門。”
古來打江山平天下的英雄好漢,即令起于草莽,亦自有一番帝王風范、雍容氣象。當年,放牛娃出身的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與幾位開國名臣劉伯溫、徐達、湯和等人一起為百年之后選擇陵址。幾個老兄弟心意相通,都看中了今天的明孝陵之地。動工時,大臣們發現門左有孫權墓,便請旨將它移走。那太祖皇帝一語驚人,道:“孫權亦是好漢子,留他守門。”這話,照我聽來,真不是驕傲!那只是一種隔代英雄之間的惺惺相惜,一種在相互認同的基礎之上、依舊能夠敢于擔當的舍我其誰。
孔子門下,弟子三千,有四科十哲,七十二賢人。其仁者、智者、勇者,各領風騷;愚者、魯者、辟者、喭者,自有所成。既好看,又有趣!這里面,有一位“有子”他老人家,無疑也是一位敢于擔當的“好漢子”。
有子,姓有,名若,字子有(一說字子若)。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少孔子四十三歲;依《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則少孔子三十三歲。《左傳·哀公八年》有記:魯哀公八年(公元前487 年),吳國伐魯。一路戰無不勝,直至兵臨城下。危急時刻,魯國組織了一支七百人的敢死隊偷襲吳軍大營,終于迫使吳王訂立了退兵盟約。在此關鍵一役之中,年輕的有若,即是七百勇士之一。不僅如此,按《荀子》所說:“有子惡臥而淬掌,可謂能自忍矣”。講有子他老人家為了苦學,生怕自己睡著了而用火來灼燒自己的手掌,這,可算是對自己也夠狠心的了!還不僅如此,《禮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子曾經問曾子說:“你在咱們的老師孔子他老人家那里,請教過干部下臺方面的事情嗎?”曾子說:“我聽他老人家講:‘希望丟官后就趕快貧窮,希望死后就趕快腐爛’。”有子說:“這不是君子應該說的話(話外意:何況咱們的老師孔子呢?)。”曾子說:“我的確是從咱們的老師孔子他老人家那里親耳聽來的。”有子又說:“這不是君子應該說的話。”曾子說:“我可有證明人啊,我是和子游同學一起聽見這話的。”有子說:“咱們老師的確說過這樣的話,那么,他老人家一定就是有所針對。”于是,曾子就將這對話告訴了子游。子游說:“有若同學可真厲害,他這話說得很近似咱們老師他老人家的意思啊!那時,咱們老師他老人家住在宋國,看見桓司馬給自己做石槨,三年還沒完成。先生就說:‘像這樣的奢靡無度之人,不如讓他死了腐爛得越快越好。’希望人死了趕快腐爛,這話,是針對桓司馬來說的。又有魯國前大夫南宮敬叔,失去官職后離開魯國。但是每次回魯,必定帶上珍寶去朝見魯君以期再做高官。咱們老師他老人家就說:‘像這樣拿錢買官者,丟官后不如讓他快快貧窮。’希望丟掉官職的人以后迅速貧窮,這話,是針對南宮敬叔說的。”曾子又將子游的話,告訴了有子。有子說:“是這樣吧!我堅信,‘希望丟官后就趕快貧窮,希望死后就趕快腐爛’,那不是咱們老師他老人家毫無原因所說的話。”曾子問:“你是如何得出這樣的結論呢?”有子說:“咱們老師他老人家任中都宰時,曾為中都制定禮法:棺需要四寸,槨需要五寸。由此可知:咱們老師他老人家,并不希望人去世后迅速腐爛。還有,從前老師他老人家失去魯國司寇的官職時,打算前往楚國,就先讓子夏去了解一下情況,后來又讓冉有去宣傳一下自己的理念。由此可知:老師他老人家也并不希望失去官職后的人,迅速貧窮。”
為學之難,難在擔當!其一,學者務須將其所學,內化德性,外諸言行,是為擔當自我;其二,所謂“見于師齊,減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是為擔當傳承。有若之擔當,既在其能苦學而忘身,亦在其能當仁而不讓與師!灑然一派英雄氣也。也因此,孔子逝世后,一些年輕的學生們因為非常懷念老師,加之有的同學感覺有若之言行也很像孔子,就有部分學生擁戴有若為師,像當年侍奉孔子一樣對待有若。此說見于《史記》,應有一定真實性,暫且不表。單說《論語》一書中,孔子學生而稱“子”者,不過四人:有子,曾子,冉子,閔子。一般學界多數人共識:《論語》中,孔子的弟子而被稱“子”者,當系《論語》之成書過程中,有其門人參與編纂故。也所以,《論語》首篇第二章,即:
這一“曰”,亦好比宋代無名尼師《悟道詩》:“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云。歸來笑捻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這尼師,她芒鞋踏遍、整日尋春,卻不得而見;歸來時,輕嗅梅花之際方知:原來春天,一直在,自己的手里。有子之言,正是此意!生而為人,其踐行“仁道”的基礎,不過是從孝順父母、尊敬兄長開始而已。因為,為人做到孝順父母、尊敬兄長,卻喜歡冒犯領導的,這樣的人很少;不喜歡冒犯領導,卻喜歡造反作亂的人,不可能有。君子必定在做人的根基上下功夫,做人的根基成就了,生命的正道就自然展開。所以,孝順父母、尊敬兄長看似是每個人自己的私事家事,其實更是踐行“仁道”的根基啊!
有子的“君子務本”之論,乃深得其師孔子他老人家在《孝經》中開篇之真傳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
那一天,孔圣人對曾子說:“孝,是德行的根基,一切教化都從這里生發開來。你坐下,我現在就跟你講!人的身體以至每根毛發每塊皮膚,都是父母給予的,為人子女者應當謹慎愛護,不敢稍有毀傷,這是實行孝道的開始;以德立身,踐行‘仁道’,使美好的名聲傳揚后世,讓自己的父母都為之榮耀,則是實行孝道的最終目標。所以說,孝,開始于侍奉雙親,承續于服務國家、造福人民,最終成就于以自己的德行和事業在社會上頂天立地。”
這一次,有子,他依舊不在現場!但是,你品,你細品,你細品那有子先生的“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不正是孔子他老人家“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的題中之義嗎?
當然,有子畢竟不是孔子他老人家。據說,孔子去世之后,子夏、子張、子游等眾同學擁戴有若為老師時,曾子就堅決反對。而且,有若當上了師兄弟們的老師后,好像也不太能服眾:
說是有一天,有個學生進來請教有子:“從前,有一次咱們先師孔子他老人家正要出行時,叮囑弟子們要帶好雨具。不久,果真下起雨來。您能告訴我們:當年,孔子他老人家是怎么知道要下雨的嗎?有子回答說:“《詩經》里不是說了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亮靠近畢星時,大雨就會滂沱下呀)。那次出行的前一天晚上,月亮正處在畢星附近,所以咱們老師孔子他老人家知道:第二天,就會下大雨。”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后,有天晚上,月亮又處在畢星的位置上。第二天,卻沒有下雨。這件事,自然,讓年輕的弟子們私下議論不已。
又有一次,有位年輕弟子請教有子:當年,咱們的師兄商瞿,成家之后多年沒有孩子,先師孔子他老人家卻還派他到齊國出差。商瞿的母親找到孔子他老人家說明情況,希望別讓商瞿外出,讓孩子多多待在家中做好家庭的人口增長工作。但是孔子他老人家告訴商瞿的母親說:別擔心!商瞿這孩子,四十歲之后必定會有五個兒子。后來,果然如此!您能告訴我:先師孔子他老人家,因為什么原因會有這樣的先見之明嗎?這問題,可真難啊!故,史料記載:“有若默然無以應。”有子默然不語,無言以對。于是,當場就有另外一位弟子開口說:有老師,您還是別坐在這個位置上了,它不適合您。
我讀《論語》此章及相關資料時,每至于此,都會為有子委屈、為有子傷感。想當初,被年輕的同學們以師禮敬之,對于意氣風發而又謙恭有禮的有子而言:那一定,不是自己的本意!但是,情勢所迫,為了滿足同學們紀念先師的愿望,他不得不為。那古往今來有多少事,不都是這樣始于別人的“美意”,卻到頭來還是成為自己的種種不堪嗎?一旦情況有變,始作俑者,自可不以為意,或搖旗吶喊,或落井下石,或抽身事外,或瀟瀟灑灑地當一名永遠正確的吃瓜群眾,只留下滿地的垃圾給后人來辨析和打掃。
好在,有子,畢竟是有子!我猜,當他聽了那個憤青學生的指責后,大概,會為這群年輕的師弟們再講最后一句孔門中的學習體會吧?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的功用,以遇事做得恰當和順為可貴。以前圣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最可貴的地方就在這里。做事情無論大小,都按這個原則去做。如遇到行不通時仍一味地追求和順,卻并不用“禮”去節制它,那也是無法施行的。
有子先生把這話說完之后,就宣布他的最后一節課,下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