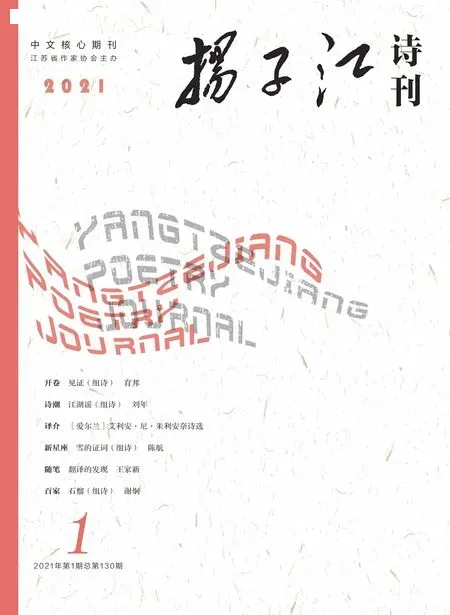立足與展望
葉 櫓
新詩百年的歷史進程,可以說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爭議的過程。其實,不管是肯定還是否定,或者是懷疑,新詩的創作始終沒有停止過。因為詩歌創作是一種精神現象,只要人類存在,精神現象是不可能停止的。
誠然,具體到中國新詩的出現和發展,的確也有其特殊的一些因素,而諸多的爭議和評說也往往伴之而生。像新詩的產生,究竟是移植的還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然的產物這種爭論,雖然被若干先賢們費過不少口舌,現在看來其實意義并不是很大。一種事物產生的來龍去脈,梳理一下也許是必要的,但當它存在以后,我們似乎更應該研究它的發展過程中那些本質性的內涵,而不是一味地去追索其產生的根源。就像一個人出現在社會以后,知道他的父母和家庭背景固然是必要的,但最終決定其社會價值的,應該還是他一生的所作所為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后果。
對于新詩,我們知道其形式是移植過來的,我們知道它是我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一種詩性品格的延續,這些都是它藝術生命內涵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這就夠了。如果立論者因為它的形式不同于舊詩,就判定其不符合國情;又因為它的藝術表現方式上與舊詩有所不同,就說它是離經叛道或缺少舊詩那種韻味,從而就否定它近百年以來的社會價值和藝術存在。這樣的立論能夠站得住腳嗎?能夠說服一般的稍具文化常識的人嗎?可是在我們的現實社會中,甚至有一些屬于文化名人的高級知識分子,卻不時地會發出這種議論,真的很令人驚訝。
一個人,不管是學富五車還是有所專長,唯有一樣東西不能違背,那就是常識。一旦違背了常識,他的立論就會顯得荒誕和無知。對新詩而言,如果有人忽略其近百年的存在這一事實而妄加否定,是不會獲得公眾認可的。
我們以一個當代人的身份來觀察新詩的百年史,一是要立足于現實,二是要展望其未來,才會對它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
所謂立足現實,首先是新詩的現實。有人說新詩沒有傳統,這個話如果放在五四時期,是有道理的,因為那時它還在初創階段,所以談不上有什么傳統。如果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如此論斷,就有點近乎荒謬了。一些人在談到我們的詩歌傳統時,首先想到的是“詩的王國”的舊詩傳統。但是不知是否有人作過調查,那些上世紀80年代以后寫詩的人,他們在詩歌觀念和藝術表現方式上,究竟是接受新詩的影響多還是舊詩的影響大?一個人從受到詩情的影響進而激發起詩性的產生,肯定是因為讀詩品詩而被促使并深化的。那一代從童年到青年時代都沒什么機會讀到舊詩的,之所以走向詩歌之路,我想大抵都是因為受當年《今天》的影響,以及與上世紀80年代中期興起的現代詩潮相關。在他們這一代人身上,如果說受過古典詩詞的影響,也大多是在以后的歲月中才吸取和補充文化養料的。我說這些話,絲毫沒有忽視或輕蔑古典詩詞的意思。這是一種歷史的事實,也是一種歷史的悲劇。作為歷史的見證人,我們是不可以忘記這一切的。
無可否認,在最早提倡新詩的那些先輩們的身上,他們身上的文學細胞或許絕大部分是滲透著中國古典詩詞因素的,在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身上,受古典詩詞的影響已經是大為減輕了。而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恐怕絕大部分都是以后在“補課”中才知道和了解什么是舊體詩詞的了。面對這樣一種近乎殘酷的歷史事實,我們要想從這些后繼者們的身上看到明顯的舊體詩的影響,豈不是近乎癡妄的幻想嗎?也正是因為這種原因,像鄭敏這樣的老詩人才在擔心青年詩人們缺乏繼承中國傳統詩歌的精神。其實,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想當年提倡新詩的先輩們,他們都是古典文學修養深厚,從小就在舊體詩詞的孕育中成長的,可是在他們提倡新詩時,甚至把舊詩說成了“僵尸”,“反傳統”是他們響亮的口號。可是多年以后,他們中的有些人竟然重操舊業寫起了舊詩。如果以此證明新詩的失敗,這無疑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了。可是新詩卻并沒有因為這些少數的先行者們的“復古”而停止其前行的步伐,反而日益擴展其創作的領域。大量的新詩人的涌現,恰恰證明了“復古”是一條行不通的道路。
說到這里,似乎又不能不涉及一個陳舊而不斷被重復爭論的話題,即新詩與舊詩的形式區別的問題。新詩已經有百年的歷史,為什么它的“形式”卻始終是一些人不斷質疑的問題呢?沒有詩的形式,何來詩?只不過因為它的“形式”,不符合一些人心目中的“形式”罷了。其實中國的舊詩,在魏晉以前,不管是四言、五言或七言,除了每行的字數一致之外,并沒有平仄對仗的嚴格規定,所以統稱為古體詩。魏晉而至唐代,嚴格意義上的律詩和絕句才被確立為正統的規范。此后的詩人如果寫詩不符合其規范,便不能成為詩。這就形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標準”:舊體詩是有評價標準而新詩是無標準的。
關于詩的評價標準的問題,可能會存在許多因時而異的外部條件,不過以我的觀點,既然是詩,它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標準,只能是詩性。一首詩的詩性,才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詩性”一詞,可能在有的人心目中就是一個玄而又玄的概念。但是在真詩人的心靈中,卻是不可或缺的感悟能力。我為《揚子江詩刊》寫過一篇《詩性何物》,就是想闡述一下我的看法。不管我的看法能否得到認同,它至少表明了我的態度。與此同時,我還寫過一篇有關新詩“詩體建設”的質疑性文章,我說“詩體建設”是一個“偽話題”也受過一些人的批評。“偽話題”一詞的確聽起來刺耳,看起來脹眼,但我說出此話,是有我的思考的。早在1950年代,就有許多前輩名家提出過新詩可以設想為九言、十一言或十三言體的“詩體建設”的理想,后來終于無疾而終。1980年代以后,雖然無人再提這類主張,但對新詩的“詩體”“形式”的或隱或現的質疑卻不時出現。一會兒說要提倡“新格律”,一會兒要討論“詩體建設”,卻總是語焉不詳。我因此想到,建設一樣東西,總得有設計的藍圖,然后才好按圖施工。像這樣無休止地議論卻提不出任何設計方案,而眾多寫詩的人在創作實踐中根本也置此不顧,這不是一個“偽話題”嗎?“詩體”成為一種“圖騰”而又不知所在之處,這種徒然浪費精力和筆墨的游戲,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嗎?有詩就有體,眾多具體的詩作就是它們的體,要想新詩像律詩絕句那樣讓人有規可循,還可能嗎?
我之所以否定“詩體建設”這個話題,絕不意味著我忽視詩歌寫作的認真和嚴肅。我是希望人們首先要尊重詩人的詩性感受和體驗,然后尊重詩人對詩歌形式的選擇和創新。詩人寫詩,如果的確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詩人,他一定是急于表達和表現他在創作高峰體驗時的詩性情境,而不會首先考慮用什么形式才符合規范。好多好詩的確是幾經琢磨和修改出來的,但那也是為了表達和表現得更完美和更能體現其詩性情境。像艾青的《我愛這土地》《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手推車》這樣一些代表作,可以說每一首的語言表達方式都是為了適應其詩性感受而寫下的,它們不會為了遵循某種形式而去改動其語言表達的方式。有過一些對艾青的不切實際的評論,正是因為脫離了詩性的要求而產生的誤解。像他的詩句“若火輪飛旋于沙丘之上/太陽向我滾來”,竟然被聞一多反問為什么是太陽向你滾來而不是你向太陽滾去。聞一多這樣的大詩人都會如此來評詩,可見有些外在因素是怎樣左右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從而損害了詩美審視的判斷力。還有人說,艾青晚年的許多詩是向格律詩靠攏了,似乎以此可以證明他的悔悟和覺醒。我們不妨反問一句,能夠讓人記住的艾青,究竟是他的哪些詩呢?評詩而不以詩性為標準,反而受種種時勢因素的左右而用非詩的標準來衡量,是不可能得出符合詩性要求的標準的。
廢名說“新詩就是自由詩”,只要不故意歪曲“自由”二字,他的話是沒有錯的。自由并不是任意地放縱和濫言。只要沒有嚴格的平仄對仗之類的要求,本質上就是自由詩。這就是我所認定的現代詩人所應當面對的詩歌現實,也是我們應當立足于這種現實之上的思考和探索,脫離了這種現實,我們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新的創造。
誠然,詩歌是一種文化現象,它是不可能脫離社會現實而孤立存在的。正是由于近百年來中國的社會現實所走過的曲折復雜的道路,所以我們的詩歌現象同樣呈現出反復挫折的經歷。如果沒有日軍的入侵和其后的三年內戰,也許詩歌之路不會如此反復挫折。1980年代以后的中國詩歌現狀,雖然說不上何等的繁榮昌盛,但總算是有驚無險差強人意。各種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論和交鋒,實屬正常的學術探討。我雖然在有些問題上堅持己見,但并不認為自己就是絕對正確的。用一句常規話語說就是放眼未來,讓歷史老人下結論罷。
我們對當下詩歌的種種現象進行評說和探討,其實是包含對它未來的發展的期待的。譬如說像“詩體建設”這樣的話題,從它的提倡者來說,肯定是希望未來的詩歌能夠走上一條規范有序的道路,使人們能夠一眼就認出它是詩,而不是讓人眼花繚亂。而我呢,也用十個字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流變的詩體,不變的詩性。”詩體既然是處在流變之中,當然就不會定型;而詩性則是人性中具有永恒性質的東西,它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本質是相同的、不變的。
有人一定會說,我們的唐詩、宋詞、元曲,不都是定型而存在和保留下來了嗎?的確,這就是歷史。而我們現在要面對的則是現實和未來,是歷史的發展和走向。作為一種歷史存在,像唐詩宋詞可以說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是我國自認為“詩的王國”的標志性產品。至今依然有一些人在“賦詩填詞”,證明著它的文化價值和意義。這些都是無須贅言的。不過我想補充一句妄言,我相信這種現象必將逐漸走向式微,這也不是少數人的愿望和意志能夠阻擋得了的。歷史是一種存在,但它在發展過程中必定是生長著一些新的事物又摒棄掉一些事物的。雖然舊詩是我國寶貴而引以為豪的文化遺產,但是由于文化語言方式的變化和發展,加上文言文同白話文之間的隔閡,未來的人們必定會同它漸行漸遠的。除了少數的文人雅士之間的互酬互慰,舊詩終將作為一種歷史遺產而存在。這并不意味著它喪失了價值;作為傳統,它的價值會是永恒的。更為重要的是,作為詩歌的抒情和感悟的方式,歷代中國優秀詩人所呈現出的獨特而精美的詩心和詩性,更是后人們應該認真學習和繼承的。人們對于傳統和反傳統,常常表現出一種兩極的態度。多年前我為《詩歌月刊》寫過一篇《反傳統:策略和目標》,認定“反傳統”只是一種策略,絕對的“反傳統”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也認為,傳統是一個流動和發展的過程和積累,當積累中存留了許多糟粕性的東西時,“反傳統”就會應運而生。一些人認定新詩沒有傳統,而只有向舊詩吸取其傳統才會有出路,就是被一種固定化的思維方式所左右了。我在該文中有一段總結性的話,至今仍然認為不錯,特引如下:“我始終認為,‘反傳統’不是如某些人所認定的那么可怕如洪水猛獸。因為從根本上說,它只是一種具有策略性的口號,它的針對性是指向那些陳腐僵化的事物的。任何一個民族,都無法避免它的肌體上滋生出的病菌,‘反傳統’無異于從事一種經常性的消毒滅菌的工作。它是為了消滅民族文化肌體上的細菌,剔除腐敗的肌肉,給身體以生機和活力,而不是為了使民族文化的肌體整個消亡。相反,如果在口口聲聲的維護傳統的掩蓋下任肌體腐敗,到時候反而是不可收拾的了。”在這里重新引出這一段話,是因為我隱約感覺到,有的人似乎在發揚傳統的主張中,有意無意地把人們的意識引向陳腐的觀念。不注重詩性的因時勢變化而帶來的內涵和形式的變化,反而一味地在探究模式化的形式規范,甚至連流沙河這樣的以寫新詩而成名的詩人,居然回到對舊詩大唱贊歌而否定新詩成績的狀態,實在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說句不好聽的話,所有關于新詩格律化的討論,我看都沒有超出當年聞一多的“三美”原則。就是連聞一多本人也無法貫徹他的主張和設想,而且他本人也意識到新詩應該是從自身的創作實踐中找到最適合的形式才有出路的。我曾經寫過一篇《分行 結構 意蘊》探索詩的形式,認為只要從這三個要素中達到相對成功的標準,就詩的形式而言,就算是基本成功的。我最后有一句追問:“世界上難道有沒有形式的詩嗎?為什么它存在著而又常常被追問它在哪里呢?”我想,這是有些人心目中一直有一種“絕句”“律詩”的模式在那里,總是想到,那么嚴格的“規矩”古人還寫出了那么多好詩,為什么我們不可以也設一些“規矩”呢?我可以肯定地說,時代不同了,詩的表現要求也不同了,人的審美心理和審美形式也不同了,所以任何“規矩”都是不可行的。
我個人有一種近乎妄自猜測的想法,我認為舊詩之所以從古體詩發展成“絕句”“律詩”這種嚴格的“形式”,是同魏晉期間文人們對四分五裂的國家形勢的失望有關,在對大勢失望之余就產生一種“把玩”文字游戲的寄托,唐代以后的科舉制度則加強了“以詩取仕”的擇優錄取方式,從而使這種詩的“規矩”得以鞏固發展。為什么到了“唐詩”的巔峰之后會出現“宋詞”,繼而又“元曲”,這些都是文人們的不甘墨守成規的藝術追求。時至今日,我們還能用什么“固定形式”來約束當代的詩人們呢?
話又說回來,寫詩固然是一件嚴肅的事,但也不排除詩人們的一種把玩游戲的心態。既然存在著把玩游戲的因素,誰愿意去自尋束縛呢?有詩心和詩性的人,一定會找到適合的表現形式而不愿意去就范于一種模式的。順便說一句,現在有人賦詩填詞甚至譜曲,但是還有人寫“漢賦”嗎?它不也曾經是一度走紅的文體嗎?它的艷詞麗句和繁復修辭,不是使眾多文人避之猶恐不及嗎?有的人在批評我的時候,常常舉一些常識以內的例子來說事,他們為什么不面對當下眾多的詩作,及其存在著許多值得研究探討的現象作出一些判斷呢?悖離歷史和現實而試圖規劃未來,從來都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和方法。
說了這么多,歸根到底,是為了展望今后詩壇的發展。當下的一些詩歌現象,因為它們的繁雜而使人感到陌生,不過照我的看法,它們在總體上仍然是呈現了符合時代變化的現象。如果說有什么異于既往詩歌的東西,可能是它的呈現方式同既往的“抒情言志”有所差別。這是客觀現實所使然,并非詩人們有意要標新立異。許多人在潛意識里一直認定詩歌是“抒豪情立壯志”的產物,是“陶冶性情,培養品德”的工具,可是這些類型的詩已經被歷史上的詩人們寫得太多,后人們如果不是碰上特別奇詭的變故,是很難從日常的生活中別出新意地超越前人的。因此我們很自然地從當代詩人的思維和感受方式中,讀到了許多既往的詩人們沒有接觸過的事物。這既是現實的發展和變化,更是詩人們的思維和感受方式的不同。
立足當下的詩歌現實狀態,我們必須堅定地相信,只有充分發揚多元化的詩歌方式,才有可能形成優勝劣汰的藝術效應。也許沒有人能夠完全準確地預見到未來的詩歌將會發展成什么樣的形態,但是我們必須允許新的秩序的形成,并且堅信只有在優勝劣汰的競爭中,這種秩序才會得到形成和完善。因此,動態地觀察一切合理的變化,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進步、發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