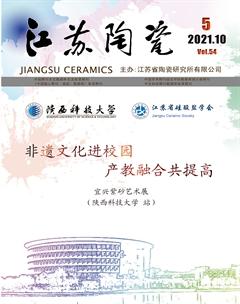論紫砂壺“勁風”的藝術審美和精神蘊含
趙歡歡

摘? 要? 紫砂壺之所以能夠很長久地打動人心,最重要的就是其中蘊含的文化意義,可以引起我們強烈的共鳴。作為茶座之上的主角和生活之中的陪伴,紫砂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實用價值,更多的是一種精神的寄托。從整體上來看這件紫砂作品“勁風壺”呈現出一種全新的姿態,作者把傳統器型和雕塑、陶刻藝術完美地融入其中,呈現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藝術享受,也讓我們在驚訝和錯愕之中想到紫砂藝術還可以這樣的傳神和寫意。從藝術審美的角度來看,這件花器和圓器相結合的設計本來就非常的具有挑戰性,同時把松樹傲立風中堅韌不拔、巋然不動的特點展示出來,通過松樹來襯托出勁風的意境,讓我們在喝茶品茗之中感悟頗多,啟迪生命。
關鍵詞? 紫砂壺;勁風;藝術審美;精神蘊含
藝術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藝術形式之中,我們最為熟悉的就是書法和繪畫了,這兩種形式和紫砂結合起來就是紫砂陶刻裝飾,簡直是天作之合,非常的完美。紫砂良好的可塑性和全手工的成型方式,讓宜興的紫砂藝人有著充分的發揮空間,可以盡自己最大的主觀能動性來設計和制作紫砂壺的形態,從而達到作者心中所需要的樣式,再通過和紫砂陶刻的結合,呈現出一種非常別致而又充滿了人文韻味的藝術效果。對于許多的壺友來說,紫砂壺之所以能夠很長久地打動人心,最重要的就是其中蘊含的文化意義,可以引起我們強烈的共鳴。在長期的把玩和摩挲過程之中,紫砂壺形成的包漿散發出幽幽的暗光,如同玉石一般令人愛不釋手,作為茶座之上的主角和生活之中的陪伴,紫砂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實用價值,更多的是一種精神的寄托。
1? 紫砂壺“勁風”的藝術審美
紫砂作品“勁風壺”(見圖1)采用了比較新穎的造型設計,把松樹遒勁的枝干和迎風傲立的姿態展示得淋漓盡致。特別是壺頸部的花器設計惟妙惟肖,和壺身松樹的陶刻裝飾相得益彰,共同塑造出我們對于紫砂藝術的審美和松柏精神的贊揚。此壺壺身可以分為兩部分,腹部主要是圓器的形態特征,特別的實用,壺底平整,端莊穩重。上面陶刻裝飾松樹的形態,每一枝松針都纖維畢現,細節的處理非常用心;頸部則是采用了放大式的松樹質感的紋理,質感強烈,把歲月的流逝和風雨的侵蝕之感凸顯出來,手法之精妙,細節之精湛,非常少見;壺嘴延續著這一概念,下半部分采用了松皮的包裹,上面則是婉約靈動,出水非常的爽利;與之遙相呼應的壺把宛如龍頭,其實還是枝干銜接自然圈卷而成,端握舒適;壺蓋嵌入壺口,嚴絲合縫,氣密性良好,通轉流暢,把玩性強;上面的壺鈕則是采用了枝干的橋型設計,和整體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同時突出江南水鄉靈動的韻味。從整體上來看這件紫砂作品“勁風壺”呈現出一種全新的姿態,把傳統器型和雕塑、陶刻藝術完美地融入其中,呈現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藝術享受,也讓我們在驚訝和錯愕之中想到紫砂藝術還可以這樣的傳神和寫意。從藝術審美的角度來看,這件花器和圓器相結合的設計本來就非常的具有挑戰性,同時把松樹傲立風中堅韌不拔、巋然不動的特點展示出來,通過松樹來襯托出勁風的意境,讓我們在喝茶品茗之中感悟頗多,啟迪生命。
2? 紫砂壺“勁風”的精神蘊含
我們國人在長期的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之下形成了比較內向的性格特征,不善于直抒胸襟地表達自己的情感和觀點,而是喜歡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于是許多的諸如月亮、秋風、竹子等等元素都在古人的詩詞歌賦和藝術作品之中具有擬人的特征,借此作者生出許多的感悟和情愫。在紫砂藝術之中,我們宜興的紫砂藝人也喜歡用松、竹、梅等等來塑造紫砂壺的外形和裝飾其上,把其中的文化內涵凸顯出來。松樹作為一種四季常青的植物,在“歲寒三友”和“四君子”之中都占有著重要的位置,也留下了許多的吟誦之詞,“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凄,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東漢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劉楨的《贈從弟》正是從松樹和勁風入手,把我們需要堅守的本性描述出來,也給予我們更多的啟示和創作的靈感,這不僅僅是我們古代文人所要堅守的氣節和本性,更是我們今天面對洶涌的時代潮流更要堅守的精神內核,這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忘初心,砥礪前行。這件紫砂藝術作品“勁風壺”正是在這樣的思緒和背景之下心生創作之靈感,于是通過紫砂的材質,細膩地把松樹的枝干捏塑出來,又通過陶刻的畫龍點睛,把松枝在風中搖擺卻挺拔傲立的姿態呈現出來,通過風來展示松的堅韌不屈,可謂是起到了預想的作用和審美,讓我們更加能夠感受到其中蘊含的精神文化和對于松柏精神的由衷贊嘆。
3? 結? 語
江南宜興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的稟賦,讓上天非常的青睞,把珍貴的紫砂資源蘊藏在此,宜興的紫砂藝人用自己聰明的才智和靈巧的雙手,把紫砂藝術傳承下來并發揚光大,直到今天一直薪火相傳、綿延不絕,而且演繹出了更多的藝術形態,和現代藝術形式結合得天衣無縫,帶給我們更多的藝術體驗和情感表達。讓我們在忙碌的生活節奏之中,靜品一杯香茗,摩挲一會紫砂,感受生活的恬淡雅致和淡泊從容。
參 考 文 獻
[1]許趙霞.從紫砂“青松壺”窺見中國松文化[J].江蘇陶瓷,2013(6):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