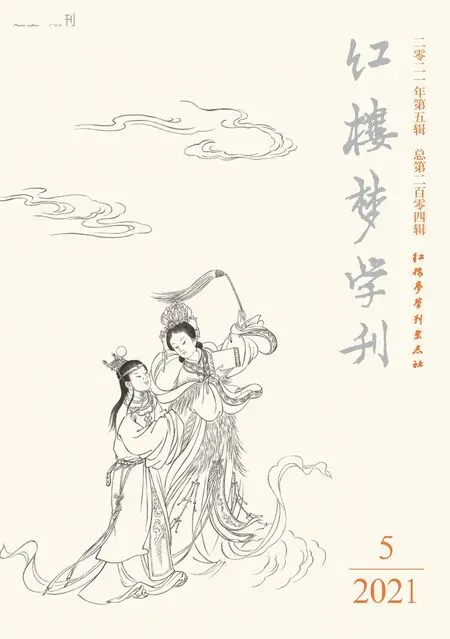后金圣嘆時代的小說認知與闡釋——《儒林外史》的文本特點及其評點的特殊意義
劉勇強
內容提要:小說史敘述大多以小說文體、題材類型或名著為小說史階段性的界標,本文主張還可以引入小說批評的因素,將小說史的審視置于小說文本特點與接受相聯系的角度進行綜合考察,認為《儒林外史》評點中的歧見紛爭昭示出這部小說文本的特殊性,亦即“《水滸》文法”與“《儒林外史》面目”的區別,而典故、素材、本事的運用與互文性的發掘、文化品味的提升與知識的揭示、主題的深化與思想的引申、內涵的多義性與評點的呼應和商榷等,正是文本與評點之間的聯動,文本的特點激發了評點的新角度、新命題,后者又使前者在接受中得到更多的體認。這一小說創作與理論闡釋互相生發的雙重意義,其實質就是古代小說進入后金圣嘆時代的體現。
中國古代小說的歷史敘述有不同維度,大多是以小說文體、題材類型或名著為小說史階段性的界標。本文希望引入小說批評的因素,將小說史的審視置于小說文本特點與接受相聯系的角度進行綜合考察。而《儒林外史》評點中的歧見紛爭昭示出這部小說文本的特殊性,使得對這部小說及其評點的討論很可能具有超出單一作品的意義。如果我們有充分地理由認定《水滸傳》與金圣嘆評點此書不可分割的歷史意義,那么,我們也許可以嘗試探討清人《儒林外史》評點的小說創作與理論闡釋互相生發的雙重意義,也就是中國古代小說進入后金圣嘆時代的體現。
一、“《水滸》文法”與“《儒林外史》面目”
金圣嘆的代表性不只是小說批評史的,從本質上說是小說史的。金批的出現,意味著通俗小說的文體自覺達到了系統化的程度。這既是小說發展成熟、興盛的結果,也為小說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一種理論基礎。如果我們把金批看成小說史的里程碑,那么,他產生前后的小說史,不妨描述為“前金圣嘆時代”“金圣嘆時代”和“后金圣嘆時代”。這種描述并非絕對的,對一部作品的評論永遠無法窮盡文本的內涵,批評家也不可能獲得文本本身所具有的獨立意義。但這不意味著不能進行這樣的描述,因為我們可以結合小說的認知與闡釋,把握小說史的演進。
為了便于說明金圣嘆的時代界標意義,我還想杜撰一個術語即“金式評點”,這指的是用金式理論意識、評點方式對小說所作的評點。這種評點萌蘗于明末“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崇禎本金瓶梅的評點”等,經金圣嘆評點《水滸傳》后,又有張竹坡評點《金瓶梅》、毛氏父子評點《三國演義》、脂硯齋評點《石頭記》等。這些評點有明顯的繼承性,它們的核心命題都是圍繞道德評判、人物性格、個性語言、結構章法等展開的,這是因為從根本上說,這些評點者所面對的文本現象有著階段性的相似性。盡管這些文本在題材類型、敘述方式等方面存在種種不同,但小說家未必充分意識和揭示了這些不同。故近代邱煒萲論及金批的集大成意義時指出:“前乎圣嘆者,不能壓其才;后乎圣嘆者,不能掩其美。”其中“前乎”“后乎”金圣嘆的說法表明了“金式評點”的時代意義。不過,后乎圣嘆者,雖然不能掩其美,卻不一定沒有發展、變化。
重要的是,“金式評點”作為理論模式運用于不同文本的闡釋,雖然會在一些特定作品的具體看法上產生分歧,但這些分歧在立場與思路上是一致的。即便是很多人參與同一部小說的評點,看法也不會有本質的區別。明代余象斗小說刊本中有“評林”的標榜,并非不同評點者評語的集評,更不是不同見解的有意匯集。清代開始出現了一些“集評”,如《女才子書》等,最典型的是《女仙外史》的評點,這部小說以回末評的形式,集結了劉在園、陳香泉、湯碩人、洪昉思等67人的評點,其中或有偽托,但也不盡然。眾多評點者對同一小說進行評點,本來有可能形成眾聲喧嘩的闡釋現象,實際情形卻是眾口一詞、同聲相應地對小說的溢美。除了作者與出版商合謀的偽托、請托,我們也許只能從文本上找原因,也就是說,《女仙外史》本身還不具備激發與容納不同聲音的解讀空間。
但是,從小說史的角度看,這種不同的解讀空間是客觀存在的,只不過需要主動的發掘。例如關于《紅樓夢》中寶釵撲蝶的描寫,甲戌本有一條批語說:“可是一味知書識禮女夫子行止?寫寶釵無不相宜。”在批點者看來,像寶釵這種身份、性格的人是不該撲蝶的。清初小說《五色石》卷六《選琴瑟》里也有“撲蝶打鶯,難言莊重;穿花折柳,殊欠幽閑”的說法。耐人尋味的是,脂批此句后面的“寫寶釵無不相宜”。在庚辰本中,這后一句與前一句間有一空格。如果這是兩位評點者先后所批,則后一句似是對前一句的反駁。也就是說,在后者看來,寶釵撲蝶沒有任何不妥。這種歧見在《紅樓夢》評點中并不鮮見,本文大量涉及的《儒林外史》評點家黃小田,同時也評點過《紅樓夢》,他對《紅樓夢》的評點,在繼承前人評點的基礎上,也每有質疑與發揮。即使是最為傳統的文言小說和最為傳統的學者,也有可能做到這一點,如紀昀經常在《閱微草堂筆記》的篇尾引入或營造對敘事的不同評論,形成敘議相生、主從相伴的多元化結構,既彰顯了敘述者主導的基本傾向,又通過不同議論者的評說,豐富了情節的闡釋空間,是紀昀在文言小說創作中的重要貢獻。
《儒林外史》及其評點的出現,使得小說的創作與闡釋更自覺地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后金圣嘆時代,其思想的深邃與多義性、知識的密度與廣度、情節的淡化與深隱的敘事等文本特性,都標志著《儒林外史》不同于傳統小說的、新的小說品格,而對《儒林外史》的評點也隨之發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變化。譚帆曾指出:“《儒林外史》評點除了以臥評為唯一祖本外,各家評點在內涵上還有明顯的傳承性,因此,《儒林外史》的評點表現為在同一源頭之下不斷累積和聚合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累積和聚合不只是因襲,更在傳承中有呼應、有分歧、有商榷。例如在第三十一回杜慎卿說杜少卿撒漫使錢,對此議論,天二評:“此等說話少卿安得而知之,而筆之于書。然則此書非少卿者所作,可知矣。”這自是基于杜少卿為吳敬梓自畫像的質疑。但平步青卻認為:“此等說話,未必出自青然,安知敏軒不能自撰自嘲?嘯山似為作者、評者所愚。”這顯然是對文本理解的另一種思路。也就是說,在大致認定杜少卿有吳敬梓影子的前提下,杜慎卿對杜少卿的議論,從文本上可以作兩種解釋,既可以是人物對杜少卿的非議,也可以是吳敬梓借人物之口的自嘲。正是文本具有這種不同的解讀可能性,使得評點也隨之產生了分歧。反過來,又正是這種分歧,印證了文本的多義性。
我們不妨再看《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的一段回末臥評及他人商榷評點。為了清晰,其他人的評點用黑體顯示:
臥評:
莊紹光是極有學問的人,
然卻有幾分做作。
何以知其有學問?
如向盧信侯所說數語,
非讀書十年,
養氣十年,
必不能領略至此。
此等學問,
書中惟有虞博士庶幾能之,
若杜少卿尚見不及此。
黃評
:少卿亦未必不見及
。是以莊紹光斷斷推為書中之第二人。
何以知其有做作?
如見徐侍郎,
居然不以門生禮自處,
黃評
:何必定認門生
?回復大學士,
其言似傲而實恭,
天二評
:如評者處此
,將以門生禮自處邪
?回復太保竟傲然不顧邪
?正如鴻門宴上,
樊噲噍讓項羽,
而羽不怒者,
以其以盟主推尊之也。
又如盧信侯被逮,
紹光作書致京師要人以解釋之,
此豈湖中高士之所為?
黃評
:此評得之
。余故曰:
卻有幾分做作。
天二評
:盧信侯惟失之好名
,非身通叛逆之比
,既由己處投監
,義當為之出力
。紹光本非山林隱逸
,不當責以高士之行
。作者于紹光無貶辭
。評家吹毛求疵
,失之過刻
。此作者以龍門妙筆,
旁見側出以寫之,
所謂嶺上白云,
只自怡悅,
原不欲索解于天下后世矣。
以上三家評點,有一致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他們的相互辯難、補充,使小說有關莊紹光的描寫呈現出較為復雜的內涵。特別是臥評最后所說的,作者以“只自怡悅,原不欲索解于天下后世矣”,更為《儒林外史》昭示了一種不強作解人、也不求定解的開放式解讀空間。
又如第四十八回王玉輝稱要編纂《禮書》《字書》《鄉約書》嘉惠來學,齊評:“此三部書真是布帛菽粟日用必不可少之物。”黃評:“迂而無當,是徽州人著述。”因為吳敬梓并沒有表示明確的態度,故評者可從自己的立場各申其說。同樣在這一回,臥評稱贊:“王玉輝真古之所謂書呆子也,其呆處正是人所不能及處。觀此人,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人之能于五倫中慷慨決斷,做出一番事業者,必非天下之乖人也。”而黃評則認為:“此評大謬。評此書者妙處固多,而錯處亦不少,總由未會作者本意,且看書亦粗心之甚。可刪。”究竟如何認識王玉輝,讀者通過這些看似對立的評點,無妨自由發揮。顯然,如果吳敬梓在敘述層面表明了自己明確的立場,評點者是不可能作出上述不同解讀的。雖然“直書其事,不加論斷,而是非立見者也”是中國古代史傳的敘事傳統,小說也屢見不鮮,但之前的小說評點更熱衷于揭示作者雖然隱含卻確定不移的意圖,而我們在《儒林外史》及其評點中所看到的卻是分歧之見,不只評點者可能有不同看法,甚至吳敬梓也不一定賦予特定敘事以單一的看法。這或許也是《紅樓夢》評點中的分歧與《儒林外史》評點中分歧的差別所在,前者的眾多評點在人物分析上也時有出入,尤其是釵黛之爭尤為突出,但那種分歧很大程度是趨于或是或非不可兩立的判斷;而后者的分歧并不完全是排他性的。
正因為如此,《儒林外史》呈現出一種不同的敘述特點與文本面貌,這也是清人評點時意識到并力圖揭示的。例如黃小田《〈儒林外史〉序》認為《儒林外史》“篇法仿《水滸傳》”、張文虎《天目山樵識語》也說“《外史》用筆實不離《水滸》《金瓶梅》”,這表明《儒林外史》和對它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仍沒有脫離小說史上“金圣嘆時代”的慣性。但是,值得玩味的是,即便是在《儒林外史》最接近《水滸傳》風格的段落,我們仍可以看到清代評點者對《儒林外史》文本特性的強調,所以,在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回有關蕭云仙等人的情節,我們可以看到如下評點:
黃評:
故作此等語。
前寫郭孝子遇虎,
一毫不犯《
水滸傳》
諸書筆路,
此段有意與《
水滸傳》
相較,
便筆路相近。
然簡潔雅馴,《
水滸傳》
萬不及也。
黃評:
此等處何減《
水滸傳》
耶。
黃評:
又故意效《
水滸傳》。
天二評:
說到封妻蔭子,
仍是《
儒林外史》
說話。
黃評:
此等言語《
水滸傳》
所無,
且正是抹倒《
水滸傳》,
以見非不能作此等書,
不屑耳。
天二評:
又襲《
水滸》
文法,
卻又似梅三相聲口。
天二評:
又是《
儒林外史》
本色來了。
天二評:
是《
儒林外史》
面目。
在這些評點中,評點者一方面指出了《儒林外史》對《水滸傳》的繼承,另一方面又強調了它對《水滸傳》的超越,以致用“《儒林外史》說話”“《儒林外史》本色”“《儒林外史》面目”這些說法來提示讀者辨識《儒林外史》的標志性特點。
實際上,關于“《儒林外史》本色”“《儒林外史》面目”之類說法,我們在清人的評點中,還能找到一些概括性的論斷,如:
第三十七回臥評:
此篇古趣磅礴,
竟如出自叔孫通、
曹褒之手,
覺集賢學士蕭嵩輩極力為之,
不過如此。
黃小田《〈
儒林外史〉
又識》:……
而世人往往不解者,
則以純白描,
其品第人物之意,
則令人于淡處求得之,
鹵莽及本系《
儒林外史》
中人直無從索解。
第三十八回黃小田回末評:
此篇略仿《
水滸傳》,
未嘗不驚心駭目,
然筆墨閑雅,
非若《
水滸傳》
全是強盜氣息,
固知真正才子自與野才子不同。
以前數十回淡淡著筆無人能解,
聊以此數篇略投時好,
且與從前演義人一較優劣,
無關正旨也。
解弢《
小說話》:
文章令雅俗共賞,
誠非易事。
若《
紅樓》
可為能盡其長,
上至碩儒,
不敢加以鄙詞,
下至負販,
亦不嫌其過高。
至《
儒林外史》,
則俗人不能讀矣,
故流傳絕少。
上述評論中“古趣”“淡淡著筆”“俗人不能讀”等,確實都觸及了《儒林外史》與“時好”“從前演義”不同的時代特點,黃小田甚至提出了“真正才子”與“野才子”的命題,為《儒林外史》的時代特點確立了小說家主體因素。
事實上,當代研究者在評價《儒林外史》時,對它與之前古代小說不同的敘述特點強調得更全面、更徹底,如商偉的《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一書中,就反復指出:“和許多其它傳統中國小說不同,《儒林外史》沒有給寓言式的解讀留下多少空間。”“他打破了以不變的人物類型來鏡照永恒道德真理的傳記傳統。這未嘗不可以說是一種新聞報道體的寫作,也就是一種開放式的寫作。”“吳敬梓和曹雪芹從不同的角度來處理白話小說的敘述傳統,由此得到的不只是新的敘述方法和修辭策略,而是感知和呈現世界的新的范式。他們的作品宣告了中國小說史上一個全新時代的降臨。”等等。雖然這些判斷針對的具體文本現象還有討論的余地,但已充分認定了《儒林外史》有別于此前小說的歷史定位。因此,我們對清人的《儒林外史》評點,也可以或應該在這樣一種歷史定位下審視。
清末民初解弢在《小說話》中說:“小說評語,吾最取《儒林外史》。金人瑞之《西廂》《水滸》,其才過人,筆亦夭矯,然吾總嫌其過于張皇。”而箸超在《古今小說評林》中,闡述了與解弢不同的觀點,箸超承認金批《西廂記》火氣大盛,但反駁了“古今評小說家,以評《儒林外史》者為第一,而金圣嘆尚在其次”的觀點。不過,他反駁時抬舉的《三國演義》評點,并非金批。無論解弢指出的金批之“張皇”,還是箸超承認的金批“有火氣”,從本質上說,其實都不只是表達方式的“刻露”“竭聲嘶態”,而是它背后強大的思維邏輯,即要揭示小說不可移易的主旨并將此酣暢淋漓地強加于讀者。因此,至少從金圣嘆評點《水滸傳》起,評點家首先會為自己評點的書寫一篇《讀法》,為讀者設定各種閱讀的規則,否則,便是“不會讀”“不許讀”,如張竹坡《金瓶梅讀法》中就說“《金瓶》必不可使不會做文的人讀”“讀《金瓶》不可呆看,一呆看便錯了”等等。而在《儒林外史》評點中,這種高高在上的霸權話語被一種更為持平的交流口吻所代替。如果說,金式批點是努力提供一種正確的觀點,《儒林外史》的清人評點則在于提供個人的、獨到的認識。重要的是,金式評點中的核心命題開始淡出《儒林外史》的評點,而由《儒林外史》文本特殊性生發出一些新的關注點或命題卻開始顯現。
需要說明的是,以金圣嘆作為一個小說史和小說觀念史的時代界標,并不意味著它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對《儒林外史》而言也是如此。它之前某些小說已經具有了一些與它相近的特點,并有可能在評點中也有所揭示;而另一方面,《儒林外史》本身也并不是對小說傳統的完全背棄,對它的評點也同樣沒有完全脫離“金式評點”。
二、典故、素材、本事的運用與互文性的發掘
正如錢鍾書在《小說識小續》指出的,“吾國舊小說巨構中,《儒林外史》蹈襲依傍處最多。”但近人論吳敬梓,從所謂“淵源學”(chronology)出發,頗多過情之譽。因為所謂“淵源學”突出“點鐵成金”“脫胎換骨”之類改變,往往會將評價的天平傾向于后繼者的創新。然而,這不一定能揭示文本間的復雜關系。
雖然在創作中有所依據是古代小說普遍的特點,但《儒林外史》中典故、素材、本事的運用不但是為了確立敘事的起點或基礎,更是有意通過典故、素材、本事的運用,豐富小說藝術思維的現實針對性和歷史縱深感。這構成了《儒林外史》的一個重要藝術特質,也代表了小說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如果說之前的小說主要用心在于故事的借鑒與敷演,后金圣嘆時代的小說對典故、素材、本事的運用,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如李漁小說中的一些所謂本事可能是莫須有的,他在《十二樓·合影樓》結尾處說:“這段逸事出在《胡氏筆談》,但系抄本,不曾刊板行世,所以見者甚少。”所謂《胡氏筆談》不過是為自己“胡編亂造”張本罷了;另一部話本小說集《生綃剪》第四回結尾說:“這一篇事,載在《吳太虛家抄》。”大概也反映了同樣的狡黠;而《豆棚閑話》則以翻案的手法,對本事進行顛覆性改造。正因為小說家在典故、素材、本事運用方面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評點者對此的發掘,也應具有更為自由的眼光,一方面要揭示小說情節構造、人物描寫的典故、素材、本事,另一方面還應引導讀者經由這些典故、素材、本事,把握小說傳承過程中的互文性。也就是說,當評點者揭示出小說家的本事依據時,不同文本間的復雜關系,可以豐富對后續文本的認識與欣賞。
就具體創作而言,《儒林外史》中的典故、素材、本事,與小說描寫的關系有遠近之別。從遠的方面看,一些典故與小說的情節未必有直接的關系,但評點者的認定,仍然可以啟發讀者從更廣泛的文化背景來把握作品的內涵,如第一回王冕拒絕縣令的邀請。華約漁評:“王冕對翟買辦一篇話,是從閔子翁(蹇)費宰一節脫來。”閔子翁事見《論語·雍也篇》載:“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吳敬梓描寫王冕對翟買辦所說的話,不一定是從此脫化來的,但約評的這種評點,指明了兩者精神上的相通,有助于讀者從更廣闊的文化背景理解小說的思想內涵。
《儒林外史》還有一些內容與典故、素材、本事可能有著直接的關系,但這種直接關系是一個發現與逐步認定的過程,評點者有時提出的只是一種推測,如第九回關于婁三、婁四公子的原型,評點家的說法有所不同。臥評認為“史文靖曾任本省總督,故疑婁乃史也。”平步青評補充道:“按文靖五子登科,著者長奕簪、奕昂(兵侍)、奕環(河東道),其二俟考。此云‘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或琫(三)瓚(四)影寫環字耶?金評以為桐城張氏,則文恪乃指文端,太保乃指文和,通政又是何人?觀卣臣少名廷瓚,必不直舉其名也。”
又如對權勿用的原型,第十二回天二評指出:“阮葵生《茶余客話》云:江陰是鏡,詭詐誕妄人也,胸無點墨,好自矜飾,居之不疑。海寧陳相國為其所惑,高東軒相國亦信之;尹健余侍郎督學江左,因二公之言造廬請謁,結布衣交。鏡遂辟書院,招生徒,與當時守令往還,冠蓋絡繹。常州守黃靜山永年亦與過從,其后因囑托公事,不復往。鏡因于書院靜室供陳、高、尹、黃四木主,俗所謂長生祿位也。”在第十三回有關蕭山縣審尼僧心遠被權勿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天二評也據董潮《東皋雜鈔》,指出是鏡“近為胞弟告發其三十余款,多有不法事……奸拐案蓋即三十余款之一也。”
再如第二十回天二評指證牛布衣的原型:“《江寧府志》:朱卉,字草衣,蕪湖人。依吉祥寺僧為童子師。性喜吟詠,游他郡,訪諸名宿,與之講切,遂工今體。中歲僑居上元,無子,依一女以終。自營生壙清涼山下。按袁簡齋集有《題朱草衣課女》詩云:‘草衣山人四壁空,繞膝吟哦惟一女。’即此所謂牛布衣也。”
上述這些說法,有的也許有點根據,有的可能并不確切,無論如何,人物有原型是吳敬梓創作的一個特點,而對原型的探討既是一種研究的結果,也可以是一種閱讀的思路。也就是說,努力發現歷史上某些精神品質乃至言行事跡與小說人物的相似之處,其實也是印證所謂“無往而非《儒林外史》”的角度。
不但人物有原型,《儒林外史》中還有許多情節與細節也有所本,如第十回敘魯編修家婚宴飛鞋事,天二評指出:“《宋書·劉敬宣傳》嘗夜與僚佐宴集,有投一芒屩墜敬宣食盤上,尋為司馬道秀所殺。變異之來誠有之。”吳敬梓的描寫,符合生活邏輯,鋪墊充分,穿插得當,不一定要遠襲前人,而《宋書·劉敬宣傳》所述,也自有其特定情景。但評點者點出此一故事,兩相對照,襯托出《儒林外史》細節描寫的歷史深度。
第十五回論及馬二先生誤信點金之術時,天二評指出:“《太平廣記》引《桂苑叢談》云:‘護軍李全皋遇道人通爐火事,求一鐵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黃金二十余兩為母,日給水銀藥物,火候既滿,開視,黃金爛然。李信之。三日之內添換有征。一日,道人不來,藥爐如舊,啟視之,不見其金矣。’又:他小說亦有載此等事者。”因為點金騙術非人人得而識之,評點者指出其古已有之,也能進一步襯托馬二先生的孤陋。
《儒林外史》情節與細節的有所本,與小說的藝術表現有關。第二十回匡超人說到“先儒匡子之神位”時,有潘世恩評:“丁守存亦嘗如此說,其人號心齋,其八股刻本甚多。”因評點語焉不詳,不知丁守存原話如何?但這也說明吳敬梓的諷刺,并非過度夸張。
無論是間接關系,還是直接關系;也無論是人物原型,還是情節素材,評點對《儒林外史》中典故、素材、本事的發掘,使讀者有可能從互文性的角度,認識這部小說的旨趣。雖然前人并無今之所謂“互文”的意識,但作為一種文本間的現象,卻是客觀存在、甚至被有意運用的。如第九回敘及一首七言絕句:“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后面一行寫:“楓林拙叟楊允草。”對此,各家評點有不同觀點,齊評:“樂天知命是賢者胸襟,究非村學究可比。”這是肯定楊執中的。天二評:“蓋亦隱寓吃官司收監事。”從這個角度看,這種詩還貼合了人物與情節。但萍叟評:“詩見《輟耕錄》,但改七律為絕句,借以點綴。”平步青也說:“見《輟耕錄》,但改七律為絕句耳。”黃評進一步指出:“詩系元人作,見《輟耕錄》,老阿呆攘為己有,改七律為七絕,得謂之呆耶?”如果一般讀者都知道此詩是元人所作的話,那么楊執中的攘為己有就與牛浦郎冒占牛布衣詩稿相似了。不過,由于吳敬梓并沒有說明這一點,不排除他隨意借用這首詩的可能。評點者揭示出這首詩的出處,顯然豐富了這一細節的解讀空間。
又如第十二回“天二評”指出《桂苑叢談》中張祜受偽豪俠蒙騙為張鐵臂本事。兩相對比,張祜故事與《儒林外史》中張鐵臂故事的相似性不只在豬頭革囊,還在于“張祜下第”后這一情節緣起,正與婁三、婁四公子相似。而除了心理基礎、滑稽意味的相似,吳敬梓又將二婁的俠客夢,置于他們訪楊、慕權等連貫情節中,更深刻地挖掘了此一故事的精神內涵。
第三十八回敘郭孝子深山遇虎,天二評:“《太平廣記》引《朝野僉載》云:唐傅黃中為諸暨縣,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有虎嗅之,虎須入鼻,噴嚏聲振,虎驚躍落岸。此借為郭孝子事。”這樣的經歷不是吳敬梓所能擁有的,將前人描寫,順手拈來,無可厚非。而且,在看似鄭重的描寫中,插入這一細節,又略有詼諧意味,與原文的傳奇性相映成趣。
第五十三回敘陳木南要輸之時,聘娘將手里抱的貓,望上一撲,攪亂了棋局。齊評指出“用楊太真故事恰好”。接著又描寫他家那些娘娘們房里,一個人一個斗大的夜明珠掛在梁上,照的一屋都亮。天二評:“王铚《默記》:宋平江南,大將得李后主寵姬,夜見燈燭輒云煙氣。問:宮中不燃燈耶?曰:宮中每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晝日。此用其事。”聘娘是一個妓女,卻一心想做官太太。楊太真或李后主寵姬故事,與她的身份都不相合。熟悉相關的歷史文本,也許可以從評點所揭示的故事中體會出一點反諷的意味。
當然,評點者對所謂本事的揭示未必都貼切,如第三十八回敘郭孝子買通了道人,日日搬柴運米,養活父親。天二評、平步青評都認為是“用后漢姜詩妻事”,但比較而論,二者實不相似。如果說有意義,那就是在事親盡孝、盡其在我這一點上略有共同點。
實際上,互文性的形成,有賴于作者、接受者的文化修養。因此,在一些評點中,評點者會提到一些與《儒林外史》并不直接相關的文本,用以揭示、襯托小說敘事的意義,如第二十二回敘董孝廉來拜訪牛浦(牛布衣):
董孝廉下轎進來,
頭戴紗帽,
身穿淺藍色緞圓領,
腳下粉底皂靴;
三綹須,
白凈面皮,
約有三十多歲光景,
進來行了禮,
分賓主坐下。
董孝廉先開口道:“
久仰大名,
又讀佳作,
想慕之極!
只疑先生老師宿學,
原來還這般青年,
更加可敬!”
牛浦道:“
晚生山鄙之人,
胡亂筆墨,
蒙老先生同馮琢翁過獎,
抱愧實多。”
董孝廉道:“
不敢。”
卜信捧出兩杯茶,
從上面走下來,
送與董孝廉。
董孝廉接了茶,
牛浦也接了。
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間。
牛浦打了躬,
向董孝廉道:“
小價村野之人,
不知禮體,
老先生休要見笑!”
對此,天二評提到《左傳》昭公十六記載一件事:
晉韓起聘于鄭,
鄭伯享之。
子產戒曰:“
茍有位于朝,
無有不供恪!”
孔張后至,
立于客間,
執政御之;
適客后,
又御之;
適縣間。
客從而笑之。
事畢,
富子諫曰:“
夫大國之人,
不可不慎也,
幾為之笑,
而不陵我?
我皆有禮,
夫猶鄙我。
國而無禮,
何以求榮?
孔張失位,
吾子之恥也。”
天二評的意思是因“不知禮體”而貽笑于人,“有位于朝者且然,況鄉人乎?”這是只有那個時代熟悉《左傳》的讀者才能有的聯想。在這一回兩個秀才打“烏龜王義安”時,天二評:“《雷峰塔·金山》一折有此奇觀。”當時熟悉此劇演出的讀者,也可以通過評點者的提示,活化自己的閱讀想像。
當然,互文性也不是無條件的。第四十回臥評:“昔者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書中賞雪一段,是隱括此意。云仙與木耐閑閑數語,直抵過一篇《李陵答蘇武書》,千載之下,淚痕猶濕。”對于這種互文性關系的構建,天二評卻譏之為“不倫”。
三、文化品味的提升與知識的揭示
在明清小說中,《儒林外史》由于題材的特殊性與作者的藝術追求,文本的知識含量有了較大的增加,這對接受形成一定的挑戰甚至障礙。因此,有不少評點是針對《儒林外史》的知識性作必要的解釋與揭示的。
第十二回敘權勿用的高孝帽子被賣柴鄉民的扁擔尖挑去,楊執中取出一頂舊方巾來與他戴了。對這一描寫,天二評:“孝服而戴方巾,奇矣!而二公子不以為非,更奇。”黃評也說:“考了十數回不進學,無故卻孝服戴方巾。”后來,婁三公子見他沒有衣服,取出一件淺藍綢直裰送他,天二評:“淺藍綢直裰乃與方巾相稱,程朱學問的人不以奪情為嫌。”通過這些評點,讀者可以更細致地體會吳敬梓通過權勿用不相稱的服飾,諷刺其做作的行為。
實際上,《儒林外史》中一些日常生活知識也需加注才能明白吳敬梓的遣詞造句或用心所在,如第二十一回見到牛布衣(實為牛浦郎)時,小說寫“郭鐵筆慌忙爬出柜臺來”,對此,黃評:“吉祥寺山門下,開小鋪面大半用柜臺自圈在內,防人走入竊物,故曰‘爬’出來,非錯字也。”一旦我們了解了那種柜臺的特點,便能明白作者用“爬”字之妙。
對于《儒林外史》描寫的地方色彩,清人評點也經常指出,如第二十一回描寫“卜信端了一個箱子,內里盛的是新娘子的針線鞋面;又一個大捧盤,十杯高果子茶,送了過來,以為明早拜堂之用”,“侄女兒打扮著出來拜年。拜過了,留在房里吃酒,捧上糯米做的年團子來”,黃評都指出為“蕪湖風俗”。
地方色彩還包括方言的使用,如不加說明,外地人有時未必能明白其中的確切意思,如第五十四回有一段精彩描寫:
丁言志道:“
陳思阮,
你自己做兩句詩罷了,
何必定要冒認做陳和甫先生的兒子?”
陳和尚大怒道:“
丁詩,
你‘
幾年桃子幾年人’!
跳起來通共念熟了幾首趙雪齋的詩,
鑿鑿的就呻著嘴來講名士。”
丁言志跳起身來道:“
我就不該講名士,
你到底也不是一個名士。”
兩個人說戧了,
揪著領子一頓亂打。
和尚的光頭被他鑿了幾下,
鑿的生疼。
黃評指出:“‘跳起來’是土語,猶言算起來。‘鑿鑿’亦土語。”后面“鑿了幾下”黃評也說明:“此‘鑿’字是以拳頭指骨打頭,如木匠之鑿也,亦土語。”假使評點者不指明,“跳起來”猶言“算起來”,實非外地人所能體會,而在明白其意后,對接下來丁言志“跳起身來”的又能別有會心,作者順勢描寫,變化莫測,將語言的運用發揮到了極致。
還有些知識來自書本,有更高的文化含量,如第二十九回杜慎卿道:“列位先生,這夷十族的話是沒有的。漢法最重,夷三族是父黨、母黨、妻黨。這方正學所說的九族,乃是高、曾、祖、考、子、孫、曾、元。”黃評指出“此竹垞翁之論”,見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十二《史館上總裁第四書》。一般讀者不一定知道或需要知道這是朱彝尊的觀點,但評點者說明其思想來源,作為一種知識,是有助于了解吳敬梓的創作特點的。又如第三十回杜慎卿道:“小弟性情,是和婦人隔著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天二評指出:“《南史》梁蕭詧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慎卿乃又過之。”杜慎卿此語是否虛偽姑不論,評點者指出其用《南史》蕭詧事,與前面所指其言論與朱彝尊相同一樣,都表明了這一人物的文化內涵頗為深邃。
第三十四回杜少卿討論《詩經》的一段話,文化內涵也很豐富,讀者要明了這一議論,至少有三方面的知識:一,對《詩經》有所了解;二,對朱注有所了解;三,對杜少卿可能依榜的觀點出處有所了解。諸家評點正是圍繞這幾點展開的:
齊評:
通儒之論。
天二評:
五十多歲想嫁也未必無。
然《
孟子》:
言親之過小則非,
此之謂。
范家相《
三家詩拾遺》
引趙岐《
孟子》
注云:
莫慰母心,
謂母心不悅也。
范云:
不悅蓋有心苛虐,
少慈恩。
此與少卿意合。
黃評:
以上數條并是竹垞翁之論,
作者借作少卿說詩。
上述評點反映出《儒林外史》思想化、知識化的特點,無疑有助于讀者對小說描寫的認識。
對小說而言,知識并不是單純的知識,而是與人物、情節相關的一種構成要素。因此,即便是一種口吻,一個語氣詞,評點者也會提醒讀者關注其中細微的意味,如第二十六回敘及有人撮合鮑廷璽與胡家女兒王太太,鮑家打聽其人,沈天孚道:“哦!你問的是胡七喇子么?”黃評:“一‘哦’字便妙,加以喇子之稱,便知有許多妙文在內。”沈大腳則搖頭道:“天老爺!”黃評:“又是天老爺,與前‘哦’字合起來,此人娶得娶不得?”而“哦”字之妙,體現在恰當的發音上。這一發音不是字典上的標準音,而是與特定情景關聯的語氣。所以,在第二十八回,寫到“說金老爺的字,是在京師王爺府里品過價錢的”,黃小田特意提到:“品當讀作去聲,俗作上聲讀。”——從本質上說,對小說中知識的領會,不是對學問的了解,而是一種欣賞能力的獲得或提高。
四、主題的深化與思想的引申
《儒林外史》不只是一部知識化的小說,同時也是一部思想性極強的小說,深刻的描寫要求讀者努力體會作者的用意,清人的評點往往也以揭示作者的意圖為目標,不但如此,有時評點者還會進一步發揮,使作品的思想內涵通過合乎邏輯的引申得到提升和擴大。
《儒林外史》第三、四回間敘范母把細磁碗盞和銀鑲杯盤逐件看了一遍,大笑道:“這都是我的了!”不覺歡喜,痰迷心竅,昏絕于地。黃小田對此加了句哲學化評點:“其實人生世上哪一件是‘自己的’?必以為‘自己的’,則痰迷心竅矣。”這一評點,使一個范母之死有了更廣泛的意義。有趣的是,第三十五回,天子允令莊紹光還山,并將南京元武湖賜與他著書立說,鼓吹休明。一日,莊紹光同娘子憑欄看水,笑說道:“你看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們的了!”天二評:“與范太太看見家貲什物都是自己的同此一喜,而有仙凡之別。”表面看,都是將外物視為己有,用語也頗相似,但境界卻截然不同,評點者將此點出,使讀者自去品味。
應該說,這樣的引申在《儒林外史》之前的作品評點中也有,如二知道人評《紅樓夢》中賈瑞之死:“風月寶鑒,神物也:照鑒之背,不過骷髏;照鑒之面,美不可言。但幻由心生,仙家亦隨人現化。賈瑞為鳳姐而病,照之則鳳姐現身其中;浸假而賈赦照之,鑒中必是鴛鴦矣;浸假而賈璉照之,鑒中必是鮑二之女人矣。至于鑒背骷髏,作鳳姐之幻相可,作鴛鴦、鮑婦之幻相亦無不可。”但比較起來,《儒林外史》評點中這樣的思想引申性評點更為多見。如第四回回末臥評:
上席不用銀鑲杯箸一段,
是作者極力寫出。
蓋天下莫可惡于忠孝廉節之大端不講,
而苛索于末節小數。
舉世為之,
而莫有非之,
且效尤者比比然也。
故作者不以莊語責之,
而以謔語誅之。
此評即將范進守孝之禮時的拘泥虛偽上升到對同類社會現象的批判。第七回臥評也對薛家集中世態炎涼的描寫作了發揮:
閱薛家集一段文字,
不禁廢書而嘆曰:
嗟乎!
寒士伏首授書,
窮年矻矻,
名姓不登于賢書,
足跡不出于里巷,
揶揄而訕笑之者比比皆是。
一旦奮翼青云,
置身通顯,
故鄉之人雖有尸而視之者而彼不聞不見也。
夫竭一生之精力以求功名富貴,
及身入其中,
而世情崄巇,
宦海風波,
方且刻無寧晷。
香山詩云:“
賓客歡娛童仆飽,
始知官宦為他人。”
究竟何為也哉!
又如第二十一回臥評提到“牛浦想學詩,只從相與老爺上起見,是世上第一等卑鄙人物”,天二評進而說:“世上此等詩人不少,馬豈偶然腫背耶?”同回臥評又說:“牛、卜二老者,乃不識字之窮人也,其為人之懇摯,交友之肫誠,反出識字有錢者之上。作者于此等處所,加意描寫,其寄托良深矣。”這幾條評語都由小說中對具體人物的描寫與態度,引申到更廣泛的社會批評與寄托。
第二十四回有一段對鮑文卿的臥評:
鮑文卿之做戲子,
乃其祖父相傳之世業,
文卿溷跡戲行中,
而矯矯自好,
不愧其為端人正士,
雖做戲子,
庸何傷?
天下何嘗不有士大夫而身為戲子之所為者?
則名儒而實戲也。
今文卿居然一戲子,
而實不愧于士大夫之列,
則名戲而實儒也。
鮑文卿是小說中的一個下層人物,吳敬梓在描寫他的所作所為時,屢借人物之口將他與儒林人物對比評論,因此,臥評提出了“名儒而實戲”“名戲而實儒”,得到黃評“評的好”的響應,在第二十五回黃評還更明確地指出:“寫鮑文卿不惜筆墨,所以深愧士大夫而為戲子之所為者,醒世之心豈尋常小說所能夢見。”
第二十五回臥評指出:“自科舉之法行,天下人無不銳意求取科名。其實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過一二人。不得手者,不稂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賈,坐食山空,不至于賣兒鬻女者幾希矣。”天二評就此評論說:“選舉無善法,即不用八股文,亦豈能人人得意?”雖然天二評沒有給出進一步的答案,但提出的問題卻是發人深省的。實際上,這還牽涉到《儒林外史》對科舉制的基本態度問題,吳敬梓否定八股取士,但未必從根本上否定整個科舉制度,同時,正如天二評中所說的,即使不用八股取士,換成別的標準,也同樣不可能解決選拔的性質及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所以,《儒林外史》指出了問題的所在,卻沒有也不可能提供解決問題的答案。
同樣,第三十四回莊紹光說:“國家承平日久,近來的地方官辦事,件件都是虛應故事。像這盜賊橫行,全不肯講究一個弭盜安民的良法。”指出了社會政治的弊端,但也沒有給出解決問題的“良法”。天二評又進一步引申:“有治人無治法。今無治人雖有治法,亦無如之何也已!‘弭盜安民’亦‘文章里詞藻’。”
第四十回敘蕭云仙坐在中間,拔劍割肉,大碗斟酒,歡呼笑樂,痛飲一天。天二評:
云仙又經濟,
又風雅,
又豪爽,
我以為在虞、
莊、
杜三人之上。
作者于大祭之后敘郭孝子蕭云仙,
非無意也,
而評者以為余波,
豈其然乎?
同一回回末的臥評,也說:
蕭云仙在青楓,
能養能教,
又能宣上德而達下情,
乃是有體有用之才,
而限于資格,
卒為困鱗。
此作者之所以發憤著書,
一吐其不平之鳴也。
上述兩條評語,涉及了蕭云仙及其言行在小說中的地位與性質,又與作者的創作動機有關,是否正確,值得思考,評點者顯然有意拓展《儒林外史》的思想空間。
正是由于評點者的引申,使得閱讀《儒林外史》不但是一種審美活動,也是一種思想活動,并導致評點中出現了許多呼應、商榷聲音。
五、內涵的多義性與評點的呼應、商榷
《儒林外史》的人物描寫、情節敘述雖有傾向性,但與此前小說觀念上的鮮明、統一有所不同,吳敬梓經常讓讀者在全書的制約性思想(如“這個法卻定的不好”等)與開放性思維之間獲得一種解讀上的自由,因此,多義性的闡發使得對《儒林外史》的評點也自然有不少是呼應性的或商榷性的。
呼應性的評點主要是對之前的評點表示贊同、補充或發揮,如第一回描寫了胖、瘦、胡子三個人在柳樹下的吃喝閑聊,回末的臥評稱:“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書中諸人之影子,其所談論又是全部書中言辭之程式。小小一段文字亦大有關系。”黃小田認為這一臥評是“妙批”,因為三人看起來“何其風雅,但不可開口耳”,這符合吳敬梓注重通過人物外表與言行的對比,表現人物的精神心理的敘述習慣。所以,當那胡子說道:“聽見前日出京時,皇上親自送出城外,攜著手走了十幾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辭了,方才上轎回去。看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黃評曰:“閱此能不噴飯否?一部書皆用此訣。”黃評與臥評在這一細節上的呼應,抓住了小說的思想藝術的一個命脈,也就是臥評所謂的“書中言辭之程式”和黃評所謂的“一部書皆用此訣”,可以說從第一回起,便提示讀者把握《儒林外史》的敘事特點。
事實上,黃評對臥評的回應很多,如第七回臥評:
此篇文字分為三段。
第一段是梅三相考四等,
令閱者快然浮一大白。
然三相既考四等之后,
口若懸河,
刮刮而談,
仍是老友口聲氣息,
恬不為恥,
世上固不少此老面皮之人。
吾想梅三相與嚴大老官是一類人物,
假使三相出了歲貢,
必時時自稱為鄉紳,
與知縣為密邇至交;
大老官考了四等,
必仍然自詡為老友,
說學臺為有意賣情也。
第九回臥評:
婁氏兩公子,
因不能早年中進士、
入詞林,
激成一肚子牢騷,
是其本源受病處。
狂言發于蘧太守之前,
太守遂正色以拒之;
不意窮鄉之中,
乃有不識字之村父,
其見解竟與己之見解同,
雖欲不以為知言烏可得已?
一細叩之,
而始知索解者別有人在。
此時即有百口稱說楊執中為不通之老阿呆,
亦不能疏兩公子納交之殷也。
黃評對上述二評都稱之為“妙批。”
又如第十一回臥評:
嫻于吟詠之才女古有之,
精于舉業之才女古未之有也。
夫以一女子而精于舉業,
則此女子之俗可知。
蓋作者欲極力以寫編修之俗,
卻不肯用一正筆,
處處用反筆、
側筆,
以形擊之。
寫小姐之俗者乃所以寫編修之俗也。
……
老阿呆才進相府,
便薦出一位高人。
閱者此時已深知老阿呆之為人,
料想老阿呆所薦之人平常可知,
然而不知其可笑又加此老一等。
譬如吳道子畫鬼,
畫牛頭,
已極牛頭之丑惡矣;
及畫馬面,
又有馬面之丑惡。
吾不知作者之胸中能容得多少怪物耶!
黃評更是連下二贊語:“此評確矣。”大表肯定。
但是,后續評點者對此前評點也不是一味呼應,商榷性的評點在《儒林外史》諸家評點中也隨處可見。如第一回敘王冕與吳王即朱元璋晤談后,對秦老也不曾說就是吳王,只說是以前相識的一個將官來訪。對此天二評:“非瞞秦老也,蓋有難言者。”但約評卻認為:“非難言也,只因鄉間眼界小,恐哄動眾人耳,如此才是真隱。”應該說,兩個評點都有道理,也并非截然對立的,但約評從王冕“真隱”的品格分析,比天二評只從人情世故著眼要深刻些。
還有些商榷性評點的對立意識就極為明顯了,如第四回有這樣一段臥評:
關帝廟中小飲一席話,
畫工所不能畫,
化工庶幾能之。
開端數語尤其奇絕,
閱者試掩卷細想,
脫令自己操觚,
可能寫出開端數語?
古人讀杜詩“
江漢思歸客”,
再三思之不得下語,
及觀“
乾坤一腐儒”,
始叫絕也。
“關帝廟中小飲一席話”指的是嚴貢生招待張靜齋、范進時的吹噓,確實活靈活現,極為傳神,但引杜詩作比,卻有些不當。因此,黃小田毫不客氣地指出:“此擬不倫,此君批語慣有此等毛病,然好處卻多。”值得注意的是,黃小田的批駁并不是簡單否定,他同樣認可臥評“好處卻多”,而且緊接這一批駁之后,針對臥評有關嚴貢生的評點,黃小田就肯定道:“妙批,一部書多用此訣。”
第八回蘧太守談到孫子時說:“近來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幾首詩,吟詠性情,要他知道樂天知命的道理。”對此,齊評:“天懷恬淡,可敬可師。”天二評卻作誅心之論,認為蘧太守:“沽名釣譽有之,樂天知命未必。”而黃評則認為:“做名士便是樂天知命。”對蘧太守仍表示肯定。
潘三曾幫助過匡超人,第二十回敘潘三入獄后,匡超人卻打官腔,不愿以朋友身份探監,甚至夸張地說,如去看望,“就是小弟一生官場之玷”。對此,臥評說:
潘三之該殺該割,
朝廷得而殺割之,
士師得而殺割之,
匡超人不得而殺割之也。
匪惟不得而殺割之,
斯時為超人者,
必將為之送茶飯焉,
求救援焉,
納贖鍰焉,
以報平生厚我之意然后可耳。
乃居然借口昧心,
以為代朝廷行賞罰,
且甚而曰,
使我當此,
亦須訪拿,
此真狼子野心,
蛇蟲螫毒未有過于此人者。
天二評很不認同這種說法,指出:“此過意。忍心作此言,以明不能進監探望之故,其實為出脫身體,惟恐累及耳。評者切齒謾罵,全未中窾。”多少有對匡超人有點理解之同情。不過,對于臥評引申所論“昔蔡伯喈伏董卓之尸而哭之,而君子不以為非者,以朋友自有朋友之情也。使天下之人盡如匡超人之為人,而朋友之道苦矣。”黃評卻以為“此評確當”。
又如第二十六回向道臺為鮑文卿題銘旌“皇明義民鮑文卿之柩”,天二評:“何不竟題老友某人之柩。義民未甚妥。”而黃評認為:“義字足以該之。”與上面的商榷相似,也是天二評不同意臥評,而黃評卻表示贊同。
有時,評點者甚至會虛擬一個討論者,如第二十一回敘牛浦郎看到牛布衣詩稿,未曾署名,便欲“刻起兩方圖書來印在上面”,冒“牛布衣”之號占為己有。天二評:“狐精變人形尚須戴髑髏夜夜拜月,此乃只須刻兩方圖書,豈非捷徑!或云牛浦因看了此詩以致變壞,不知本具賊性,即不見此稿亦必作穿窬。”其中“或云”就是天二評虛擬的一個討論者,表明商榷的方式體現了評點家的態度。
從類型上看,商榷性評點的側重各有不同,有的涉及小說的基本思想,如第十一回臥評:“書中言舉業者多矣,如匡超人、馬純上之操選事,衛體善、隋岑庵之正文風,以及高翰林之講元魁秘訣,人人自以為握靈蛇之珠也,而不知舉業真當行,只有一魯小姐。陸子靜門人云:英雄之俊偉不鐘于男子,而鐘于婦人。作者之喻意其深遠也哉。”對于臥評所引陸子靜門人云,黃評說:“引書不當,評此書者往往有此病,可刪。”因為書中對魯小姐的描寫是憐憫的而非贊許的,臥評所引“英雄”云云,確有牽強之處,并不符合作者的本意。
也有的商榷性評點涉及人物的不同看法,如第六回回末臥評提到“嚴老大一生離離奇奇,卻頗有名士風味”,黃小田即認為:“此批不合。如此混帳那得以名士例之?即曰譏之,亦不合也。”
第八回臥評:“二婁因早年蹭蹬,激成一段牢騷,此正東坡所謂‘一肚皮不合乎時宜’也。雖是名士習氣,然與斗方名士自是不同。”而天一評卻認為:“斗方名士借幽雅以博榮名,兩婁因蹭蹬而激為幽雅,畢竟異流同源。”這里,天一評的“異流同源”說,對于認識《儒林外史》中不同名士的精神品質,確有啟發。
第十九回臥評為潘三辯護,說“此篇專為寫潘三而設。夫潘三不過一市井之徒,其行事本不必深責。然余獨賞其爽快瀏亮,敢作敢為,較之子曰行中鄙瑣沾滯之輩,相去不啻天壤。讀竟不覺為之三嘆曰:嗟乎,作者之命意至深遠矣!”并進一步發揮,認為潘三等鉆科舉的空子,是“其中一二狡黠者,既挾其聰明才智,自分無可為出頭之地,遂不得不干犯當時之文網,巧取人間之富厚。法令滋張,而奸盜不息,豈盡人之自喪其天良歟?抑亦上之人有以驅之使然也?”對于這種過度引申,黃小田不以為然,認為臥評“所言不切潘三,評者往往有此敗筆”,“潘三舞弊豈止此一事?文前后不合。此書評者妙處固多,然謬亦不免”。
第三十一回臥評:“慎卿、少卿,俱是豪華公子,然兩人自是不同。慎卿純是一團慷爽氣,少卿卻是一個呆串皮。一副筆墨,卻能分毫不犯如此。”黃評認為:“加慎卿以‘慷爽’字大謬,加以‘呆’字正合。少卿可謂呆矣,然純是慷爽,其呆亦不可及。”
第四十回臥評:“才寫過蕭云仙,接手又寫一沈瓊枝。云仙,豪杰也;瓊枝,亦豪杰也。云仙之屈處于下僚,瓊枝之陷身于傖父,境雖不同,而其歌泣之情懷則一。作者直欲收兩副淚眼,而作同聲之一哭矣。”對此,黃評認為:“沈瓊枝何得與蕭云仙并論?此評大謬。書中沈瓊枝者,取其聊備一種人,《春秋》所謂‘雜羈’也,豈許之耶。”天二評也認為臥評有比擬“不倫”之處。
還有的商榷性評點涉及藝術方面的商榷,有助于讀者更全面深入地體會小說的敘事技巧,如第一回敘王冕七歲上死了父親,天二評:“據《曝書亭集·王冕傳》,父命牧牛隴上,潛入塾聽村童誦讀,暮亡其牛,父怒撻之。不云早孤。此處不可以誣先賢。豈傳聞異耶?《明史》傳與朱集略同。”平步青的評點對此卻持不同看法,他認為:“如本傳,則敘次不能一線。故云父歿,非誣先賢,亦非傳聞異也。”也就是說,吳敬梓在利用本事進行人物設置、展開描寫時,不僅要考慮人物品行,還要兼顧線索的清晰、敘事的流暢等藝術上的需要。
第八回提到王惠“各上司訪聞,都道是江西第一個能員”。天二評:“陽明先生不聞乎?亦以為能員乎?”這里將王惠當成了真實人物,所以,平步青評:“王惠事本子虛,此評可刪。”他還認為,王惠“作者本寫得支離”,評論時不必“粘滯”。
第二十五回鮑文卿把過繼倪老爹之子的事向乃眷說了一遍,小說寫“乃眷也歡喜”。對此,天二評:“此時是歡喜。”黃評則說:“此喜非真,觀后文自知。”聯系鮑文卿死后,其妻對繼子的態度,“此時是歡喜”而又“此喜非真”的微妙態度,確實值得玩味。
第二十六回提到向鼎升了福建汀漳道。天二評:“明時布政司有左右參政、左右參議,按察司有副使、僉事,皆即今之道員。既托名明官,不當徑稱今制,此亦疏忽之過。”對此,平步青認為:“此等皆稗官家故謬其辭,使人知為非明事。亦如《西游記》演唐事,托名元人,而有鑾儀衛明代官制;《紅樓夢》演國朝事,而有蘭臺寺大夫、九省總制節度使、錦衣衛也。江秋珊《雜記》嫌其蕪雜,亦未識此。此評可刪。”平步青的評點更切合小說的本質。
《儒林外史》偉大也要有人懂,不意味著一味的吹捧。所以,在一些商榷性評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清代評點者追求持平之見的努力,如第二十六回臥評:
金次福初來說親,
其于王太太,
蓋略得其概,
故但能言其奩資之厚,
箱籠之多,
蓋此事已七八年,
而次福新近始知之,
其意不過慫恿成局以圖酒食而已,
本無他想。
沈天孚即能知其根底,
是以歷歷言之,
然猶是外象三爻。
至沈大腳,
然后識其性情舉動,
和盤托出。
作三段描寫,
有前有后,
有詳有略,
用意之新穎,
措辭之峭拔,
非惟稗官中無此筆,
伏求之古名人紀載文字,
亦無此奇妙也。
天二評似乎不認可這種過于褒揚的藝術分析,認為沒有抓住要害,故加以“浮話”的批評。
針對沈瓊枝的描寫,第四十一回臥評說:“名士風流忽帶出一分脂粉氣,然絕不向綺羅叢中細寫其柔筋脆骨也。想英姿颯爽自是作者本來面目,故化作女兒身為大千說法耶!”也有夸飾過度之嫌,所以黃評說:“此評似是而非,前文謂之‘豪杰’亦是此意,實未解作者用意。”天二評也有“浮談”之譏。
總之,商榷性的評點從不同角度豐富了小說內涵與藝術的認知,如第二十五回倪老爹嘆氣道:“我從二十歲上進學,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死書。”對于他的這一感慨,齊評:“一語傷心。”黃評:“書是死的,人卻是活的,甘死于書下,不得怪書。”天二評:“張靜齋云禮有經有權,乃是活書。”三個人三個角度,正體現了《儒林外史》廣闊的解讀空間。關鍵在于,它啟發讀者以一種寬容而不封閉、靈活而不拘泥的態度面對小說文本。
綜上所述,典故、素材、本事的運用與互文性的發掘、文化品味的提升與知識的揭示、主題的深化與思想的引申、內涵的多義性與評點的呼應和商榷是《儒林外史》與評點之間的聯動,文本的特點激發了評點的新角度、新命題,而后者又使前者在接受中得到更多的認同。雖然《儒林外史》文體上的新變還沒有達到充分自覺的程度,清人對它的評點也沒有形成更為系統的理論意識,也就是說,后金圣嘆時代可能還只是小說史研究的一種判斷或描述,而非小說史已經卓然成型的姿態或流程,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隱約可見的新變沒有意義,相反,即使不從小說發展的角度而只從小說創作多元格局的角度看,對《儒林外史》及其評點特殊性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乃至給予更高的評價,也是有足夠的理由和必要的。
2017年7月2日于奇子軒
注釋
① 邱煒萲《
菽園贅談》,
引自陳平原、
夏曉虹編《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
第一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第34-35頁。
② 參見譚帆《
中國小說評點研究》(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第59頁)。
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甲戌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
第424頁。
④ 筆煉閣主人著,
蕭欣橋校點《
五色石》,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第146頁。
⑤ 茲據影印庚辰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二冊,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
第609頁。
⑥ 參見宋慶中《
紅樓夢黃小田評點研究》(
知識產權出版社2019年版,
第114、
134頁)。
⑦ 參見劉勇強《“
言”、“
曰”
之間:〈
閱微草堂筆記〉
的敘事策略》(《
明清小說研究》
2013年第1期)。
⑧ 參見劉勇強《
儒林外史的文本特性與接受障礙》(《
文藝理論研究》
2013年第4期)。
⑨ 譚帆《
中國小說評點研究》,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第155頁。
另外,
石麟《
中國古代小說評點派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
第26-27頁)
曾指出評點中“
后評”
言及“
前評”
的現象,
并指出在《
儒林外史》《
紅樓夢》
評點中最多見。
⑩ 本文所引《
儒林外史》
正文、
評點及評點簡稱(
如“
天二評”“
黃評”
等),
均據李漢秋輯校《
儒林外史匯校匯評》,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下文不再贅注。
[11] 黃小田不同意臥評的“
此篇古趣磅礴”
的說法,
認為“
此評甚迂,
不過相題立言而已,
何必過贊?”
[12][14][15] 朱一玄編《
儒林外史資料匯編》,
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第461、
464、
468頁。
[13] 商偉《
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
三聯書店2012年版,
第193、
207、
265頁。
[16] 朱一玄編《
金瓶梅資料匯編》,
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第440、
443頁。
[17] 錢鍾書《
寫在人生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
三聯書店2002年版,
第147—
151頁。
[18] 李漁《
十二樓》,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第15頁。
[19] 佚名《
生綃剪》,
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第97頁。
[20] 一粟編《
紅樓夢資料匯編》(
上冊),
中華書局1964年版,
第100—
1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