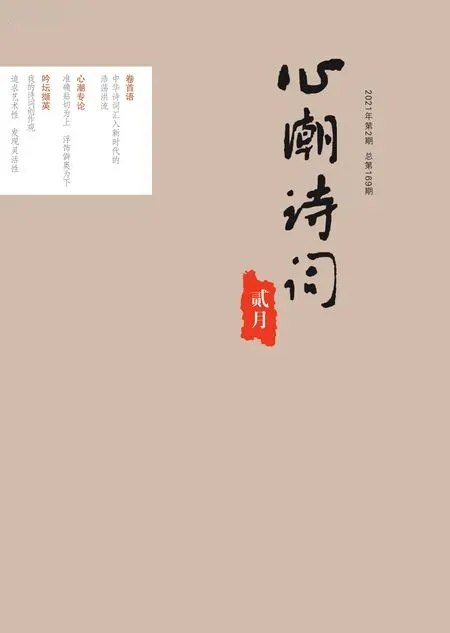傳統詩學命題漫議
王國欽
(河南省詩詞學會副會長):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這不僅表現在浩若星海的詩歌(詞)創作,而且表現在傳承有序的詩學理論“命題”等方面。“詩言志”最早見于文字記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尚書·堯典》)其后,又有“詩以言志”(《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詩以道志”(《莊子·天下篇》)、“獻詩陳志”、“教詩明志”等理論的陸續出現,更使得“詩言志”的命題影響至今。
東漢文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提出的“感于哀樂,緣事而發”,是鑒于漢樂府創作而提出的一個新“命題”。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的觀點,應該是與此比較接近的另外一種說法。
西晉著名文論家陸機的《文賦》,是我國最早、最系統探討文學創作問題的賦體論著,提出了“詩緣情而綺靡”的“命題”。陸 機 對 當時“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等十種文體進行了分別論述,而今來看,只有“詩”“賦”“頌”等文體的生命力最為頑強。
“詩緣政”的“命題”,源于唐代孔穎達等人對《詩經》的研究性著作《毛詩正義》:“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由此可見,他在理論上是將《詩經》作品都看作“緣政而作”的。
在筆者看來,以上幾個“命題”之間最主要的聯系,就是以“詩”為原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不同的學者站在不同的視角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命題。具體到當今詩詞創作,筆者自己的感悟是:
其一,根據筆者《“詩言志”之言在“當下”》一文分析,“詩言志”作為最簡單也最經典的主、謂、賓句式,其完整意義可理解為:“詩”(主語)是作者“表述”(謂語)個人“情志”(賓語)的一種文學作品。“詩”,必然是其中的主體、重心。
其 二,“詩 緣 事”“詩 緣情”“詩 緣政”三個“命題”,都屬于被動句式,即“詩緣之于……”。若分別理解就是:
(一)“詩歌”因為“事物”而生發,不同的“事物”產生了在內容上“哀樂”不同的詩歌作品——言“生發”所至之格調也。范仲淹在《岳陽樓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作者所表達出的一種高尚情懷,與此并非一樣。
(二)“詩歌”因為“情感”而綺靡,不同的“情感”產生了艷麗、浮艷、柔弱等風格不同的詩歌作品——言“情感”所至之風格也。而“綺靡”,也僅僅是詩歌眾多風格之一也。
(三)“詩歌”是因為“時政”而述作,不同的“時政”產生了在體式上各不不同的詩歌作品——言“時政”所至之體式也。詩歌體式因“時政”而生?介于是與不是之間也。
由此得知,只有“詩言志”才是真正簡潔、準確、經典的傳統詩學“真命題”。其余的“詩緣事”“詩緣情”“詩緣政”之說,只是以偏概全地道出了詩歌“緣何而起”的一個方面而已,若謂之“偽命題”應不為過。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緣何而起”的“偽命題”,無疑也為歷史上的詩歌發展產生了種種影響與作用。
對于“詩言志”中的“志”,理解則是多方面的。可以是詩人“情志”“心志”“意志”“才志”的表述,也可以是詩人“立志”“勵志”“告志”“矢志”的過程。根據作品的不同情況,“志”又可類分為“天下之志”“眾人之志”“君子之志”“小人之志”,還可以細分為“高遠之志”“謙卑之志”“宏大之志”“微小之志”“典雅之志”“庸俗之志”等。而“情志”之不同,詩人在作品中所塑造的“大我”“小我”“有我”“無我”之形象,自然已不言而喻地體現了作品及人品之高下。具體到當下的詩詞創作,諸位詩家必將各有自己特殊的感悟與選擇。
楊子怡
(惠州經濟職業技術學院教授):“言志”與“緣情”是詩學中的一個很重要的理論,“言志”較早見于《尚書·虞書·舜典》,其中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的說法。“詩緣情”較早由陸機提出,其《文賦》有“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話。先秦時期“志”與“情”是有區分的,“志”是屬于理智的東西,常指的是思想、志向、抱負,應該是不包括“情”的范疇。但是到了漢代有所變化,“情”也囊括在“志”中,如《毛詩序》就說:“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很顯然在此把情志并稱了。后來,甚至有人把“言志”與“抒情”劃上等號,“情動于中而言以導之,所謂詩言志。”有人索性說“志也者,情也”。到了宋,人們甚至把“志”“情”與“事”相關聯:“何故謂之詩?詩者言其志。既用言成章,遂道心中事。”(邵雍《論詩吟》)顯然,“心中事”也納入“志”的范疇。甚或把“志”擴大到“政”,如顧炎武就有“故詩者,王者之跡也”(《日知錄》)的話。可見,“志”的外延逐漸擴大。“言志”與“緣情”成為中國的詩學傳統。我認為兩者仍然有不同的側重點。“言志”主要說的是詩歌的創作問題,是詩歌寫作的內容與方向,也即詩歌應該表達什么,應該寫些什么,它為詩人指明創作方向。這里的“言”即是“述”,表達與抒發的意思,詩人應該表達或抒發自己的志向、意圖、思想、抱負,甚至對社會的看法及對時事的感受。如白居易就把自己的“諷諭詩”看成是“兼濟之志”,把“閑適詩”看成是自己的“獨善之義”。總之,不管寫怎樣的詩,詩人都得有想法,有觀點,這就是“志”,把這些“志”表達出來就是詩。當然也一定程度包含詩人情緒,誠如陸游所說“古之說詩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讒,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曾裘父詩集序》),“緣情”側重的是詩歌的發生,即詩是如何產生的,《毛序》所說的“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就是對“緣情”的一個最好的注腳,它描繪了由情感的沖動而產生詩的創作過程。因此,“緣”字可作姻緣、緣由解,詩因情而發,湯顯祖所說的“世總為情,情生詩歌”(《耳伯麻姑游詩序》)就是說的這個道理,沒有情感的沖動是不能產生詩的。沒有情感的誘發而“強覓愁”,自然會滑到無病呻吟之中,寫出哼哼唧唧的無生命的作品。也正因詩是情釀就的,因此也就規定了詩必然有情,情真也就成了評定詩作好壞的最高標準。可見,“言志”與“緣情”涉及到詩歌的創作內容與詩歌的情感發生兩個側重點不同的問題,邵雍《伊川擊壤集序》中有一段話可資我們參考:“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詩人對其所處之時,有一定想法和思想,帶著情感去觀照它,把它表達出來,把情感宣泄出來,自然就形成詩。這樣,詩中自然會寓含詩人思想與情感。
“言志”與“緣情”這一詩學傳統仍是我們今天詩詞創作應恪守的經驗。它給我們兩點啟示。其一,言志乃詩之本。詩人思想、傾向、觀點及對時事、社會之看法宜寓于詩中,做到言之有物。如明吳寬《中園四興詩集序》所言:“古時人之作,凡以寫其志之所之者耳。或有所感通,或有所觸發,或有所懷思,或有所憂喜,或有所美刺,類此始作之。”當今詩壇之失就在于:應景者多,寫實者少;閑吟趨奉者多,寄托有志者少。尤缺思想,一首下來,莫知所云。其二,情動于中始作。宋人胡仲孺《簡齋詩箋敘》云:“詩者,性情之溪也。有所感發,則軼入之不可遏也。”他告訴我們:情到不可遏時才作詩,詩才真。“詩可數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劉熙載《詩概》中這句話仍值得我們深思。當今詩壇,很多詩人忘記了這個道理,只求數量,不求真情,不管沖動與否,不管感動與否,有節必頌,有飲必吟,有唱必和,有壽必賀,有喜必歌,有風必跟,應景趨時,忘記了詩歌發生的藝術規律,也忘記了詩人的責任與擔當,假語套話連篇累牘,看不見詩人的情感所在。因此,我們應該回歸“言志”“緣情”的傳統,杜絕假大空的東西,永遠記住:詩本述志,詩緣性情,詩道性情。
羅積勇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關于“詩緣政”說及其對當代詩詞創作的啟示意義,經查核文獻和對比詩詞曲創作現狀,我得出了如下幾點體會。一、不應過分夸大歷史上“詩緣政”說對當時詩歌創作的影響。眾所周知,孔潁達等人是秉承“疏不破注”的原則來做正義的,因此,其在《毛詩正義》中提出的“詩緣政”說主要是對《詩經》大、小序和鄭箋的闡釋、彌合,如果對唐代詩人和詩論有影響,那也是依附于《毛詩序》和鄭箋的。事實上,學者引來證明“詩緣政”說之影響的陳子昂、李白、杜甫、李益、元結等人的話語,都沒引用“詩緣政”說,都是直接指向《詩經》大、小序和鄭箋的,或者指向《禮記·樂記》的。當然,指出這一點并不影響我們今天批判性地繼承“詩緣政”說。
二、《毛詩正義》提出“詩緣政”說有對抗“詩緣情”說的意味,今天則宜兼收并蓄。“詩緣政”的“緣”應與“詩緣情”的“緣”同解,即理解為“詩因為政治(影響)的緣故而創作。孔疏為何不用“言”而一定要用“緣”?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詩經》“風”詩反映社會風俗、男女情愛的詩并未直接言政(但它被看成是政治影響的結果,并且在上者可以通過這些詩觀察政治的成敗得失);二是有以“詩緣政”對抗陸機以來“詩緣情”說的意味,因為孔疏中有“情志一也”的論述,試圖將“情”歸諸于“志”,其依據是《詩大序》所言“發乎情,止乎禮義”。魏晉以來言情過頭,至于“橫陳”,唐代要糾偏。我們今天應辯證對待“詩緣政”說,因為“詩緣政”說還有一個重要論據,就是人們的喜怒哀樂的產生都與政治有關。而我們知道,當今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非全是政治影響的結果,也就是說,當今社會有比較明確的“小我”“大我”之分,“詩緣政”與“詩緣情”并非處處對立。
三、“詩緣政”的“君子作詩”說啟示當今詩人要以主人翁姿態來創作。為了“詩緣政”的證成,孔穎達提出了“君子方可作詩”和“詩述民志”的主張,這些個主張盡管不能涵蓋《詩經》所有篇目特別是國風中的詩篇創作情形,但雅、頌之作者確實大多是當時“國人”或“國人”中地位比較高的“士”所作,這部分人是懂歷史且預國事的。所以,今天弘揚“詩緣政”理論,詩人就也應學習歷史和了解政事,深入實際,植根人民,以主人翁姿態來寫作。
四、《詩》對政的功能不僅僅是“美”“刺”兩項,還有“群”這一項。詩序、毛傳、鄭箋、孔疏將《詩》跟政的關系歸納為“美”“刺”兩項,是不全面的。《詩經》中還有《秦風·無衣》等表現積極參與政治的篇目,這一類詩在今天就更多了,抗擊新冠疫情的詩詞有不少是屬于這一類的。對照《論語》中孔子詩論所說興、觀、群、怨,這一類功能可稱之為“群”,即在關鍵時候激起民眾的集體主義情懷,應該說,這也是表現“大我”的一種方式。
五、今日“美”“刺”的標準不可盡依“詩緣政”說。詩序、毛傳、鄭箋和孔疏所講以詩美政和以詩刺政,是以“政”是否符合禮制、是否符合“舊貫”為標準的,這一點在今天肯定要揚棄。今天宜以是否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標準,黨中央確定的核心價值觀繼承了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同時也反映了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人民的共識。
六、“刺政”是詩的重要功能但并非獨占功能,中華詩詞的刺政仍宜遵守比興原則。客觀地講,今日的報告文學和小說,其“刺政”的作用遠較中華詩詞發揮得好,劉醒龍的一部小說促使政府下決心解決了鄉村代課教師待遇問題,中華詩詞現在還不能與之比肩。不過,我們在急起直追的同時,還是應該堅持詩詞的比興傳統,《毛詩大序》在解釋“風”時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毛詩正義》對此加以認同,《毛詩正義》還認為“美、刺俱有比、興者也”。婉曲的表達也能感人至深,同時更能為人所接受,揆之人情,古今當無大異。
蔡世平
(一級作家、中國當代詩詞研究所所長):討論詩歌寫作中“大我”與“小我”的問題,需要搞清楚兩個時期的社會文化背景:一個是五四前期的中華詩歌社會文化背景;再一個是五四以來的中華詩歌社會文化背景。中華詩歌產生于上古時期,茁壯成長于春秋戰國時期,詩歌體式成型于魏晉南北朝(我認為“古風”亦是一種重要的詩歌體式)、唐宋及元,體現漢語言文字特征的格律詩、詞、曲是其重要標志。
大體說來,《詩經》是春秋時期的作品,“楚辭”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作品。《詩經》是中華詩歌現實主義源頭,“楚辭”是中華詩歌浪漫主義源頭。
五四前期的中華詩歌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意識深植于詩人的頭腦,甚至成為一種民族文化基因,作用于中華詩歌創作。漫長的中國農耕社會,雖然也有強調個體的“小我”寫作,但其主流還是“詩言志”——言儒家思想文化之“志”。近現代雖有不少討論文章認為,孔子的這個“志”其實是“志意”,是詩人心里面的一個小小想法,是鄉情、友情、愛情,亦或是悠哉游哉于自然山水什么的,與江山社稷無關。即便當時孔子真是這么個意思,但是,也被漢以后歷朝歷代的“注經師”們拉到了忠君愛國的儒家文化“正統”軌道上去了。他們認為這才是詩歌寫作的“大我”和“大理”,詩人就是要有放江山社稷于心中的理想抱負,時刻準備著效力朝廷,建功立業,然后是封妻蔭子,衣錦還鄉。
那時候的詩歌寫作者一般都站位很高。無論是鄉下的私塾學子,還是縣衙當差的吏員,提起筆來寫詩就先端正了態度,洗了手臉,正了衣冠,有了“廟堂”之思,應是今日謂之的“高大上”“正能量”寫作吧。這也是中華舊體詩歌的一個重要傳統,對今天的詩詞寫作仍有較大的影響。當然啦,那時候的詩人大多是士人,是朝廷命官,與今日之人民大眾的詩人還是有不小的“身份”區別的。
以上說的是五四前期詩歌寫作的社會文化背景。
再來看五四后的詩歌社會文化背景。
我們應注意到五四后的文學創作是白話文生態己經形成,這一客觀現實的要害在于,首先它從語言、語境上顛覆了幾千年以來形成的文言文寫作傳統。新的筐子便要裝新的東西,這是毫無疑問的。因此如何從舊體詩歌的桎梏下突圍出來,創造新的詩歌體式,就成為五四時期詩人的時代使命。于是,自由體新詩應運而生。自由體新詩帶來的不僅是詩歌語言、文體的變化,而是寫作思想、寫作思維的變化。
其次是國家政體的根本性改變,人民大眾成為國家的主人。詩人的自主意識增強,再也不像封建時代文人寫作的那種小心翼翼了。
再次是五四后的中國文學藝術是西方文化全面進入,或者說是中西文化合流形成的文學藝術觀念和文學藝術文本。歐洲中世紀發源于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人文主義思想迅速發展,“人”的全面解放,生命個性的張揚,同樣深刻地影響了今天的中國文學創作。那么“小我”的詩歌寫作便成為時代之必然,這在自由體新詩寫作中尤為顯眼,它也當然地滲透到今天的舊體詩歌寫作。
當新、舊詩歌寫作的小情調、小情緒、小感傷成為一種“小時髦”的時候,那么問題來了。它雖然感動了自己一陣子,但卻沒有能感動讀者哪怕是一陣子。詩歌還能擔負起凈化人心,改造社會的重要作用嗎?詩人、詩歌沒有了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那么文學的價值何在?而當這種“小我”寫作成為“常態”時,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顯示為一種“病態”。我想這也是《心潮詩詞》給詩歌寫作“療傷”,專題來討論“大我”“小我”的一個時代背景吧。這種討論無疑是切中時弊,很有必要的。
好了,當我們對詩歌創作的社會文化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大我”與“小我”的答案似乎也就蘊含其中了。從藝術創作這一層面說,我無法給出是“大我”重要還是“小我”重要的價值判斷,在我看來他們的寫作都無可厚非,這是詩人的個人選擇、個人特點、性趣使然。揚“劉”抑“曹”,以維護劉氏江山正統地位的《三國演義》好,表現中國封建社會必然走向衰亡的《紅樓夢》也好。
“小我”也好,“大我”也好,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詩人的立場與態度,文字里有沒有民間煙火、天下蒼生、人類關懷。有它“小”亦是“大”,無它“大”亦是“小”。文學創作不是碼幾個社會大詞,唬唬人就可以的。詩歌也不是秀場,詩人都來“秀”一把自以為得意的聰明漂亮文字。切記:文學是對作家靈魂的考驗。
如從生命至上的觀點看,“小我”亦“大我”,可能還是更大的“我”。誰能說一只小鳥、一株小草就不重要呢!沒有了它們,地球還會是地球嗎?人還會是人嗎?天、地、人,鼎足而三,撐起了這個世界。從一定意義上說,“我”,是世界的主體,亦是“美”的主體。是“我”感知了世界,并且參與了多彩世界的建設,人類靈魂的建設。沒有了“我”,萬物即不復存在,天地歸于“無”。
當然這個“我”是要把他人、家國、天下放在心上的“我”。于此,才是寫作的意義,詩人的意義。
沈華維
(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長期以來,詩論家們在討論詩歌的抒情方式時,總會提到“小我”與“大我”這兩個詞。清袁枚性靈說指出:作詩,不可以無我。有人無我是傀儡也。《續詩品》專辟《著我》一品。突出“我”,既是強調詩人特有的秉性、氣質、審美能力等的個性化和獨創性。從詩中有“我”的概念提出后,又生發出有我、無我、小我、大我等命題。詩因“我”而有感生情,進而形成與別人相異的獨特的個性化的感受。詩中的有我與無我、小我與大我,都是詩人抒情言志的一種方式,“志”無輕重,“情”無先后,“我”無大小,他們既屬個人的,又是大眾的,很難截然分得清楚。就詩人所處的“大我”環境而言,詩人是時代的、人民大眾的代言人,詩人的立場、觀點,應站在時代的前列,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訴求。但創作時,仍需充分投入個性,即“小我”情感,不能以公眾化的共性情感,來置換詩人抒情主體地位。自然,將孤立地抒發個人情感和抒人民之情對立起來是不對的。有時候,純粹的個人情感也有時代的烙印,有時代色彩的折光。只強調“小我”或只強調“大我”,都未免偏頗。現代著名詩人艾青曾說過一句很有見地的話:“個人的痛苦和歡樂,必須融合在時代的痛苦和歡樂中,而時代的痛苦和歡樂也必須糅合在個人的痛苦和歡樂中。”實際上,“小我”與“大我”的關系,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就是通過個性來反映共性,是個性與共性的關系。杜甫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不僅抒發了自己的苦難和哀愁,而且大聲疾呼“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代表了天下窮苦百姓的心聲。使自己的感情具有了“大我”的普遍性。
我們以今年的抗疫詩詞為例。庚子年初,當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突發后,廣大詩人詞家弘揚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覺拿起手中的筆,投入這場防控疫情的阻擊戰,謳歌抗疫英雄和感人事跡。其作品數量之多,作者之眾,意想不到。其中許多作品都偏重于“大我”的展示,即大視野、大場面、大胸懷式的展現抗疫局面,宏觀描寫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萬眾一心,馳援湖北,白衣逆行,八方支援的場景。如武漢詩人四維先生《定風波·致敬武漢金銀灘醫院》:“誰料過年如過關?金豬銀鼠陷泥潭。 風展紅旗齊領命,問病,小家在后大家前。封路封城封感染,武漢。仁心妙手著先鞭。橘井靈泉千萬眼,化險。爭來春意亂云邊。”作品以局部觀全局,刻畫了疫情就是命令,各方領命出征,白衣戰士舍生忘死,不顧小家為大家,妙施仁術,化險為夷,終于迎來春意無邊。作品彰顯了詩人的家國情懷,也印證了唐代詩人白居易早在千年前就提出的好詩的主張:“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于言,莫切于聲,莫深于義。”
我們再看一首以“小我”的視角,來抒發抗疫經歷和體驗的作品。武漢詩人泉名先生不幸染疫中招,被隔離治療。當他從方艙醫院出來后,曾經寫下一首《核酸轉陰性作》,向友人們報平安:“東風入幔瑣窗晴,一紙報如天下寧。連日自羞貪食飯,巡床醫囑罷懸瓶。楚江尚禁可憐麗,春癘猶存未覺馨。應許離人皆似我,歸期已近暫伶仃。”詩人以自己特殊的經歷,探究自身心理活動狀態,真實的記錄被封鎖隔離的無奈,飲食治療的過程。在那個唯核酸談“陽”變色、畏之如虎的特殊時刻,病人得知自己核酸檢測轉陰,已脫離險境,重獲平安時,喜悅之情溢于言表。他希望所有人都像自己一樣成為方艙醫院的“離人”,“一紙報如天下寧”,寒冬已過,春意將臨,傳遞出守望命運,共擔苦難的云水襟懷。此詩以鮮明的“小我”之境說明,對平凡的避疫生活的提煉,同樣可以折射出浩蕩的時代潮流。
從以上兩首作品(我暫且把它們歸于一大一小之類)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小我”與“大我”,只是詩中表現情感的一種手段,一種視角方式,本無孰優孰劣,寸有所長,尺有所短,表現好主題,寫出好詩才是目的,才是硬道理。作品中的小與大是相互包容、相互轉化、相輔相成的,二者不是對立的關系。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大中含小,大氣磅礴,這是詩詞的特性,也是詩人的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