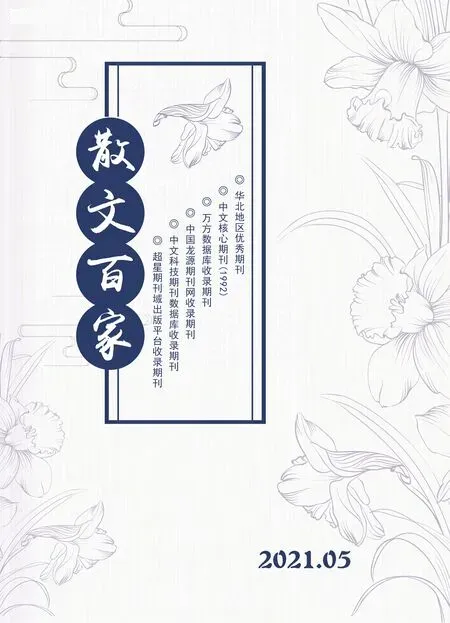概念整合理論對莫言小說中隱喻的認知分析
原 蓉 田興斌
貴州大學外國語學院;銅仁學院國際學院
自從莫言在2012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文學界出現了莫言熱,而學術界中對莫言小說的研究也是層出不窮。喻曉薇于2018 從語言、文體和敘事角度研究莫言小說,分析討論了莫言小說在哪些方面對明清小說進行了繼承和改造,從而形成了莫言特有的新筆記小說文體。此外,王學謙和邵麗坤于2014 研究了莫言小說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內涵。然而,從認知語言學視角下對莫言小說的研究相對較少。但隨著認知語言學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從認知的角度研究莫言小說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特別是莫言小說中存在著多種形式的隱喻。目前大量的認知語言學角度的研究集中于對莫言小說中概念隱喻及隱喻翻譯的研究,如蔣正悅于2019 以《紅高粱》為例從認知角度探討文中紅色隱喻的使用情況,馮全功于2017 以莫言和畢飛宇為例探討了概念隱喻的系統表征及其英譯的的利弊。而鮮少有以概念整合和隱喻理論為理論基礎對莫言小說中隱喻的認知過程和認知機制的研究。為了進一步闡釋莫言小說中的隱喻,本文以隱喻理論和概念整合理論為理論框架,對《紅高粱家族》和《蛙》中隱喻的認知機制和過程進行進一步研究。
一、隱喻理論及概念整合理論的相關概念
傳統隱喻被認為是一種修辭手段,而被納入修辭學范疇。于1980 年Lakoff 和Johnson 在其著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中提出的概念隱喻則標志著認知隱喻理論的問世。書中提出,隱喻不僅是一種修辭手段,而且是一種思維方式和認知手段。換言之,思維的過程本身就是隱喻性的,我們賴以思考和行動的大部分概念系統都是用隱喻性的方式構建和定義的。隱喻被概念化為兩個認知域,即源域和目標域。隱喻是從源域到目標域的系統映射。源域是具體而熟悉的東西,目標域是抽象而陌生的東西。如,通貨膨脹搶走了我們的儲蓄是一個擬人隱喻,包含隱喻通貨膨脹是人,而人是具體的、熟悉的源域,具有攻擊對手、搶奪財務、有智商且可生育的實體,另一方面,通貨膨脹是一個人們無法直觀理解的抽象的目標域,這個例子將人這一概念直接投射到了通貨膨脹這一概念上。莫言的小說中存在著大量的隱喻。隱喻便是莫言在創作小說時的隱喻思維,同時隱喻思維也在幫助讀者更好地解讀莫言小說。
隱喻理論有其不足之處,只能做到源域到目標域的直接投射,即雙域隱射,單向映射,并不能解釋隱喻生成的認知機制。如外科醫生是屠夫,是從源域屠宰業直接投射到了目標域外科手術中,其中包含著屠夫到外科醫生、屠刀到手術刀、牲畜到人、宰割方式到手術以及商品到病人的一系列固定的映射。況且一般來說,屠夫是有技術的且可以勝任自身工作的,雖地位沒有醫生高,但因其技術一流也能獲得社會認可,所以這一系列的跨域隱射并不能夠分析得出這個外科醫生是不勝任的意義。直到1994 年,由Fauconnier 和Turner 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論是一種比概念隱喻更大、更普遍的概念投射,被稱為多空間模型,可用于分析隱喻的認知機制。概念一體化網絡處于概念整合理論的中心位置,涉及輸入空間1 和2,類屬空間和合成空間等四個心理空間。一個整合空間至少由有兩個輸入空間組成,兩個輸入空間中的各個要素通過投射聯系在一起,在整合網絡發展過程中輸入空間中所共有的東西將被投射到類屬空間中,同時兩個輸入空間的部分要素有選擇性地投射到合成空間,并得出在某個輸入空間中原本并不存在的關系。在上述例子中,輸入空間1 包括的要素有屠夫、屠刀、牲畜、宰割方式和商品,形成屠夫用屠刀宰殺牲畜的框架,輸入空間2 包括外科醫生、手術刀、人、手術和病人等要素,形成外科醫生使用手術刀為病人手術的框架,兩個輸入空間發生跨域映射,在類屬空間中形成X1 用什么方式施刀于X2 的框架,形成外科醫生手法細膩地拯救生命,而屠夫兇殘地屠宰生命,兩個目的手段相沖突的兩件事。隨后選擇性投射到合成空間,得出醫生運用屠宰的方式給病人手術的結構,繼而得出外科醫生拙劣、不能勝任的意義。由此,利用概念整合理論就可以解釋清楚隱喻生成的認知機制和隱喻意義具體的產生過程。
二、概念整合網絡下莫言小說中的概念隱喻
1.從認知角度解讀結構隱喻。
結構隱喻指的是用一種概念的結構來建構另一個概念的結構,使用一種概念的詞匯來描述另一種概念,如人生是一次艱難的旅程這一結構隱喻中,憑借人生和旅程兩個概念之間的相似性,將源域旅程的要素映射到目標域人生中,旅程的概念結構用于描述人生這一概念。但是簡單的雙域映射得不出人生是艱難曲折的這樣的意義,還需要進行概念整合。輸入空間1 包括的要素有起止點、旅程時長、沿途的風景、經歷等,形成旅行者艱難地跋山涉水終到終點的框架,輸入空間2 包括出死、壽命的長短、生活閱歷等要素,形成人經歷困難和挫折直至死亡的框架。然后,兩個輸入空間發生跨域映射,在類屬空間中形成X1 以什么方式到達某地的框架。下一步兩個輸入空間的要素選擇性地投射到合成空間中,產生人生就像是旅程一樣要跋山涉水、歷經險途,才能到達終點的意義,得出人生是艱難曲折的。
(1)計劃生育是戰爭。例如在《蛙》中,“就是這樣,她還帶著人前來搜捕王膽和王膽也被抓捕歸案”。這兩個例子均是以搜捕、抓捕歸案這樣的描寫戰爭的詞來描述姑姑的計劃生育工作,產生結構隱喻計劃生育是戰爭。結合結構隱喻對計劃生育和戰爭兩個概念進行整合。其中,輸入空間1 戰爭是殘酷的、血腥的、殘暴的,輸入空間2 計劃生育工作是緊鑼密鼓進行的、強制性的,類屬空間是一個抽象的結構,戰爭和計劃生育工作的共性結構有選擇性地進入其中,隨后兩個輸入空間中的全部要素有選擇地投射到合成空間中,得出新的概念,即計劃生育工作是殘酷的、血腥的、粗暴的,讓讀者更加明白當時在計劃生育工作上,政府抓捕四處躲藏的懷孕婦女,而人民甚至挖地道保護這些婦女,政府和民眾之間存在著極大的矛盾。
(2)人是蛙。例如在《蛙》中,“常言道蛙聲如鼓,但姑姑說,那天晚上的蛙聲如哭,仿佛是成千上萬的初生嬰兒在哭。姑姑說她原本是最愛聽初生兒哭聲的,對于一個婦產科醫生來說,初生嬰兒的哭聲是世上最動聽的音樂啊!可那天晚上的蛙叫聲里,有一種怨恨,一種委屈,仿佛是無數受了傷害的嬰兒的精靈在發出控訴。”例子中用蛙聲(動物)隱喻嬰兒聲(人),通過仔細閱讀可以確定這里的蛙聲和嬰兒聲都不是字面的意思,二者都包含各自的組織結構。首先輸入空間1 是蛙聲,而輸入空間2 是嬰兒聲。蛙聲像鼓聲和雷聲一樣響亮,是普通的聲音,但是作者賦予了它更多的意義,即仇恨和怨恨,幫助讀者跳出橫向思維,構成了蛙聲的組織結構。輸入空間2 是嬰兒聲與輸入空間1 中如鼓的蛙聲相呼應。很顯然,蛙聲和嬰兒聲的組織結構并不相同但是二者又有一定的聯系,是兩個組織結構。第二步是將概念整合理論應用到句子中的合成階段。最后在合成空間中,我們可以得出:嬰兒哭聲如蛙聲一樣充滿怨恨和憎恨。在莫言小說中,青蛙聲音的不滿指的是育齡期男女對高壓政策下被迫流產的不滿。這些孩子應該得到尊重和正確對待。他們希望自己能夠活下來,但在出生前便已被殘酷地殺死。這些本來能存活下來卻被高壓政策剝奪了生存希望的孩子們發出了仇恨的哭喊聲,他們的父母亦是如此。
2.從認知角度解讀本體隱喻。
本體隱喻是將抽象的概念映射到與我們經驗有關的物質實體上,也就是將抽象模糊的思想和心理情感狀態轉化為有形的實體。如《蛙》中寫道:“這棵樹連著我家的命脈,這棵樹旺,我家的日子就旺。”用樹的成長映射我家的生活、日子這樣抽象的概念。一棵樹起初只是一株只有主干的小苗,隨著大自然的養護逐漸生長出多個枝干,再在這些枝干之上生長出諸多更加細小的枝葉,到這時原本細弱的小樹成長為茁壯繁茂的大樹。樹的部分形象特征與家庭特征的相似性都是呈網狀向上生長,但是隱喻并沒有成功解讀出我家的生活、日子蒸蒸日上、越來越好的特征。為進一步獲得語句意義就需要概念整合。輸入空間1 中為樹的結構特征、形象特點,提供合成空間的要素,而輸入空間2為我家的生活、日子,同時也提供合成空間的結構,類屬空間中所包含著輸入空間1 和2 共有的抽象特點,如主體、主體成長的過程以及結果。最后,在合成空間中誕生了新的語義概念,即我家的日子如樹一樣枝繁葉茂、蒸蒸日上的形象。
林語堂的譯創作品深受當時美國人的青睞,在翻譯成多國文字之后,還受到了世界各國的歡迎。亞馬遜書店的統計結果表明,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啼笑皆非》《吾國吾民》《美國的智慧》等作品于2008年11月得以再版,可見其譯創作品有著持久的生命力(馮志強2011:180)。如同林語堂的好友喬志高所說,林語堂的成功不僅僅依靠著文字的精湛,還基于他對祖國文化的熱愛以及獨到的見解。對于世界各國的讀者,林語堂都以平易近人的、溫和的筆觸進行“交流”。這也是林語堂的譯創作能夠品遠近流傳的重要原因(馮志強2011:194)。
3.從認知角度解讀空間隱喻。
空間隱喻指的是人們借助自己的方位概念來認識一些抽象事物,即運用上下、前后、遠近、內外等表達空間的概念來構建隱喻的概念系統。在《紅高粱家族》中,莫言寫道:“從八月底開始,秋雨綿綿,高粱地里黑土成泥,被雨水漚爛了的高粱秸有一半倒在地上…高粱穗子像蓬松的狐貍尾巴一樣高揚著,或是低垂著…”例子中用高粱的生長狀態,如倒在地上、一起發芽、新綠、高揚著、低垂著等,來隱喻高密鄉中爺爺及其部隊戰士的命運,即被壓垮、又重拾信心、繼而站起來、繼續戰斗,高粱和高密鄉的人民都包含著各自的組織結構和要素。首先輸入空間1 是高粱,而輸入空間2 是高密鄉爺爺部隊的戰士。高粱在經受綿綿秋雨之后倒在了地上,空間方位為下,但之后又扎根發芽、長出新綠、高揚地活了下去,此時空間方位為上,構成了高粱的組織結構和要素。輸入空間2 是高密鄉爺爺部隊的戰士與輸入空間1 中的高粱相對應。很顯然,高密鄉爺爺部隊的戰士和高粱的組織結構及其要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二者又有一定的聯系。第二步仍然是將概念整合理論應用到句子中的合成階段。最后,在合成空間中,我們可以得出:高密鄉爺爺部隊中的戰士就像高粱一樣經受風雨之后雖然倒下了,但是很快便又重新站了起來,繼續戰斗,體現了高密鄉人民遭受戰爭卻意志堅定、越挫越勇的精神。
三、結語
很長時間以來,隱喻一直被認為是一種修辭手段,而不是一種思維或認知的方式和手段,直到1980 年,Lakoff和Johnson 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中提出了概念隱喻。但是隱喻有其不足之處,它只能呈現出源域和目標域之間單一的映射關系,卻并不能解讀出隱喻生成背后的認知機制,而在心理空間理論和概念隱喻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概念整合理論能指導我們更詳細地分析隱喻意義建構的認知過程,開拓了隱喻研究的新視角。本文基于概念整合理論和隱喻理論對莫言小說中的隱喻進行了細致分析,有助于人們深入理解和使用本土文化中的變化言語隱喻,從而提升語言交際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