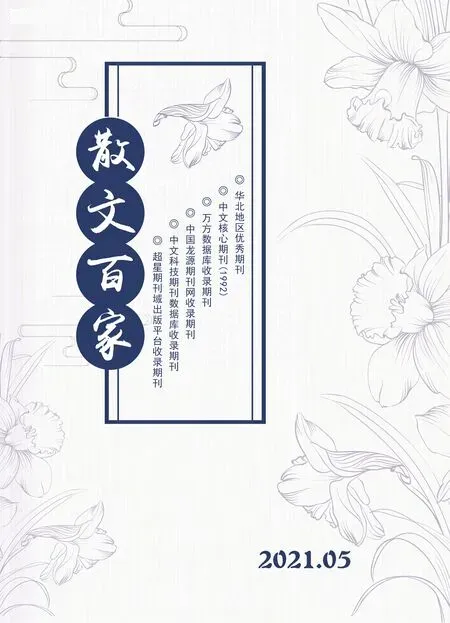《花木蘭》—中國傳統女性英雄形象的當代英雄主義書寫
代云芮
黑龍江大學文學院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木蘭的勇敢愛國的巾幗女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正因如此,木蘭成為第一個被搬上熒幕的中國迪士尼公主,但由于對中國文化的詮釋融入了西方對東方的想象和西式的審美和價值觀,從而導致真人版《花木蘭》從文化符號的還原人物形象的塑造被中國觀眾所詬病。
一、“氣”—文化符號的錯位
《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莊子·知北游》中也提到:“人之生,氣之為聚也。聚之則生,散之則死。”可見,春秋時期“氣”被認為是神秘的、難以捉摸的宇宙的組成部分。與老子大約同時代的子產說:“人生始化為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左傳·昭公七年》)杜預注曰:“魄,形也”“陽,神也。”故“營魄”乃 “神”與“形”,一陰一陽,這是春秋時期人們對人體構造的理解。也是“陰陽二氣和合”的穩定狀態。可以看到,先秦諸子認為“氣”是每個人維持生命體征的關鍵,而不是影片《花木蘭》中的天賦異稟和成為巫婆的必要條件。李澤厚認為中國古代文化有由“巫”到“史”的艱難過程,這也是老子思想轉變的過程。因此,巫與“氣”雖說同氣連枝,但卻不可混合而談。
西方世界的巫文化起源于古希臘神話,女神赫卡忒精通藥理和巫術,不僅在古希臘時期被稱為女神,在羅馬時期也被尊稱為“白巫醫”。人們畏懼“巫”背后的強大力量,但心中仍然保有一份尊敬。直到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斗爭逐漸加劇,發展到人人自危的地步時,尋找替罪羊成為了必要手段;另一方面,許多巫醫都是年老色衰者,正是國家和社會企圖甩掉的經濟負擔。在一定程度上講,獵巫運動成為了具有政治導向性的性別屠殺。女巫的文學形象也從性感又危險的女神變成了擁有黑暗魔法的女魔鬼。到了17-19 世紀,啟蒙運動的開展和理性主義的發展使得人們的獵巫熱情逐漸冷卻,女巫的文學形象也有所轉化,具有代表性的是浪漫主義詩人濟慈,在1820年寫了名為《無情的美人》的“女巫與騎士”的柏拉圖之戀。此后,女巫成為自然、野性和美的同義詞。
在影片《花木蘭》中鞏俐飾演的女巫仍然是西方中世紀時期人人喊打的女巫,她試圖憑借自己的魔法為柔然集團服務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來實現自身的價值。將這種西方古老的女巫形象與中國的“氣”進行嫁接而創造出的女巫形象仍然是西方對遙遠東方的古老幻想。
二、木蘭—人物形象內核的西化
巾幗女英雄是木蘭這一形象在中國的核心內涵,而在迪士尼出品的真人版影片《花木蘭》中木蘭這一形象因沾染了西方個人主義與英雄主義的傳奇色彩而變成了超級女英雄。中華文明是以黃河為中心發展起來的,以土地為依托、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農耕文明,并逐漸形成了以家國情懷為底色的尋求安穩并注重人際關系的思想觀念。與此相對的是西方的海洋文明。由于陸地面積狹小不利于耕作,出海擴張土地也成為一種榮耀。面對狂暴又深邃的海洋,個人的膽識和英雄氣概就顯得尤為重要。這種地理環境的不同造就了中西方兩種文明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屬性。
歐洲人乘坐著五月花號飄洋過海來到北美這片荒蕪的土地后,更加注重個人理想的實現,也更加意識到個人奮斗的重要性。他們期待以勤勞的雙手創造一片屬于自己的繁榮之地。自華盛頓·歐文開始,文學作品不斷地對“美國夢”進行書寫,一方面激勵那些渴望成功卻遭遇困難的人,另一方面以文化手段在國際間對美國的國家形象進行塑造。真人版《花木蘭》中花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其實質已經轉變為中國古代的“美國夢”,木蘭這一形象的內核也已轉變為憑借一己之力實現階層跨越并改寫歷史的個人主義英雄。
木蘭形象原本是具有深厚的家國情懷的,承擔的是家族的使命,彰顯的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而在影片《花木蘭》中,木蘭雖然也是因為不忍年邁的父親重返戰場受苦而替父從軍,但是從進入軍營正式訓練后到與柔然大戰再到最后孤身一人拯救軍隊和皇帝這整個過程中,木蘭展現給觀眾的更多的是她個人的天賦異稟和英姿颯爽的超級女英雄形象。從古希臘神話與《荷馬史詩》中流傳下來的個人英雄主義敘事傳統是西方民族鐫刻在骨髓中的基因和血脈,以拓荒精神為底色的美國夢是美國民族文學的傳統,再加上美國好萊塢式的現代化的特效制作,呈現出了以中國歷史為外殼,以西方價值觀為內核的中國故事。
三、結語
木蘭這一形象所體現的中國的文化符號的錯位以及人物形象內核的西化無不體現著這種對異域文化的誤讀,這必然造成電影票房的滑坡以及中國觀眾的不滿,這啟示我們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要想準確地走出國門,在全球范圍內獲得關注與影響,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