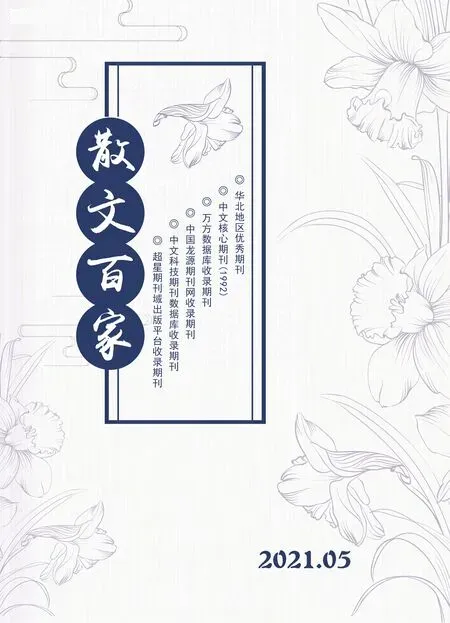兩晉時期的合肥文化論析
朱夏初
安徽大學
第一章 兩晉時期合肥政局
西晉統一后,南北劃江對峙局面結束,合肥地區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行政建置,相應發生變化。此時的合肥地區分屬淮南郡和廬江郡,郡治又轉移到壽春,合肥的行政地位也隨之江隔為縣級行政中心。城市的軍事職能發生轉化以后,繼續區域經濟都會的發展軌道。晉惠帝后期朝廷發生動亂動蕩,“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官員陳敏建議:“南方米谷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于是,“朝廷從之,以敏為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合肥地區的農業生產恢復之后陳敏為“合肥度支”向洛陽運送糧草。西晉的后期社會動蕩不斷,百姓也流離失所。
東晉立國,合肥又成為南北對峙的前沿,不時卷入動蕩之中。合肥又一次成為戰場,東晉失去了對合肥的控制;后東晉又與前燕前秦交鋒,合肥作為后方,為前線戰斗提供支持。西晉永嘉亂后,當時當時的南方交通便利,生產資料充足,人口紛紛往南方轉移。當時出行遠路,水路最為方便,安徽境內“淮域諸支流皆東南向,故河南人大都東南遷安徽,不由正南移湖北也。”因此成為交通要道。同時壽春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淮南地區也有很多耕田,史云:“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修,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而自漢代起,合肥就有大量南北物品交換的痕跡,“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因此合肥成為吸引光大流民的主要安居之地,“南渡人戶中以僑在江蘇者為最多,約二十六萬;山東約二十一萬,安徽約十七萬,次之”。這樣也極大的推動了各種文化在合肥的交流發展。
而此一時期的合肥有三次易手,宋齊內亂北魏占據了合肥;梁魏爭戰、合肥再度歸北;先后歸南朝梁。之后南陳與北齊、北周在合肥爭戰。可見合肥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歷史上地理位置重要,區位對于合肥的文化發展影響重大。
第二章 兩晉時期合肥經濟商業發展
1.經濟商業手工業發展情況。
合肥地區的手工業商業在此時期由于社會觀念和流民的遷徙帶來了很大的發展。雖相較之前的時期社會動亂厲害,發展時間不長。但也有自己的特色。東漢以后,隨著傳統儒家義利觀受到現實的沖擊,貶低經商的觀念改變,民眾更從自身出發努力發展經濟改善生活條件。孫休在詔令中說:“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
手工業方面也有一些恢復發展。冶鐵業,冶金業,從民間工匠到軍中生產。更規范程序化。此一時期合肥地區還有出土了大量的銅器,有銅鏡、銅五銖錢、錢紋銅缽、銅洗、銅熨斗、西晉銅行燈。說明西晉時期銅器生產已是主要生活用品。同時還有瓷器外省如越窯等生產的瓷器在安徽廣泛流通。
南北朝時期各地的商業,總的呈現出興盛蓬勃的趨勢。據考證市場經濟體系有初見端形。蕭梁時的沈約說:“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于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文犀,飛不待翼。”《隋書·食貨志》說,東晉南朝時,“人競商販,不為田業”。經濟的發展會推動文化的發展。
第三章 宗教發展情況
1.佛教的傳播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如前朝對思想的禁錮。佛教在安徽地區傳播加快。合肥地區特有何氏家族對于佛教傳播的貢獻作用。史傳嘗言:廬江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并建立塔寺。何尚之向宋文帝說明“神道助教”闡發佛教的贊治功能,指明了佛教的傳播不是削弱帝王統治,而恰是封建政治的傅翼。于是佛教在西晉漸次流行,至南朝時期形成了所謂“北造像,南造寺”的局面,廬江何氏家族是兩晉南朝時期安徽境內少有的名門望族,也是當時著名的佞佛世家,得到了宋文帝褒揚。《弘明集》說,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當然這一時期的推廣也為后世佛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宋代佛法,元嘉時有較大發展,于此看來,這顯然與何尚之積極促成是有聯系的。
2.道教的傳播發展。
同一時期的道教也在合肥地區有著廣泛的發展。因為源于古代鬼神崇拜、民間巫術,道家的神仙方術和黃老道家思想一直在民間流傳。再加上合肥地區名山勝水,風景秀麗,為道教的傳播提供了溫良土壤。在巢湖地區就有建很多道觀,湖心還有座姥山島,魏晉以前就已經有不少神仙傳說。
第四章 民俗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發展
這個時期,戰亂連綿不止,朝代更替頻繁,合肥地區大部分處于戰亂狀態,但是社會動蕩給各種思潮的滋生與傳播提供了土壤。
由于社會動亂,官學受到沖擊,但更需要人才,官學雖然艱難但很多學者開始創辦私學,特別是廬江的何氏子弟共同推動著這一時期的私學發展。推動著合肥的教育發展。而當時的合肥文化:一處在南北文化交鋒、交流的前沿;另一處成為江淮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曹操將揚州刺史治由壽春移到合肥,有其戰略考慮。合肥也因此成為江淮之間的交流中心,對于合肥而言也是史無前例的。最后一處產生了一批文化教育科技成果和人才。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作為官學的主要思想,統治地位未有間斷,但也受到了挑戰。同時在玄、佛、道的共同影響下有了一些新的發展。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是玄學的興起,雖缺乏資料考證具體對于合肥地區的影響,但由廬江何氏的研究來看,他們有注《莊子·消搖篇》。
這一時期的合肥的社會風氣是尚武輕文,與長期的戰爭動亂影響是分不開的。《宋書》說“淮南楚子,天下精兵”,比喻合肥地區能打勝仗,好武起義也多,更多意氣用事。可看出魏晉南北朝長期的戰亂給合肥地區帶來的戰爭傷害。
第五章 結語
總得來說,合肥地區在兩晉時期,受到戰亂爭據的影響。社會動蕩不安,人們流離,好在有天生的地域優勢,物資豐富。吸引大量外省流民在合肥地區定居,加強了商業,手工業的發展。也加強了文化也風俗的融合。這一時期的合肥文化更多是融合包容。在保留自身存續性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社會經濟由于商業的發展,和官學漸微,思想也逐漸動蕩。
注釋:
[1]《晉書·陳敏傳》合肥和平的發展了一段時期。但是不就之后到東晉十六國時期,合肥又開始戰爭頻發、動蕩不安。合肥的農業、手工業、商業等經濟領域處在不斷遭到破壞和試圖恢復的情況下,經濟難以得到發展。
[2]譚其驤:《晉永嘉喪亂后之民族遷徙》,長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31 頁。
[3]《南齊書·徐孝嗣傳》。
[4]《史記·貨殖列傳》。
[5]譚其驤:《晉永嘉喪亂后之民族遷徙》,《長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220 頁。
[6]《三國志·孫休傳》。
[7]《宋書·傳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