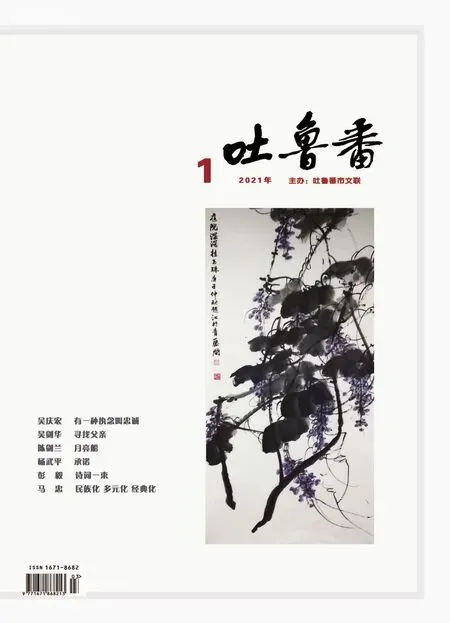有一種執念叫忠誠
吳慶宏
在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有一座舉世聞名的火焰山。火焰山不高,卻能俯瞰山腳下葡萄掩映的大片綠洲。在綠洲深處,遍布著170多個大大小小的村莊。在這些村莊里又有無數個身份特殊但又極為普通的老人,常常被村民稱之為“老黨員”。他們扎根基層從艱苦創業到發展巨變,在這片熱土中默默耕耘半個多世紀,然后一個個慢慢老去,直到悄無聲息地離開這個世界。或許時間久了,就不會有人知道他們是否存在過,但他們始終為了心中的那份執念,用自己平凡的一生詮釋著一種忠誠。這里我謹向讀者講述幾位古稀老人的故事,就是為了從他們身上找尋精神的力量。
1
距火焰山最近的村莊有一個叫做勝金口,曾經是《西游記》中唐僧師徒取經路過火焰山時晾曬經書的地方。這里很少刮風,一年只刮一次,一次刮一個月。每年的大風季節主要集中在三、四月間。這個時候也正是當地的農民投身于葡萄開墩,進行春耕生產的大忙季節。2014年的這個季節,我作為第一批“訪惠聚”駐村工作隊隊長,就穿過火焰山勝金口,住進了勝金鄉勝金村。
由于住村的前一天晚上剛刮過一場大風,整個天空還是灰蒙蒙的,空氣中彌漫的浮塵還有些嗆人。那天一大早,當我走進村委會大院門口時,差點與一位低著頭準備出院門的老者撞個滿懷。老人個子不高,弓著精瘦的身材,或許因為天氣原因不停地咳喘著。我趕忙攙扶著他說:“老人家,慢著點,您這是有什么急事么?”“咳咳咳……”,老人邊咳嗽邊向我搖搖頭擺了擺手,急匆匆地走了。我望著老人漸漸遠去的背影,心想,他一定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今天第一次來村里就和他偶遇,應該是一種緣分吧。此后在住村一年多的時間里,我幾乎是一有空就會看望這位老人。
這位老人名叫王昌喜。那一年他83歲。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支邊進疆后,再沒有離開過吐魯番。
老人雖然耳朵有點背,但身體還算硬朗,思路也很清晰。說起現在的幸福生活,他那瘦削的被一道道深深淺淺的皺紋包裹的臉上即刻綻開了笑容。他說:“改革開放以來,咱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黨和政府不但為農村、農民出臺了許多優惠政策,而且從合作醫療、農民享受低保、養老等方面給予了高度的關懷,這是我們過去想都不敢想的啊。”說著,他還從家中拿出了《回鄉務農抗戰老戰士和在鄉復員軍人定期定量補助金標準明白卡》和《優撫對象醫療證》,來證明自己所說的事實。這“一卡一證”,既清楚地告知了補助金發放的各類標準,又表明了老人的身份經歷。說起老人過去的經歷,老人還記憶猶新。他說,我是1953年6月參加抗美援朝志愿軍的。1958年復員回家鄉,鄉領導本來讓咱留下來,但看到家鄉的其他許多年輕人都紛紛報名要去遙遠的新疆支邊,咱也不甘落后,主動報名要求到新疆去。沒想到來這一待就是50多年。
說起村里的水和地,原本被村里人漸漸淡忘的王昌喜老人又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勝金村一組曾針對本村組原來的機井干枯,用水緊張問題,通過召開村民大會“一事一議”,經村民表決后一致同意重新打一口機井。但由于部分村民拿不出錢來,打井的事就放下了。后來有個別村民反映本組村民老黨員王昌喜占用了集體的9畝澇壩地,打井的錢應當王昌喜承擔。實際上,王昌喜來勝金村時全家4口人,共有10余畝土地,1964年王昌喜被鄉政府派往附近的鄉辦水電站任站長期間,該村將王昌喜的十幾畝地改為棉花試驗田,不久又將土地分給其他4人改種葡萄。王昌喜從水電站退休回村后,希望村委會返還本屬于自己的地,但鑒于他的地已經被別人種植,于是原村民小組長經請示鄉里同意又將集體的澇壩地劃給了王昌喜,但說明此地比他原來的地少2畝,王昌喜認為自己是老黨員,應當從大局出發,少就少點吧沒啥。此事大家也都默認了,也沒有發生任何糾紛。但如今,牽涉到要打井出資,村民認為王昌喜現在占用集體土地應當交出承包費,或是將土地退還集體,由集體出賣轉讓后籌資解決打井資金緊張問題。還有人出主意讓老人自己追回原來的地,老王說:“咱是老黨員,影響民族團結的話我不能說,有損民族團結的事我更不能做。”后來,考慮王昌喜原來被其他村民占用的土地無法追回,故最后的結果是:無論如何王昌喜至少要出3000元錢用于打井。原來,我來村第一天之所以能和王昌喜遇上,正是因為他那天到村委會商量打井的事出來。3000元錢,對一個在農村辛苦一輩子的老人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是老人一句怨言也沒有說,第二天就叫女婿將四處籌借的3000元現金送到了村委會。老人說:“不說別的,就是看在這么多年黨和政府的關心、關懷和勝金村民族團結大家庭的情分上,作為一名老黨員,為了村集體和大家的利益,這個錢咱出的心甘情愿。”
其實,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老人對自己的老伴十年前因患病而半身不遂,每年要花費大量醫療費的事兒卻只字未提。對此,我們問起老人還有什么要求時,老人卻連搖頭帶擺手說:“前些年,市里的領導來慰問時,提出為老伴辦個低保,我拒絕了。現在生活比過去好了幾百倍,政府不但每月給我發補助金,而且上級領導還經常來看望,我們感激不盡啊,哪里還有什么其它要求呢。”
2
重回三年前的秋天,在葡萄鎮英薩村,陽光格外溫暖,一排排整齊的晾房里,掛滿正在晾制的葡萄干。當時,我正在這個村入戶走訪,在一條巷子的盡頭,老遠就看到一位拄著拐杖的老人一邊緩緩移步,一邊向我們打招呼。于是我好奇地向旁邊的村干部打聽這位老人的情況:“他是你們這里的五保戶嗎?”“不,他是村里的老黨員白本云,今年84了。”
在我的印象里,每到村里看見他,他總是坐在家門口曬太陽,一身標準的藏藍色中山裝,一支拄得像鍍了一層蠟的榆木手杖放在身旁,指尖還夾著他最愛的“嗩吶形”手工卷煙。他以濃重的河北口音,跟我打著招呼。無人時,他便哼著自己最愛的那首朝鮮民歌:“桔梗喲、桔梗喲、桔梗喲、桔梗,白白的桔梗喲,長滿山野……哎嘿喲,這多么美麗、多么可愛喲……”或許誰也不會想到,這個貌不驚人又慈祥樸素的老人,同樣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在隨后的入戶走訪中,我從他口中斷斷續續地了解到了他參加抗美援朝的那段故事。
那是1953年除夕前一天,19歲的白本云離開河北張家口,隨著大部隊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戰場。軍列“哐吃哐吃”像只巨大的穿山甲在朝鮮的大地上掘進。車廂里都是像他一樣的年輕戰士,背上背著清一色二戰時蘇聯用的莫西干步槍,大家像新媳婦一樣,低著頭,一聲不吭。駐扎下來后,白本云分配在后勤排,每天負責戰壕挖掘、裝卸物資和后勤補給。每次后勤任務分配下來,白本云就頭一個沖上去。他悟出一個道理:戰壕挖得深了,戰士就能少流血;物資送得快了,戰士就能少挨餓;武器彈藥給得及時,就能多消滅一些敵人……
全面反擊開始后,敵人近似瘋狂的反撲。一天,白本云所在的排正在清理補給線上的三角釘,突然,一顆炸彈在離白本云不到10余米的小岡上炸開一朵巨大的碎石花,白本云身負重傷,隨即同傷兵和部分當地群眾一起轉移。入夜后,他們在一座山體的空洞里休整,但腳沒落定,又遇到掃蕩,槍聲很近很緊,如果隊伍整體再轉移容易暴露,但如果反抗,僅靠醫護排和傷兵,勝算幾乎為零。轉移的隊伍陷入兩難境地,就在這時,一個朝鮮婦女為了掩護所有人,讓自己的兒子背上槍,穿上志愿軍的服裝沖出了防空洞,邊跑邊放槍,把敵人引開了……
白本云身體恢復后,戰爭已經結束,他繼續隨部隊留守朝鮮,每天除了幫助當地群眾修建被摧毀的房舍,便去山溝里搜集廢棄的裝甲車、汽車、槍、炮架等物品,然后想辦法把他們“變廢為寶”。借此,白本云慢慢掌握了一些機修技術。后來,白本云隨軍離朝,踏上回國的列車,列車一路向北駛向久別的國界,突然有人輕聲唱起了《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整個車廂里的戰士都跟著唱了起來,唱著唱著大家都哭了,“他們的生命已經不僅僅屬于自己,還屬于那些犧牲的人,在以后的人生里,我們不僅要為自己活,還要為那些犧牲的人而活。”直到現在,回想起那些留在朝鮮戰場上的戰友,白本云都會禁不住老淚縱橫。
回到家鄉后,白本云時刻牢記自己是祖國的一個兵。1967年,他積極響應“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號召,離開河北老家,來到了大西北,在吐魯番扎下了根。起初,白本云被分配到農場,雖是退伍軍人,但他個子小,身形瘦,外加沉默少言,每天只是干些拾柴、割草、喂馬的力氣活。但白本云干起這些活來卻非常認真,拾柴他拾得最多,割草他割得最多,就連他喂的馬在全公社都是出了名的好。
1968年,鄰近農場的英薩村從公社分下了一臺柴油機,縣上派來的技術員當天只教會村里的專干怎么使用后便走了。沒過幾天,柴油機出小毛病,專干會使不會修,干瞪眼。白本云聽說后,主動請纓去修理。那天英薩村的人都見證了一個奇跡,又瘦又小的白本云只是看了看柴油機,拔了機殼,拆了大件,在公社買了軸瓦回來裝上,柴油機又似烈虎一樣咆哮開了。村里人如獲至寶,殺雞宰羊款待白本云。為了能讓白本云留在村里,聯名寫信把白本云從農場請到了英薩村。
1969年,公社里的每個隊基本都配了柴油機,擅長機械維修的白本云出了名,縣上水管站聽說了,想調白本云進城。那個年代進城就等于有了“鐵飯碗”。可白本云卻婉言拒絕了,他仍固執地待在村里將機修技術教給別人。別人給他糧票做酬謝,他一概不要。他說,誰家都不容易,拿了別人的糧票,別人咋吃飯?后來,白本云教會了很多人,自己卻“失業”了。
主動“失業”的白本云,又撿起了掏挖坎兒井的苦活干起來。坎兒井是村里生產生活用水的命脈,人畜用水和莊稼用水都靠坎兒井,然而,每年因為坎兒井水在暗渠里的蒸發,會導致部分豎渠的拱壁出現塌方,水流減少或斷流,這樣就得有人下到坎兒井底去疏通渠道。在老一輩人眼里,掏撈坎兒井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兒,是“勇敢者的游戲”。坎兒井由暗渠和豎井組成,一條坎兒井有許多豎井,最深的豎井能達到八十米深,在那個沒有機械的年代,掏撈坎兒井的人只能帶著一盞馬燈和刨器、鐵锨、籃筐等一些工具下到豎井,在又陰又黑又濕又冷的環境里作業,還要防止豎井不會二次塌方把人埋在里面,所以在村里掏撈坎兒井沒膽量、沒技術根本別想干這活兒,每次坎兒井的掏撈都是從死門回到生門、從生門走向死門的過程。1971年春天,英薩村發生了一次最大的坎兒井塌方事件。春灌迫在眉睫,井水卻斷流了。按照以往經驗,疏通上下游,只能一個人下到井底,爬過狹窄的橫井,到達塌方區,鑿通塌方區。但塌方區一旦被鑿開,積水無疑會像泄洪一樣沖出來,在狹窄的空間里,面對洪流,下去的人生還率很低。這種事村里人都避之不及,白本云卻又一次主動請纓。他讓井上的人用麻繩綁住他的一條腿,自己帶著刨器,交代井上的人,只要他一鑿通,扽一下繩子,就把他往出拉……
如今,坎兒井水涓涓流淌,白本云的身上卻因數年掏井留下了幾十處大大小小的疤痕。這就是白本云,從不談過去,只知埋頭干。“俺是黨和祖國培養出來的革命戰士,啥時候都要干最苦最累最難的活,只有這樣才能報答黨和祖國對俺的養育之恩。”
3
在吐魯番葡萄鎮巴格日村(社區),有一條書香路,呈“L”型分布著面積400多平方米的“努爾丁書屋”、“努爾丁書畫室”和“努爾丁紅色記憶收藏館”。
10月初的一個早晨,走進巴格日社區書香路,幾棵桑樹在一排排民房間格外顯眼,樹上懸掛著一條條民族團結的標語,樹下是環繞式的木椅。與共和國同齡的努爾丁,此刻正坐在木椅上看書。就在一周前的9月27日,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努爾丁被評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個人”,與其他34個集體和42名受表彰的個人組成“新疆代表團”,應邀參加了此次大會。6天的“國慶之旅”讓70歲的努爾丁難以忘記。他說,這一次出行,所到之處,都是驚喜;所見所聞,都終生難忘。
“獲得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個人稱號,既是黨和國家給予我的崇高榮譽,也是極大的鞭策和鼓勵。今后我要繼續發揮余熱,履行好共產黨員的義務,引導各族群眾自覺維護民族團結,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民族團結,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建美好家園。”努爾丁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
“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在黨的關心關懷下,努爾丁從一個普通的農家子弟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一直以來,努爾丁秉持民族團結這條生命線,始終如一地維護民族團結。他說:“是黨給了我們幸福的生活。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是我一生的追求。”
1969年3月,18歲的努爾丁報名參軍,從一個煤礦工人光榮地成為人民解放軍戰士,駐守在帕米爾高原。當兵第一年,因語言交流不便,努爾丁在班里很少說話。戰友們發現后,主動找他聊天,幫他練習國家通用語言,還教他識漢字。在大家的熱情幫助下,努爾丁逐漸融入了這個大家庭。當兵的5年,他和來自五湖四海的戰友一起訓練、學習、巡邏,結下了深厚的戰友情。這段記憶一直留存在他的心底。1971年,努爾丁加入中國共產黨。
“五年的軍旅生涯讓我明白,只有各民族團結在一起才能更好地保家衛國。”翻看著泛白的戰友的老照片,努爾丁深有感觸。
努爾丁退伍后,通過自學,考入新疆大學中文系。畢業后被分配到吐魯番地區師范學校教書;1982年,調入吐魯番地區黨史辦工作。這些年來,努爾丁一以貫之地堅守著民族團結這條早已扎根身心的“生命線”。他說:“我從一個普通的農家子弟成長為一名黨員干部,離不開黨的培養和教育,離不開各族兄弟姐妹一直以來對我的幫助和支持。”
1997年10月,努爾丁退休后,用十幾年收集、購買的近2萬冊書籍在自家小院辦起了書屋。他希望通過開辦農家書屋,建設一個宣傳民族團結的基層陣地,讓基層的老百姓能夠有個讀書看報的地方。后來,在市、區宣傳文化部門和葡萄鎮的幫助下,“努爾丁書屋”和“努爾丁紅色記憶收藏館”相繼建成。
從那時起“努爾丁書屋”成了社區居民的好去處。“努爾丁書屋”共有種植養殖、經濟、歷史、政治、科技等書籍6.8萬余冊。書屋不僅是學習知識的場所,還是民族團結教育的陣地。農閑時節,大家圍坐在一起,伴著一本書、一壺茶,度過閱讀的時光。在這里,有的居民通過書籍了解了國家的發展變化、新疆的發展歷程;有的村民掌握了最新的農業信息、葡萄種植技術……一年四季,這個小院總是很熱鬧。
如今,他做到了,他用自己的生動實踐,唱響了新時代民族團結贊歌。“努爾丁紅色記憶收藏館”已經成為了民族團結教育的主陣地。努爾丁也成了葡萄鎮無人不知的“名人”。
2016年,“努爾丁書屋”被命名為“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基地”。努爾丁說:“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我收藏的藏品和書籍,引導大家更加熱愛偉大祖國、維護民族團結。”
不久前,我的一位老師高崇炳先生剛剛完成了一部電影文學劇本《努爾丁》,其中有一段歌詞這樣寫道:火焰山下有個葡萄鎮/葡萄鎮有個巴格日村/巴格日村有個努爾丁/努爾丁有顆火熱的心/工作干一行愛一行/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哪里艱苦哪里去/甘做一顆螺絲釘/一心為黨顯忠誠。
我想,這應該就是老黨員努爾丁最樸實而又最真實的寫照吧。
4
在吐魯番老城街道椿樹路社區,還有一位93歲高齡的老黨員名叫王冬梅。她說:“我是一名黨員,黨員就不能落后,就得有所追求。”雖年事已高,但她除了堅持參加社區的每次黨組織生活外,還為自己定了一份日計劃表,每天都會列出自己要做的事情。
王冬梅老人出生在河南的一個小山村,小時候物質條件很艱苦,經常餓肚子。令她記憶猶新的一件事是十幾歲那年,家里斷糧,她餓了三天,媽媽從鄰居家借來小米,煮了清水粥,媽媽光喝清水,沉到鍋底的米粒都盛給了她。王冬梅老人感慨地說:“那時特別希望能吃頓飽飯。”后來家里分了3畝地,農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全村人都夸贊共產黨好。20來歲的王冬梅第一次萌生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念頭,她說:“黨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跟著黨走準沒錯。”
1950年,王冬梅隨夫到了陜西臨潼縣,因為在老家讀過幾年書,被臨潼縣第八區第四完全小學聘為教師。執教的6年里,她虛心向黨員學習,定期向黨組織匯報思想,并寫過入黨申請書,可后來因生活奔波,隨夫來到新疆支邊,入黨一事就被擱置,這一擱置就是50年。但王冬梅始終沒有放棄入黨的追求。
1964年,因為王冬梅有教學經驗,當時政府找到她和幾位老師,辦起了吐魯番第一家70余人的托兒所。建校之初,條件異常艱苦,她和幾個老師積極找教室、籌資金,當時她任中班老師,每天除了照顧班里的孩子,還要推著車去校外2公里的坎兒井邊打水,秋收時還幫助困難孩子家里收麥草;1975年,王冬梅退休后,因不甘心平庸的退休生活,又托人從北京買了幾本服裝裁剪和制作的書自學,那時在王冬梅所住的小區,人人都知道有個“王阿姨”免費為人做衣服……
提起那些年,王冬梅老人激動地說:“我那時啥也沒想,就是一心想把自己當成黨員,像黨員那樣多為社會和大家做些事,因為我知道餓肚子的年月是多么的苦,所以我想自己認真做好每一件事,來感恩黨和國家為我們老百姓的付出。”
2003年,對于王冬梅老人來說是“圓夢”的一年,她按照組織程序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此時的她已78歲高齡。在當地“老年大學”進行書法學習時,有些同班同學就問她:“你年紀都這么大了為什么還要入黨。”王冬梅嚴肅地說:“只有入了黨,我才覺得這輩子沒有遺憾。”入黨后,王冬梅對自己的要求更嚴了,雖然她腿腳不便,家離社區也有2里多的路程,但依然堅持參加每周一早晨升國旗儀式和各項黨組織活動,而且絕不缺席。
2017年底,王冬梅不慎跌倒,導致右肩膀骨折,腿腳也因為輕度摔傷變得不靈活,在家里養傷。雖然她不能前去參加社區的各項活動了,但仍然掛念社區的人和事,經常向前來家里走訪的工作隊詢問社區的動態:最近有沒有召開組織生活會,有沒有召開黨員代表大會。每每聽到工作隊幫社區修了路、慰問困難群眾等等實事好事,她總是豎起大拇指,把工作隊夸獎一番,也懊悔自己的傷好得慢不能親眼去看看。
有一次,當王冬梅聽前來家里走訪的工作隊員說社區要在“七一”組織“黨旗映天山”大型黨日活動,她按耐不住了,說一定要去參加。她說是黨培養了她,參加黨組織生活是每個黨員都要履行的責任,何況是黨的生日。她說只要她身體還能動,就要自覺擁護黨組織。然而,就在7月1日那天,讓王冬梅沒想到的是工作隊和社區黨支部全體黨員干部來到她家,舉辦了一次特殊的黨日活動。
“近一個世紀以來,我目睹著祖國在黨的領導下一步步變得強大,我們的家鄉在黨的領導下變得繁榮,我很自豪自己是一名黨員……”黨日活動中,王冬梅老人用親身經歷生動地講述了入黨初衷、老一輩共產黨人的艱辛、祖國和家鄉翻天覆地的變化,為在場的年輕黨員上了一堂生動的黨課。在“重溫入黨誓詞”環節,王冬梅雖然雙腿無法站立,雙臂無法舉起,但她仍用左手吃力地托起打了鋼板的右手臂,握緊拳頭,面向黨旗,鄭重地重溫了入黨誓詞,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了共產黨員的初心。活動整個過程,王冬梅因為激動,不時用手揩去眼角的淚水。
這次的黨日活動對社區第一書記趙鎖成觸動很深,當天晚上,工作隊和黨支部就研究商討,計劃在王冬梅老人傷勢痊愈以后,在她家里設立“黨員學習觀摩點”,組織年輕黨員學習老人的精神,讓年輕黨員受教育。當趙鎖成把這個想法告訴王冬梅老人時,她高興得像個孩子。
這些年來,我每當看到村(社區)委會的屋頂上“聽黨話、感黨恩、跟黨走”那幾個紅光閃耀的大字時,都會想起基層那些健在或者逝去的老黨員,并為他們那種對黨無限忠誠的執念心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