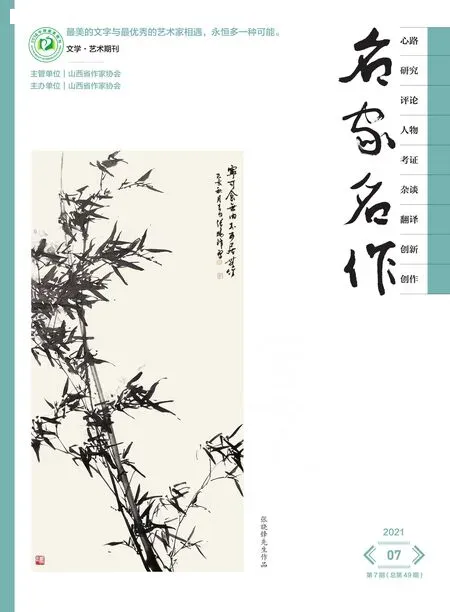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淺析中庸思想下孔子的文質觀
任 婕
春秋時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文學批評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為中國批評史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庸思想貫穿孔子人生的始終,在文質觀中體現(xiàn)尤為明顯。
一、“文質彬彬”與“和而不同”——孔子的文質與中庸
孔子文質說的提出見于《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 然后君子。”他認為“文”與“質”要二者兼?zhèn)洌噍o相成,配合得當,才能達到“君子”這一和諧的狀態(tài)。孔子作為第一個正式將“文”與“質”對舉的人,這種要求文質兼?zhèn)涞闹鲝垼瑢笫赖奈膶W批評產生了深遠影響。
同時,孔子一生主張“中庸之道”。“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他認為中庸是最高的德行,事情不要“過”,也不要“不及”,要恰到好處。“仁”與“禮”的思想也與中庸關系密切。“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記·仲尼燕居》)真正的君子既有仁心又能遵循禮法,以仁心循禮者,是為中庸。“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章句》)可見,孔子主張文質并舉,仁禮并存,不偏不倚,這正是中庸之道的體現(xiàn)。
二、文質并重——文章的文采與內容
許慎《說文解字》中有言:“‘文’, 錯畫也。象交文。凡文之屬皆從文。”孔子的“文”可理解為文采、文辭。他一方面重視“文”的作用,贊美言之有道,一方面反對不誠實的花言巧語,反對“虛文”。如“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孔子重視言辭的同時,又反對言行不符、言過其行。可見君子既要做到言之有理,又要避免言過其實,不偏不倚,才符合中庸之道。
“質”在《說文解字》中為:“質,以物相贅。從貝,斦聲。”孔子的“質”可理解為內容主題。孔子強調“文”的作用,也強調“質”的作用。《論語·衛(wèi)靈公》中有言:“辭達而已矣。”此處所謂“辭達”正是指言辭恰到好處地表達內容,言之有理,中心明確,又不言過其實,拖沓冗長。文章中辭采的作用在于充分表達思想主題,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文章的形式則在于完美體現(xiàn)內容,條理清晰。文章內容的表達離不開形式,思想價值體現(xiàn)亦離不開文采。同時,文采與形式又和諧統(tǒng)一,構成完整的文章整體。這樣的思想同樣展示出中庸的成分,深切地影響了其弟子及后人。
孔子的文質說為其弟子及后人所繼承并發(fā)展。《論語》中記載子貢與棘子成曾產生爭論。二人爭論的重點就在于“文”與“質”的關系。棘子成認為君子有優(yōu)“質”即可,無需表面儀式。而子貢則引虎豹與犬羊相較,以“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反駁前者的言論,點名“文”的不可或缺。子貢所言“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充分繼承了孔子的文質思想,強調了文與質的不可分。
孔子強調文質并重,又對“文”提出具體要求。文章的辭采與形式都是文章重要的成分,忽視文章的文采會使之讀起來艱澀拗口,索然無味;忽視文章的形式,會使之條理不清,徒有其表。文質二者相輔相成,有機融合,共同為文章表達而服務。這樣的觀點正體現(xiàn)了其中庸思想,“文”與“質”作為矛盾雙方,應該在能掌握好各自分寸的同時,又能不偏不倚、和而不同。
三、仁禮合一——君子的行為與品性
孔子對“文”的理解并不局限,大到禮樂儀式、典章制度,小到文章、文采,又不僅限于此。“文”同樣可指人的外在言談舉止、禮節(jié)儀容。“質”同樣也并不單指文章的內容,在《論語》中也曾用“質”來表示人的思想品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句話并不單指文章需要做到“文質彬彬”,還對君子的個人修養(yǎng)提出要求。由此觀之,孔子的文質觀又包含了新的含義。
“禮”作為孔子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對君子行為的規(guī)范要求。前文中提到的子貢與棘子成的文質爭論,從君子人格修養(yǎng)的角度來看也有了更深的含義——君子之質是皮,君子之文是毛,君子的內在品質要通過外在禮儀表現(xiàn)出來。熟練掌握禮儀本身也是君子富有涵養(yǎng)的體現(xiàn)。可見君子之文十分重要,“禮”不僅是君子內在品性的體現(xiàn),更是君子證明自己的方式。
“仁”作為孔子另一核心思想,與“質”息息相關。有“質”的君子應當能夠做到“仁者愛人”,以“文”表現(xiàn)出來即以忠恕之道侍奉君主、父母,與人相處。《論語·里仁》有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道德高尚,光明磊落,問心無愧,“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君子為“仁”,即為“質”,即為“修身”。可見君子之質是君子之文的根源,質先于文,無質之文如同無源之水,隨時可能改變或斷絕。劉寶楠《論語正義》中有言:“禮有質有文。質者,本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能立能行, 斯謂之中。失其中則偏,偏則爭,爭則相勝。君子者,所以用中而達于天下也。”可以說一個人內在的品性就是質,他的言談舉止等外在表現(xiàn)就是文,二者缺一不可。身為君子,要以禮為形式,以仁為內容,不偏不爭,中正平和。
孔子強調的君子人格修養(yǎng)文質并重,君子內在的品性和外在的儀容言談都十分重要。君子沒有“仁”的品性便不能算是真正的君子,有了“仁”的內心卻不能以“禮”表現(xiàn)出來,同樣也算不上君子。唯有文質統(tǒng)一、內外相合,然后進退有度、謙謙有禮,方為君子。
四、“不偏不倚”——時代中體現(xiàn)的中庸文質
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像儒家這樣提倡文質并重的人極少,受時代環(huán)境影響,多數(shù)人都認為“質”勝于“文”。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一個大變革時代,從經(jīng)濟、政治到思想、文化,無不飛快地轉變著。經(jīng)濟發(fā)展,禮崩樂壞,諸侯割據(jù)爭霸,廣招賢士,士階層興起,百家爭鳴。思想家們四處游說,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希望為國君所采納,故對主題思想的實用性要求極高,而將言辭作為其表達思想的附屬品,先“質”而后“文”,即“質”勝于“文”。
墨家與儒家作為當時兩大顯學,對文質看法卻大不相同。《非樂》篇有言:“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而是由于他們“不中萬民之利”,即實用性不足,不能切實解決百姓的問題。墨家的思想明顯體現(xiàn)出實用性,雖并未否認“文”的價值,但講求文藝要服務于功利的目的,否則便如空中樓閣,再美也是無用的,從根本來講是“質”先于“文”。
同時期道家是與儒家并駕齊驅的大門派,以老莊為代表。但是道家更看重內在客觀規(guī)律,與儒家不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老子》第十二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老子》第八十一章)老子強調尊重客觀規(guī)律,道法自然,明顯體現(xiàn)出對事物本身即“質”的重視。而莊子在繼承老子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自身的理論。“毀絕鉤繩而棄規(guī)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胠篋》)莊子崇尚人的原始天性,反對后天的藝術創(chuàng)造。他認為真正的藝術是天然的、不依賴于后天雕琢的,同樣崇尚自然。這也是“質”勝于“文”的體現(xiàn)。
戰(zhàn)國后期以商鞅和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思想在文質觀上也與儒家不同。“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商鞅《商君書》)商鞅認為那些講詩書、善辯的人只會對法治、農戰(zhàn)起破壞作用。“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fā)之說也。”(韓非《韓非子·問辯》)韓非重視文學的實際功用,尤其看重內容,即重“質”而不重“文”。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孔子堅持自我,始終認為二者并重,這正是其堅持的“中庸”思想的體現(xiàn)。
孔子的中庸思想作為儒家代表思想之一,充分地展現(xiàn)在其文質觀中,無論是就文章的形式與內容而言,還是之于君子的行為品性,兩者兼顧始終是孔子力排眾議所堅持的。“文質彬彬”的觀點也為后來的批評理論發(fā)展提供了辯證思想的基礎。其對君子的要求,不僅影響了當時社會的人們,更是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的行為準則,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