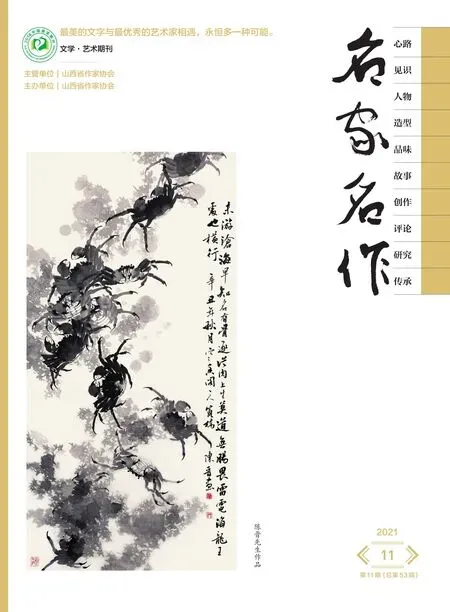淺析漢唐古典舞《河洛·顏子兮》的舞蹈形態
皮 琳
一、中華傳統舞蹈文化
舞蹈,是藝術之母,是人類最早的藝術形式之一。它是以人體本身為物質載體的藝術,其特殊的存在方式決定了這門藝術的“特殊性”。作為一門特殊的文化藝術,其內涵和功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原始時期,人們以舞蹈傳情達意、求偶交配、征戰慶祝、祭祀崇拜。在文字出現以前,舞蹈同語言藝術一起,擔負著記錄歷史、向氏族后代進行傳統教育的任務。夏商時期,奴隸制的開啟出現了奴隸主,為了滿足奴隸主的享樂需要,“奴隸女樂”應運而生,舞蹈進入娛人領域。西周時期,禮樂教化、教育國子,雅樂舞體系正式建立,不同等級的人,用不同規模的樂舞,等級嚴明,不容僭越。秦漢時期,以俗為趣、以俗為雅、以俗為美為當時的社會風尚,尤以“百戲”最具代表。魏晉南北朝時期,時代動蕩、民族遷徙的時代背景,促進了中外樂舞文化大交流。隋唐時期,舞蹈已發展成為一種完整獨立的表演藝術,并具有相當高的藝術水平。宋朝時期,專門表演各種技藝的固定場所“瓦子”“勾欄”的出現,使民間舞蹈大肆發展。明清時期,舞蹈衰落,繼之而起的是“戲曲”,舞蹈融入其中繼續發展。
千古華夏文明,舞蹈從未缺席。“在中國,有一個叫孫穎的老教授正在發掘和復活中國古代的舞蹈文化。”孫穎老師的舞蹈動機和語匯不是向芭蕾尋找、向現代舞尋找,而是尋找中國自己的身體文化。她循著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秦、漢、唐慢慢摸索,以漢、唐兩大古代舞蹈發展高峰時期的審美特征、舞蹈文化傳統為基石,形成了風格與眾不同的漢、唐古典舞。七個手位形成了西方“古典舞”的典型規范,但僅我們國家出土的陶俑舞姿就是這些舞姿的幾十倍,這難道不應使我們驕傲自豪?不應是我們應該把握住的財富嗎?孫穎老師循著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基礎,探索著屬于中國人身體語言的舞蹈藝術。漢唐古典舞《河洛·顏子兮》就在一方面傳承著河洛文化,另一方面為漢唐古典舞的創作增添新的血液。
二、《河洛·顏子兮》的舞蹈動作形態
《河洛·顏子兮》原名為《漢洛·顏子兮》。漢洛,是指東漢時期洛陽都城;顏,意為五顏六色。陸上絲綢之路時期,各國文化的融入使得人們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子,古代對文人雅士的尊稱,也可用于形容美麗女子;兮,作為古語中的助詞,與“晞”同音,它的含義還有天亮,心中有希望,永遠向陽。“漢洛”一詞生硬,又具有局限性,為使名稱更切合主題,也為了更加彰顯河洛文化的地域特色,故更名為《河洛·顏子兮》。
舞蹈《河洛·顏子兮》所描繪和塑造的是東漢時期洛陽城內一群身著紅裝、衣袂躚翩、舞姿輕靈、擰身出胯、折腰的溫柔輕盈的舞者形象。編導一方面尊重歷史:身著紅裝、衣袂躚翩、舞姿輕靈、擰身出胯是延續楚國輕盈、飄逸、柔婉風格的表現;使用道具“水袖”是絲綢之路興起后,中原藝人進行舞蹈創新、巧用道具的體現。另一方面,舞蹈編導通過舞蹈動作獨特的表現形式,來讓觀眾直觀地感受到漢朝時期洛陽都城的人們文藝生活的氣氛;利用觀眾對舞蹈獨有的審美形式,來宣傳在特殊時期下,極具開放性的河洛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對文化藝術發展的影響。同時,舞蹈《河洛·顏子兮》是以漢唐古典舞為基本元素廣泛吸收了古今河洛地區的優秀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地繼承、弘揚、完善了河洛文化。
在舞蹈中,大多是以掩面傾頭的羞澀、擰身出胯的盡顯嫵媚、回眸一笑的令人動容的姿態為主題動作。這些姿態也反映了當時的文化背景。漢代奠定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舞蹈文化中也多有體現,如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漢唐舞多有謙卑、掩面、嬌羞這樣的動作。
三、《河洛·顏子兮》的舞蹈道具形態
漢朝時期的舞蹈在技巧與藝術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技藝結合、技藝并重是這一時期的舞蹈特色。如出現的《盤鼓舞》《袖舞》等舞蹈都是漢代道具舞的代表。
舞蹈編導尊重歷史事實,運用舞具舞服,抒發感情、加強美感、強化感染力。在舞蹈《河洛·顏子兮》中,舞蹈編導不僅運用了兩米長的雙水袖,還增添了一米長的單水袖。舞蹈演出進入發展階段之時,舞者們突然從右手袖子中拉出一米長的水袖。舞蹈編導在此時將舞蹈隊形與漢代“絲綢之路”開啟的歷史背景相結合,同時伴隨著舞蹈隊形變化為兩條交叉的斜線,后有隊形的層次高低分明,又展開隊形的大齊舞,展現了當時漢代國力強盛、對外交往頻繁,許多域外及少數民族藝人相繼來到中原,同時在“絲綢之路”影響之下人們文藝生活的興盛繁榮。舞蹈中拋袖、抬胯、提腿、下腰、轉頭擰手的一系列主題動作,是漢代注重吸收外來文化、兼收并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精神的體現,也是這種精神讓漢朝時期的舞蹈增添了幾分異域的神秘色彩。之后,音樂突然激烈地變化,并伴隨著五名舞者激昂的舞蹈將舞蹈拉近,舞者們右手的一米小袖也變成了兩米長的大水袖,舞蹈進入高潮,隊形變換為給人以力量的三角形,音樂也加快了節奏,舞者們跟隨著音樂的節奏做著變幻多姿的舞袖動作,情緒激昂、整齊劃一,展現了漢朝時期舞者們對舞蹈的極度熱愛和舞蹈文化的大繁榮。之后舞蹈進入尾聲,音樂也隨之慢了下來,人們又進入了一種安靜祥和的環境之中,舞蹈作為一種文化慢慢發展下去,并且在新的環境中創新出更燦爛的文化。
四、“本”心之“本”
民族大美。民族,是身份與文化表達的紐帶。民族性,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基本特征,集中反映在本民族的文化意識、身份認同中。對于西方古典舞和現代舞,中國古典舞不能采取借用、挪用、仿照西方創作模式的拿來主義,而應“創建自我成章、自立標準、自有規范的中國古典舞”。孫穎老師認為,在塑造中國古典舞的民族身份時,必須充分了解中華文化和中國歷史。首要的問題,便是從歷史形象入手,激發人們的民族認同感與文化歸屬感。民族身份的確立與民族形象的建構,是孫穎老師藝術語言開掘的前提,是藝術實踐的立場問題。“民族”這兩個字貫穿在舞蹈作品創作的始終。
歷史傳統精神。歷史,是中國古典舞的立本之源。在中國古典舞的當代重建中,續接文明和重構中國古代舞蹈的文化碎片,是體現唯物史學的基本態度。那些湮沒在史料碎片和殘存壁畫中的舞蹈形象,是我們需要利用起來的寶貴財富。
現代創作。中國古典舞在藝術表現、文化格調及審美情趣上要能夠體現中國傳統精神與中國風范。活在當下,指向未來,基于歷史傳統的本源,創作屬于這個時代的中國古典舞。雖然舞蹈《河洛·顏子兮》還有可以改進的地方,但它另辟蹊徑地與本地文化相結合創作舞蹈作品,為中國古典舞的發展提供了新穎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