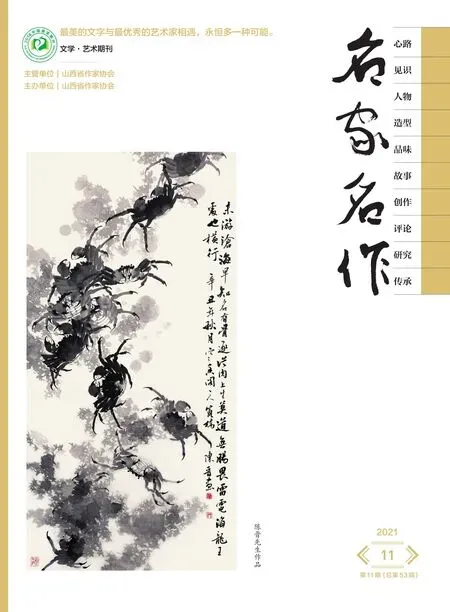廣西民族志電影的敘事表意與美學特征思考
——以《放雁》為例
耿偲特
民族志電影《放雁》是廣西民族志電影在中國民族志電影作品中異軍突起的一部力作,影片在結構主義經典敘事的基礎上偏向奇觀敘事,從最基本的傳統線性白描中辟出一個“性別身份”的切口,“奇觀性”落點在敘事文本中所展現的敘事表意美學指征,導演以敘事反身性作為敘事動力帶領觀眾進入精神體驗和共情場域,其能指符號——“生命性”折射出廣西少數民族地區族群文化的影像美學趨勢,田野拍攝和對個體生命成長的記錄觀察讓這部電影產生了新的美學特征,“順應當代電影敘事美學經歷的從參與性、語境性到‘雜交性’的轉向,呼應著觀眾需求和時代背景,體現出多元審美意義”。
一、敘事結構與表意
廣西民族志紀錄電影創作風格體系的建構尚處于一個多維度闡釋和創作的樣態中,從廣西民族博物館主辦的歷屆影展作品中可以窺見對本地民族題材的堅守和對國內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包容,作為“文化記憶工程”,影展“關注中國及東南亞國家的社會歷史文化變遷及民族文化多樣性,致力于推動紀錄影像的多元取向,創造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紀錄影像交流平臺,力求增進各民族及地域間的文化交流與對話”。 同一民族題材用不同視聽表現手段在影像藝術風格上形成了豐富的文化景觀,不同題材的影片也彰顯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內核。聚焦廣西地區民族志電影,在敘事進程上呈現出一般規律。
(一)民族集體敘事中人的獨立性傾向
影像文本作為象征建構媒介,民族志敘事語言的藝術性本身來源于人的獨立性。《放雁》將敘事策略偏重于個體觀察,這得益于創作者與拍攝對象同鄉同族的地緣關系,對生命個體體驗的影像記錄也毫無疑問刻上了民族集體敘事中個體表意的符號。盡管這部影片的鏡頭語言尚顯粗獷,但瑕不掩瑜,將敘事視角成功集中于人物的時間與情節發展,出乎意料的敘事切入點在民族志電影拍攝的主流話語中將觀察中心瞄準在人的獨立性上。紀錄片與民族志電影的拍攝紀錄在創作技法上最大的區別就是主動與被動的迥異。紀錄片可以參與、可以介入、可以把控;民族志電影則完全被動地跟隨紀錄,在這樣的創作語境中對個人的田野拍攝會稍顯受限。《放雁》的敘事中心點落在具備民族身份和社會屬性的主人公的生存和成長過程中,的確完成了一種既個性又共性的信息傳遞。個體獨立于民族集體性之外的部分,才是更值得藝術語言表達的出發點,與其說《放雁》在紀錄民族集體的文化樣態,不如說是導演通過攝影機鏡頭去體驗集體樣態下個體拍攝對象的生命哲學。
(二)雙線敘事中的隱喻與詩意
《放雁》的敘事脈絡清晰,依照時間漸次呈現事件和情節,空間關系表述傳統規整。情感線上則呈現出極具想象力和洞察力的隱喻。紀實影片的敘事邏輯和隱喻正在于此,殘酷的生活本身依然構成一種景觀。意象是本片的創作語言,導演隱匿與觀眾共情的心理,在剪輯中使用素材賦予影片人物時代象征意義,敘事中強調的個體命運直接輔助主題。《放雁》的詩意不在于敘事語言的浪漫輕松,鏡頭的捕捉意圖也并非人文關懷,但正是冷靜客觀的背后,李恩平獨自應對的精神成長和他生活的底色才是詩意本身。在家鄉給親人送葬、異地求學、奔波打工演出和處理社會關系等一系列有關成長的敘事線中,隨處隱藏著的對抗性的暗線是形成李恩平人格特征的技法表達。這種對抗的代表場景有二:其一是對李恩平的采訪,他的自述是對同性求愛拒絕、異性相處困惑的自我剖析,故事通過人物本身進行傳達,盡管這并非第一人稱紀錄片,但自說自話的形式帶給觀眾的真實感更加確鑿,反抗意味更加明顯。對抗場景之二則是李恩平與同齡人之間的社會身份和地位的對照。李恩平的演出在社會評價層面被定義為是與傳統背道而馳的媚俗表演,商家邀請他演出目的是為了娛樂效果,為生計尋找出路的李恩平對于自己的藝術表達形式不置可否,然而這場景中出現的情節產生新的對抗——主辦方臨時取消表演,當畫面中一群和他同齡的年輕人歡聲笑語地聚會歌舞時,鏡頭轉向因取消演出而無所事事地看手機的李恩平,鏡頭呈現的兩種生命狀態不言而喻。正如福柯所言,“當今社會的主要問題在于反抗服從”,導演對人物隱私的曝光是適度而絕對尊重的,包括片中其他副線人物的出場和一些宗教儀式的呈現,家庭葬禮場景的記錄與人物情感狀態的表述都始終包含了一種反抗心理,在敘事策略上沒有販賣和揭露,影片自身帶有更耐人尋味的探討空間。
二、美學特征的內涵元素
《放雁》具備真實建構意義上的美學體驗。影片的敘事擱置于個體成長的悖反情境中展開,借由人物的精神被閹割和反抗來達成他成長中的和解。民族志電影語境中所呈現的美學質感厚重,既遵循敘事倫理,也未跳脫美學詩性邊界。對于民族志紀錄片的美學驅動和核心元素來說,最值得變革轉型的關鍵是人,人在社會中的生存形態,人在家庭中的精神情感訴求,人在自我矛盾與困斗中的淬煉。人背后的群體性才形成文化的樣態,才有反思,才能討論。《放雁》中人的悖反情境始終以紀實美學為前提,緩緩從生活本質中體現,由此產生愈發銳利的美學表達。
(一)父權
李恩平的家庭倫理結構中,父親的形象始終缺席。屢次離家出走、家庭責任由兒子替代完成的現實反差,通過畫面中躲閃在門框后摩托車上的父親視點構成一個象征意味的精神參照。但影片并未將父親當作敵對形象作為敘事策略,父權是映襯李恩平個體成長的能指符號,李恩平頻繁在經濟上支撐父親,這種倒置的資助者地位轉換帶給李恩平的并非“弒父”,而是其內心同情母親、想借此幫助母親重新得到家庭完整性、自身重新回歸“兒子”身份的驅動,因此李恩平對于父權的“俄狄浦斯情結”結構在片中并無外放顯影。孱弱不意味著消逝,偶爾歸來的父親讓李恩平清醒地知道父權本質對于自己而言是隱匿而消極的,他將這種父權困境擱置,力求擺脫困境的方式是自己面對和解決一切問題。值得思考的是,父權在李恩平所處的社會性別語境中必然產生影響,甚至可以說此種父權是導致李恩平性別自我認知產生模糊的幫兇。
(二)女性形象反哺
《放雁》中的女性形象有三種,第一種是倫理關系之內和李恩平緊密相關的——他的母親與奶奶,第二種是社會評價賦予李恩平的“女性形象”,第三種是李恩平自我評價中模糊曖昧的“女性形象”。從家庭結構出發,父親“男性形象”的坍塌從側面對李恩平進行了精神閹割,他扮演自我重構后的“男性形象”,且荒誕地建立在消費女性之上,充分利用男性審視目光來達成性別消費,男性自我精神肖像的含混,其產生的心理癥候的幻影形成了這部影片“女性”意識美學層面的確立。李恩平謀生的藝術特長源于龍州地區的傳統藝術形式,在文化保護和社會規范的語境中他飽受當地人詬病的是性別身份的外顯,社會輿論對他的施壓和社會中男性對其“女性”媚態的覬覦甚至性騷擾,使李恩平處于矛盾的困獸之斗中,既不愿放棄女性化表演,又拒絕女性獻媚,人性的搖擺和立場的猶疑在影片敘事中達成美學意象。然而值得探討的是,《放雁》的男性形象的曖昧含混,不意味著“男性形象”的徹底破碎。三種“女性形象”對李恩平的自我身份與性別認知起到了反哺作用,李恩平對自我性別意識的解構和“男性形象”的建構理應基于上述三種“女性形象”。
三、結語
《放雁》的性別美學意象的形成建立在長期跟拍和鏡頭細膩的捕捉之上,也得益于導演敏銳而仔細的剪輯考量,作為廣西民族志電影作品中的佼佼者,這部影片無形中帶給廣西本土民族志電影拍攝者們一種啟示和“小浪潮”,是否可以更藝術化、更耐性地“深描”族群背后作為人的本體?對于民族志電影當下語境而言,探討人和少數民族族群的關系,探討人和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這是民族志電影的意義所在,對個體生存狀況的凝視必然持續,但因此產生的美學意象值得繼續深入探索。在創作表達的方向與路徑上,毋庸置疑,需要遵循客觀真實的敘事,然而紀實美學還可能有何種呈現樣態,如何通過敘事來突出這種樣態,在民族志電影拍攝創作中能否形成新語境,是民族志電影在未來的紀錄拍攝和剪輯創作中應不斷思考的問題,也是廣西民族志電影拍攝者在表達方向上可拓延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