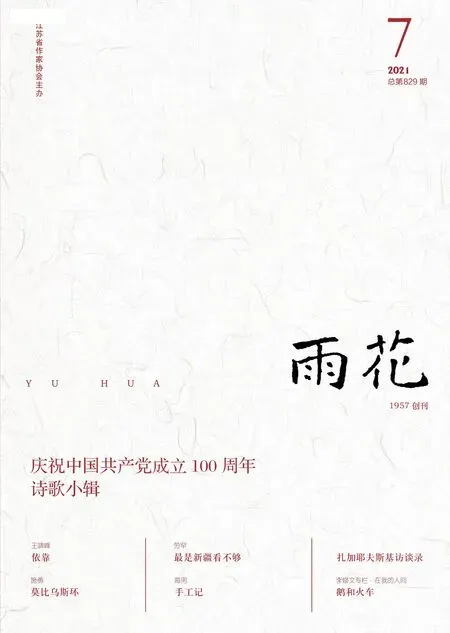母親
曹愛東
我的母親去世已有二十四年,如果她還健在,今年九十二歲。
母親一生養育了八個兒女,飽嘗的辛酸和吃盡的苦頭,只有當我們長大以后才能漸漸體會到。
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口袋里總有一塊包裹著零錢的舊手絹。每當我和弟弟嘴饞時,她總是斜側著身子從右褲袋里掏出手絹包,翻滾著打開,從為數不多的角票和硬幣中拿出幾分錢為我們買些吃的。炎炎夏日,賣冰棍的人推著自行車在我家門前“啪啪”敲著冰棍箱,我和弟弟便纏著母親給我們買冰棍。母親每次掏錢時的表情和動作,我至今記憶猶新。
小時候,我家朝東的三間草屋前長著三棵梨樹。每年,母親把成熟的梨摘下來后,拿到集市上去賣,然后用賣得的錢給我們兄弟姐妹添置新衣或購買日用品。她對這三棵梨樹管得很嚴,沒有她的允許,我和弟弟輕易不敢偷偷從樹上摘梨。每當沉甸甸的梨壓彎枝頭時,我和弟弟坐在草屋前的矮凳上,看著滿樹的梨,心里只有一個愿望:刮大風!而且越大越好!梨被風刮下來,屬于自然掉落,我們吃梨也就心安理得,母親一般不會怪罪。終于有一天,罕見的臺風把三棵梨樹刮倒在地,滿樹的梨雖半生不熟,但我們兄弟倆每天大飽口福,歡喜不已。那時,我們尚不能領會母親愁容下生活的艱辛。
母親生氣時,也會懲罰我。常常是揚起手掌,滿臉怒氣,看上去很嚇人,但手掌落下時已經沒有什么力度。受到母親的訓斥或懲罰,我通常會哭泣著表達委屈,一般不會主動認錯。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朝東的屋檐下,常留下我蜷縮在墻角的身影,憋氣或哭泣到夜幕降臨。因為我知道天一黑,吃晚飯的時間到了,母親一定會來安慰我,并說上那句慣用的話“以后聽話,快去吃飯”,我便飛跑進廚房。
母親是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婦,在我的印象中,她廚藝絕佳。只有家中來客,母親才舍得在市場上買點豬肉,再加上自養雞生的蛋,便能忙出一桌菜。我和弟弟平日肚中缺少油水,在飯桌上自然沒有什么好吃相,所以家中有來客吃飯時,母親對我們的要求也極其嚴厲。我和弟弟從小就養成了看母親臉色去夾菜的習慣。母親臉色好,我們就多夾幾筷子菜;母親面露怒色,尤其是流露出責備的眼神時,我們就不敢再伸筷子了。每到此時,我們都希望母親離席,比如去炒菜、端菜,這樣就能趁機偷偷多夾上幾口菜。不過,我有一項特殊的待遇。那時母親做飯炒菜必須在灶臺上完成,而我在灶臺后燒柴,雖比較辛苦,但常能得到母親的獎勵,比如讓我嘗嘗豬肉的火候、肉圓的咸淡等等。
由于兒女多,母親一直非常節約,處處精打細算。雖然家庭條件不好,但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條。每回中秋節,別人家的孩子能夠吃上整塊的月餅,而我們家往往是由母親將一塊月餅分成兩份,有時甚至四份,兄弟姐妹們分食。
我和弟弟從小沒有新衣穿,母親常是將哥哥姐姐穿過的舊衣服修補或改制后讓我和弟弟穿上。在我的記憶中,第一次穿新衣是在五年級即將畢業時。母親大約是察覺到青春萌動的我開始在意自己的外表,特意去扯了幾尺草綠色的確良,給我做了一件中山裝,這件衣服在拍畢業照時派上了用場。
最讓母親感到為難的是我和弟弟穿鞋。那時,她總覺得我們的腳長得太快,鞋穿在腳上一般不是鞋底、鞋幫先壞,而是腳趾頭“老大”先出來。開始,母親幫我們在“老大”出口處用棉線織網,后來,經過我們細心觀察和母親指導,這種活兒一般由我們自己完成。
那時,也沒有襪子穿。為了不讓腳挨凍,母親剪下舊衣服的袖管,套在我的腳上,腳頭處向上一折,作為我們的襪子。冬天里,腳穿布鞋,袖管做的襪子常常游到腳尖處,造成腳后跟凍裂開一個個大口子,流了好多血。母親發現后,便將這種衣袖管襪改成用棉毛衫制作,并在小腿處用自行車內胎做的皮筋加固。
母親不會騎自行車,出門一般都是步行。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有過很多次與她步行十多里地,到姨媽和姑媽家做客的經歷。那時,我總覺得母親走路特別快,一般人趕不上她。遇到我走不動時,她總是用背馱著我,邊走邊喊出輕微的號子聲。別看我肚子里油水少,在外吃飯時卻規規矩矩的。每回帶我做客回來母親都會表揚我,說別人夾一筷子菜,我也夾一筷子,并且只夾自己這一面的菜,咀嚼時閉緊嘴巴,不咂嘴(母親說只有豬吃食時才咂嘴),盡量不發出聲響。
母親這一生,到過的最遠的地方是南通,同父親一起來看我這個在南通師范讀書的兒子。頭一天打電話給我,第二天上午到學校,中午在師范食堂吃飯。我向同學們借了十余只搪瓷飯盆,盡可能多打了幾個菜,母親一直在說不要打這么多,吃不下。當時,通師學生食堂里只有方桌,沒有凳子,我們只好站著吃完午餐。下午,我陪他們到南通人民公園玩,記得在一架飛機前拍了張照,我站在中間,父母分列兩邊。非常可惜,這張照片后來弄丟了。從公園出來,我帶他們去逛南通市中心的百貨大樓。母親第一次看到像履帶一樣長長的電梯,不敢乘坐,一直坐在樓下等。她這次來南通給我帶來了一件毛線衣,聽父親說是母親花了八十元買了一斤毛線,然后請生產隊里手藝最好的人織成的。他們是當天離開的,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們在南通長途汽車站沒有買到直達老家曹埠的回程票,只能乘坐到西亭,然后步行五十多里回家。那天,他們摸黑一直走到天亮。
1992年,我分配到馬塘小學工作,每周騎自行車回家一次。每次回家,自行車后面的小拖籃都塞滿了母親栽種的各種瓜果蔬菜,洗得干干凈凈,捆扎得整整齊齊,偶爾還有一塑料壺自釀的米酒,好讓我在宿舍中與同事們把酒言歡。學校住宿條件簡陋,母親和父親商量后砍伐了種植十多年的幾棵大樹,專門請木匠幫我制作了三件家具:新式床、書桌和書柜各一。其中書柜是木匠按照我畫的圖紙制作的,說是書柜,其實是一個綜合柜,上面開放式,可以放書;下面有門,可以存放衣服。有意思的是,上面還設計了一個小抽屜用來存放小雜物,和一個帶玻璃門的食品柜用來存放炒米糖、饅頭干等零食點心;下面衣柜空間大,可以存放過夏的棉絮被單,還安裝了長木棍用來懸掛上衣。時隔三十年,我先后經歷數次搬家,家具進進出出換掉不少,但這三件一直保留至今,因承載著對母親的思念而不忍舍棄。
母親年紀大了,身體越來越不好。她常把膏藥剪成小方塊,貼在太陽穴處,以緩解頭痛。1997年陰歷三月初五的半夜時分,馬塘小學集體宿舍的一位鄰居老師叫醒了我,說老家打來電話,母親病重讓我速回。
見到母親時,她躺在曹埠醫院的急救室里,醫生說母親是腦中風,顱內大出血,拔掉氧氣管,呼吸就停止。母親躺在床上,臉色蒼白,眼睛半睜開,身上還穿著一件我上初中時就見過的舊馬褂,褲腿上沾滿了泥土。
母親從醫院拖回來后,被放在堂屋地上的門板上。我摸著母親的手,慢慢地感覺到母親的體溫逐漸冰冷。我知道身體冰冷,就不能再復活,這個世界上,我從此沒有母親了。
年輕時,感覺母親就是天,母親沒了,天也就塌了下來。我也記不清母親去世的那些天,自己是怎么過來的。只知道每天早晨,眼睛睜開,第一個念頭就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母親了,繼而轉入無盡的痛苦和思念中。
如今,母親已經去世二十四年了,她的面容和身影在我的腦海里逐漸淡化,有時我極力想找尋她的樣子,很可惜母親在世時沒有留下一張像樣的照片。我只能從我姨媽的臉上感受一點母親當年的面龐和笑容。
母親生我時,已四十四歲。因年齡懸殊,我們常被不知情的人認作祖孫。那時,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她來學校找我。因她一來,同學們就會喊:你奶奶來了。有一次,她戴著一頂破草帽來找我,模樣滑稽,令我羞愧難當。而今憶起當日的種種細節,卻總不免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