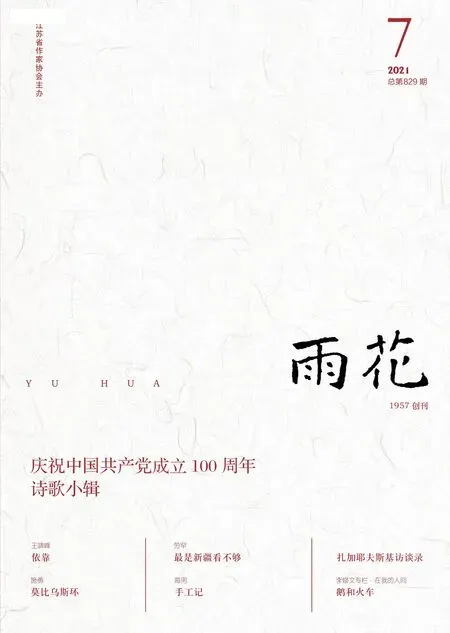我最感興趣的是我還沒有寫出的詩
——扎加耶夫斯基訪談錄【1】
斯維塔·古特金娜;亞當·扎加耶夫斯基 李以亮 譯
編者按:
亞當·扎加耶夫斯基,波蘭著名詩人、散文家、小說家。1945年出生在利沃夫(今屬烏克蘭),畢業于雅蓋隆大學哲學系,波蘭“新浪潮”詩歌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詩集《無止境》《公報》《肉鋪》《信》《嘗試贊美這殘缺的世界》《永恒的敵人》《無形之手》等,散文集《團結,孤獨》《兩座城市:論流亡、歷史和想象力》《另一種美》等。曾獲特朗斯特羅姆獎、諾斯達特國際文學獎、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等多項權威獎項。近年來他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之一。2021年3月21日,扎加耶夫斯基逝世,為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本刊特刊發此訪談。斯維塔·古特金娜(以下簡稱斯):美國詩人兼評論家愛德華·赫希曾把你的詩歌等同于祈禱……
亞當·扎加耶夫斯基(以下簡稱扎):我想我的某些詩可能會引起這樣的聯想,對此我并不反對,但是事實上,它不應是唯一的模式。我的一些詩本質上有些哲學意味,另一些則比較抒情。我很喜歡愛德華·赫希,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在這一點上,我不同意他的看法。
斯:詩歌能像祈禱嗎?
扎:當然。許多詩,很優美的詩,都有像祈禱的一面。寫詩的沖動某種程度上類似于祈禱的沖動,這也是因為大多數詩人相信某人或某事好像在向他們口授詩歌。對許多詩人來說,寫詩的前提,本身就是某種宗教性的東西,就好像有一個更高的權威在幫助他們寫作。當然,這并不能從科學上被證明。
斯:你曾經寫過“詩歌尋求著光芒”。詩歌也是對上帝的尋求嗎?
扎:我可能不會那樣做。這是對“光芒”這一隱喻的解釋之一種,但我不會把所有的詩歌都歸結為對上帝的尋求,因為詩人也會觸及非常世俗的主題。有政治詩,也有愛情詩,詩人在詩中尋找他們所愛的人,而不是上帝。詩歌是多樣的,具有各種各樣的目標。有些詩人是完全不信教的,這應該受到尊重。
斯:在《略帶夸張》一書中,你引述了一位法國詩人的話,他告訴你說,因為法國人知道沒有上帝存在,所以他們寫的是另外的東西。
扎:在這方面,法國詩人是一個例外,盡管在法國也可能有宗教詩人(我不知道,我沒有跟上最新情況)。
斯:波蘭詩歌有什么不同?
扎:我認為它的不同之處在于對推動共同體的那些因素非常感興趣,也就是說,關心政治性事務。波蘭詩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現在的形式直接涌現出來的。米沃什和魯熱維奇重新定義了它,赫貝特后來也加入進來。波蘭詩歌有了一個顯著的轉變,對共同體的發展著迷。不是以一種新聞的方式,而是以更復雜、隱喻的方式,我覺得它不同于其他許多忠于古典模式的民族的詩歌,也就是說,那些民族的詩歌不一定需要深入研究歷史和公民問題。波蘭詩歌并不反對這一點。
斯:波蘭詩歌的未來是什么?
扎:我不知道。我想我屬于堅持米沃什、魯熱維奇和赫貝特的詩學視野的最后一代人。更年輕的“草稿派”那一代詩人開始偏離這一點,詩歌重新變得私人化,詩人只寫自己的事情和經歷,而不關心社會在想什么。另一種反應也許會隨之而來,對公眾想什么又會發生興趣,因為詩歌不會只朝著一個方向發展。今天那些二十歲的人,我們對他們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有可能會回歸到這種關心共同體的趨勢中來。
斯:你關注當代詩歌嗎?
扎:我不像米沃什,他說波蘭詩歌是他的故土家園。我在年輕詩人中間有一些朋友和熟人,他們把詩寄給我看。我有一定程度的接觸,但只是一些個別的樣本。他們通常是一些還沒有發表作品、詩集的詩人。在五十歲以上的人當中,我最喜歡的是托馬斯·羅瑞茨基,我非常喜歡他的詩。他并不完全認同我提到的模式。他的家人也來自利沃夫。他寫了許多詩,來表達他對事物的敏感,那些事情直接影響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家庭的命運。
斯:為什么大多數波蘭詩歌都是以自由體寫作?
扎:有些詩人試圖回到古典形式。波蘭語曾經因為擺脫了音韻的束縛而大松一口氣。不幸的是,波蘭語中所有的重音都落在倒數第二個音節上,這限制了詩歌的聲學可能性。俄語在重音上的變化就較多,英語也是,而法語則把重音放在最后一個音節。某些語言在某種程度上是“殘疾的”,但這并不妨礙每個人都希望有像法語那樣的詩歌!這就意味著波德萊爾和阿波利奈爾是可憐的詩人。其次,自由詩的模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我努力(但我并不知道我是否總能做到)使我的詩豐富、表達優雅。
其實押韻讓我有一些煩,它有點像教堂里的鐘聲叫你跪下。我不喜歡押韻,而且,押韻是一項最近的發明。押韻在中世紀才被發明,而希臘和拉丁語詩歌以及《圣經》詩篇并不包含押韻,也不計數音節和節步。
在自由詩中,我試圖通過意象和隱喻來包含豐富的形式。我不喜歡貧乏的自由詩,那種東西通過分行分節、寫幾個句子就“創造”出一首詩。這是不夠的,描寫和隱喻必須要有獨創性,沒有隱喻的詩歌對我沒有吸引力。詩的靈魂既不是押韻,也不是詩節的長度,只是隱喻。必須賦予語言某種豐富性,這是報刊文章、甚至散文所不具備的東西。
斯:你如何定義詩歌?
扎:我特別喜歡一個非常古老的定義,它是18世紀初一位意大利耶穌會詩人和哲人提出的:“詩歌是在理性在場時做的夢。”我非常喜歡這個定義,因為它包含兩種元素——某種與想象和夢想相聯系的狂野的東西,同時又被理性納入秩序。一種與想象的對話。
斯:你如何看待你早期的(波蘭新浪潮時期的)詩歌?
扎:我認為我后來的詩更有趣更豐富,但我的某些讀者卻持相反的觀點,他們喜歡我早期的詩。那些沒有隱喻的直白的詩歌,我現在不喜歡,但它們是特定環境下作為特定一代人的表達而出現的。我相信它們在當時是必要的。詩人通常在幾乎真空的環境中寫作,只擁有幾千名讀者。很少有詩人能像馬雅可夫斯基或高烏欽斯基那樣擁有廣泛的讀者,但我們確實想過爭取大量的讀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是作為《未被呈現的世界》一書的合作者而為人所知,但那是將近五十年前的事了!
斯:你能背誦你的詩嗎?
扎:不,很遺憾我不能。這里有一個軼事:美國詩人W·S·默溫最近去世了。1960年代赫貝特生活在加利福尼亞,他們是朋友。他講過一個故事,有一次他看見赫貝特一副悶悶不樂的樣子,便問:“怎么了,茲比切克?你看起來不太好。怎么了?”赫貝特回答:“嗯,我寫了幾首新詩,我也很高興。不過我乘出租車,把詩忘在車上了。”默溫問道:“怎么,你沒有把它們背下來嗎?”赫貝特回答說:“只有俄國詩人才會把他們的詩背下來。”這在今天的俄羅斯仍然很常見。布羅茨基有時會在詩歌晚會上忘詞,但對他來說,背誦只是一個起點。
斯:也許押韻會有幫助?
扎:押韻確實有幫助。有一種理論認為,中世紀的僧侶將押韻作為一種助記手段來幫助記誦宗教詩歌。他們想讓人們記住它們。
斯:在1968年,你說過你考慮的不只是政治,而你那時候也很年輕和快樂……
扎:年輕人不知道自己年輕。我們很高興,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做了一些積極的事情,我們的詩走到了人們中間。有一次我在羅馬參加一個關于布羅茨基的會議,有人在談論他在列寧格勒的可怕時光,那時他在警察的監視下被流放到了北方。我說那不是真的。他還年輕,知道自己是個天才,他感受著才華帶來的樂趣。我認為年輕藝術家們開始的時候缺乏確定性:我真有什么要說的嗎?作為一名年輕詩人,布羅茨基很快就證明了自己的才華并且贏得人們的推崇。我說我不相信他作為一個年輕詩人是悲慘的。在某種程度上,他還是很快樂的,洋溢才華的活力。幸福不是自動的,有時人們能夠通過詩歌、藝術、科學,甚至足球,表達某些東西。快樂源于找到一種表達方式,同時贏得認可。
斯:童年也可以說是這樣嗎?你寫過“把我的童年還給我”和“現在我確定我懂得如何做一個孩子”。
扎:孩子當然不知道自己是孩子。但我的童年并不凄慘。我想很多人都夢想著回到童年,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都知道。有時我們只有在童年即將結束時才真正體驗到童年。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們不知道用其他的方式來體驗這個世界。只有當我們成年后,我們才會經歷另外一種生活方式,更平凡、更立足于生存,然后才會突然意識到童年是多么珍貴。
斯:你夢想過回到童年嗎?
扎:不,這只是一種修辭。我的一些童年回憶似乎還留在我的心里,所以我的童年并沒有徹底消失。
斯:你多次寫到童年……
扎:是的,我并不是唯一說“沒有童年就沒有詩歌”的人。童年是生活的詩意。每個人都有作為孩子的天賦,有些人失去了,但另一些人保留著它。
斯:有些人認為詩歌的主題是愛和死亡。你的詩里有很多愛,但更多的是死亡……
扎:我沒統計過。我為去世的人寫過很多挽歌。當然,這是我對待死亡的方式,寫哀歌的人不會忘記有一天他也會逝去。從根本上說,挽歌是一種對抗死亡的姿態,它讓我們所寫的人瞬間得以復活。挽歌是一種安慰或重生的形式,因此它是一種與死亡的決斗:“把那個人還給我,哪怕是很短的時間!”雖然挽歌是關于死亡的,但它更是對抗死亡的。很明顯,有些詩我在其中思考的是:我的死亡可能會是什么;我想,這樣的詩我也沒有許多。
斯:你也寫過“逝者,你們是我的大師”……
扎:部分原因是,當我們去博物館或音樂會時,我們會遭遇逝者的現身:偉大的作曲家或偉大的畫家,他們可能已經逝世幾個世紀,卻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一個角色,這個角色不是慶祝死亡,相反,賦予我們以生命。人們經常聽巴赫,他帶給人力量。一個已經死去幾個世紀的人還能給人力量,這難道不是不可思議的嗎?!
斯:在《兩座城市》中,你寫道,人被分為定居者、無家可歸者和移民者。你認為繪畫是定居者的藝術,音樂是無家可歸者的藝術,詩歌是移民者的藝術。你覺得自己像移民嗎?
扎:現在不再是了。我想說,現在我很少是無家可歸的人,因為克拉科夫現在是我的城市。事實上,定居者就是那些從未離開過出生的地方,而且對那個城市或小鎮了如指掌甚至感到厭倦的人。對我來說,克拉科夫是一個新的城市,我十八歲到這里來學習,然后愛上這里。我也有出生在這里的朋友,他們會對我說:還記得這里原來有一個小商店嗎?……而我不記得了。有一個克拉科夫時代,我對它一無所知。我來到這里的時候幾乎是一個成年人了,而我不是那個“什么都知道”的克拉科夫教派的一員。
斯:但是后來,你離開克拉科夫很長一段時間……
扎:是的,那是由于當時現實的原因,因為愛情。我離開克拉科夫不是因為我厭倦了克拉科夫。有一個“熟練學徒期”的概念,很多藝術家都有過這樣的經歷。藝術家在中世紀就已經習慣在歐洲各地旅行——意大利、羅馬、佛羅倫薩。那些年是我的“熟練學徒期”,確實相當長,但它符合古典時代的模式。
斯:有人可能會說你的人生始于旅行。
扎:我還是個嬰兒的時候就受到了旅行的影響,在這件事上我沒有什么可說的。
斯:在你的詩歌中,錯位的主題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扎:是的,但不是馬上發生的。這個主題出現在我三十多歲的時候。我在父母和姑姑那一代人身上看到這一點,因為我沒有經歷過他們失去利沃夫的悲傷。我知道我失去了什么,但在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我在《另一種美》里提到過的阿尼婭是最悲傷的一個,她在職業上也不是很順。我父親在工作上很順,但他退休時,那種悲傷的感覺又回來了。不僅僅是我的父母,那一代人都不想回利沃夫。他們不愿損傷戰前留在記憶里的形象,他們再也沒有回去過。從與朋友的交談中,我發現這是一種常態。那一代人就是不想回去。
斯:很可能是因為它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城市?
扎:這會讓舊傷口重新撕開。他們不想再經歷那種痛苦。他們以某種方式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但直到最后一刻,他們都覺得自己失去了自己的母國。格利維策是一個如此偏遠的城市……
斯:你把格利維策形容為“一個平庸的城市”“一個丑陋的城市”“一個沉默的城市”。格利維策沒有好的東西嗎?
扎:那是有點夸張。我有時還會去格利維策,對此我的朋友們還有些責備我。可以說,我有兩種看法。我個人的看法是:我喜歡格利維策,很長一段時間里,它是我知道的世界上唯一的城市。但我也贊成我父母的觀點,那就是,作為一座城市,它更糟糕:“好吧,利沃夫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格利維策太平庸了……”
斯:你訪問過利沃夫嗎?
扎:是的,每兩三年都會去。
斯:所以,利沃夫神話仍然存在,但格利維策神話已經不復存在了?
扎:是,也不是。我曾回頭看過我的詩,它們更多是關于格利維策而不是關于利沃夫的!格利維策才是我真正的童年。我最初的發現和主要的經驗都出現在格利維策。利沃夫是后來才出現的,就像一個過去的祖國。
斯:二十多年后,你在2003年回到了克拉科夫。多少已經發生變化了?
扎:我看到更多的是沒有變化,而不是變化。我還記得我學生時代的克拉科夫,初到的那幾個月,當時我才過十八歲,仍是某種童年。每一次重新發現都是童年的一種形式。在那些日子里,我經常出去散步,探索不同的區域,我很興奮。克拉科夫的朋友告訴我說,“這座城市那個時候是多么灰暗”,但我看到克拉科夫美麗的一面,并且感受到它潛在的東西。我對歷史的存在相當敏感。我喜歡這樣的城市,你走在街道上就能感受到曾經發生的很多事情,有時那是可怕的事件,但這里存在一個歷史的維度。我也不是直接永久回到克拉科夫的。1989年后,我才可能回到波蘭,所以這不是什么衣錦還鄉。它分了幾個階段。變化發生后,我就想回去。
斯:你寫作詩歌和散文。有沒有什么主題?寫詩比寫隨筆更容易?
扎:沒有什么是“容易”的。我有時也想知道其中的區別,但我認為寫詩更像是一個未知數。隨筆是寫你所知道的題目,詩歌寫的是我們不知道的東西;詩歌是潛入那些未知的領域,隨筆可以傳達更多的學識。
斯:詩歌更感性,散文更理性?
扎:在某些方面是這樣,但這并不意味著詩歌不需要思想。詩對我來說更重要,如果必須選擇的話,我選詩。在我不能寫詩的時候,我就寫寫隨筆,但我也享受寫隨筆,這樣在寫作的時候,我就不會感到受罪。
斯:你有固定的寫作時間嗎?
扎:一般來說,我的工作時間是在上午;幾乎從不在晚上。快到中午的時候,就是一天的頂峰,最適合工作。
斯:你每天都寫作嗎?
扎:沒有。比如我現在就沒有寫作。從古時起我們就在夏天休息,那時世界最美麗,樹木郁郁蔥蔥;我們放下工作,休息一下,就像兒童的假期。我喜歡工作,它一點都不乏味。有時候夏天我也會盡力寫點東西,但通常不會。
斯:這很有趣,因為夏天常常出現在你的詩里。
扎:是的,因為我崇拜夏天,但這并不能鼓勵我去工作,我告訴自己生活并不全是工作。對我來說,夏天是享受世界的時候,我想盡可能多看看世界。
斯:你也多次寫過鳥兒:畫眉、燕子……
扎:……還有雨燕。我不是什么專家,但我喜歡鳥兒。比如說,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有一本小書剛剛由A5 出版社出版,克利尼茨基翻譯。我沒有聽說過他,但我看過他一首關于雨燕的詩,所以恩岑斯伯格也喜歡雨燕。我想你可以找到其他關注過鳥兒的詩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喜歡捕殺鳥兒的貓。
斯:你喜歡貓嗎?
扎:非常喜歡!
斯:你寫過一首詩叫《假如俄羅斯知道就好了》。你如何看待今天的俄羅斯?
扎:那首詩對我來說還是有意義的。我發現,有兩個俄羅斯,非常有趣:阿赫瑪托娃的俄羅斯,19世紀它就是那樣了;普希金的俄羅斯。我不認為其他國家像這樣具有分裂的個性,有如此精致的文化、文學和音樂。
斯:你是約瑟夫·布羅茨基的朋友。你能講講他的事嗎?
扎:我喜歡布羅茨基,我很欽佩他。我非常喜歡和他交談,我知道他也喜歡我。那段友誼,是發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之一。
但他也是兩面的,與俄羅斯的表現方式不同。一方面,他有出了名的傲慢;另一方面,他非常聰明,他也很清楚這一點。當他遇到陌生的新人時,他會立即判斷自己是否會喜歡他們。我想,他會馬上試著判斷一個人的智力,看他們是否會讀詩。詩歌是他絕對的關注點。如果他發現他們讀詩,那么那個人就可以加入“他的俱樂部”,一切都好說,但他也可能不喜歡那些他認定為平庸的人。說到藝術,包括詩歌,他是一個十足的沙文主義者,藝術和詩歌才是他生活的中心。
我聽說他傲慢到那樣的程度,跟美國人在一起時,他甚至也會糾正他們的英語。他是那樣強勢,以致他們不敢說:“約瑟夫,我們最清楚。”他的英語說得很好,但是偶爾也會使用過時的習語。每一種語言都有20年代流行過的習語,但現在它們都被放進了詞典里。布羅茨基會閱讀詞典,有時還會從中學到一些習語。但他一旦接受一個人,他就是一個偉大的、細心的、關心人的朋友,他會詢問你感覺如何,或者是不是生病了。
斯:你能想起和他在一起發生的趣事嗎?
扎:讓我想想……我想起一件無趣的事,我們都在美國劍橋的一個朋友家里過了一夜。他有他的房間,我有我的。他有嚴重的心臟問題。第二天早上,他躺在床上,我跟他說了幾句話。我看到了恐懼。他知道總有一天他的心臟會是他的死因,我還從來沒有見過他那樣。我看見一個嚇壞了的人;一個心臟埋有炸彈的人。他從未得到完全的治愈。我驚訝地看到他身上存在的焦慮,因為他在同伴中是那么的聰明,喜歡講笑話、喜歡大笑。
斯:布羅茨基熱愛美國。你呢?
扎:布羅茨基決定再也不回俄羅斯。他的英語說得很好,他對這門語言也有積極的興趣。對我來說,美國是一個季節性的地方。我當時住在法國,要去美國做一個學期的講座,我不想留在美國,因為我喜歡歐洲,我喜歡古老的城市。我喜歡我認識的美國人,但我從未想過要在那里定居。布羅茨基覺得在美國就像在家里一樣,他取得難以置信的成功,很快加入了精英階層。他是蘇珊·桑塔格的朋友,我覺得他們甚至有過一段婚外情。我也可能以某種方式被那個精英階層接受,但主要的區別在于,對我來說美國只需要做一個學期的講座,一年來一次。布羅茨基有護照,他是正式的美國人。盡管受到邀請,但他再沒有回過俄羅斯。
斯:立陶宛詩人托馬斯·溫茨洛瓦說,在美國會想念故鄉的建筑和古老的城市。你也一樣嗎?
扎:是的。我在德克薩斯州的休斯頓講學很多年,休斯敦是一個非常新的城市。我喜歡有中心的城市,比如克拉科夫有老城廣場,美國卻沒有。少數城市是按照馬格德堡規則建造的,但并不多。我真的很喜歡紐約,它沒有中心(盡管你也可以說它有中央公園)。在這方面,我就像溫茨洛瓦——我總是在尋找中世紀的東西,那是美國缺失的。我最喜歡大學圖書館:寬敞而豪華,你可以自己從書架上挑書。
斯:你做過翻譯嗎?
扎:我沒有這方面的天賦。我不知道如何把一首詩的文本熟悉到足以進行那種轉化。很遺憾。我試過很多次,但我不知道如何做好。
斯:你讀過你的詩歌的譯本嗎?
扎:讀過,但是還不夠。我對分析翻譯沒有太大的熱情,所以我不能強迫自己那么專心地去讀,所以有時書里也會出現一些小錯誤。我的解釋是,我最感興趣的是我還沒有寫出的詩,某種程度上那些已經被翻譯的詩對我來說是死的。當我在詩歌晚會上朗讀它們時,它們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中。我認為這在詩人中是很常見的——強烈的寫作新詩的欲望,就像在證明,我們還活著,在形式上還活著。
譯注:
【1】本文是扎加耶夫斯基與斯維塔·古特金娜談話的文字記錄。斯維塔·古特金娜是莫斯科國立教育大學研究生,學習斯拉夫和西歐語言學專業,到華沙大學學習應用語言學。她兼職《波蘭文化》雜志俄羅斯版塊的編輯,該談話記錄稿即發表于《波蘭文化》。
【2】托馬斯·羅瑞茨基(Tomasz Ró?ycki 1970—),波蘭詩人、翻譯家,著有《十二個車站》《殖民地》等詩集。他把一些法語詩歌翻譯成了波蘭語。
【3】雷沙德·克利尼茨基(Ryszard Krynicki 1943—),波蘭詩人,翻譯家。主要詩集有《出生證》《一無所剩》《未被虛無征服》《歐洲之子》等。現居克拉科夫,與妻子一起主持A5 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