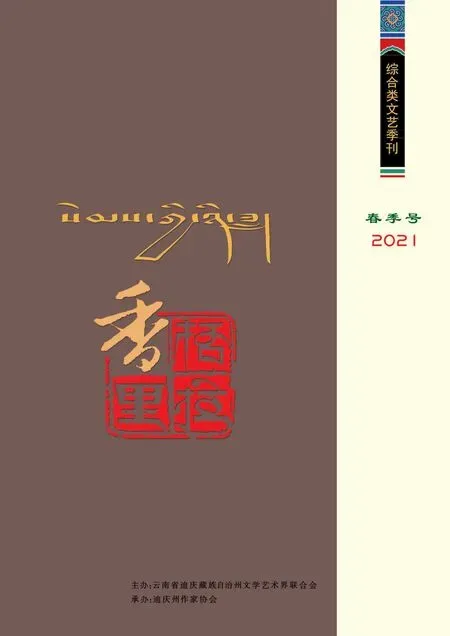故鄉大樹拴著我詩歌的馬匹——阿布司南文學創作論析
◎魏春春
故鄉大樹拴著我詩歌的馬匹——阿布司南文學創作論析
◎魏春春
阿布司南在小說集《雪后的陽光》的《后記》中提出他的寫作觀,“只要不停地寫下去,我們就創造了很多連接在一起的文字, 我們的價值也就充分地體現在寫作里……寫作著也是十分幸福的,這同生活著、愛著是十分美好的一樣,在我們的生存中也顯得無比重要”,寫作是一種生活態度,是一種美好的生活。這就與博爾赫斯所言的“我寫作, 不是為了名聲,也不是為了特定的讀者,我寫作是為了光陰流逝使我心安”,具有相似的寫作態度和寫作情趣。阿布司南在名為《只要》的詩歌中又一次談及他的創作觀:
只要有書 / 我疲倦的靈魂 / 就不會流離失所 //
只要有筆 / 我歌唱的翅膀 / 就不會悲哀地墜地 //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 以愛與善良播種 / 而不問去收獲什么 //
哪怕冷漠如西風漫卷 / 相信會有綠枝 / 穿破沙漠 //
哪怕孤獨如黑夜不散 / 只要有信念 / 如星光閃爍 //
在詩歌中,我們能看到一位堅韌的寫作者的形象,在書中尋求寄托、慰藉靈魂的所在, 用手中的筆展現世界的愛與良善,相信世界的美好,堅信人心的美麗。實際上,所謂的“書”包羅萬象,他生命中所經歷過的、接觸過的一切皆可稱之為書,那是人生的書卷, 是心靈的書卷,若我們單一地將之理解為圖書的話,我們就難以理解他念念不忘的歌謠開始的地方,難以理解他曾深情謳贊過的“故鄉大樹拴著我詩歌的馬匹”。由此,我們就能發現阿布司南持續四十余年的文學創作還能保持強勁的創作力的原因,大概就在于“只要有書”“只要有筆”的“只要”。
總體上看阿布司南的文學創作,從時間上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20 世紀 80 年代的軍旅文學創作,主要是詩歌方面;第二階段是 20 世紀 80 ~ 90 年代,更多的是20 世紀 90 年代創作的詩歌和小說,主要展現的是在改革開放的經濟文化語境下,周遭的人、事物所發生的變化以及自我思考的蛻變歷程;第三階段是 21 世紀以來,阿布司南對民族性的地方性的歷史文化的梳理,表現出阿布司南力圖疏通文化血脈,建構文學骨骼的努力,主要體現在詩歌領域。由此來看, 在阿布司南整個的創作生涯中,詩歌是其中最為持久的文體,也是他最為著力的文體, 因此,我們的分析也主要是從詩歌方面加以展開,間或涉及小說。
一
阿布司南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有過五年左右的軍旅生涯,這段時光打磨了他怎樣的心性,由于未見相關資料,我們不能妄加論說。但在此期間,他寫作了一大批詩歌作品,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他的青蔥歲月的一把鑰匙。
阿布司南服役于當時的昆明軍區,在部隊主要從事新聞采編工作。這透露出的信息是,第一,阿布司南參軍后較為出眾,或者說他已經表現出文學創作最起碼的文字寫作能力;第二,阿布司南參軍入伍正值中越武裝對峙時期,戰爭的硝煙彌漫他整個的軍旅生涯,他對生命、榮譽、和平、友情等等的理解是我們無法企及的;第三,部隊的采編工作要深入一線,直面戰士的容顏和心靈, 并且要在短時間內編發出來,這鍛煉了阿布司南敏銳的觀察能力和敏感的職業心理,這對阿布司南整個創作生涯來說至關重要,這是成為一個作家的基本條件。五年的軍旅生涯,阿布司南見到了此前從未見到的景象, 也激發了他的軍旅文學寫作熱情,在詩集《我的骨骼在遠方》中,他采錄了 1980 年創作的15 首詩,以緬懷那一段激情難忘的歲月。
阿布司南的這 15 首軍旅詩歌,涉及到他軍旅生活體驗的多個方面。第一是對純真戀情的描述。20 世紀 80 年代一大批青年走進軍營,奔向戰場,引起了多少少女的崇拜,她們通過各種渠道與青年軍人建立聯系,表達她們的愛慕,放飛她們的情愫,在《靜夜》一詩中,阿布司南描述了一位姑娘思念心上人的景象,寧靜安詳的夜晚,一位“捧起一張英俊的彩照 / 緊貼在突突的胸口 / 閉上深情的眸子 / 兩頰卻滾燙滾燙”的姑娘的形象躍然紙上,阿布司南采取剪影式的寫作方式,擷取生活中的一個片段,展現姑娘對戰士的思戀,這種寫作方式是中國古典詩歌中常見的方式,如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中通過女性思念游子的片段,間接展現游子對愛人的思戀,李白的《子夜吳歌·秋歌》中的“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不直接寫邊關將士對閨中人的思念,而是通過女性對男性的思念,含蓄地表明將士們的思親之情,若由此來看,阿布司南的《靜夜》應該理解為是雙向的思念,而非是單線性的女性對戰士的情感,這樣就雙線互動地聯系起男女青年在特殊的環境中對于彼此的想念,以及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展現出對戰爭贏得和平的期盼。
第二是對戰爭的反思,在《在戰爭舞臺上》阿布司南通過刻畫一位戰士的犧牲展現出中國軍人大無畏的革命犧牲精神以及中國軍人對于和平的無比珍惜,戰爭不是演出, 是血淋淋的犧牲、是轟隆的槍炮、是未知的莫名的消失,但是戰士們追求的卻是和平,“請你對世界愛好和平的觀眾說 / 在戰爭舞臺上 /所有身背沖鋒槍的中國演員 / 都能在鴿子悠揚的哨音中/ 表演出這般氣貫長虹的壯舉”, 通過勝利獲取和平,這顯然是一個悖論,人們珍視和平,厭惡戰爭,但為了求得長久的和平,不得不投入戰爭,這對于年輕的阿布司南而言,在他充斥了革命英雄主義的內心中隱約包含著對戰爭的復雜認識。因此,在《太陽·月亮·生命》中,我們看到了哭泣的詩人, 他在為死去的鮮活的生命而哀悼,但這無不意味著他的情感哀沉,更多的是為情感的升華作出了鋪墊,“那光、那色、那彩 / 與昨天不同了 / 這是一個新的太陽 /——一個新的生命”,因為“無數次死亡/ 無數次再生”, “這就是生命的內涵、意義”,這是一種向死而生的精神。
第三是對將士們英雄形象的贊頌。殘酷的戰爭給將士們帶來無盡的傷害,或傷殘或犧牲,面對戰友的傷亡,阿布司南情難自抑。在《綠茵場邊站成一尊雕像》中,他為我們塑造了一位 20 歲的軍官球迷的形象,生動地展現出作為軍官的年輕人在戰場上指揮得力, 奮勇殺敵,因傷致殘,“右腿空空蕩蕩空空蕩蕩”,這使得他無法在綠茵場上“阻截盤球傳球飛起鐵腳射門”,軍官贏得了戰爭的勝利卻失去在綠茵場馳騁的機會,在人生的斗場上,英雄的軍官“擁抱女友又推開女友”, 倔強地“拄著杖”繼續做著“球王夢”,他的肢體殘缺了,但他的靈魂是完整的,他要贏得自己生活的勝利,而非在別人同情的目光中走完余生,因此,他“站成了一尊雕像站成一個馳騁的意象”,永不言敗,永遠執著于自己的理想。至于永遠倒在戰場上的戰友,阿布司南在《祭酒》《永恒的年齡——寫在中甸烈士陵園的墓碑前之一》《墓碑——寫在中甸烈士陵園的墓碑前之二》等詩歌中, 展現出對濃郁的袍澤之情,杯酒寄懷,令人心傷,他指出“可怕的遺忘和淡漠 / 是黃土和白骨的真正不幸” ,如果我們以及后來人忘掉為國捐軀者,就會“發生脊骨般的塌方 / 鴿子便找不到歸宿”,如魯迅所謂的“中國的脊梁”一旦坍塌,中國人的自信力就直接受到傷害。
不同于同一時期的作家們集體式地經受歐美文藝觀念的洗禮,20 世紀 80 年代的阿布司南沒有直接經歷理論和方法的塑造,他的文學第一課就是直面戰爭的殘酷、死亡的慘烈,生活實踐讓他對于和平產生了一種持久性的關注,他渴望和平,希望享有和平生活的人們能夠牢記為了和平而獻身的那些英雄人物。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阿布司南洋溢著革命英雄主義的激情,或者說帶有濃重的英雄情結。
二
1988 年阿布司南結束了軍旅生涯,轉業回地方工作。近鄉情怯可能是此時的阿布司南最強烈的感受,他回到熟悉的地方尋找記憶故鄉的痕跡,他試圖以歸來者的身份重新展現故鄉的容顏。于是,在詩歌《人在旅途》中, 阿布司南為我們呈現出他的鄉情逐漸深沉的過程,當他“把家園里的情感裝進行囊 / 去感受外面無奈的世界/ 行程一頁頁都很精彩”, “在希望與失望的列車上 / 漸漸理解鄉情和遠方”,行走在人生旅途中的詩人恍然意識到, 遠離的故鄉就是遠方,返回就是親近遠方的方式,就是詩情勃發的基礎,因此,回家就成為阿布司南這一時期最為重要的文學主題。
但“堆積在履歷里”的過往,不會隨著返鄉而被拋灑在風中,而是豐富了人們的情感和記憶,于是,阿布司南在《風在緩慢地吹》中,表達出自我心靈畫像的構建過程。“我是一把傾斜的梯子”是阿布司南對自己這個遠游的還鄉者的最切近的認識,所謂的“梯子”連接的是阿布司南不同階段的生命記憶,而此時的阿布司南的“梯子”大概有兩組,連接的是三段體驗,第一截“梯子”連接的是少年阿布司南與軍人阿布司南,戰火中淬煉了他的精神品格;第二截“梯子”鏈接的是戰士阿布司南與轉業安置干部阿布司南,他要回歸日常生活,“烈士成了橋梁”,他心中蘊含著要讓“烈士”為之奮斗犧牲的人間生活更美好的希望,他期待歲月靜好,于是“烈士通過我進入了永生”,但現實生活的瑣碎與平庸,讓阿布司南生發出原來在生活的舞臺上“小丑通過我贏得了虛榮”。那么“我” 到底是怎樣的面相呢?阿布司南意識到“我認不出這些 / 擦肩而過的人就是我自己”, 我們的生命在時光中流逝,我們的容顏在時間之河中不斷變化,我們在人世間每個人都是自己生活的梯子,我們追求“把自己 / 送往高處”的理想虛構,但實際上我們又都在“梯子”的世俗一頭,或者說我們就徘徊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有時離理想近一些,有時離現實近一些,但無論如何,我們生命中“梯子” 是無法逾越的橫欄,就像我們不能揪著自己的頭發把自己從大地上拋出去一樣。基于此, 阿布司南認識到返鄉者最直接面對的就是立足故土的自己,就要塑造重新走進故土的自己,因此,阿布司南開啟了一段嶄新的故鄉人事物的書寫篇章。
阿布司南首先塑造的是“巴東村 我的出生之地”的景觀。這是他的血脈臍帶所在。阿布司南在這里接受了最基本的教育,經歷最初始的人生體驗,也經受了最早期的身體塑造,“祖國 太陽 母親 大地……”等等不只是書面的字詞,更是浸透到他骨子里邊的伴隨他同生共長的原初記憶,因此,他形象地說“讓我給你們打個簡單的比方吧 / 你們看校園松樹上有個鳥巢 / 我就是那只依依鳴叫的雛鳥/ 繞樹之匝 遲遲不肯飛去”。由此出發,他重新審視故鄉的雪山、草原、河流、山風、疾雨、綠樹、紅花、神鷹等等一切帶有泥土氣息的存在,展露出一種特別的溫情,即便是寒冬侵襲下的鄉村依然能給我們帶來溫暖的感覺,這也是阿布司南這一時期詩歌中常見的寫作方式,不因故鄉的貧瘠而須臾喪失對故鄉的深深眷戀,那是兒女對故鄉大地母親的愛戀,也就是他所謂的“故鄉大樹拴著我詩歌的馬匹”。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阿布司南畢竟沒有回到巴東村生活,他生活于城市,體驗著現代生活的喧囂與浮華,如同所有的現代人一樣,他陷入了精神與物質錯位的困惑。對于阿布司南一樣的從鄉土走進城市的人們, 城市有物質的誘惑力,可以滿足人們日常生活幾乎所有的物質必需品,人們可以獲得衣食無憂,前提是擁有足夠多的流通貨幣,由此, 貨幣或者說金錢就成為城市生活富足的重要指標,但是人們的精神世界似乎又不是完全依靠金錢能夠獲得滿足的,這幾乎是生活常識,但我們就是在這種常識中依然固執地鑄造城市生活安逸富足的迷夢。事實上,巴東村如中國的大部分鄉村一樣,在城市的龐然大物面前,顯得那么的微小、那么的微不足道,但在阿布司南的眼中,巴東村是精神的慰藉之地,是情感的療治之地,貧困的鄉村是精神富地,富裕的城市是精神洼地,當然, 這是相對而言的,而且對此有切身感受的更多的是從鄉村走向城市的人群。阿布司南恰巧屬于這一類,于是,在詩歌《走在街上》, 阿布司南看到的是“走在街上 / 人們在想什么 / 都皺著眉頭 / 像哆嗦瘦弱的病鳥”, 即便是“天空晴朗”,但城市“陰郁而單調 / 色彩和人們的心一樣 / 缺乏豐富”。生活在城市中的一些人“在夾縫里擠來擠去 / 擠出生活的必需品 / 養家糊口”,生活似乎只是為了活著而奔波,“最好的日子是漲工資 / 在每一個生活的角落里 / 物價依然是人們最關心的問題”,瘋狂的近乎本能的生活似乎成為城市生活的整個狀態,“人們已經忘記了活著為什么/ 人們更關心活著不缺少什么”, 于是,與“活著”暫時沒有直接沖突的一切都被我們視而不見,是“因為人們無知嗎”, 阿布司南顯然不這樣認為,更多的應該是“還來不及關心這些”,因為“為了活下去 / 就得向生活拼個勝負 / 拼出錢來 / 拼出想要的一切”,但這樣的生活,其意義和價值何在呢? 阿布司南發問“在每一條街上 / 在每一塊廣場方石上 / 在每一個站牌上 / 在候車室和進站臺/ 等待著我們的/ 該是怎樣的生活呢”, 或者說這樣的生活值不值得我們珍惜和眷戀呢。一般而言,我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但真正落腳到每一個的生活中,我們又該如何抉擇呢?這實際上是,阿布司南給我們每一個人包括他自己提出的一個有關生命價值和生活趣味的話題,值得我們深思。
阿布司南的解答頗帶有浪漫色彩,“不知道是誰 / 在一個難忘的瞬間引領我們 / 越過千山萬水 / 讓夜晚充滿了輝煌的幻覺”, 白日里的城市難以產生如是的夢幻,唯有在暗夜遙望星空,才能產生出“讓我們回到故鄉吧”的想法,“從今有一駕帆船 / 紅色的帆與碧綠的草場”,這是夢中出現的景象, 這是對抗現實生活的一種想象,我們的“天空、雪花和星星”只能在暗夜悄悄地溜出來慰藉我們疲憊的心靈,如同酒神狄俄尼索斯一樣在星空照耀下的篝火旁縱情釋放,一旦白日來臨,所有的這一切瞬間安靜下來,蟄伏下來, 我們又依從生活的倫理投身現實的種種。無疑,阿布司南的藥方并不能解決問題,但卻能讓他獲得暫時的休憩,以應對生活的冰冷。
因此,詩人阿布司南又面臨著鄉村與城市間的“ 梯子”, 在城鄉之間游弋, 尤其是在兩種生活倫理中游弋,鄉村是歌謠產生的地方,城市是流行更迭的空間,鄉村可以蜷縮在人們的夢中,城市只能延展在我們的眼前。
三
可能在思考“梯子”問題的同時,阿布司南開始了他的小說創作。收錄在《雪后的陽光》中的 15 篇小說,據阿布司南說,皆是創作于 20 世紀 80~90 年代,查閱資料得知,《智者扎巴》刊發于《西藏文學》1994 年 1 期,《鄉長判婚》刊發于《西藏文學》1995 年 6 期,《望盡天涯路》刊發于《西藏文學》1997 年5 期,《外遇》《失落》《神秘的鬼樓》(刊發名為《鬼樓》)刊發于《西藏文學》2000 年 4 期,《香格里拉夜總會》刊發于《西藏文學》2002 年6 期,又根據他的生活經歷,這些作品應該是他轉業之后創作的成果。
阿布司南的小說批判性和反思意味非常強烈。所謂的批判性,指的是阿布司南站在現代文化的立場上對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習以為常行為展開激烈的批評,凸顯某些約定俗成行為的不合理,表現出人文啟蒙的特點。所謂的反思性,指的是阿布司南對生活中的一些現象表現出濃重的好奇,希望還原事件發生的過程及其生成的內在依據,把握住隱匿于其后的某種文化質素,并在現代生活的背景下對之予以認識和解讀。
小說《望盡天涯路》包容性非常大,主要展現的是偏遠地區的婚姻生態。作品中的“阿爸”嗜酒、豪爽、風流,他精力旺盛, 經歷豐富,參過軍、剿過匪,是村莊中少見的有見識的人。盡管“阿爸”丑陋,但在村莊中的女性們的眼中,這是真正的男子漢的表現,甚至“在阿媽的眼里風流成性的阿爸比那些縮在老婆褲腰帶邊的男人強一萬倍”。盡管“阿爸”懷疑二姐不是他的骨肉,平時對二姐“惡聲怒氣”,但同意楚姆上學、不干涉楚姆的自由戀愛,似乎又表現出“阿爸” 所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現代觀念。但是當“阿爸”與“黑胡子”在酒桌上定下楚姆與桑培的婚事后,為了完成自己的諾言,“阿爸” 并不理會女兒楚姆的感情,也不在乎女兒的感受,以暴力抓回了并且將她鎖起來,在完婚的當天,“阿爸”自制工具將楚姆捆綁在“大”字型的桑木扁擔上,助力桑培完成了對楚姆的強暴,認為完成了作為家長的職責,也實現了作為家長的權威。至于作品中的其他人, 似乎都是“阿爸”的幫兇,即便是最為疼愛楚姆的“阿媽”面對楚姆的婚姻,也只是說“虧了我的楚姆”,而在成親時面對二姐的反抗,“阿媽不停地哆嗦著向黑胡子打招呼”以示歉意,也就是說,在家人的眼中,楚姆只是他們獲得別人尊重的工具,至于楚姆的生活幸福與否,似乎與他們無關。這種類型的小說在 20 世紀 20~30 年代中國現代啟蒙文學中最為常見,解放區文學中的扛鼎之作《小二黑結婚》也屬于這種類型,20 世紀 80~90 年代,所謂的偏遠地區仍然存在這樣的現象,這說明家長權威在 20 世紀的婚姻生活中并未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消退,而是以另一種面貌展現出其野蠻性和強力性。因此,阿布司南的《望盡天涯路》讓我們感受到 20 世紀 80~90 年代偏遠地區婚姻生活的駁雜與無奈,文章結尾的“好了”“妥當了”似乎在提醒我們注意所謂的“好”和“妥當”指的更多是家庭乃至家庭間的關系, 而無關年輕人的幸福。而在這樣的環境中, 楚姆的反抗注定無法成功,注定她的婚姻生活的坎坷。
順延《望盡天涯路》的寫作思路,阿布司南又創作了《生命谷》和《失蹤的生活》, 反映的都是女性婚姻生活的不幸。《生命谷》呈現的是扎西取初成婚后的愛情遭遇,《失蹤的生活》展現的是此里卓瑪追求愛情的坎坷遭遇。扎西取初被譽為伊拉草原上的杜鵑花,但婚姻不幸,嫁給了酒鬼扎西農布,盡管作品中沒有言明此樁婚姻的緣由,若結合《望盡天涯路》大致可以推斷出其中的緣由, 不外乎是父母之命之類。扎西取初能干漂亮, 但酒鬼丈夫的無所事事,使得家庭生活難以為繼,為此,她幾經掙扎,順應了嘎崩的愛欲,盡管她的借口是為了擺脫家庭的貧困, 實際上是在為無愛的婚姻尋求解脫的理由, 最終扎西取初因難產而死。扎西取初勇敢地追求可能的愛情生活,是在報復生活的無情和無奈,最終,她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此里卓瑪為了擺脫村人的風言風語,到城里尋求姨媽夫婦的庇護,曾經的桃色新聞始終追隨著此里卓瑪,讓她始終卑微地活在姨媽鄙視的目光中,為了討好姨媽,此里卓瑪不斷地改變自己,盡管鄰居們對此里卓瑪夸贊有加, 但她卻感受到自我的逐漸喪失,生活的貧乏與單調,直至遇到農布旺堆,此里卓瑪的生活才在愛情的滋潤下綻放出光彩,不幸的是, 此里卓瑪遇人不淑,決絕地離開城市,回返家鄉,決定走出別人預設的“虛假的背景” 而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堅守著心里那個真實的背景”。這或許就是阿布司南所理解的女性應該有的生活樣貌,遵從內心的選擇, 走出屬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及至《香格里拉夜總會》,阿布司南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講述了一位現代都市女性的情感波折,堅信愛情純潔的則吉,既無法忘懷愛人格茸的溫情, 又無法忍受格茸混亂的私生活,在幾經周折之后,她決定拋棄由來已久的世俗觀念,熄滅心中“黑色的火花”,服從內心的召喚, 接納格茸的愛情,與格茸共建一段全新的純潔的嬰兒般的愛情生活。這說明,阿布司南意識到阻礙女性走向幸福的不僅僅有傳統的習俗,還有在生活過程中自我形成的某些病癥似的阻隔,只有拋開這些外在的強加于女性身心的因素,女性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
阿布司南關注社會生活中的一些嚴肅的話題,諸如社會強權導致的社會不公等問題。關于社會強權,阿布司南側重指的是在特定的社會格局中,有部分人獲得了更多的社會資源,進而希望以此為基礎再獲得全新的權利空間,以滿足個體的心理欲求,就是所謂的欲壑難平。《智者扎巴》中扎巴為了得到部長的職位,無所不用其極,手段隱蔽而卑劣,將有真才實學的澤仁攆走,霸占澤仁的勞動成果,結果到頭來因激動過度,在接到部長任命的當天晚上腦溢血突發而癱瘓了, 盡管阿布司南殘忍地設計了扎巴的結局,但在實際生活中像扎巴這樣的官僚往往大行其道,因為他們巧妙地抓住了人性的特點,借助世俗的力量、社會的輿論獲得自身的利益。另一部小說《何處覓天涯》同樣展現的能者受壓的故事。炮兵團長茨仁品楚通過努力將瀕臨破產的農具廠發展成有影響的現代企業, 卻觸及到了某些當權者的利益,為此受到排擠甚至被迫離開農具廠,其結尾同樣是茨仁品楚離別時受到群眾的歡送,似乎這樣就能體現出茨仁品楚的才干在社會強權面前的失敗,在人心中的勝利,表達出阿布司南的批判鋒芒和建設意圖。但事實,這兩篇小說的結尾皆是失敗的,原因在于阿布司南只就現象本身展開敘述,而缺乏對敘述生成的歷史文化原因和社會人文語境的深入挖掘,因而憤青意識濃烈而深層次的建設不夠。
可能是阿布司南吸取上述創作不足的教訓,及時扭轉創作方向,將目光投置于他最熟悉的日常生活。顯著的表現是發表于《西藏文學》的一組短篇小說,分別是《神秘的鬼樓》《失落》《外遇》。這三篇小說涉及到我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一些略顯尷尬而又值得深思的話題,如《神秘的鬼樓》關涉的“鬼樓”,實則展現的是對社會顯貴的辛辣的嘲諷, 建房蓋樓本來是為了為職工謀福利,但卻被社會強權者強行霸占,民間智慧中的“鬼” 一登場,擊敗了人心之中的“鬼”,最終使得“樓”回歸到正常的使用渠道,順應了民眾的心理期待和社會訴求;《失落》展現的是家庭生活中“羞恥”的問題,父母與子女之間談性色變,性的話題是家庭禁忌,但有時家庭生活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即便是茨仁扎西偷窺父母房事遭毒打而自殺,也不能平息父親的怒火,父親竟然對死去的兒子大打出手,以維護家長的尊嚴,這樣就表現出少年正常的性期待在社會秩序中的被閹割和被傷害;《外遇》涉及到的問題是精神或靈魂外遇的問題,在阿布司南看來,所謂的外遇, 尤其是心靈外遇,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妥貼地安置靈與肉,才是我們每個人必須面對的問題。這三篇小說談論的話題皆不大,但都是關涉日常生活中心靈安放的問題,由此,我們會發現阿布司南從細微處著手、從人心的深層次來理解現實生活周遭境遇的文學努力。
阿布司南的小說作品數量不多,但帶有一定的問題小說的意味,這可能是他小說創作的主要價值。另外,阿布司南的小說語言非常有意思,很貼近地皮,很貼近日常生活, 這大概與他善于觀察生活,揣摩生活有密切的關聯,同時也體現出他的語言靈敏性。如《望盡天涯路》中“阿爸不論喚二姐干什么事兒嗓門都像糞桶那么粗”,慣常的人們說嗓門粗, 其中的粗強調的是聲大和音硬,當阿布司南用“糞桶那么粗”來形象說明“粗”的樣態, 我們似乎可以想見阿爸言語的惡俗、粗魯, 已不是聲音大小和軟硬的問題,而是發自內心的對二姐的不喜歡;再如“他每喝一次酒就要帶酒客們到神秘的西藏觀光一次”,至于如何觀光、觀光內容如何,阿布司南付之闕如,但我們在閱讀中可以想象阿爸的豪爽、揮斥方遒、娓娓道來等等形態,另外其中的“每喝一次酒就要”說明這是阿爸生活的常態, 但酒客們似乎百聽不厭,又點染出酒客們生活的封閉,阿爸千篇一律的言談似乎撬動了鄉村日常生活的巨石,但在后文中,我們發現這種閱讀想象是不成立的,鄉村固有的生活模式實際上消泯了阿爸的神奇言談,他們之間達成了一種新的更為密切的和解,這就為二姐命運的悲慘鋪墊了基礎。至于在其他作品中,阿布司南往往能根據特定的語境以較為恰當應景的方式展現出人們日常生活的形態,表現出他強大的語言模擬和再生能力。
四
21 世紀以來,阿布司南的創作主要以詩歌為主。這一時期,阿布司南注重原鄉式的詩歌書寫,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個人心靈的自我精心營構,另一個是自我民族地域文化身份的自覺建構。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現象,一方面是阿布司南在尋求適合自己表達的詩歌語法體系,漸次走向了情思的內化之路,他開始拷問個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探究個人內心深處的悸動,試圖對自我進行深度地剖析,以堅定人生的步伐。另一方面的原因,21 世紀以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迅猛,一大批少數民族族裔的作家開始全方位地審視自己的民族身份,并立足各自的民族身份屬性創作了一大批深受讀者好評的作品,這對中國文學從業人員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大概是在這種潮流的推動下,阿布司南開啟了他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原鄉建設之路。當這兩種原鄉書寫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阿布司南的詩歌格調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阿布司南的個人心靈展現屬于心靈的囈語,是唱給自己的歌,他不斷地揉搓自己的情感,在想象的空間中不斷地展現自我的多面性,力圖從其中發現一個與眾不同的自己, 以確證自己存在的獨特性。這表現在他的一系列以夢為馬的詩歌中。
在《最初的記憶》中,阿布司南寫道“一個童年開始的幻夢 / 卻充其量只是世界向著 / 內心重新返回”,我們不斷地馳騁在生命的單行道上,我們不斷地向世界敞開自己,渴望被世界所接納,我們更多的是外向展示, 在阿布司南看來,我們的生命夢幻不在外邊, 而在內部,在我們的心靈深處,當我們慢行下來,回顧曾經,我們的心花就會復蘇,我們的藝術才能真正地撫慰人心,因為“命運的另一種象征/ 是春天里復蘇的事物/ 樹木、動物、流浪者 / 在這些復蘇的事物中”。在《遠離最后的懷想》中,阿布司南極力摹寫“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感啊 / 遠離你的日子里”, 他重點展現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因某事件而引發的情感波動,或者說是情感作為事件對于他的意義,情感在時間的長河中逐漸地剝離了情感生成的現實基礎,只留下了情感的記憶和情感的體驗,因此,咀嚼情感的記憶和體驗而產生的新的情感,是直觀自己最好的方式,當若干次這樣的情感行為產生的體驗疊加在一起,就具有了一定的厚度,就產生了迷離恍惚的感覺,以至于追問自己“我可以在夢中見到你嗎”,“你”帶有不確指性,若我們將之理解為是“我”對情感事件中的“我”的感知,就產生了現實之“我” 對記憶之“我”的塑造,也就是說人們就是在對“我”的不斷“懷想”中實現自我的暫時性生成,因此所謂“最后的懷想”中的“最后”只是相對概念,不存在永遠的“最后”, 就像不存在永遠的“現在”一樣。完成了對時間之我的認知后,阿布司南并未停止下自我認識的腳步,他繼續頑強地一次又一次地探究自我的秘密。
《某種微笑》中阿布司南為我們塑造了他的自畫像,“獨坐午夜 / 打開珍貴的標本 / 與一顆星遙遙相對”,其中最為關鍵的“獨坐午夜”和“與一顆星遙遙相對”的孤獨感, 但沒有疏離時空,反而產生了一種寂寥廣袤的情感質素,“獨坐”遙看孤星,不論如何想象,都難掩其中的悲涼之意;《幸福的事物》中阿布司南明言“世界上沒有幸福 / 有的只是事物短暫的形式”, 這是他的生命觀,我們所擁有的只有生命的當下,因此,幸福就是當下的感覺。至于《心靈的挽歌》則可看作阿布司南自我反思和自我建構類型的大成之作。關于往事,阿布司南以為“往事 / 縈繞著你 / 日子久了 / 便成了記憶的收藏品”, 那我們所擁有的只是記憶,只是記憶中的體味和感受,就像是在滴水成冰的大雪風飛的隆冬時節,圍坐在火爐旁我們慢慢咀嚼往事, 在回顧中即便是“眼睛里裝滿留戀”“情愫豐潤了生命”甚至是“延伸著希冀”,但我們終究還是會從沉思中回返到現實生活,在新的時空中再生成新的事件,在時間的河流中新的事件又會成為新的往事,由此循環, 直至生命的結束,所以“誕生在冬季 / 結束也是冬季 / 隨風而至又隨風而去”,這就是生命的軌跡。
阿布司南的心靈之歌盡管如訴如泣,悠長憂婉,盡管他不斷地追思自己的過往和自己的模樣,但我們還是會發現他的自我塑造更多的是對時間、對生命的反思,他極力要拓展個人生命的厚度,極力向人們展現出一個深邃靈動的自我。從另一方面而言,這類型的詩又缺乏與生活的互動,容易陷入自說自話的自我迷醉狀態,若找不到新的突破, 就會陷入不斷重復自我的境地。阿布司南由個體的反思延伸到民族地域文化的反思,他開始編織出一幅較為宏大的個人文化景觀, 實現了從個體向族群的躍遷,盡管還是以個體的心靈漫步為主,但畢竟走出了個人的逼仄空間,邁進了一個宏大的民族地域文化的空間。
相比較此前的故土記憶的寫意書寫,這一時期的阿布司南更注重故土的文化根柢的塑造,他試圖從根性的角度鋪展開他的文化原鄉的話語建設。創作于 20 世紀 90 年代的《奶子河》,阿布司南在詩歌中與歷史互動, 我們能明顯看到阿布司南站在當下實現歷史再現,或者說是歷史的想象,如“我聽到風在傳訴著經卷 / 古老的寺廟里有神的腳步聲 / 大地沉穩/ 一串經幡向另一串經幡打著手語”,就是說他是在場的存在,卻是個旁觀者。等到本世紀以來,阿布司南不再以旁觀者自居, 而是成為一個參與者,他甚至產生了再造某一歷史文化景觀的沖動,攜帶著這樣的激情與自覺,他創作了《走不出的河谷》,他想象族群歷史的容顏,“那時圖伯特人們被神山召喚來 / 他們的腳步就從這里穿過 / 起伏的荒原 / 最初的歲月”, 祖先闖入了神山,穿越了歷史的長河,堅韌地耕種著歲月的荒原, 最終鑄就了歷史的豐碑,這是后人出走的力量源泉,也是后人們永遠走不出的民族心理維系,民族的歷史基因鐫刻在每一個族人的心里,“在有光和無光的夜里守著河谷 / 生命的血液在深深的紅土層下奔涌”,導致“這些人知道或不知道 / 他們注定要與河谷相依為伴”,直到永遠。
云兒的舞蹈 / 在山巒上赤紅著臉頰 / 將長袖拋來拋去/ 走在山路上我視線迷離/(/《歲月之殤》)
在這可以與你們一同步入黑夜的黃昏 / 證明你們確曾緩緩地在那條碎石鋪砌的小路上 / 經過頭頂直達黃昏暝暗的臉頰 / 緩緩地吹奏著快樂的曲子 / 音符和歸巢的鳥兒集結在一起 / 明亮它們光滑的羽毛 //(《吹奏樂音的圣徒》)
在這樣的詩句中,我們看到了阿布司南對民族文化的自覺表達,或者說民族文化喚醒了阿布司南的文學自覺,他主動地矗立在民族文化的立場上進行文學書寫,倔強地開拓新的民族文學空間,“眾鳥遠遠地去了 / 最后一只鳥仍留在雪地上”(《雪地上最后一只鳥》)可看作是阿布司南新的自畫像, 他試圖做民族文化的守護者。阿布司南滿懷崇敬之情展現民族歷史的過往,解密那逝去的文化符碼,如“你奔騰抑或凝固 / 古老的通天河 / 消失了最后的聲音 / 很遠很遠的地方在呼喚著/ 有一個亙古的夢境/ 期待解釋”(《通天河》),“我們看不見你們 / 摸不著你們 / 只有一個遙遠而朦朧的聲音 / 自冥冥傳來 / 日夜撲打我們的夢 / 證明你們的存在 / 其實你們無時不在 / 無刻不在”(《血光照耀的四月》),歷史的榮耀與苦痛并存,這就要人們撥開歷史的迷霧,還原民族歷史的樣貌,引領出人們的民族文化自豪。
但是,若一味地沉溺于民族文化的歷史中難以自拔,一味地為民族的過往招魂,阿布司南的文學寫作就會進入到極端私己排外的狀態,阿布司南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 他“放下歷史的鋤頭”,匯入到火熱的現實生活,這就產生了他的《時光序列》和《歌謠開始的地方》。
組詩《時光序列》,以一個農業生產年為單位,刻畫生活在香格里拉大地上的鄉民們耕耘大地收獲幸福的溫馨場景,“我的鄉民穿著粗布衣衫 / 用犁鏵保護碗和純潔的感情 / 兩只手在泥土里勞作 / 而我們在春天里撒開 / 等待氣候把我們淪為 / 粒粒種子”, 在秋天“割青稞后的日子一片坦蕩 / 我看見成串的陽光 / 掛在鐮刀的鋒刃 / 晶瑩的汗水熄滅了疲勞 / 幸福流出新鮮的傷口”,在冬天“大雪覆蓋,鳥聲絕跡 /……我們煮茶當酒/ 一生的喜悅含在壺中 / 而往昔的情景橫在眼前 / 我們的掌紋和友人的掌紋 / 像最后的星星 / 妻和女兒始終圍繞在身邊 / 這是很平常的日子”,人們在續寫民族新的歷史,在展望民族生活新的未來,正是大地上的這些無名的鄉民們推動著民族的發展,由此,阿布司南突破了自我的民族歷史文化的藩籬,進入到更為廣寬的現實生活空間。
《歌謠開始的地方》是阿布司南目前最重要的詩作,從這首詩中,我們能夠看到阿布司南心靈跋涉的步伐,看到他以民族地域文化為根的文學新起點。在他的民族地域文化源頭的想象中,他構射出“皮膚黧黑,面部粗糙的人們,拿起 / 合適的工具去養活自己”,并且產生了文明的曙光,即“歌謠開始的地方,黑暗退去 / 地平線打開,多么新鮮”,由此掀開了香格里拉大地上文化的帷幕,傳說、故事、傳奇等紛紛產生,一代又一代口耳相傳,“房屋比炊煙更古老,現實比理想更管用”,生活在這片大地上的人們依靠這樣的認識建構著屬于自己的幸福,這一切的輝煌盡管“被反復地回想”,但終究“稍縱即逝”,阿布司南要尋找自己詩歌的“歌謠開始的地方”,既在民族地域歷史的土壤上, 又在現實生活的喧囂與浮華中,以此來夯實他詩歌的基礎,綻放情思的流光溢彩。至此, 阿布司南才真正完成他的原鄉心路歷程,也為他新的文學創作奠定了扎實的文化基礎, 也生發出他更深遠文學走向的可能性。
五
仁增旺姆認為阿布司南“早期的小說, 所寫的地域顯然是全然漢化的地域……因為他或她,無論外表與內在,都已經不像藏人”, “然后在后期的小說里,阿布司南找到了屬于他自己的講故事的方式……作為生活在 21 世紀的藏人,在這個充滿各種可能性的時代,以全球化和漢化為主的多樣性從未如此復雜地交織在一起,沖擊著早已失去了在自我封閉中保持寧靜的雪域高原。那么,用自己的方式講故事,即是在無比喧囂中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種觀點有些偏頗。
一段時間以來,有很多評論者、作家認為少數民族身份的作家應該展現本民族的文化生態和日常生活,這樣才能體現出民族性書寫的屬性。但是,文學是人學,是展現社會人的生存方式和價值取向的藝術方式,作家本人的民族屬性與他藝術作品是否展現本民族情態之間并無必然的關聯。作家張承志是新時期以來涌現出的優秀作家,他的作品充滿時代氣息,展現了新時期中國青年的生活情態,這和他的民族身份沒有必然的聯系; 吉狄馬加是享有國際聲譽的作家,他的作品也并不都是展現彝族文化生態,這并不影響他的文學創作的深度和質感。因此,作家尤其是少數民族作家有其民族身份,但并不是說非要在作品中展現他的民族標簽,作家取得的文學成就與其民族身份并無直接的聯系。我們以藏族作家達真為例,他的《康巴》展現的是生活在康定的各族民眾的生活方式, 不僅有藏族,還有回族,不僅有鍋莊生活, 還有草原爭斗,恰恰是他的融會貫通,展現出了康定獨特的文學景觀。再有藏族作家尹向東的作品也并非全是書寫藏族民眾的日常生活,而更多展現出在文化交融碰撞中不同人的多種面相。正如阿來所說,“我是藏人, 但我用漢語寫作”,言下之意,就是阿來并不否認其民族身份,但他的寫作是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展現當代中國人的生存樣貌,他是以中國作家自居,而非以藏族作家自居,即便是確定其身份也應該是中國當代的藏族作家,如是的限定說明這些作家并不局限其民族身份,而是在更為宏大的歷史文化空間中展現中華民族文化的時代嬗變、中國人的心靈沉浮。即便是生活在藏族文化濃郁的西藏和青海等地的藏族作家,如央珍、次仁羅布、梅卓、萬瑪才旦等人也并不局限于展現藏民族的生活情趣,但他們作品的質量也未見得受到影響。
另外,一些非某一民族的作家展現的關于特定民族生活的作品,也不見得沒有民族屬性,不見得沒有民族洞察力,如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反映了東北鄂溫克族民眾的生活變遷,同樣因其濃郁的文化深度和質感獲得人們的贊譽。
由此來看,阿布司南的作品尤其是小說作品展現的是藏地生活,但他更注重的是民族文化和習俗在當代語境中的文學表達和文化碰撞,即便是藏族民眾也是現代生活中的人,而不是人們想象中的縱馬馳騁草原、游牧快意人生的生活情態,因此仁增旺姆對阿布司南的批評是不成立的。從這個方面,我們也能看到阿布司南文學創作的意義,他突破了單一民族的文化藩籬,在更大的當代中國文化生活中展現現代人的生活旨趣和文化選擇,這是值得肯定的。
對于阿布司南 40 年創作歷程中的文學演進,我們要將之納入到具體的經濟文化語境中去加以辨析,將之納入到中國當代作家的序列來審視,這樣,我們就能發現阿布司南的文學價值,即以其內在的民族地域性拓展了中國文學的書寫范圍,豐富了當代中國文學書寫的立體性和多樣性,完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故鄉天下黃花的文學書寫。
本文是西藏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專項資金項“西藏當代文學幸福書寫的人民性話語實踐研究”(20BZW02)、西藏民族大學重點項目“西藏當代文學的人民性話語實踐研究”(20MSZ01)的階段性成果。
魏春春 山西懷仁人,文學博士,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當代藏族文學和西藏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