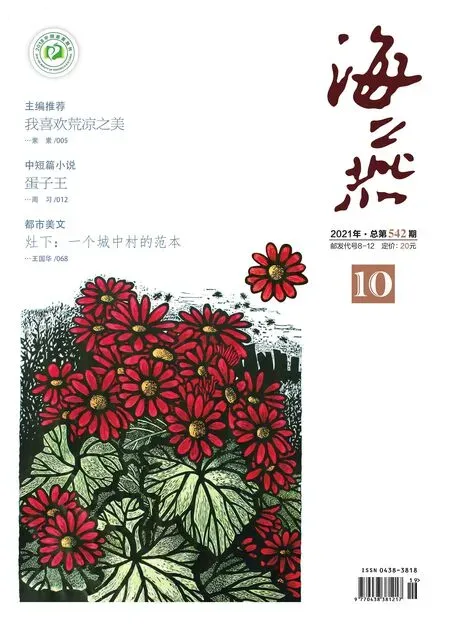父親的高地
文 李海燕
父親病了。
父親以各種忙為由,推脫不去醫(yī)院做檢查。三個(gè)月后,病情加重便只得去了醫(yī)院檢查。
醫(yī)生說住院吧。
父親說,家里有很多事脫不開身,能不能給我開點(diǎn)藥回家吃去?
醫(yī)生說,想活著,就得住院治療。
父親把目光轉(zhuǎn)向我,我拿著醫(yī)生開的單子去繳費(fèi)。
父親住院了,村里的齊瘸子父子一起來探望。他兒子手里拎著一些營養(yǎng)品。
齊瘸子坐在父親身邊,用袖子擦一把臉上的汗水,哥,你安心治病,跑腿兒的事有你侄兒。父親住院半個(gè)月,齊瘸子隔三岔五地過來,他兒子每天下班都來醫(yī)院幫著護(hù)理父親。
齊瘸子在村里最窮,父親做村支書這些年,他受益最多,就連他兒子考上大學(xué),都是父親幫籌的學(xué)費(fèi)。如今他兒子已大學(xué)畢業(yè),在縣林業(yè)部門做技術(shù)員,后來我們村的果樹栽培,新品種引進(jìn)等,沒少沾他的光,這是后話。
那天下午父親剛灌完腸,準(zhǔn)備第二天手術(shù),胡玉芬提著大袋小袋的營養(yǎng)品,匆匆趕來,進(jìn)了門就埋怨我,我哥病了咋不告訴我?又對(duì)父親說,哥,咱上省城的大醫(yī)院吧。同病室的人都以為她是父親的親妹子呢。
父親手術(shù)那天,胡玉芬請(qǐng)了一天假,和我們弟兄姐妹一起守在手術(shù)室外面,當(dāng)看到父親的被醫(yī)生割下來的大半個(gè)胃時(shí),胡玉芬泣不成聲,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滴滴答答地滾落下來。
當(dāng)年公社給我們大隊(duì)一個(gè)工農(nóng)兵大學(xué)生名額,大隊(duì)黨支部開會(huì)研究此事時(shí),大家一致推薦我去,可是最后父親拍板,讓沒爹沒娘的胡玉芬去了。胡玉芬?guī)煼懂厴I(yè)后,在縣一中教書,現(xiàn)在是縣一中的校長。
母親總說父親這個(gè)官當(dāng)?shù)脹]有一點(diǎn)親情味,私下里我們對(duì)父親也有微詞。我們姊妹六個(gè),除了小妹自己考了出去,現(xiàn)在鄉(xiāng)中學(xué)當(dāng)教師以外,我們五個(gè)都是普通的農(nóng)民。村小學(xué)經(jīng)常招民辦教師,也就是父親一句話的事,可父親這句話就是不肯為我們說。大妹十八歲那年有個(gè)改變命運(yùn)的機(jī)會(huì),公社的話務(wù)員調(diào)到縣里去了,母親讓父親找找公社領(lǐng)導(dǎo)給大妹求情,父親說死都不去,直到另一個(gè)村的書記女兒走馬上任,父親都一直沒去求這個(gè)情。
母親氣得一個(gè)月沒跟父親說話。
后來,大妹嫁得不如意。有一次父親過生日,大妹喝醉了,借著醉意,把自己對(duì)父親的埋怨都說了出來。
父親聽罷一聲不吭,只悶頭喝酒,直到把自己喝醉。
父親住院后,村里每天都有人來醫(yī)院看望父親,就連坐著輪椅的張茂都來了。不會(huì)說話的張茂,久久地握著父親的手,一個(gè)勁地?fù)u頭。
父親說,你不用擔(dān)心,我死了,我讓我兒子管你。
張茂干巴巴的眼眶里就有了淚……
一九四八年的中秋時(shí)節(jié),那時(shí)候仗打得挺兇,十七歲的父親和十八歲的張茂被國民黨抓了壯丁,被帶到葫蘆島港。父親說他肚子疼,經(jīng)一個(gè)當(dāng)兵的允許,父親鉆進(jìn)旁邊的一塊高粱地里解手,一直蹲到那艘大輪船開走。而張茂在海上被解放軍截了下來,他參加了最后的解放戰(zhàn)爭,后來參加了抗美援朝,被一顆炸彈炸沒了雙腿和聲音。父親常說,比起張茂,自己有腿有聲音的人生都是賺的,要是當(dāng)年他不逃回來,也和張茂一樣是國家的功臣了,說不定還為國捐軀了呢。
父親出院那天,我們下了公交車,他打發(fā)走二弟和三妹,把我留了下來。
我和父親坐在道旁的土楞子上,父親看著南山的槐樹林子,眉眼舒展開來。當(dāng)初規(guī)劃這片槐樹林的時(shí)候,父親剛過四十歲,土地承包制度剛開始試行,父親每天扛著鎬頭上山刨坑定位,直到滿山綠樹成蔭。此時(shí)槐樹剛剛冒出紫紅色的嫩芽,像一層縹緲的紫色的霧。
父親說,這片林子明年滿十五年了,明年秋天賣了,給村里修一條通往山外的大道,剩下的錢,把小學(xué)校修復(fù)一下 。
父親把目光轉(zhuǎn)向北山,北山整面坡是層層梯田,有油畫一般的層次感,那是父親帶領(lǐng)村民們一鎬一鎬刨出來的,那時(shí)候村民還叫人民公社社員。父親就是那時(shí)得的胃病,起五更爬半夜,饑一頓飽一頓的。
父親說,北山是咱村子的最高點(diǎn),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把我埋在北山頂上……我忙說,別瞎說,醫(yī)生說手術(shù)做得非常成功。父親笑著站起來說,回家吧。
村莊的新舊建筑就像一張對(duì)疊的紙,東邊是整齊的新房,西邊是參差不齊的舊房。按照父親的富村計(jì)劃,每年至少要有十戶人家翻蓋新房,蓋新房的人家,在東邊重起房基地。母親曾問父親我家啥時(shí)翻蓋房子。父親說,壓軸的都是最好的。
父親是第二年初夏去世的,癌細(xì)胞骨轉(zhuǎn)移,時(shí)年五十七歲,時(shí)間是一九九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