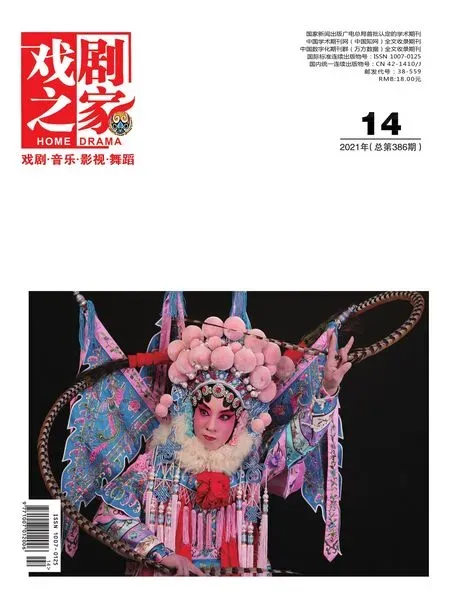藝術接受視閾下審美價值的動態之維
——芻議電影《梅蘭芳》的鏡像闡釋
孫姝怡
(北京城市學院 北京 100048)
作為完整的藝術活動,藝術接受決定著藝術文本的價值重塑、藝術創作者的情感反饋、以及藝術體驗的多聲部對話;從價值動態的實現角度來看,藝術接受闡釋了符號學視閾下的價值結構與主體心理圖式的動態價值之維,而接受主體這一動態環節,在創作者、作品與讀者、受眾這一長期割裂的兩端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從而展現出審美價值在接受鏈上被充盈的動態實現過程。本文將以陳凱歌的作品《梅蘭芳》為例,探究其人文符號背后的藝術抉擇與兩難困境,體驗其藝術創作與真實辯證的自我矛盾,透視其審美價值如何在接受活動中呈現。
一、價值發現熔鑄形式讀碼:實鏡映情的初探
藝術審美價值在藝術接受中的動態實現首先表現在價值的發現中。藝術審美接受中的價值發現是一種特殊的對象化投射,是審美情感的最原始激發,是隔離了現世之景與實用態度,全身心投入到藝術文本的誘導空間內而產生的獨特心理機制,也是對藝術文本語言與形象維度的解讀。在這個讀碼階段,是形象載體作為知覺的常態對象發揮著積極的能動作用的初始基礎,也是藝術接受審美心理生發的前提。
蘇珊·朗格曾言“在藝術中,形式之被抽象僅僅是為了顯而易見,形式之擺脫其通常的功用也僅僅是為獲致新的功用——充當符號,以表達人類的情感。”在電影《梅蘭芳》中梅蘭芳與戲影人生的“鏡花緣”終于落腳在舞臺上孤清的《夜深沉》之間。“輕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猛抬頭見碧落月色清明。”“鏡子”這一符號的運用,恰恰消融在臨鏡貼花的低眉不語中。影片中第一處“鏡語”特寫在十三燕與戲園老板的敘事段落中。以老板的外聚焦視點切入,揭開貌似和諧的三人共處關系,在鏡中窺探梅蘭芳與十三燕的對峙,以戲劇性的弧光燭見人性。鏡頭從十三燕的面部特寫開始進行層層遞進,景別的不斷推進,偏重構圖使得二人的戲劇張力不斷增強。落幅在鏡頭的深處,透過梳妝的鏡子隱約折照出十三燕的面影。鏡頭只是在戲劇性的“改戲宣鼓”節奏中潑墨畫式寫意新舊時代的交迭,而蘊藏其中的是十三燕不經意的特寫內聚焦視角,是那些被主流話語遮蔽的意氣風發后與深陷時代漩渦的苦楚掙扎。影片并未將時代的迭變凸顯于視覺畫面的交鋒中,而是用京劇的戲點與黯然的全景讓“斗戲”片段一氣呵成。一邊是鏗鏘有力的沙場之戰,一邊是凄情繾綣的思夫之曲,當最后的一場大戰在黛玉“花飛花謝花滿天”的浪漫曲調中悄然落幕之時,十三燕一生的京劇演出也在“定軍山”處儀式性收場。
第二處的“鏡語”則從一個降鏡頭配合搖鏡頭起幅,降鏡頭是指攝影機沿垂直軸線往下移,起一種揭示作用,而搖鏡頭也有揭示信息的作用,比切換鏡頭有連貫感。師徒二人在12 個鏡頭建立起來的對白很少,話語交流幾乎不存在,潛在或顯在的信息集中在“鏡”與“燈”中,一虛一實,兩人處于同一畫面的景深鏡頭,燈影處的梅蘭芳微光泛泛,而鏡影里的十三燕在最后的面影中一聲嘆息。師徒二人分處于前后景,在臨鏡對空妝的狹小空間內,是舊時代的婉然謝幕也是新時代的熠熠微光,在鏡頭內部的潛在對話框中,梅蘭芳的實景與十三燕的虛景在鏡像中形成倒置,呼應二人濃墨重彩的戲劇沖突已成定論,而鏡頭本身的內在張力已形成強烈的敘事節奏體系,在波瀾不驚的鏡像前潛流涌動。正如胡塞爾所言,“形象載體作為藝術品審美鑒賞的第一層面,是作為審美對象而存在的藝術作品的結構特性基礎”,而電影通過鏡頭結構與構圖畫幅以及從中體現出的和諧關照與感知,感受到心靈層面的快感。
二、價值再造序化空白解碼:鏡像人生的還原
價值再造是接受藝術中審美價值實現的中心環節。審美接受的價值再造是將藝術文本從物的王國帶入意義的王國,是在“看的方面純粹的美感經驗”激發的快感后喚起的均勻的情感。此時的藝術接受已經從對象材料的表層愉悅進入內在的情感體驗中,將接受主體自身原有的審美經驗、藝術旨趣作為衡量藝術文本的價值尺度,體驗接受之途的解碼階段。
首先,價值的再造體現在對文本中“空白”的填補與文本意義的解碼。接受美學代表人物姚斯認為“我們只能想見本文中沒有的東西;本文寫出的部分給我們知識,但只有沒有寫出的部分才給我們想見事物的機會;的確,沒有未定的成份,沒有本文中的空白,我們就不可能發揮想象。”影片中的“鏡”在虛實相生中“留白”了遐想的空間。“鏡”的實像定格在長鏡頭中孟小冬雨巷里的霧影,而“鏡”的虛像則是貫穿整部影片的梅雨田的紙枷鎖。對于紙枷鎖的闡述采取透明性的情節織體敘事,用梅蘭芳百老匯成名前的戲劇性結構展開故事。該段落以鏡前特寫入場,加入復調式的背景音與人聲,象征盛名下的梅蘭芳被囚禁的情感漩渦。而在閃回的兒時讀信段落,通過外場視角切入的形式,弱化敘事主角的同期聲,將敘事作為一種中性的抒情手段,留給觀眾“無痕”化的敘事空間想象。而此時接受主體離間了現世之境,沉溺于梅蘭芳如影隨形的自我矛盾中。在梅蘭芳走向樓梯選擇舞臺的一剎那,仰視鏡頭的高光沖淡內心的抉擇,滯留的時空使得接受主體沉浸于同頻共振的情感重塑中。
其次,價值的再造表現了價值接受主體的自由性。杜夫海納說“美并不象任何刺激物那樣生產刺激,它只是產生啟示,它調動整個心靈,使它自由自在。”對于紙枷鎖虛化的詮釋影像并非只是現實的漸近線,在梅蘭芳拒絕揭開“伶界大王”牌匾的片段,平移與全景的客觀鏡頭里不動聲色刻畫的是梅蘭芳對于紙枷鎖羈絆的反叛,而孟小冬的出現,采用移鏡頭的小景別變幻,除將鏡頭內部敘事本身的完整性打破之外,在空間上減少了接受主體對于同一空間多聲部的信息傳達過于繁瑣的視覺疲勞,使得二人的再次相逢在時空跨度上的隔閡符合影片節奏的期待視野。乾旦與坤伶難逃常態之若隱若現的牽絆,在全景鏡頭的落幅中給接受主體留下自由吁求的探索空間,而這種一氣呵成的靜觀與凝視不是單向度的,確切地說是藝術欣賞中自由價值的動態對話。
三、價值飛躍意旨符號組譯:心靈史詩的呈現
價值飛躍是接受藝術中審美價值動態實現的質的飛躍。在此階段藝術接受活動的價值運行是由審美觀照中的意象作用把握的,是建立在讀碼、解碼符號系統之上的藝術意蘊呈現。在組碼與譯碼的共同作用下,接受主體完成了秩序感與節奏感的確認,指引到一種脫離了現實常態的深沉而悠遠的境地。“人,詩意地棲居”,是接受主體超越自身所完成的情感與反思以及心理蕩滌的最高指示,也是接受主體感性與理性的和諧一致。于此,藝術審美接受動態實現最終的目的。
藝術審美價值動態實現中價值的飛躍體現于人的最終解放。馬爾庫塞曾言“藝術不能改變世界,但是,它能夠致力于變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識和沖動,而這些男人和女人是能夠改變世界。藝術對人的解放作用體現在通過改變審美者的心理世界來推進社會的變革。”影片中,梅蘭芳的一生濃縮于鏡中。特寫鏡頭下的臨鏡而照,是扮戲前的期許與沉入;拉鏡頭下的平視而照,是對內心紙枷鎖的反抗與心靈深處的自我叩問;全景鏡頭下對影三人的平移鏡頭,是對舊時代的昭示也是梅蘭芳對于自我時代來臨的慨嘆。對鏡悲吟是人類之通感,而在導演的組合鏡頭中,鏡賦予了一級“能指”符號之上的二級指示系統,在鏡這一物象的意蘊傳達中,第一層面的對鏡描眉與第二層面的“紅顏易老”構成一級指示關系;而昭示于心的時光流逝在第二層面變為能指,引導接受主體去關注第三層面即梅蘭芳對于“自我”到“本我”的超越之態。在逐層結合的二級指示系統中,“鏡”完成了心靈層面上生動載體的認知。影片中的鏡是無聲的,它于靜態摹寫之處將接受主體帶入靜觀與凝視的鏡語風格中,體驗時光回眸流逝之處一代名伶生命華彩之后的黯然沉穩與平滑;而鏡卻又是有聲的,它如同亞里士多德在《倫理學》中對于自我之鏡的反復叩問,“人應該如何度過他的一生”,在多聲部的同期聲攝入中,在戲劇主題的涉獵里,在“清如水,明如鏡”的視聽闡釋中,接受主體穿梭時間與空間的跨度仍能聽到“超我”的陣陣回聲,這是藝術審美接受活動中質的飛躍。
藝術接受中讀碼、解碼、組碼、譯碼往往是密不可分、相互包容的。依次遞進的四階段劃分,只是一種理論的抽象。而審美價值在接受活動中的動態實現過程從價值發現、價值再造到價值飛躍中審美標準完成超越以往的新的生產轉換。電影《梅蘭芳》采用“戲中戲”結構將歷史舞臺虛化、典型人物前置,摒棄了概括歷史史詩的宏觀巨制,將人物對影自照的紙枷鎖投入了共鳴式的關注。這種“平凡化”的傳記處理恰恰是對鎂光燈下一代名伶在歷史洪流中的內心審視重新觀照和結構,向審美接受主體忠誠的展現“隱藏在世界中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