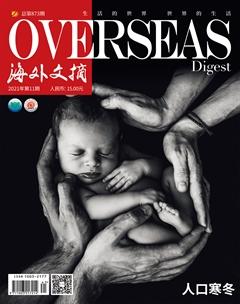突襲的那一晚
安德魯·奎爾蒂
|“9·11”事件以前的阿富汗 |
阿卜杜勒1965年出生于阿富汗中部省份瓦爾達克的謝爾托吉村,那里距離最近的高速公路有三小時車程。他父親靠種小麥、土豆、蘋果養家,后來,阿卜杜勒子承父業,繼續在同一塊土地上耕作。他小時候,阿富汗局勢相對穩定,經濟也不錯。
1979年,局勢發生了變化。蘇軍入侵,扶植了新的領袖,并和反共圣戰組織開戰。1980年,阿卜杜勒九年級畢業,和哥哥一起加入了阿富汗共產主義軍隊。完成七年的受訓任務后,他被派往坎大哈省,并一路成長為少校。
1989年,蘇軍撤離阿富汗,阿卜杜勒也隨之離開部隊。十年軍旅生涯,也是時候回家了。回到謝爾托吉,他沒多久就成了婚,妻子叫卡里瑪,也是瓦爾達克人。后來,哥哥們陸續出去闖蕩,他成了一家之主,一邊照顧年邁的父母,一邊種田。
1992—1996年阿富汗內戰期間,首都喀布爾在圣戰者的炮火下淪為廢墟,好在瓦爾達克山谷地區位置偏遠,并未受到戰爭的多少影響。后來,坎大哈興起一股力量,他們的成員自稱“塔利班”,意為宗教學生。塔利班反抗圣戰者的暴行,并最終入主喀布爾,但這并沒有對謝爾托吉的局勢造成多大影響。阿卜杜勒表示,當地的毛拉(譯注:精通伊斯蘭神學和宗教法律的人),有的被塔利班任命為指揮官,有的被任命為縣長,但“這些人是和我們一起長大的”。
塔利班掌權后確實有了一些變化,比如禁止播放音樂、男性必須留胡子。但當地大多數文化傳統,即使和塔利班法令相悖,也都延續下來了。如阿卜杜勒所說:“塔利班對大城市管控較嚴,但鄉下要寬松許多。謝爾托吉的婦女就可以種地、喂牲口,塔利班并不會因此找我們的麻煩。”
| 塔利班式微 |
2001年9月11日晚,阿卜杜勒在家聽新聞。兩天前,北方聯盟將領沙赫·馬蘇德遇害,新聞正在報道該事件對局勢的影響,沒多久就插播進來一條快訊:紐約和華盛頓兩地均發生了飛機撞擊大樓的事件。
不久,美國入侵阿富汗,塔利班垮臺,但在瓦爾達克的農村地區,人們依舊感受不到多少變化。美軍空襲的目標是塔利班和“基地”組織,主要集中在阿富汗東部和南部。塔利班失勢,喀布爾的居民載歌載舞,但在謝爾托吉村所在的戴米爾達德縣,人們完全看不到這樣的慶祝活動。阿卜杜勒回憶道:“當地的塔利班官員卸下頭銜,重新過起了老百姓的生活,僅此而已。”
塔利班主政期間,瓦爾達克局勢平穩,但當時內戰剛剛結束,又趕上大旱,日子并不好過。“塔利班主政期間挺好的,”阿卜杜勒說,“但經濟不行,我們那會兒比較樂觀,想著美國來了,經濟或許會有所好轉。”
美軍雖然進駐阿富汗了,但直到一兩年后,美軍裝甲車隊從戴米爾達德縣經過,阿卜杜勒才第一次見到美國人,車隊里還有一些阿富汗軍人。車隊自喀布爾而來,到了戴米爾達德的中心地帶會停下來,但不會久留。阿卜杜勒的二兒子納斯拉圖拉回憶道:“一開始,我們對他們既好奇又警惕,覺得他們看上去很奇怪。他們在路上看到行人,會停下來分發蛋糕和甜品。”
| 塔利班卷土重來 |
2003年,美國將戰略重心轉移至伊拉克。而阿富汗這邊,之前就有人對外來者懷有敵意,沒多久,一些人聯合起來反抗美軍,塔利班也隨之卷土重來。美國在瓦爾達克的軍事存在相當有限,塔利班游擊隊結合實際情況,采取打完就撤的軍事策略,騷擾往返于喀布爾和坎大哈的美軍車隊。與此同時,塔利班開始在多個地區招兵買馬,組建影子政府。
2009年,美軍加強了在瓦爾達克的軍事存在,向該地區派遣了2000名士兵。2010年,在奧巴馬的政策下,瓦爾達克的美軍數量只增不減。同一時間,塔利班招募成員的能力也快速增強。到了2011年,塔利班與美軍的斗爭愈演愈烈。塔利班甚至擊落了一架CH-47“支奴干”直升機,導致30名美國大兵和8名阿富汗士兵喪生,這是美軍進入阿富汗以來損失最慘痛的一次。美軍用大掃蕩反擊塔利班,還對其實施了夜襲、空襲和炮擊。2013年,美國駐阿富汗的陸軍特種部隊陷入人權丑聞,當地群眾對美軍的敵對情緒發展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為此,阿富汗時任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讓美國陸軍特種部隊撤出了瓦爾達克省。
戴米爾達德縣的塔利班指揮官奧馬里回憶道:“一開始,并沒有人支持我們,后來,老百姓支持我們,給我們提供食物和彈藥,并加入我們的隊伍,這都是因為美軍向他們揮起了屠刀。”
那幾年,阿卜杜勒和卡里瑪都在為家庭操勞。到了2014年,二人總共育有四男四女,老大法華德和老二納斯拉圖拉關系很好,但經常打鬧。“我們倆經常干架,”納斯拉圖拉笑道,“為了足球和自行車,我們可以大打出手,父親每次帶回新玩意,我們都會爭得面紅耳赤。”
兄弟倆在同一所學校念書,哥哥是勤奮的好學生,弟弟就不怎么愛學習了。納斯拉圖拉回憶道:“我一有機會就會翹課,有時在學校周圍閑晃,等別人放學了,再跟他們一塊兒回去。我可不想讓家里人知道我翹課。”阿卜杜勒知道二兒子不愛學習,但并不覺得兒子會經常逃課。他說:“我拜托過校長和老師,幫我盯著點他。我們全家都很重視教育。”
外界要進入戴米爾達德縣,除了一條坑坑洼洼的土路,別無選擇,再加上這里本身沒什么戰略意義,于是在2010年,塔利班就基本接管此地了。塔利班成員在縣里暢通無阻,阿卜杜勒非常擔心二兒子會受這些人的影響。他的擔憂是有道理的,納斯拉圖拉四年級時就見過塔利班戰士。據納斯拉圖拉回憶:“我那會兒正在清真寺祈禱,我問毛拉他們是干什么的,毛拉跟我說他們在打圣戰。”
2017年,法華德高中畢業,前往喀布爾的私立大學學醫。納斯拉圖拉次年畢業時,有不少朋友加入了塔利班。在父親的敦促下,納斯拉圖拉心不甘情不愿地準備大學入學考試,并幫家里干些雜活。過了一段時間,父親對他的狀態還是不滿意,于是讓他去伊朗打工。阿富汗每年都會有數十萬失業人口從阿富汗西南部沙漠出發,穿過巴基斯坦,前往伊朗,納斯拉圖拉就這樣加入了遷徙大軍。當然,他們都沒有護照,更談不上簽證了。
阿富汗的經濟因國際援助繁榮過一段時間,但2014年,援助停了,失業率也隨之飆升,大量阿富汗青年就此涌向歐洲。阿富汗的許多政府官員不是靠能力爬上去的,而是靠裙帶關系。就業機會銳減,民眾對政府更為不滿。到底有多少阿富汗人偷渡去伊朗工作,沒人說得上來,但根據國際移民組織的數據,僅2018年,從伊朗返回阿富汗的阿富汗人口就有76萬之多。
| 血腥的夜襲 |
2018年9月,特朗普派人赴多哈和塔利班代表展開多輪和談。其實早在2017年,五角大樓就放寬了在阿富汗實施空襲的交戰規則,不僅增加了空襲次數,還擴大了空襲規模。2018年,駐阿美軍數量為1.4萬,但美軍戰機投下的彈藥總量卻比2010年多,要知道,2010年駐阿美軍數量多達10萬。美國空軍將領解釋道:“我們發動大規模空襲,只有一個目的——給塔利班施壓,讓他們意識到和談才是最佳選擇。”
瓦爾達克面臨的不僅是更多的空襲,還有血腥的夜襲。這些夜襲往往由美軍01作戰小隊發動,只有極少數受害者是塔利班成員,多數受害者是生活在塔利班控制區的普通民眾。2019年,瓦爾達克的民眾和政府官員接受采訪時表示,有數十個當地居民在夜襲中喪命。
2019年2月23日,謝爾托吉天氣晴朗,之前連著下了三天雪。多虧降雪,當地居民這幾天不用擔心夜襲。三周前,法華德放寒假,從喀布爾回到家鄉,弟弟納斯拉圖拉仍在伊朗打工。
這天晚上,法華德、父親阿卜杜勒、母親卡里瑪和另外五個弟弟妹妹,以及一個名叫瓦西杜拉的15歲長工一起吃晚飯。到了夜里9點,一家子都在起居室的床墊上睡著了,瓦西杜拉則睡在廚房。法華德頭頂是窗戶,向外望去,可以看到通往戴米爾達德縣的唯一一條土路,雪地上是光禿禿的楊樹和蘋果樹。
最先醒來的是卡里瑪。“快起來!有夜襲!”她喊道。
法華德起身后,聽到了直升機的聲音。他望向窗外,看到不遠處的空地上停著兩架支奴干直升機,雪地上可以看見剛從上面下來的人影。他看了眼手機,是夜里10點。
他讓父親趕緊穿上衣服。“他們可能會搜我們的家,搜查前會先把人帶出去,”他說,“外面冷,我們穿上穩妥些。”他父親則讓他取出學生證,隨身帶著。“弟弟妹妹們都在哭,”他說,“我告訴他們:‘這是夜襲不假,但目標不是我們。”
人影向西方移動,幾分鐘后就看不見了,直升機起飛后也跟著消失在了夜空。遠方陸續傳來槍聲和爆炸聲,這應該是來自村子中部的一個小清真寺,里面住著15個塔利班士兵,阿卜杜勒的侄子奧馬爾就住在附近。奧馬爾回憶道:“我們的衣服晾在家門口的空地上,直升機飛得很低,把衣服都刮掉了。我女兒嚇壞了,緊緊抱住我。”
法華德時不時會瞄一眼外面的情況,雖然看不真切,但能聽見噴氣式戰斗機、直升機和AC-130攻擊機的轟鳴聲。他還和15歲的弟弟尹亞圖拉開玩笑:“等他們走了,你可以出去轉轉,或許能撿到一些裝備。”槍聲終于停了,但村子上空仍有戰機的聲音。凌晨3點,法華德一家還在聊天。倏忽之間,外面被閃光彈照亮,空中布滿了閃光彈留下的煙霧軌跡,再后來,法華德聽到“砰”的一聲。
家中另一側的空房間被炸彈擊中,法華德頭頂的玻璃瞬間被震碎。他右眼受傷了,感覺眼珠子都要掉出來了。家里一片漆黑,一家人也不知道誰受了傷、情況如何,但在阿卜杜勒的敦促下,大家還是成功轉移到了廚房。透過窗戶,他們看到黑色的人影和槍口噴出的火舌。在槍聲下,大家蜷成一團,接著,又是“砰”的一聲,威力比上次更大,整棟房子都晃了起來。
滿臉是血的阿卜杜勒帶著家人躲進洗手間,那里只有一扇窗戶。法華德站上水箱,想瞧瞧外面的情況,家人大喊著讓他立馬下來。他人剛下來,子彈就射穿了窗戶。
砰!又是一發。“我的耳朵嗡嗡響,”法華德說,“但我還是能聽到家人的哀嚎。”他的身子被重物壓住,想動也動不了,“我甚至覺得我已經死了,我深吸一口氣,發現空氣中都是灰塵。”法華德左眼看見身邊盡是炸碎的泥板和斷裂的木梁。接著,他抬頭一看,看到了夜空。
法華德掙扎著將自己的身體從殘骸下抽了出來,接著幫尹亞圖拉脫了身。二人一起將父親阿卜杜勒和14歲的妹妹澤尼布救了出來,阿卜杜勒一動不動,已經失去意識,澤尼布的臉部和腿部傷得很重。母親卡里瑪、兩個小妹妹仁娜特和法蒂瑪都在求救,她們還活著。“我哭了出來,”法華德說,“但我還是控制住了情緒,繼續救人。”尹亞圖拉想出去找人幫忙。“別出去,”法華德說,“跟我一起把人救出來再說。”他將瓦礫從媽媽和妹妹身上搬走。“一架直升機突然從頭頂飛過,還開了火,”法華德說,“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射死了尹亞圖拉。”
母親和妹妹還困在下面。為了讓母親順利呼吸,法華德開始清理她嘴邊的瓦礫,就在此時,他身后出現了士兵,他們正用普什圖語和達里語喊著什么。法華德剛一回頭,膝部就中了一槍。“我舉起雙手,開始祈禱。”法華德說,“我覺得他們肯定要殺了我。”一個士兵上前搜他的口袋,發現了學生證,跟后面的士兵說:“別殺他,搜一下屋子。”法華德求他們不要搜了,救人要緊。他們不但沒聽,還綁住了他的雙手。
法華德10歲的弟弟拉菲勒僅受輕傷,但嚇壞了,哭得很大聲。士兵讓法華德想想辦法,讓弟弟趕緊老實下來。這些人里有美國大兵,也有阿富汗士兵。拉菲勒回憶道:“他們一直朝我們大吼大叫,我媽媽和兩個妹妹還埋在廢墟下,他們卻在廢墟上走來走去。”還有一名美國女兵在拍照、錄視頻,據法華德描述,她還坐到了他身旁,讓另一個士兵幫她拍照。“他們完全可以救出我媽媽和妹妹,但他們沒有,”法華德說,“那會兒她們還活著啊!”
阿卜杜勒、法華德、澤尼布和拉菲勒活了下來,并被轉移至喀布爾的一家醫院接受治療。天亮后,奧馬爾等親戚趕到現場。他們以為阿卜杜勒一家子都喪生了,但只找到了五具遺體,分別是卡里瑪、15歲的尹亞圖拉、長工瓦西杜拉、8歲的仁娜特和6歲的法蒂瑪。中午,醫院打來電話,告知法華德等四人還活著。
| 塔利班新成員 |
納斯拉圖拉從伊朗趕回后,看著眼前的廢墟,心情沉重,哭都哭不出來,只能為死去的親人祈禱。2月的夜襲并非個例,實際上,這樣的夜襲在2019年有數十次之多。2020年2月,美國和塔利班簽署停火協議,夜襲才隨之結束。
2020年5月,我聽說納斯拉圖拉加入了塔利班。法華德也考慮過走這條路,他說:“一想到美軍和阿富汗政府,我就恨得牙癢癢,但家里有一個人加入塔利班就夠了,我得繼續學業,總得有人賺錢養家吧。”
塔利班能在瓦爾達克招募到新生力量有兩個原因:一是美國扶持的是當地民族和部落的敵對勢力,二是美軍和阿富汗部隊殺害老百姓、虐待被拘留者。
20年來,阿卜杜勒一直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加入塔利班,他希望孩子們以學習為重,但這一次,他沒有阻止二兒子。“政府和美軍干的根本不是人事,我的妻子和孩子有什么罪?”他說,“這場夜襲發生以前,納斯拉圖拉就有朋友加入塔利班,我總讓他離那些人遠點。但那一晚以后,我再也想不出阻止他的理由了。”
[編譯自美國《哈潑斯雜志》]
編輯: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