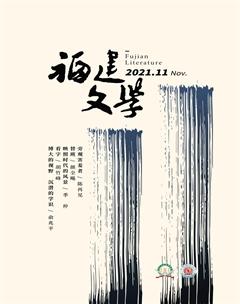映照時代的風景
季仲
1960年一個大暑天,我背著簡單的行囊,走出大學校門,步入《熱風》月刊社,從此開始長達三十六載的文學編輯生涯。
《熱風》是《福建文學》的前身,隸屬福建省文聯,與省作協、美協、畫報社等單位合署辦公,總共不過三十余人,擠在福州屏山南麓的一幢二層青磚小樓里。那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福州市民每個月供應二十四斤糧食,半斤肉,四兩油。我們天天饑腸轆轆,無精打采。編輯部的領導和作協的知名作家,如張鴻、馬寧、郭風、蔡其矯、何為諸位先生,年長者也就四五十歲吧,已頗負盛名,我在學生時代就讀過他們的大作,很是景仰。但是,叫我大惑不解且稍有失望的,是老前輩們大都不茍言笑,沉默寡語。有的一支煙、一杯茶,埋在書報稿件之中,就像休憩于水草葳蕤中的魚,久久地無聲無息。有的開會從不發言,非得開口,囁囁嚅嚅,不知所云。我暗自納悶:一個文人云集、精英薈萃的文化單位,怎會如此壓抑、沉悶、死氣沉沉?
時日久了,個中緣由便有些明白:前兩三年,文藝界經歷一次“震動”,這個小小的文藝團體,有多人被戴上右派帽子,發配農村勞動,幸免于難而留任者,能不心有余悸,噤若寒蟬?
刊物與編輯,總是血脈相通,心律共振的。編輯如此,《熱風》也乏善可陳。因經費拮據,稿源枯竭,不得不由月刊改為雙月刊,小十六開,六十四碼,是那種劣質的發黃的新聞紙,還常常無米下炊。于是,經常派出自己的編輯去采寫一些所謂的“特寫”,湊足版面。我也干過此類差事,如今偶爾回眸自己炮制的那些粗俗文字,不禁汗顏不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五十周年,福建省編選出版各類文學作品集,我曾參與其事,那個時段可以入選的詩文,實在寥寥無幾。文學原應該是海闊天空無涯無際的,《熱風》卻鉆進一條狹窄的小胡同。無論小說、散文、詩歌,大都公式化、概念化,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怎么能出好作品?
峰回路轉,歷史常有柳暗花明時節。
三年困難時期基本度過之后,曾在廣州召開一次知識分子座談會,文藝界迎來短暫的“小陽春”。《熱風》的青磚小樓里的空氣開始活躍,自發來稿漸漸增多。“忽如一夜春風起,千樹萬樹梨花開。”作為一名小編輯,我親身感受到撲面而來的陣陣春風。人們臉上有了笑容,談文論藝成為日常課題。為了加強文聯專業基礎建設,文聯曾開辦夜間讀書班,利用工余的夜間時間,學習古典文論,歷時兩月有余。文聯副主席兼《熱風》主編張鴻先生親自給編輯、作家們授課,講解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文心雕龍》。全書五十篇,大體瀏覽,《神思》《情采》《風骨》等重點篇章則逐句講解,遇到不易疏通的文字障礙,則能者為師,自由議論。毫無疑問,這次學習對同人們進一步認識文學創作的特性、規律,以及作家學養的重要性與創作心理的奧秘,大有裨益。
惠風和暢,言路廣開,各種座談會漸漸多了起來。影響較大的有兩次:一次以歐陽山1960年9月發表于《人民文學》的短篇小說《鄉下奇人》為中心,另一次以王汶石1961年3月發表于《人民日報》的短篇小說《沙灘上》為主題。兩篇小說都著力塑造苦干實干的農村基層干部的藝術形象,主編張鴻試圖借助他們的經驗來破除文學的“假大空”。座談會面向社會,不僅有文聯的作家、編輯出席,而且邀請許多高校和中學教師以及戲劇界的作者參加。偌大的會議室座無虛席。會上發言熱烈,各抒己見,往往爭得面紅耳赤。那個年代,文聯連工作餐也無力招待,與會者上街扒碗素面,啃個饅頭,又連忙回到會場。連續數日,興猶未盡。
此時的《熱風》也蓓蕾初開,有所改觀。本省幾位老作家都有新作問世。如郭風的《你是普通的花》中的許多鮮花都是這兩三年間綻放于《熱風》園地。青年作家張賢華的短篇小說《茶花》,何澤沛的電影劇本《地下航線》,姚鼎生的長篇小說《土地詩篇》,曾毓秋、王尚政的短篇小說以及范方、周美文的自由體新詩,嶄露頭角,引人矚目。莆仙戲《春草闖堂》、高甲戲《連升三級》,從省城演到首都,譽滿京華。幾位戴了帽子的作家此時摘去帽子,而且開始以真名實姓在《熱風》刊發新作。恰似天國的福音,溫婉裊裊,慰藉人心。
在福建,文藝界“小陽春”的標志性盛事,
當屬全省貫徹“文藝八條”的文藝座談會。會上暢所欲言,歡呼雀躍。著名詩人蔡其矯即興寫下短詩《三伏的風》:“給焦灼的心送來海的清新/給干旱的土地送來帶雨的云/及時的風啊/以又可見又不可見的腳跡/遍及山嶺、原野、森林/讓樹梢從昏睡中蘇醒/在池沼和湖泊,在浩浩的江河上面/激起綠波滾珠如鱗……”
這是當時全國文藝界的寫照,也是福建文藝界的心聲。當然,《熱風》也開始沐浴于“三伏的風”,從裝幀到內文,都大有改觀,有如詩人所描繪,陣陣“熱風”“激起綠波滾珠如鱗”……
然而,世事發展往往還有另一法則——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全國文藝界春風初度的日子不過兩年多吧,大約于1965年春夏之交,《熱風》忽然受到上面批評。我多次看見副主編郭風、苗風浦先生(主編張鴻其時已調北京工作)徑直被頂頭上司叫了去,回來傳達時總是誠惶誠恐,十分沉痛地說,《熱風》犯了方向錯誤,我們的屁股要趕快坐到工農兵方面來。于是,“文革”前夕,《熱風》曾戰戰兢兢地做過改版的努力。首先是開本改小了,由十六開改為三十二開,所設欄目也面目全非,小說、詩歌、散文、評論一概不見,只發福州評話、閩西山歌、民間故事和相聲、伬唱等民間曲藝,封面封底的名家名畫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木刻、剪紙、農民年畫之類的通俗美術。總之,是想改成農村俱樂部那樣的通俗讀物。結果是弄巧成拙,不倫不類。
事實證明,此路不通!通俗版《熱風》只出三期,一命嗚呼,被迫停刊。
十年浩劫,各文學期刊經歷的風風雨雨大體相似,不忍贅述。但我要用歡欣的文字記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終結,改革開放的展開,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以及與我們闊別已久的世界文學新作品新思潮的涌入——全國迎來了生機勃勃的文藝的春天。
那真是欣欣向榮的文藝復蘇的歲月。我仿佛聽到雪域高原冰融雪化的滴答聲,我仿佛看到江南稻田綠油油的秧苗拔節上竄的長勢,我聽到鳥鳴,我聞到花香,我聽到大江大河的春潮涌動,我看到一行行紫燕飛落檐頭殷勤報春,我還望見一輪被朝霞烘托得特別鮮艷被海水洗刷得特別清新的旭日從閩江口外的海面冉冉升起……我們這一代文學編輯真是歷史的幸運兒,千真萬確迎來了文藝的春天!
這個春天,《福建文學》從大學生和知識青年中廣納英才,編輯部人丁興旺,規模空前。甫一復刊,我即倡議實行半天坐班制,既要求當好編輯,又鼓勵讀書寫作。只要處理得好,二者是相輔相成、異曲同工的。我的伙伴們當年不愧為“甘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好手,若干年后,大都成長為知名的詩人、作家、評論家、編輯家與畫家。
這個春天,文學成為千萬年輕人追求的美夢,自發來稿有如雪片,紛紛飛來,落在每個編輯案頭,堆積如山。小說、散文、詩歌、評論“四大塊”的老模式不能適應新形勢了,多年以來,開辟了“閩海小說界”“中青年詩人評介”“關于新詩創作問題的討論”“臺灣文學之窗”等專欄以及每年一期的散文專號。長江后浪推前浪。雛鳳清于老鳳聲。從這塊園地出發而走向全國的文學新人,可以排成長長的隊列,是一個連?還是一個營?數不勝數!
這個春天,《福建文學》從偏居東南一隅而漸漸跨越省界,飲譽華夏。承蒙諸多名家的青睞與呵護,有文學巨匠巴金、世紀老人冰心與著名作家、詩人孫犁、鄭敏、蔡其矯、汪曾祺、柯靈、宗璞、何為等惠賜佳作而大增光彩。
這個春天,《福建文學》所蘊藏的創造活力常有噴泉似的噴涌。比如1984年初夏,我的伙伴們突發奇想,建議創辦一份《臺港文學選刊》。從全體編輯開會議定、層層上報審批獲準,到省委書記項南同志親自撰就代發刊詞《窗口和紐帶》,僅三天時間。一路綠燈,效率神速,嘆為觀止!
這個春天,是個全民求知若渴的年代,是個年輕人熱愛文學的年代。感謝讀者厚愛,《福建文學》最高發行量逼近十萬大關,《臺港文學選刊》最高發行量闖過四十萬大關。
每憶及此,我和我的同人們都難以自抑地有點小小的成就感。
古人云:“以銅為鑒,可以整衣冠;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我不揣簡陋畫蛇添足,曰:“以文為鑒,可以觀風景。”文學,特別是作為詩文的載體的文學刊物,總是映照著時代的風景。三十多年,長途漫漫,我一路走來,或狂風驟雨,險山惡水,或風和日麗,花團錦簇,一幕幕風景盡在眼前閃過。耄耋之年,回首往事,無怨無悔,我的編輯生涯是幸運、充實、快樂的。
責任編輯 楊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