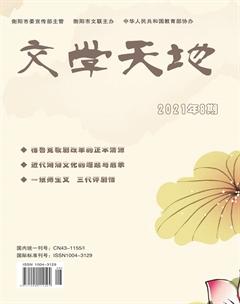民間剪紙中的“葫蘆崇拜”研究
摘要:“葫蘆崇拜”是從上古時代沿用至今的本原文化觀念。時至現代,還有眾多民族如漢、彝、怒、白等都有關于中國各族出自葫蘆的傳說。本文試圖從從符號化、植物圖形、動物神祇、人物神祇四個形態對民間剪紙中“葫蘆崇拜”的圖示類型進行分析、歸納與梳理。民間剪紙中的“菊蘆崇拜”圖示雖包羅萬象,但其包蘊的“陰陽”與“生生”哲學觀念卻始終作為中華民族民間群體生活中的行動指南而存在。
一.中華民族的原始葫蘆文化
“綿綿瓜爬,民之初生”。這是我國最古的史詩《詩經》中《大雅·綿》的一句詩。意思是:中華民族的先民,最初是出自共同的母體——瓜瓞,它世代綿延,子孫繁衍。 這種民從瓜出之說,也可以歸入葫蘆崇拜。傳說中的伏羲、女媧、盤古等中華民族的始祖們,其本質實為葫蘆。《周易》中記載伏羲,稱其為“包犧”。“包”即指“匏”,意為“葫蘆”;至于女蝸,古籍上有的直接將“女媧”寫作“?媧”。“媧”,古音為“瓜”。按古漢語音韻學之規律,則“女媧”完全可讀為“匏瓜”,也就是葫蘆;而《搜神記》、《水經注》諸書中將“盤古”寫作“槃瓠”。據著名民族學家劉曉漢考證“即槃瓠為葫蘆的別稱。槃轉為盤,瓠轉為古,由槃瓠轉為盤古。”而其他民族的這類傳說盡管情節各不相同,但萬變不離其宗,就是認為人類始祖出自葫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葫蘆形體頗象女性生殖器或巖洞,因而人從葫蘆出,隱寓著人從母體,以及人類早期穴居生活的深層意義。二是東西方文化圈內都有關于史前洪水泛濫的傳說。在西方,有關“諾亞方舟”的傳說家喻戶曉。而在東方,葫蘆一直是洪水故事的核心。大量關于葫蘆生人神話,都與洪水有關。如瑤族傳說:“洪水淹沒了一切,伏羲兄妹躲在葫蘆里過了七天七夜,水退后好不容易結了婚,留下了人種。” 在漢族的神話記憶中共工振滔洪水、女蝸止水,以及伏羲與女蝸造人的神話是葫蘆文化的經典版本。傳說水神共工,是天上一個有名的惡神,人的臉,蛇的身子,紅色的頭發,性情愚蠢兇暴。
后來水神共工與火神祝融打了一場惡戰,代表光明的祝融勝利了,代表黑暗的共工失敗了。這時共工眼見自己的隊伍部率凋零,又羞又惱,也覺得沒有臉再活在世界上了,就一頭向西方的不周山撞去。
這一撞,不得了,共工把撐天的柱子給撞斷了,大地的一角也被撞壞了,半邊天空也坍塌下來,天上露出了一些大窟窿,地面上也破裂成縱一道橫一道的深溝,洪水從地底噴涌出來,波浪滔天,使大地成了海洋。人類簡直無法生存下去了。這時,女蝸出來補天。她在大江大河里挑選了許多五色的石子,架起一把火將石頭熔化后填補天上的窟窿。然后又殺了一只大烏龜,斬下它的四只腳,用來代替天柱,豎立在大地的四方,平息了水災。
洪水平息后,女蝸又為人類的再生而摶土造人,但神話記憶卻有女蝸與伏羲的傳說。
聞一多先生就認為伏羲就是葫蘆,他在《伏羲考》中說:根據伏羲女蝸與匏瓤的語音關系,“伏羲、女蝸莫不就是葫蘆的化身。或仿民間故事的術語說,一對葫蘆精。于是我注意到伏羲女蝸二字的意義。我試探的結果,‘伏羲’‘女蝸’果然是葫蘆。”
至今在甘肅天水一帶還流傳著伏羲是葫蘆娃的故事:伏羲為民女與龍王所生,后人間發大洪水,民女將初生的伏羲裝人葫蘆放回人間,保留了人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葫蘆文化除在漢族的神話中留下了集體記憶外,在中華民族多元的先民中,尤其在南方的少數民族或族群中也留下了神話記憶。葫蘆是人類最原始的避水工具,同時也成了“人類再造”的搖籃。葫蘆是中華民族最原始的吉祥物之一,人們常掛在門口用來避邪、招寶。上至百歲老翁,下至孩童,見之無不喜愛。因此,受到中國原始葫蘆崇拜的影響,民間剪紙中也出現了眾多葫蘆意象。
二.民間剪紙中的“葫蘆崇拜”
民間群體生活相關生老病死的人生禮儀和風俗當中,剪紙是非常重要的表現手段和媒介方式,也是民間群體世代相傳的文化載體。“剪紙是民間生活土壤上長出的文化樹,活態的民間生活傳統造就了剪紙,剪紙又維系了民間活態傳統的持久存在。” 葫蘆圖示的民間剪紙,用途極為廣泛,幾乎包涵了人生生、老、病、死的全部儀式以及在傳統節曰中都有應用。例如用于婚慶洞房的“寶葫蘆”剪紙喜花,用于求子繁衍的“葫蘆蓮花”剪紙,用于端午節辟邪逐疫的“老虎葫蘆鎮五毒”、“童子騎葫蘆”剪紙等等,都是葫蘆作為生育繁衍、子孫興旺、綿綿瓜瓞母體信仰這一原始內涵的反映,以及葫蘆作為母體養護的保護神意象。例如山東地區一幅晚清的“老虎葫蘆”剪紙,實際運用于端午惡月用來驅邪消災、祛病除祟的,剪紙圖案中葫蘆腹部剪有“王”字符號的老虎,這種圖形組合與甘肅正寧宮家川出土的虎面葫蘆彩陶瓶圖案、云南彝族祭祖中“虎面葫蘆吞口”都極為相似,毫無疑問這種樣式是遠古原始信仰一脈相傳的遺存。這些葫蘆題材的民間剪紙,通過民間婦女代代相傳的形式流傳下來,因此較為完整地保留著它的原始文化觀念和原始內涵,同時這些民間剪紙的葫蘆圖示語言也相對穩定地世代相襲下來。在民間,用什么圖示和符號語言去表達什么樣的文化觀念,都有約定俗成的規約和限定,這些歸約性的表達本身也是民間群體文化的主體內容。
民間剪紙中的葫蘆圖示表現手法可謂豐富多樣,不同的地區、不同的作者所表現出的風格和類型也有很大的不同,但共同之處就是都屬于中國本原哲學觀物取象的表現方式,體現出一個完整的中國本原哲學的哲學觀。這些民間剪紙,根據具體的表現形態和特點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類型:
1.符號化圖示
在民間群體文化中,經過幾千年來的文化積累和群體創造,將許多較為復雜的觀念和文化轉化為簡練、醒目的符號語言,并在民間群體生活中起到約定俗成的共識和解讀。 符號類型的圖示語言也是民間剪紙藝術中最常態的形式之一,具有簡約大方、內涵豐富、極具表現力的藝術特點。比如陜北地區應用在婚慶禮俗中的“寶葫蘆”、“葫蘆套方正”、“如意雙葫蘆”等剪紙喜花,運用極其簡練的符號化語言來表現葫蘆母體中陰陽相交、化生人類的深厚內涵。“寶葫蘆”剪紙運用用簡潔的線條,構成極其簡約的符號圖示語言。葫蘆內雙線相交纏繞迂回,形成通天通陽的雙嘴葫蘆造型,中間線條穿插構成了廣為流傳的“如意”、“方正”、“盤長”的民間祥瑞符號。這在陜北農村被稱為“蛇盤九顆蛋”、“八寶”、“盤長”,有些地區也稱為“方開結”、“八卦”,預示著陰陽雙蛇相交、子孫萬代、生生不息的生命和繁衍。“寶葫蘆”雖是單體葫蘆造型,卻包含雙嘴雙頭形式,其實就是漢代墓葬畫像石中伏羲、女媧雙蛇相交圖示的抽象變體而已。寶葫蘆”、“葫蘆套方正”、“如意雙葫蘆”剪紙喜花,用在婚慶洞房的目的就旨在表現子孫繁衍、多子多福、物產豐收的生育意識。在古代祭儀上,初民要食瓜,以求將瓜的多籽變為自身旺盛的生殖能力,多多蕃衍人口,如同綿綿瓜瓞。瓜瓠多籽,因此,遠古先民將瓜其視為女性子宮的象征物,實行生殖崇拜。瓜崇拜,實際上是以剖開的葫蘆、金瓜、南瓜象征生命繁衍中女性母體的形象符號,中心為女陰,周圍飾以圓點比喻子孫繁衍,這是一種生殖崇拜。
2.植物圖形圖示
在中國民間群體觀念中,萬事萬物都可劃分為陰陽兩性,天地、人類、植物、動物無一不是陰陽相合的產物,也各自所具有自身的陰陽屬性。在植物形態里,蓮花圖示是民間剪紙里最為常見的主題,魚戲蓮、蓮里生子等傳統主題中的“蓮花”是女性、女陰、母體的象征;葫蘆是母體崇拜的代表,同樣具有母體、陰性內涵的還有南瓜、白菜、蓮藕、石榴、白梨、佛手、青竹等植物果蔬。牡丹、葵花、玫瑰、芍藥等具有中心向四周放射花瓣的植物則作為陽性符號。蓮花與牡丹的配合,就是陰陽相合、男女相交的生育繁衍圖示。隴東、陜北地區也有民間諺語:“蓮拉牡,必定富”、“葫蘆拉牡丹,越來越喜歡”,“石榴賽牡丹,一賽一大攤”、“瓶里插牡丹,兒女一鋪攤”。內蒙古商都縣高勿素鄉韓家村王大女大娘的“葫蘆”剪紙,葫蘆里剪了一朵蓮花和一朵牡丹,就是葫蘆母體里伏羲、女媧陰陽相交,象征著綿綿瓜瓞、子孫昌盛、五谷豐登。就是團團圓圓和圓滿;葫蘆就是囫圇、混沌,子孫滿堂才是圓滿。
3.動物神衹圖示
在民間剪紙中存在大量的動物造型的圖示,它們起源于遠古時代動物圖騰的原始信仰。原始社會時期,人類還未具備征服自然界的能力,或是在與大自然和動物生靈的斗爭中處于下風,那些超自然力的自然物象和超能力的動物就成為人類的崇拜物,形成早期人類的自然崇拜信仰和動物圖騰信仰,因此這些動物是被作為“神衹”來膜拜的。例如人類自身無法具備的多子多孫生育繁衍能力的魚、蟾蜍、青蛙、蛇、蟬、龜、老鼠、兔子等動物,被作為陰性、大地、水等母體陰性圖騰文化符號;而人類無法征服的猛獸虎、熊、公牛、野豬,具有自由飛翔能力的鳥類、蝴蝶、飛蛾,而在一年最炎熱時出現的、具有身體為中心向外放射的八腳昆蟲類動物蝎子、甲蟲、蜈蚣、蜘蛛、壁虎、螃蟹,還有能夠在髙山山巔上飛奔的羚羊、鹿,都是觀物取象地被作為陽性、天或太陽的陽性圖騰文化符號。
以陜北地區一則剪紙喜花“蛤蟆扣碗”為例,上下相扣交合的扣碗形成了葫蘆母體崇拜的象征,也是寓意天地相交、萬物萌生的哲學意象。扣碗中間,是一個從上一躍入水的青蛙形象,但面部刻畫明顯具有人臉特征,因此這里表現的不是普通青蛙,而是“蛙神”。蛙神,也就是活躍于黃河流域黃土高原的黃帝氏族繁衍神祇——女媧。“蛤蟆扣碗”剪紙喜花,表現的就是古史傳說中始祖神“女媧造人”,也就是“洪水神話”中伏羲、女媧“葫蘆生人”的流變和異體。扣碗、“蛙神”都是很具體的圖示形象,這些形象都觀物取象地表達了深厚的文化內涵。
葫蘆圖示的民間剪紙中也經常出現動物類和植物類圖示混搭組合,共同表達陰陽相合的內涵。陜北地區的一幅葫蘆剪紙喜花中,葫蘆內的主題是“蝶戀花”,蝶兒采花粉的生物本能現象,被寄予男女構精、陰陽相交的寓意,用于結婚新房內的象征意圖不言而喻。
在陜西榆林地區佳縣、榆陽、神木、府谷一帶,嬰兒出生后,奶奶要趕緊剪出一幅剪紙墻畫貼到門外,生男孩,就要剪一幅紅色葫蘆剪紙;生女孩,就要剪一幅紅色蓮花剪紙。佳縣張錦芳所剪的這幅用于生育的紅色葫蘆墻花,整體的造型是一個葫蘆,葫蘆里面端坐著一位神祇,在陜北地區被稱作為“抓髻娃娃”,其實就是繁衍之神“皋楳”或女媧始祖的化身。神祗頭上有雙髻,通天通陽。作者將神祗的腹部處理為石榴造型,石榴、葫蘆都具有多籽繁衍的母體生殖意象,葫蘆里套石榴的組合圖示更加強調地表現了多子多福、子孫昌盛的生命意識和吉祥祈愿。
除了以上分析的幾種以葫蘆形態和葫蘆母體信仰為主體的剪紙圖示類型,民間剪紙也有將葫蘆作為道具來表現與葫蘆相關的傳說故事。在民俗和生活禮儀中的剪紙圖示完全是觀物取象的生命符號,既滿足人們生活的實用功能也是人自身生命原則的體現。現階段的民間剪紙藝術作為獨立的藝術表現手段,呈現出圖像的敘事功能,換句話說,就是剪紙也能說故事。剪紙作品《瓢葫蘆舀水沉不了底,不想爹娘單想你》,將青年男女談情說愛與葫蘆組合成同一個畫面,與民間流傳著伏羲、女媧兄妹成婚繁衍人類的葫蘆傳說產生了關聯。葫蘆在這一類題材的剪紙作品中,起到點題的作用,本質上還是中華民族原始信仰的葫蘆崇拜觀念若隱若現的文化遺痕。
參考文獻:
[1]劉堯漢.中華民族的原始葫蘆文化[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3(3):136-137.
[2]薛世平.葫蘆崇拜·魚崇拜·水崇拜--中國文明史上的奇特現象[J].福建師大福清分校學報,1997(01):36-38.
[3]喬曉光:《活態文化: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初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頁。
[4]胡繼寧.民間剪紙中的"葫蘆崇拜"圖示研究[J].西北美術:西安美術學院學報,2019(1):90-93.
作者簡介:朱美云(1996-),女,漢族,甘肅白銀人,碩士研究生在讀,單位:陜西師范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研究方向:民俗與非物質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