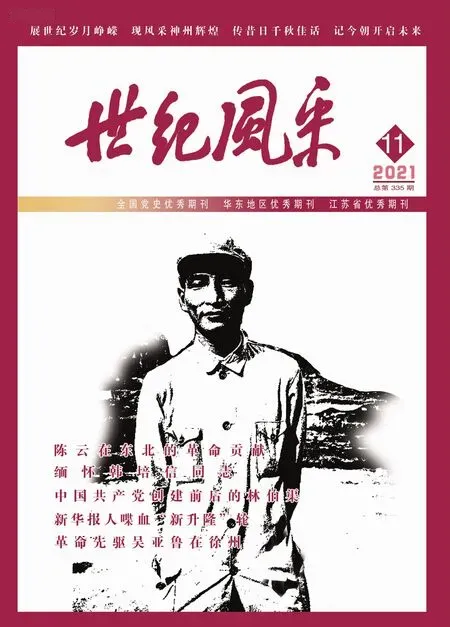中央蘇區的首位女軍醫
鐘燕林
她出身貧寒,經歷了苦難的童年;她投身革命,掙脫了封建婚姻的枷鎖;她從軍學醫,為救治傷員盡心盡力;她舍生取義,為革命流盡了最后一滴血。她就是隨紅七軍來到中央蘇區的廣西女青年,中國工農紅軍軍醫學校培養的首位女軍醫——韋榮。

韋榮畫像
苦難的童年
韋榮,女,1907年3月出生在廣西田東縣思林鎮的一個窮苦人家。她家無田無地,僅有一間破茅草房,一貧如洗。韋榮的母親叫梅蔬燕,是一位勤勞慈祥儉樸持家的家庭主婦。父親韋杰,和善忠厚。為了糊口,母親靠擺米粉攤、父親短途販運些黃豆、食鹽,有時還和別人合伙殺豬賣肉,含辛茹苦地支撐著一家極為清貧的生活。
韋榮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正是中華民族多難和風云變幻的年代。軍閥掠奪民財、搜刮地皮,地痞游勇趁亂而起,土匪遍地,盜賊如毛。韋榮的家庭除了貧困,還常常被人欺侮。她11歲那年,家里遇到米荒,母親借了本鎮一家地主的谷子渡荒,因一時沒法還,地主就趁機敲詐勒索,甚至搗毀米粉攤鍋灶,幾次想拉韋榮去頂債,后來在鄰居的幫助下,湊足了米還給地主,事情才算平息下來。然而禍不單行,一天晚上,她媽媽剛借來準備做米粉出售的兩擔谷子,被盜賊偷了去。全家又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親身經歷和耳濡目染,使少年韋榮的心里開始埋下了對舊社會仇恨的種子,也培養了她熱愛勞動、關心他人疾苦的崇高品德。在家庭的熏陶下,韋榮過早地成熟了。小小年紀就跟著媽媽磨米、蒸粉、擺攤,開始為維持生計而辛勤勞作。
值得父母欣慰的是,韋榮長到17歲時,出落成一個窈窕淑女,眉清目秀,玉嫩紅潤的鵝蛋形臉龐,就像一朵盛開的桃花,加上她愛說愛笑,舉止大方,天真活潑,很快“思林一朵花”的美稱名傳四方。僅幾個月,登門求親者絡繹不絕。
韋榮覺得婚姻是人生的轉折點,福禍難卜,須慎重考慮。因此,在諸多的求婚中,她本想認真挑選一個如意的郎君,無奈因生活所迫,父母硬著心腸,答應把她嫁給思林縣縣府雇員亞忠為妻。事前,媒人及韋榮父母已經收下男方的聘禮,盡管韋榮竭力反對這門親事,但父親固執地認為,韋榮年已17歲,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經地義。于是,韋榮就這樣在極度恐慌中當了新娘。
舊社會婦女沒有地位,被壓在最底層,而當媳婦就更是底層的底層了。韋榮過門后,就如花落坑,似玉沉泥地。她每天起早貪黑,把挑水、劈柴、做飯、洗衣、喂豬等家務全包了,此外,還要承擔繁重的地里勞動。韋榮干的是牛馬活,吃的卻是殘湯剩飯,動不動就是挨打受罵。婆婆常瞪著眼睛訓斥,故意找碴罵韋榮家窮沒有妝奩陪;丈夫亞忠抽煙、酗酒、賭博,脾氣十分粗暴而乖戾,經常賭輸了錢后,便拿韋榮出氣,稍不順眼就揪著韋榮的辮子拳打腳踢。一次,亞忠埋怨韋榮沒有及時把他換下的衣服洗干凈,開口就罵。韋榮氣急了,爭辯說:“一大早,我就上山砍柴了,哪有時間洗衣服?”婆婆說韋榮不會干事還頂嘴,亞忠看著母親的眼色逞兇,沖過去,一把捋住韋榮,“啪啪”打了她兩個巴掌。韋榮實在忍受不了,就跑回娘家去了。媽媽見韋榮身上青一塊,紫一塊,傷心地哭了,只好暫時把她送到親戚家躲起來。可是不管韋榮躲到哪里,亞忠都好像一頭獵犬,很快就把她找回來,又遭毒打一頓。就這樣,韋榮的鼻子不知出過多少血,舊疤未愈新疤又添。
這是什么世道啊,自己的生活還不如婆家的牛馬,滿肚子的委曲,向誰去訴呢?韋榮前思后想,陷入深深的迷惘和痛苦之中。殘酷的現實使她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反抗情緒,決心早日離開這個充滿欺騙、屈侮的“家”,去尋找一條新的生活道路。
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7年春天,右江兩岸的木棉花正含苞欲放,江沿岸各縣的農民運動,在韋拔群領導的東蘭、鳳山等縣農民運動的影響下,蓬勃興起。在共產黨員余少杰、黃永達的領導下,思林縣成立了農民協會、婦女協會,響亮地提出打倒列強、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實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號。與此同時,思林縣建立了農民自衛軍,黃永達擔任總指揮。
一天,黃永達在思林鎮貼出組織農民協會、婦女協會的號召書,并對爭先恐后趕來的貧苦農民們說:“思林縣已成立農民協會、婦女協會及農民自衛軍,大家盼望的好世道來了,那些吃窮人肉、喝佃戶血的地主豪紳就要完蛋了!要擺脫自己的不幸命運,就要革命。歡迎鄉親們都參加我們的組織……”
“革命!”這個字眼多新鮮。此時,在一旁看熱鬧的韋榮還不理解這個詞的深刻含意,但是她品味出這和改變自己的不幸命運有一定的聯系。追求革命就是追求新的生活道路。看到許多青壯年搶著報名入會,韋榮眼前驟然閃出了一縷希望的曙光。盡管婆家揚言:“如果韋榮膽敢參加農民協會,就要打斷她的腿。”韋榮還是不理睬這一套,理直氣壯地決心沖出家門鬧革命。她擠進報名的人群,怯生生地問正在登記名字的農協會員黃明開:“大哥,我可不可以報名?”黃明開瞧瞧韋榮那精靈的大眼睛,一副叫人愛憐的相兒,就笑著說:“當然可以嘍,你同家里人商量了嗎?”“不用和誰商量,我自己可以作主。”韋榮回答得十分干脆。“好吧!從現在起,你就是農會會員了!誰再敢欺負你,就來找農會,農會就是你的靠山!”眾鄉親聽后都為她拍巴掌叫好。
第二天,韋榮走進了農民協會辦公室,站在她后面的亞忠顯得有點驚慌。在黃明開面前,韋榮理直氣壯地訓了亞忠說:“你打罵婦女,是不是有罪惡?”亞忠想不到平日在他眼里像羊羔一樣馴服的妻子,現在竟敢指著自己的鼻子罵。但面對滿屋子威風凜凜的農會的人,亞忠不敢抬頭。他抖抖索索地說:“我是有罪惡,我是有罪惡!”
韋榮問道:“我要與你離婚,你敢不敢反對?”“我不敢反對,不敢反對!”黃明開把事先寫好的離婚書擺在桌子上。亞忠顫巍巍地用食指沾墨,在離婚書上按了手印。一張離婚書,使韋榮掙脫了這個囚牢般的“家”,結束了那不堪忍受的非人生活,從此勇敢地投入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她不顧流言蜚語,沖破封建阻力,帶頭剪掉發髻,她不知什么叫苦和累,挨村挨戶宣傳革命道理。
1927年9月,思林縣農軍總指揮黃永達帶領農軍,浩浩蕩蕩開進思林縣城。韋榮又勇敢地報名加入這支農民隊伍,并隨農軍參加多次戰斗。思林縣蘇維埃政府成立時,韋榮擔任婦女部委員。1929年10月,農軍在黃永達的率領下,再次攻打思林縣城。戰斗中,韋榮冒著槍林彈雨,負責帶領部隊繞過敵人崗哨,搭梯越墻進入敵人緊閉的城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活捉敵團務總局局長凌利堂,并繳獲了一批武器彈藥。農軍向外游擊時,韋榮負責送飯送水,搶救傷員,為戰士們縫補洗曬衣服。她還經常踩著凹凸不平的山路,翻坳越嶺,走村串戶,組織婦女擁軍支前,幫助農民做鞋縫衣。一次,韋榮接到縣蘇維埃政府通知搶運糧食,立即帶領婦女部的同志,連夜把糧食送到了指定地點,受到農軍指揮部的表揚。

興國縣鼎龍鄉茶嶺村的紅軍軍醫學校舊址
不服輸的“鐵姑娘”
1929年12月,鄧小平發動和領導了百色起義,同時宣布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思林縣農軍隨即編入紅七軍序列。不久,韋榮被調到紅七軍政治部當宣傳員。參加紅軍后,韋榮隨紅七軍主力部隊轉戰于滇、桂、黔邊區,參加保衛紅色政權的斗爭。每到一地,她都做演講,教唱歌;提著石灰水桶,參加寫標語。在這個初創的紅軍隊伍里表現出她的機智、勇敢和才能。
1930年秋,紅七軍主力準備北上。韋榮知道這個消息后,多次找領導要求跟隨部隊行軍。領導知道韋榮是個堅強的女性,同意了她的請求,并安排她到軍醫處擔任護士。父母為女兒即將遠行而難過。親戚們也再三勸阻韋榮道:“爸媽就你這么一個親生女兒,你走了,萬一有什么三長兩短,誰來照顧他們?”韋榮也不舍得遠離父母,但她更離不開紅軍。她激動地說:“干革命總不能老待在家門口呀!我們北上擴大革命根據地,將來革命勝利是要回來的。”于是,她安慰了父母,告別了親友,踏上新的征程。
在艱苦卓絕的北上途中,韋榮既是宣傳員,又是護理員。每天行軍她都和大家一樣,背著行李輾轉于崇山峻嶺之中。開始,她看到男同志一個個走路那么輕松,爬山那么快,她得小跑才能跟上。漸漸地她感到體力不支,氣喘噓噓,一停下來四肢發抖,但她仍咬牙堅持。一次,她走著走著,再也支持不住了,便不顧一切,倒地就睡下了。夜幕已降臨,大家只好拉著她往前走,好不容易才趕到駐地。這時有人鼓勵,有人憐憫,但多數人認為北上路途太艱苦,勸她趁早回去。但韋榮不服,男同志能走的,女同志就走不了嗎?她決心和男同志一道將革命進行到底,表示決不半途當逃兵。
部隊向湖南江華進軍時,正值嚴冬季節。由于連續轉戰,服裝一時難以補給。一路上北風呼嘯、大雪紛飛,韋榮和戰士們一樣,身上仍然穿著單衣,奇寒刺骨,砭人肌骨,饑寒和疲憊一齊向紅軍戰士襲來,許多人倒在雪地里再也起不來了。韋榮全身也像散了架似的,真想倒在雪地里睡一覺。但她沒有倒下去,一個宣傳員和護士的責任感驅使她掙扎著爬起來,拖著疲倦的身軀,一個個檢查倒在地上的戰士。她先用手放在同志們的嘴內測試,手凍僵了,又伏地用耳朵聽。“都還活著。”她說著這句話,淚水順著消瘦的臉龐撲撲簌簌往下掉。看到同志們饑寒交迫,她怎能不傷心落淚呢!
1931年2月2日,部隊剛趕到廣東乳源縣梅花村,一個更為險惡的情況出現了:國民黨粵軍部隊向紅七軍包抄過來。情況十分危急,韋榮和另外兩名軍醫負責10多個傷病員的轉移任務。她不由分說,彎腰背起傷病員,就向村外的山林跑去,藏好后又返回來再背。不到半小時,她這個身材纖細的女戰士,用她稚嫩的背脊,連續背了三、四個傷病員,分散隱蔽下來。韋榮這種堅強、勇敢的革命精神,深受紅軍指戰員們的喜愛,大家稱她為“鐵姑娘”。

瑞金市萬田鄉麻地村金崗崠原紅軍醫院舊址
軍醫學校的“女學員”
1931年7月,韋榮跟隨紅七軍歷盡艱難險阻,終于到達中央蘇區,歸屬紅三軍團編制。日思夜想與中央朱毛紅軍匯合的日子,真的盼到了,韋榮心里不知有多高興。經中央軍委批準,1931年11月,紅軍軍醫學校(后改名為中央衛生學校)創辦,韋榮被派去衛生學校學習。當時學校的條件很差,幾間破民房做為校舍和課堂,土墩上搭幾塊破木板當課桌和板凳。學員的生活也極為艱苦,大部分主糧是紅薯,有時還吃野菜。由于環境艱苦,有的學員吃不了苦,返回原部隊了。但韋榮十分珍惜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她心里只有一個念頭:盡快學好本領,早日回前線為戰友們治病。
韋榮沒有上過一天正規學校,只是參加農軍后在農軍的文化夜校里聽了一段文化課,加上她平時勤奮好學,懂得一些簡單的文字。就憑這點“墨水”,對她這次參加學習來說,又是一次嚴峻的考驗。然而她心里明白,這次學習是部隊首長交給自己的任務,她決心拼命拿下這塊陣地。于是,她比別人更加刻苦努力,白天認真聽課,晚上加班溫習,不懂就問,經常去請教老師,腳不出校門。在悶熱的天氣里,經過苦熬,她學業進步很快,僅幾個月就對所學過的業務知識成竹在胸了。
從衛生學校畢業后,韋榮被分配到紅三軍團當軍醫。她一邊虛心向老醫生學,一邊把書本上學到的知識應用于臨床實踐。在戰場救護中,韋榮并不比男醫生差,袖子一卷,撲下身子就忙開了,止血、包扎,動作干脆利索。在醫院里韋榮給傷病員們喂水、喂飯、端屎、端尿、擦身、洗衣服……她還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利用救護間隙為傷病員唱歌,深受傷病員的喜愛。
血染金崗崠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主力從瑞金云石山等地實施戰略轉移,途經萬田麻地村時,僅留少量紅軍留守根據地開展游擊戰,不能隨軍長征的傷病員,在醫護人員的帶領下東躲西藏養傷治病。一天夜里,從九堡方向走來百余名紅軍傷病員,天亮前露宿在王師吊。當地百姓紛紛開門迎客,把饑寒交迫的傷病員迎進家里,而韋榮就是隨行的軍醫。
白匪猖獗,整日瘋狂搜查紅軍傷病員和紅軍家屬,情勢日見危急。地處大路旁邊的王師吊人多眼雜,不能久留。10多天后,紅軍醫院匆匆轉移,沿古驛道登上崇山峻嶺,來到當地最偏僻隱秘的小村落金崗崠落腳。
那時的金崗崠,住著清一色的修姓一族,十多戶人家三五十口人。修氏族人熱情接納紅軍,把傷病員安置在山坳里的兩棟修家祠堂。傷病員得以靜養數月,住了一段時間后,村民與傷員和醫生都熟悉了。村民送菜給傷員吃,醫生會幫村民看病。韋榮醫術好,做事麻利,把找她看病的人都醫好了,大家對她都很敬重。
幾個月后,國民黨組建了熟悉鄉情的清鄉團,展開“清剿、抄剿、駐剿”,大肆叫囂“芒掃筷子要過斬,屋換石頭人換種”,形勢極為嚴峻。當地村民清楚記得,一天夜里,白匪悄無聲息圍住醫院,突然槍聲大作、殺聲四起。除身手較便捷的輕傷病員往后山突圍外,大多數重度傷病員束手待斃。忙于協助輕傷員突圍的韋榮,因來不及撤離而被俘,敵人將她推搡到一個叫豺狗排的地方,殘忍地將她殺害,修氏祠堂也被敵人放火燒毀。
巍巍高山垂首,滔滔江河悲鳴。這樣一位忠誠革命的女戰士,就像一顆流星在這個偏遠山區隕落。人們不勝震驚,分外悲痛。歷史不會磨滅韋榮的不朽功勛。1949年后,韋榮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她的英名將流芳百世,永遠為人民所傳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