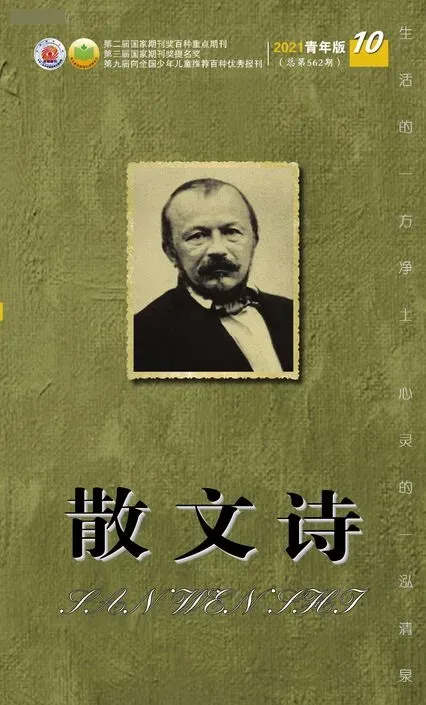一個人在河西修砌北國風光
王世虎
一
在冬日即將過去或過去很久之后,我們又一次在某個清晨翻閱云端,輕觸高高的太陽,由東而西。戀人在冬日撒下種子,戀人是屋前窗格上滑落的水珠,一切滄桑的歌詠從一場夢里開始預見。當你說出口或羞于說出口時,太陽剛好冒出山頂,鴿子也要出門去。那些緩慢前行的人,在我凝視時,沉淀為一把古代的銅鎖。
二
火焰助長著麥苗,在秋收以后、立春以后。一整塊平原在山川里陡峭,一整塊平原在時代的角逐中區分春秋,在土地里傾倒永恒——永恒的雪,永恒的母親的手……總會有一湖宿命的水源,在群山中懷抱森林,在你抬頭遠眺時悄然涌現。土地多么遼闊,一個人還未走出頭頂的森林。黑得讓人踏實的黑土地,是我因之摯愛太陽的緣由,再遠一些吧,那些常常被人們忽視的白云,那些未能捕捉的山風,在一個小山坡上,在一個荒蕪的部落,與你攜手同行。
三
如此輕柔的身子,在眾神的路上,森林和多個草原平鋪直敘,有人看到你歸于黃土的紛擾,有人珍愛你過冬的辭采,終是沒人在你探出頭的時候,撒下一地采薇。在一個風和日麗的午后,和我的雨水一樣輕叩柴扉,離經叛道。看這白茫茫、灰蒙蒙的戈壁,看這綿延不斷的山峰萬籟俱寂,這是深秋夜晚的北方。同一顆月亮下,有赤紅的土壤。戈壁里,有人再次高舉客棧的酒旗,摸摸頭頂,踏踏土地;天空里,飛過的大雁是我一生追求的命題。再回一次故鄉吧,孩童百步穿楊!再看一次親人吧,老人聞雞起舞!
四
賦予生命的常態在瓦刀上絲絲打磨,在一間封閉的屋子里等同于一棵千年的大樹。偶爾踢到一塊小石子,咯噔的節拍在破舊的殘垣下嗡嗡作響,楊柳不停地擺動,走得再快一些,或者慢一些,一個人終會打破自己的平面,修砌北國風光。入冬以后,各自忙碌在荷花里,背影細長,一枚硬幣和一泓清泉在墻的兩壁倒垂,有燭燈搖曳。這是一個節氣里叨擾的塵埃,吸煙和喝酒是真實的兩種錯誤,再近一些,你會看到河水并不是蔚藍,蔚藍的是天空里的白鴿,在伊人的翠綠裙擺下拍打歌謠。
五
破碎后的二次接壤是一次裂縫的詭辯,意外的泉水滾動。一次次遠眺長城上的月亮,沉積的細沙和水的女兒笑逐顏開,討論過巖石和斷層的來路,芝麻開花,挑著扁擔的王二在市井上輕唱謠曲。這是寂靜過后的又一次寂靜,這是我又一次盯住太陽,一瞬的混沌,一瞬的眩暈,在閉上雙眼前,大河何其寬敞,冬日的天空下大雁不再南飛。就讓我說出一個關于光點的奧秘,垂直的光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坦蕩的地平線上,駝隊搖著鈴鐺;坦蕩的地平線上,君子詩寫春秋。
六
匍匐在墻壁上的報紙,鶯飛草長,這是冬天里我第一次清晰地臨摹出新與舊的替換,時間里涌動著洪水和麥苗。匯于一處的江山,入木三分,入戲三分,發乎情而止乎禮的規矩是第一聲鳥鳴,第一聲痛哭后,母親的額頭上印滿世間最真的艱辛。在冬天,是更為恒久的陣陣琴音,是雪地上站立的一匹馬、年邁的稻草人和雪。一只黃鸝飛出樹林,更為精致的是一截樹干,在西風過后,與自己的影子再次貼近。孩童的胸膛上藏有輕盈的風聲,一棵松樹孤立生長。
七
黑暗對著黑暗,空白對著空白。祖母佝僂著身子,在燈下用針腳縫補秋冬春夏,時而一個人吃茶,對坐,面對茶水中的家園。窗戶緊閉,窗戶敞開,窗戶里有光的水露,偶爾一棟樓下會出現臨時支起的帳篷,擺放一個人的生死。花圈,白紙,悼詞,下跪的膝蓋,折疊悲傷。這是一整個冬天里你會遇到、想到、看到的辭令,這是完整的一天。
八
焉支以西,祁連以西,高高的鈴鐺在高處搖晃著風。平安夜的鐘聲里,我穿過河西大地,這一切在晨光的熹微里正冉冉升起。以一生為契合點,在河西論證愛的辭令,幸福的大河肆意翻滾。在我穿過河西大地的時候,西域的天空下傳遞著喜鵲報喜的福音。總想聽一聽楊樹的葉子怎么響,總想看一看楊樹的葉子怎么搖晃。在午間的寂靜里,一只蝴蝶歇息于冬天,蟲子們停止鳴叫,一切都回藏起來了。屋子里,母親忙個不停。她的事一件跟緊一件,偶爾,她也會放下一件,又去做別的事。窗外的陽光耀眼得厲害,母親的臉上也有不定的花紋。
九
兩地之間縮短的是山峰的主心骨,悠揚的草場上穿梭著歲月。馬蹄聲疾,一垛垛柴草是發黃的草料。養蜂人走了,牧羊人又趕著羊群進來,反反復復的,是千里馬、汗血寶馬、高原牦牛和常年不化的積雪。站在雪域高原上抬起頭來,天空一無所有,又似乎擁有一切,是形而上的矛盾、形而上的哲學。穿過悠長的民謠,映入眼簾的便是平原了,土地和房屋,白雪和鐵路,牛羊和愛的荊棘,在北方的冬日里雄赳赳,氣昂昂。總是要在漫長而廣闊的戈壁上走一走,數一數云朵的色彩,數一數太陽的七種底色;總是要在遼遠圣潔的天空下走一走,翻閱散落的部族和一壺青稞酒。巍峨的你一如千年的雪峰,我的父親,你把這一生的藍和白都裝了進去,又搬了出來,在我像朝圣者一樣走過這無言的草原時,陽光下,我的背影和你的身子正一起慢慢變矮。天空里有鳥群飛過,那是一群黃鸝鳥,它們有著堅硬的嘴唇,柔軟的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