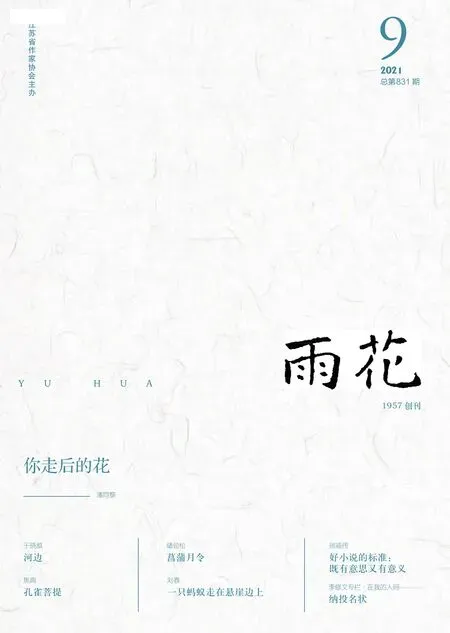殘年
江少賓
是你啊,回來過清明吧?我有些疑惑,眼又看不大清……
幾個月不見,玉大娘又老去了一輪,她坐在門邊,手搭涼棚,直到我摘下口罩,快步走到她面前,她才扶著門框,歡天喜地地站起來,皺紋密布的小臉浮起笑容。她是真的歡喜,在一眼望不到頭的垂暮光陰里,她盼星星盼月亮一樣,盼著每一個主動走近她的人。出門的人是不敢輕易盼望的,他們是一群不知疲倦的候鳥,春節短暫的居留過后,又陸陸續續飛往大江南北,那里有他們含辛茹苦、經年累月壘就的新巢。這些年,舉家外遷的牌樓人不勝枚舉,有些人連戶口都移走了,多年杳無音訊,牌樓成了他們成功逃離的“老家”。定旺、從龍、文革、和貴、志高……曾幾何時,這些打著赤腳一路“啪嗒啪嗒”的莊稼漢子,從田埂上不聲不響地消失了。熟悉的田疇一季季更迭,稻子彎了腰,棉花白了頭,綠油油的麥浪無拘無束地翻滾,一波波涌來,又一波波散去……在異鄉,他們過得還好嗎?我不知道。
“采芹呢?”我問玉大娘,玉大娘抓著我的手,不由分說地直接把我摁在凳子上。她的手太干枯了,一層皺巴巴的老皮,包著幾根生硬的瘦骨頭。“采芹啊?做禮拜去了!我跟你講咯,攔都攔不住,怎么勸都不聽,天沒亮就出門,也不打個手電筒,十二里路哎,高低要步行,也不怕刮大風,也不管下大雨,也不顧大日頭,魔怔……”玉大娘越說越激動,四肢微微顫抖,淚水漣漣。我有些意外,做禮拜只能去掃帚溝老街,采芹怎么就肯步行十二里,風雨無阻地堅持做禮拜呢?玉大娘抓著我的手,一直在絮叨,我心不在焉地聽著,安慰說:“又不是做什么壞事啊!你別管了,把你自己的身體照顧好。”玉大娘的失望溢于言表,小臉皺起來,聲音矮下去:“不是壞事?難不成還是什么好事啊?”
玉大娘八十七歲了,是牌樓還健在的最年長的老人,每次回來,我都要去看看她,聽她天南海北地扯閑篇——幾個月不見,她憋了一肚子話,急于說給我聽——東頭那個誰誰誰得了絕癥,沒法子醫了,只能躺在床上等死,看著真寒心;西頭那個誰誰誰家進賊了,兩個人,每人手里拿著一把刀,那個誰誰誰大氣都不敢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搬家一樣扛著電視機,拎著煤氣罐……我羞愧地聽著,內心涌動著一陣陣風暴。“沒有記錄就沒有發生。”玉大娘知道我在新聞單位工作,但從業二十多年來,我既沒有給她寫過一篇報道,也沒有給她拍過一個鏡頭,換句話說,玉大娘的病痛、畏懼、悲歡,從未真正成為一個新聞事件。她的存在,同時也是她的消失,她是親歷者,同時也是見證人。
玉大娘老伴過世早,我對他的印象已經很淡了,只記得他個子不高,抽旱煙,頭發稀疏,而且很早就白了;兩個兒子都是瓦工,常年不著家,兩個孫子三個孫女都是牌樓人,如今戶口都遷到了外地;留在玉大娘身邊的,只有小女兒采芹。玉大娘罹患類風濕(牌樓很多婦女都有類風濕),久治不愈,左腿很早就瘸了。瘸腿之后的玉大娘并不格外懊惱,她以為自己的苦日子就要熬到頭了,誰能想到呢,又病懨懨地活了十幾年,活得她自己都有些不耐煩了。她毫不掩飾自己的不耐煩,人前抱怨,人后也抱怨:“腿走不動,眼又看不清,廢人一個了,活著還有什么意思呢……”她翻來覆去說了十幾年,大家的耳朵都磨出了繭子。她自知無趣,便對搖頭擺尾的畜生說,對墻上笑瞇瞇的老伴說,甚至會在農歷七月半這天,對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說。
農歷七月半,中元節,牌樓人俗稱“鬼節”,這是老一輩牌樓人不敢怠慢的大日子,重要性不亞于清明和冬至。老一輩牌樓人篤信,七月半這天,亡魂會從另一個世界回到人間。這一天,大人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囑:腳抬起來,不能踩門檻!腳抬起來,不能踩門檻!為什么不能踩門檻呢?問大人,大人都答不上來,只虎著臉,佯裝生氣。天一擦黑,年幼的孩子便被媽媽摟在懷里,從一個房間抱到另一個房間,生怕被人搶了去。這種日子,誰敢出來作惡呢?實則是,小孩子“火焰低”,能看見大人看不見的東西。何謂“火焰”?我解釋不清楚,玄而又玄。玉大娘經常提起青苔的離奇經歷,說他小時候不止一次“看見”自己早逝的老爹爹,坐在老奶奶旁邊,光禿禿的腦袋埋在藍邊碗里,狼吞虎咽,幾天沒有吃飯的樣子。還有一次,青苔“看見”老爹爹盤在篾片散落的破藤椅上,手里捏著半個白面饅頭,兩眼空空的,像兩個黑洞……青苔“咯咯咯”地笑,說,那個禿頭又來了……童言無忌。苦了老奶奶,老淚縱橫,從一個房間轉到另一個房間,雙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詞:“你不要嚇孩子,你不要嚇孩子……”青苔“咯咯咯”地笑,他自幼膽大,奶奶稍不留神,他便泥鰍一樣溜出門去。
青苔成年之后淪為一個遠近聞名的賭棍,賭到傾家蕩產,過著在刀口上舔血的日子。他三十二歲就從牌樓消失了,生不見人,死不見尸,留下一座被叢叢蒿草圍起來的老房子。
七月半這天是不宜出門的,老人們約好了似的,一大早就起來了,粗衣,素食,洗鍋刷碗,灑掃庭院,忙而不亂地準備著一場約定俗成的神圣儀式。日落時分,炊煙裊裊,儀式在脈脈余暉中開始了。家家戶戶大門外,供桌已經提前擺好了,桌子上供著三碗飯、三碗菜、三雙筷子、三盞小酒杯。也有供五碗飯五碗菜的,以三碗的居多,無論是五碗還是三碗,其中必有一碗山芋粉絲——牌樓人自己做的山芋粉絲很好吃,也很有名。臘月里,經常有外地人開著車子,挨家挨戶上門收購。三和五都是單數,為什么不能是四碗、六碗,又為什么必有一碗山芋粉絲呢?我不知道。等主婦把一切都準備妥了,主事的男人(牌樓人謂之“孝子”)再恭恭敬敬地請出祖宗牌位,用事先擰好的潮毛巾小心翼翼地擦拭,一年了,牌位上積滿灰塵,臉盆里的水很快就黑了,至少得換兩盆水才能擦干凈。平時為什么不擦呢?我問過我媽,我媽瞪了我一眼,神情嚴肅,再無下文。舊時的鄉村,凡是與祭祀有關的事情,孩子的好奇心是很難得到滿足的,清規戒律太多了,有些事甚至不能開口問,問,也是一件犯忌的事情。如今看來,那些清規戒律大多莫須有,但正是那些莫須有的清規戒律,讓尋常的祭祀活動有了一種神秘感和儀式感,也讓我們自幼便對天地萬物存了一份敬畏心。
擦拭過后的祖宗牌位忽然有了重量,黑黢黢的顏體字看上去墨汁未干,仿佛祖宗們又活了過來,我對漫漶的字跡很不滿意,自己忍不住又描了一遍。神圣的時刻終于到了,孝子將牌位輕輕放在供桌上(坐南朝北),然后蹲下來,擦亮火柴,窩著一只手,慢慢引燃鋪在地上的一堆大裱紙。火苗很快就躥出來了,越躥越高,成了灼熱的火焰,呼呼呼,像一個人躺在地上吹著嘶啞的口哨。一家人圍著火焰,神情肅穆,取暖似的站在四周,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抽煙。事實上是不能抽煙,也不能放鞭炮。七月半是唯一一個不放鞭炮的祭日。玉大娘解釋說,鞭炮聲太吵了,歸來的亡魂會受其驚擾。我不能接受這樣的解釋,這樣的解釋也無法自圓其說,但玉大娘不許我質疑,她是信其有的,老一輩人一直信其有。或許,正是這種發自內心的敬畏,構建了鄉村社會原始而樸素的宗教。
磕頭是最后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火焰漸小漸熄時,就能磕頭了,孝子先磕,然后是主婦,再然后是孩子,長幼有序。不能隨便壞了規矩。磕頭也有講究,要么磕三個,要么磕九個——風燭殘年的老奶奶和有孕在身的新媳婦喜歡磕九個——不能是雙數,要一面磕一面在心里默數。若是不小心磕了雙數,得站起來,重新磕。
祖宗牌位祭完之后,還得原樣放回去,再取,又是新的一年了。牌樓人家的祖宗牌位一般都擱在大門樓上,沒有大門樓的人家,會在堂屋墻上開一個小神龕。玉大娘是個例外。她家既有大門樓,也有小神龕,門樓上擺著祖宗牌位,神龕里供著觀音菩薩。井水不犯河水。
祭祖是儀式的第一項,第二項是路祭,要找一個岔路口,給那些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燒幾刀大裱紙。孩子和婦女是不宜路祭的。婦女怎么也不宜呢?牌樓有些婦女膽子大著呢,敢一個人走很長很長的夜路,一個人黑燈瞎火地摸上山偷柴……你不是去燒過紙嗎?那一回我問玉大娘,玉大娘的小臉浮起一片陰云,好半天之后才自言自語似的說:“我不去,誰去呢?采芹不信這個的,回回都要和我吵,吵不贏就是了!那些孤魂野鬼,我有的還認得,總要燒幾刀紙吧……”我沒有想到這一層,一時間竟然愣住了。那些暮色四合、眾鳥歸巢的黃昏,玉大娘孤零零地蹲在路口,一面慢條斯理地燒紙,一面自言自語:“腿走不動,眼又看不清,廢人一個了!活著還有什么意思呢……”路祭結束急急回家的人心有戚戚,卻不方便停下來勸她。也沒有人愿意停下來勸她,她一天到晚神神叨叨的,像個巫婆,翻來覆去地盡是些車轱轆話。實則是,這個巫婆一樣的老人已經被漫長的歲月榨干了。當骨頭縫里的疼痛一陣陣襲來,她只能咬緊空蕩蕩的牙床,皺著小臉,靠在門框上,眼巴巴地望著空蕩蕩的機耕路,長時間自言自語。她不止一次在錐心蝕骨的疼痛中生出這樣的幻覺:老伴站在遠處,面目模糊,一面招手一面說,來啊,來啊……大半天之后,她從一身虛汗里慢慢緩過來,瞅一眼墻上的老伴,悵然若失。機耕路依舊空蕩蕩,綠樹掩映,光影斑駁,一眼望不到盡頭。她確信自己還活著,幽幽地長吁一口氣。
她顫巍巍地踏進八十歲的門檻,八十歲,多少個日日夜夜啊,牌樓沒幾個人活到這個歲數。她知足了,也早已看淡了生死,什么都能放下了,唯獨放不下采芹。她還記得那個四月的響晴天,四十二歲的她一個人把采芹生在芹菜地里,那么多的血,菜地染紅了一大片。當婆婆踮著小腳急慌慌趕來,她懷里那個血跡斑斑的女嬰把婆婆嚇傻了——看上去就是幾根骨頭裹著一層皮,活像一個剛剛破殼的外星人,不超過四斤——好半天之后婆婆才回過神來,憋出一句話:“這伢恐怕養不活啊。”玉大娘躺在血泊里,只覺得心慌,口渴,天旋地轉。
吊在玉大娘干癟的乳房上,采芹掙扎著活了下來,轉眼長到十八歲,大姑娘了,圓潤的蘋果臉,泛著近乎透明的光澤。媒人不分白天黑夜地上門,走馬燈似的,門檻都快被踏平了。玉大娘喜滋滋地,左看右看,最后相中了一個在牌樓干活的小木匠,這人不抽煙,能喝幾杯酒,娃娃臉,大眼睛,面善。那時候手藝人吃香,不問資歷,不管年齡,都是師傅,都得好煙好酒地伺候著。最讓人羨慕的還是“下午茶”——豬油下面條,碧綠的菜葉,焦黃的荷包蛋,聞起來香噴噴的,饞——這是手藝人的福利,豬油下面條和荷包蛋都是奢侈品,除了過年,平時我們是吃不到的。
女大不由娘,采芹悄悄相中了一個“兵哥哥”,國字臉,小平頭,喜歡扎馬步,穩穩當當,像一根樹樁。他脫下軍裝之后進了軋花廠,負責過磅,不知道是正式工還是合同工,是工人還是干部,這些其實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不是一個“泥腿子”,而是一個不用赤腳就能掙錢的“公家人”。
手藝人吃百家飯,但農忙時還是要赤腳下田,面朝黃土背朝天,公家人多體面啊,國家每個月按時發錢,太陽曬不到,雨也淋不著。玉大娘自然也是愿意的,只是舍不得采芹,媒人把日子都掐好了,她竟死皮賴臉地單方面毀約,還毀了兩次。采芹不答應了,坐在房里生悶氣,當真是女大不中留,玉大娘無可奈何,只好兩眼含淚,看著采芹穿著紅繡鞋,小鹿似的,歡快地奔向村口的機耕路……
采芹命好,嫁過去就過上了少奶奶一樣的幸福生活,牌樓待嫁的姑娘眼熱了,毫不掩飾自己的嫉妒與羨慕。誰能想到呢?采芹的幸福生活沒能維持多久,她婚后遲遲不開懷,吃盡各種偏方,始終沒有效果。那年臘月,采芹好說歹說,總算把將信將疑的丈夫哄進了醫院,一查,丈夫整個人就蔫了,抱著頭,蹲在地上,悶聲悶氣地抽煙。那個閉塞的年代,鄉下人不孕不育尚是不治之癥,他絕望地甩開采芹,醉漢一樣歪歪倒倒,一頭撞上一輛疾駛而來的嚴重超載的農班車。那是采芹揮之不去的噩夢,她目睹丈夫在巨大的撞擊下騰空而起,像一片輕盈的枯葉,在空中翻卷著,又碌碡一樣,跌了下來。她被這猝不及防的一幕嚇傻了,渾身篩糠一樣瑟瑟發抖,一個人居然能夠變得那么輕,那是她身強力壯的丈夫嗎?她不相信!
她奔過去,冰冷的馬路上蜿蜒著一大攤血。啊啊啊——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黃昏搖搖欲墜。炮仗聲此起彼伏,就要過年了。
七七四十九天,她沒有睡過一個囫圇覺,醒著的夜里,她幽靈一樣在臥室和客廳間徘徊,頭發掉了一萬根。家里空蕩蕩的,像一座專門儲存時間的冷庫。
一百天過去了。一周年過去了。三周年過去了。她收拾好自己的衣物,朝婆婆跪了下來,說,我要回牌樓。婆婆摸摸她的臉,干枯的眼里滲出幾滴淚。
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但牌樓人一致同意接納采芹,采芹成了第一個離開牌樓之后又申請遷回牌樓的人。
重新回到牌樓的采芹仿佛變了一個人,蘋果臉成了鴨蛋臉,腌過似的,不復舊時光澤。你這不算事哦!遇到合適的,遲早還是要再嫁啊……老人們勸她,她堅定地搖頭,淚水決堤一樣漫出來,漫的次數多了,老人們也不好再勸,私下里各種猜測。她也真是命硬哦!那么好的一個男人,說沒就沒了……她影子一樣來來回回,路上遇到人,條件反射似的垂下頭,像被人活捉的小偷。玉大娘心疼女兒,每每出面維護,她慌不迭地沖過去,推推搡搡著,將采芹一路扯回家。
她守著玉大娘,獨自打理五畝多田,起早貪黑地,像一個不知疲倦的長工。稻子一顆顆黃了,麥苗一壟壟青了,棉花一片片白了……她在一季季收成里慢慢活了過來,臉上又有了久違的笑容。
她活了過來,玉大娘也跟著活了過來。農閑時,母女倆時常結伴上街,慢騰騰的,有說有笑,像是遇到了什么開心事。有幾次,她甚至把扭扭捏捏的玉大娘牽進老杜茶館,泡一壺茶,老少爺們一樣坐在凳子上,大大方方地撕油條,吃春卷。婦女進茶館,那時還是稀罕事,老少爺們竊竊私語,“呵呵呵”地傻笑。
媒人又開始登門。她們以為,采芹公開拋頭露面是釋放信號,她已經治愈了內心的創傷,拂去了內心的陰影,開始為下半生打算了。采芹也一改往日的冷臉,大大方方地給媒人泡茶,續水,遞扇子。玉大娘仿佛年輕了十歲,她毫不掩飾自己的喜色,謝天謝地,菩薩終于顯靈了!
“想通了就好,哪有一生守寡的人呢?總不能守著一個死人過一輩子啊!”
“伢啦,你也算對得起他了!趁早,尋個人過自己的日子。”
……
媒人領來一個,她見一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年紀大的,年紀輕的……玉大娘惶惑了,伢啦,這個看不中,那個不如意,你到底想找什么人啊?
她捂著臉,哽咽道:“這幾天,一到晚上,我就看到他,躺在血里,望著我,抽搐……我以為,已經忘了,哪曉得,還是,忘不掉……”
玉大娘兀自一驚,顫巍巍地盯著她,仿佛驀然間撞見女婿的鬼魂。
再無媒人上門。
玉大娘的臉越皺越小,腿完全瘸了,隨手拄一根用松木削成的拐棍。
漠漠平田新雨后。布谷聲聲,牛背鷺結伴飛來,又結伴飛走。她又成了長工,埋著頭,沒日沒夜地,自虐似的勞動。那時候,牌樓還有四個人種田,只有她一個人堅持到了最后。她是在牌樓之外見過世面的人,不吵,不鬧,只是據理力爭,爭到后來,大家都不高興了,牌樓哪有你說話的份哦?同意你回來,已經算不錯的了,怎么還能這樣不知深淺呢……她啞口無言,轉身去找種糧大戶。
種糧大戶姓仇,五十歲左右,黑白相間的運動鞋,牛仔褲,藍格子襯衫。她在心里笑了,這一看就不是種田的人,種田的人,怎么可能穿運動鞋、牛仔褲呢?
仇老板,我沒地了,也沒事做,你可缺人手啊?
仇老板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緊了緊褲腰帶,說,缺是缺,我開不起工資啊……
我不要工資,我只要自己種的小麥、棉花、稻子。
仇老板笑了,你怎么不出去打工啊?種田,掙不到錢的。
她不言語了,轉身,失魂落魄一般在田畈里轉悠。她不能閑著,也閑不住,一個人在山坳里開荒,栽了幾十棵桃樹。桃樹活了,成了桃林,她又在桃林四周扎起竹籬笆,養雞。那片雜草叢生、無人問津的山坳,漸漸成了她的私人農場,她在其間勞作,手里拎著把鋤頭,腰間別著把砍刀。次第開放的桃花真美啊,紅的紅,白的白,像一片片云霞掛在枝丫間。
那些輾轉反側的夜晚,她不止一次勸自己,采芹啊,丟手吧,出去打工!總不能在牌樓老死啊,好講也不好聽啦……東方既白,又是新的一天。她一如往日,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全無離開牌樓的打算。
玉大娘愁死了,平白無故找她茬,拿她撒氣,變著各種法子攆她,她心知肚明,只顧埋頭干活,不搭腔。
母女倆幾乎成了仇人。每次說到采芹,玉大娘總要惡狠狠地捶打自己的瘸腿,一面捶一面咒自己:“我真巴不得死啊!早一天死,早一天不煩她的神!”有一次玉大娘夢見老伴了,下雨天,老伴戴著斗笠,挽著褲腿,腳上都是爛泥。奇怪的是,她看不見老伴的臉,破舊的斗笠下面空蕩蕩的,像一只透明的碗。
2016年,七十六歲的滿升大爺在睡夢中走了,孤零零地,身邊沒有一個人。
2017年,朱家二嫂得了糖尿病,這個不能吃,那個不能喝,兩個月瘦了三十斤。
2018年,大強不小心跌了一跤,前額磕出一個血窟窿,他從鍋洞里掏了一撮柴火灰,摁在額頭上止血。大強的四個孩子都在外地,他誰也沒告訴,硬扛著沒去醫院,結果,血是止住了,他說話卻不利索了,舌頭仿佛短了一截。
2019年,風平浪靜,牌樓沒有大事發生。
2020年,新冠疫情過后,定旺忽然回來了,黑且瘦,顴骨聳立,峭壁似的,薄薄的嘴唇包不住參差不齊的牙齒。我至少二十年沒見過定旺,他常年在外做生意,家里的老屋已經塌掉一半。這次回來,他雇了幾個人,在老屋基上重新蓋起三層小樓。那是牌樓迄今為止最氣派的房子,一水的鋼化玻璃,一水的琉璃瓦,高大的門樓前立著兩根水桶粗的羅馬柱,左邊的柱子上盤著一條龍,右邊的柱子上雕著一只鳳,栩栩如生。誰能想到呢,房子還沒蓋好定旺就走了,雇了一個遠房親戚負責后面的裝修、水電與里里外外的地坪。老人們面面相覷,都不敢相信,新房落成這樣的大事,定旺自己怎么能不在場,怎么能不放鞭炮,又怎么能不請大家吃頓飯呢?更令大家吃驚的是,新房落成后的第一個春節,定旺竟然沒回來過年,他怎么敢哦!大年三十,新房子黑燈瞎火的,這多犯忌啊,牌樓沒有這樣的先例。這個定旺,壞了規矩!
壞規矩的還有采芹,她突然就信了主,置玉大娘的責難、老人們的勸阻于不顧。年輕的一代牌樓人已經被外面的世界改變了,他們更加自我,有著與老一輩牌樓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
傳統意義上的鄉村已經不存在了,農耕文明的退場和鄉村倫理的瓦解,或許是鄉村振興最大的瓶頸。
那天進山途中,意外遇到禮拜歸來的采芹,我脫口而出:“做禮拜啊?”她含糊地應了一聲。“沒多少人做禮拜吧?”她停了下來,清澈如水的目光越過我的肩膀:“牌樓就我,桃園、杏莊那邊多些,統共也不超過二十個。有些人,做做也就不來了,家里人攔著……”
“地方遠了,來回都不方便。”
話音剛落,她便步履匆匆地走了,圓潤的臉上閃過曇花一現的笑容。我茫然地僵在原地,這個比我小十個月、和我結伴上過四年小學的女人當真要在牌樓終老嗎?如果她離開牌樓,又將在何處安放余生呢?
山巒肅穆。淡藍色的煙嵐在山坳間浮游,樹冠上的日光瀑布一樣迸射,仿佛不是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