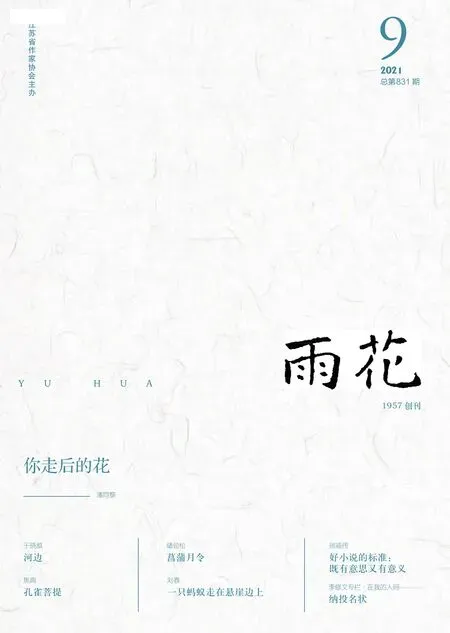野鹿蕩:暗夜星空
姜 樺
川東閘口南側的一片寬闊的蘆葦場,因為瀕臨世界上最大的麋鹿野放區,茂盛的葦叢里時常有野鹿、牙獐、柴狗、野兔等動物出沒,故名“野鹿蕩”。四月,天氣清明,大地升溫,一群有頭無臉的蟲子從草根下鉆出來,爬過那一片片新鮮的樹葉。被泥土抬高的野鹿蕩的“麋鶴營”中,幾頭雄性麋鹿屏住呼吸,顫抖的犄角直挺挺地釘在地上,睫毛上掛滿了青草種子,一股濃烈的欲望,伴隨著撲朔迷離的眼神,正滲入春天的深處。
以一條寬闊的復堆河為界,與“麋鶴營”隔著一道河堤,野鹿蕩東邊一片更大的區域屬于野生麋鹿的活動范圍,通常被稱作“麋鹿野放區”。早些年,這片野放區僅僅是指川東閘口到梁垛河口的一片蘆葦灘和沼澤地,如今,隨著野生麋鹿在響水灌河口以及東臺條子泥灘涂相繼被發現,鹽城沿海從南到北數百公里的海岸線,幾乎都成了野生麋鹿的生活區。只是,作為麋鹿活動的核心區域,“麋鶴營”和野鹿蕩的地位一直不曾改變,有時候,在這個區域聚居的麋鹿會達到近千頭。
大地在不同季節里捧出的一束束野花,仿佛一封封寫給遠方的質樸而親密的信。十月,灘涂上的風從麋鹿野放區一路吹過,一直吹向野鹿蕩,站在那一條條高高的老木船上,水波晃動著一群群麋鹿的倒影。深冬的灘涂大地天寒地凍。正是麋鹿脫角的季節。夜晚,一輪月亮從野鹿蕩里升起來,圓圓的月亮被勾出一道白色的霜邊。大野安靜,一只只鹿角從半空中脫落,也有走著走著就掉了的,但是都會在堅硬的灘涂地上留下空空的回響,那“咔吧咔吧”的聲音很遠就可以聽到。這樣的情景是獨特的,但你且不急著去管它,等到翌日清晨,一片耀眼的陽光照耀著那片堅硬霜白的灘涂,那塊空曠的土地上留下的一只只鹿角一律平穩倒置,猶如一只只堅定有力的手掌緊抓著這一片灘涂。圍繞著那一只只巨大的鹿角,灘涂地上布滿了麋鹿新鮮的蹄花,一只又一只,一圈又一圈,那是一只只麋鹿圍繞著剛剛脫落的鹿角向大地致敬,也是它們就著清冷的月光寫給灘涂大地的秘密經文。
四月末,堆滿灘涂的油菜花結出了飽滿的籽粒,稍晚一些,白色的洋槐花又會在頭頂上盛開。緊挨著野鹿蕩,一條海堤公路由遠及近。這條路是從附近的一座已經有半個多世紀歷史的國有林場走出來的。道路兩旁,到處是蒲公英、狗尾草和野薔薇。偶爾會遇見一群野山羊和海仔牛,一個個健壯肥碩,它們身披露水,似乎一夜未歸,讓你懷疑它們是不是原本就沒有主人。身邊不時有趕海的人們騎著摩托車經過,都是一些趕往海邊小取的人,有本港人,也有外地的,連云港人、南通人、山東人、浙江人,甚至是河南人和福建人。他們凌晨三點多就出門了。一個多小時后,當海水退去,一片巨大的海灘從海水里裸露出來,一波又一波趕海人,他們用隨身攜帶的長長的竹鉤在灘涂上左勾右刨,東奔西跑中就將一只只海蟶和文蛤捉進自己的魚簍里。追逐著淺淺的潮水,這樣的勞作一般會從上午一直持續到晌午,在下一個潮汛到來之前,這些趕海人會撤出灘涂。傍晚時分,他們帶著滿滿的收獲退回到岸上。裝滿魚獲的蛇皮口袋一般都是扛在肩上,魚簍則會放在灘涂上一路拖著往前走。這活計看似簡單實則極其消耗體力,因為剛剛退潮的灘涂上,那潮濕的淤泥總是充滿了阻力。為了減少這種阻力,趕海人會在魚簍底下放上一塊特制的木板,薄薄的,前面高高翹起,像拱起的船頭,又像一只飛揚的雪橇。當然,拖魚拉貨這些活兒基本都是男人們的事,跟在后面的女人,腿上身上沾滿了點點泥斑,在春天的風中,那些飄動的頭巾五顏六色,依舊被裹得嚴嚴實實。這時的野鹿蕩更像一個巨大的蘆葦城堡,一直跟隨在他們的身旁。
走進野鹿蕩最好的季節還是在初夏,五月。清晨五點,你起床,跟著一塊很有些年代感的木質門牌,走出一條條被風雨剝蝕的已經成了客棧的古船。徒步向前,去往野外。寧靜的野鹿蕩里,青葦環繞的湖面被一層薄薄的晨霧籠罩著,時而有魚兒躍起,時而有宿鳥飛過。一輪初升的太陽浮出水面,紅彤彤的,美輪美奐。越往前走,蘆葦越深。隨著云霧逐步散去,一片巨大的草原在灘涂上鋪開,那是野鹿蕩最核心的部分,已經快到了“麋鶴營”。最早發現這片海邊大草原的是攝影師老宋(我們更習慣叫他從然)。2013年深秋,我和老宋一起去灘涂采風。車子開上川東河大橋,迎著川東閘口的方向,老宋從航拍器里意外地發現了這片系著金色腰帶的紅灘涂,那是一大片鹽蒿草灘和大米草灘。棕紅的大地火焰噴薄,川東閘口方向,一座座巨大的風電塔伸向藍天,轉動的葉輪要將天空的白云一片片絞碎。
一次貿然又意外的闖入,讓我們的內心充滿了驚喜。穿行于這片海濱灘涂,仿佛行走在遼闊的北方大草原。幾十年的灘涂濕地田野考察中,我曾經在響水陳家港的灌河口和東臺弶港的圍墾區多次見過鹽蒿草灘,卻不知道在川東閘口也有這樣一片神秘之地。航拍的小飛機在天空轉了一圈又一圈,老宋拍了一張又一張灘涂草原的照片,我則為這些圖片配上新寫的詩,然后在本地的一家報紙以專欄形式推出。
這一組灘涂草原的詩我前后寫了近二十首。報紙連續刊載了十多期,有幾期還特意印在了封面。
記得有一首《黑蓑衣的雨》:
林中密布穿著黑色蓑衣的雨滴
趕往五月的路上,隨著一陣風
那些蝴蝶、蜜蜂和鳥鳴
跌落成身底下星星點點的油菜花田
一叢叢菖蒲站在水邊,我知道
它們喉嚨里的饑渴。疾飛的鳥劃過雨水
它們的身體,翅膀,長長的腿腳和喙
而我最疑惑的是那些樹,枝干灼燙
它們藏于內心的綠色,是否要等到
油菜花開滿了,才會徹底說出!
十多年來,這片美麗到驚心的灘涂草原無數次在我的夢中出現,我和老宋也一次次重回野鹿蕩,重新走進這片海濱草原。我們還策劃了一個個和灘涂相關的采風活動,有幾次,我們甚至將朗誦會開到了灘涂上。在高可沒膝的紅草地和大米草灘上鋪下一張巨大的塑料布,一行二十多人,大家或立,或蹲,或臥,或者干脆躺在干凈的草地上,一邊看著那片湛藍的天空,一邊高聲朗誦自己新寫的詩。白云飄舞,飛鳥誦唱,天遠地偏,萬物皆忘。太陽落下,紅色的鹽蒿草被夕陽抱回家去,我們在一大片空地上燃起篝火,在歡快的舞蹈和歌聲中徹夜狂歡,那樣的時刻,沉醉于詩歌中的我們,乃是整個世界的中心。
也就是在那一段時間,我們有幸結識了這片野鹿蕩的主人——地方史研究專家馬連義。頭發有些花白的老馬是一個典型的自然環保主義者。20世紀70年代,他曾在西藏的阿里地區工作生活多年。80年代調回江蘇老家后,在當時的縣委宣傳部做了兩年多的副部長,但是很快老馬便棄官,非要到海邊灘涂去做一名義工。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老馬一次次只身深入黃海灘涂的農場、林場和麋鹿野放區,跟蹤那一只只野生麋鹿,進行黃海濕地麋鹿生態和灘涂文化的田野調查。十多年間,他精心撰寫的一本厚厚的《麋鹿本紀》成為他有關麋鹿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一組為祭奠從英國烏邦寺回歸祖國的三十九頭麋鹿而創作的“十四行詩”,迄今也一直都是中華麋鹿園的“鎮園之寶”。
從2009年春天開始,為了更好地研究野生麋鹿種群保護和生物遺民的歷史,老馬將目光轉向了麋鹿野放區以外一處更為偏僻的灘涂地,也就是今天的野鹿蕩。據老馬和一群志愿者考證,大約一萬年前,靠近川東閘口的一大片野蘆蕩,包括東臺的新曹農場、蹲門口(野鹿蕩下游三公里)、巴斗村一直到弶港一帶,都是古長江的入海口。江河東流,大船出港,小船靠岸,彼時的長江入海口水道寬闊,一片巨大的河口三角洲,兩岸居住著一個遠古的移民部落。在這里,他們打魚、捕獵、曬鹽,看著那野草蓬勃生長,與身邊的蘆葦菖蒲、灰鶴蒼鷺一起,見證了一片灘涂海岸的千年滄桑。
千百年河流沖擊,最終造成了長江口的不斷南移,這條老河口也變成了一片更大的灘涂地。老馬出生在大豐裕華,是典型的本場(本地)人。一百多年前,民國實業家張謇組織大批移民從南通北上鹽城,帶著上萬名啟(東)海(門)移民在荒涼的蘇北海邊灘涂廢灶興墾。作為一個自然生態作家,老馬對這一段移民的歷史情有獨鐘,從骨子里認定可以在這片灘涂地上找到更多祖先的足跡。整整兩年時間,老馬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起早貪黑,不辭辛勞,從南到北,踏遍了沿海地區上百公里的灘涂,從干涸的淤灘上拉來九條一百多年以前著名實業家張謇興辦“大豐公司”時留下的古老沉船,還將擱淺在海灘的晚清和民國初期的幾十只鐵錨也運到了這里,最終在麋鹿野放區附近,這片蘆葦叢生的三角地上,建起了一座生物移民所,并將這片蠻荒的土地命名為“野鹿蕩”。起初,老馬試圖將野鹿蕩建成一座專門研究移民史的半開放的工作場所,同時兼及旅游和濕地文化傳播,只是事情一波三折,整個過程并不順利。但是無論如何,因為一個人的努力,一塊原本荒寂無人的亙古荒原,最終成為了一片面積寬闊、蘆葦環繞的野鹿蕩,成為了一處歷史文化遺產。站在灘涂,面朝大海,頭頂著暗夜星空,野鹿蕩像一個飽經滄桑的老人,講述著一個個生物移民和灘涂變遷的故事。
六月,面向大海的灘涂晨光熹微。掛滿露水的野鹿蕩,一群高大壯碩的雄性麋鹿將顫抖的鹿角猛然抬起,一場充滿魅惑的鹿王爭霸戰拉開了序幕。
電視正在直播——
春天,野鹿蕩的水位被一棵棵新生的蘆葦所提高,灘涂大地上花木生
發,槐花飄香,成年麋鹿開始進入發情期。在這個生動的季節里,每一頭業已成年的雌性麋鹿身上,都會自內而外、從下而上地散發出一種神秘而特別的氣味,即便是沒有風,這種氣味也會穩定地震顫在空氣中,并且沿水平方向朝著四面八方的灌木和草叢間彌漫。
鹿王爭霸戰說到底就是一只只雄鹿為了爭奪嬪妃而展開的角力與較量。開闊的灘涂上,尖銳的鹿角挑起的泥土四處飛散。陶醉于某種濃烈的氣味,一群雄鹿漸漸靠向另一群雄鹿。一場充滿激情的鹿王爭霸戰,使得整個城市也跟著荷爾蒙上升。你看,大街上的人們臉上都是紅撲撲的。幾乎所有人都參與了這樣一次即將開始的充滿激情的狂歡。
麋鹿爭霸的灘涂,是一個充滿激情和力量的競技場。電視直播的鏡頭緊跟著那一群行進中的麋鹿在不停調整著角度。那些雄鹿大口呼吸著雌鹿身上散發出的獨特氣味,然后屏住呼吸,沉默良久,再舒緩地呼出。而游動機位則給到了那些雌鹿,它們健壯,美貌,站在遠處靜靜地觀賞,粗大潮濕的尾巴揚起又落下,神態專注又如醉如癡。
隨著體內的荷爾蒙的驟然增多,競技場上,那些仰頭長嘯的雄鹿緊張而忙亂。成年雄鹿會突然開始裝扮自己,它們往身上涂抹泥漿,用尖銳闊大的雙角,挑起地上的泥土和青草、樹枝作為裝飾,分泌出的液體,也被隨意涂抹于高大的樹干之上。伴隨著身邊的草浪,平時看似散淡的雄鹿們突然變得性情暴躁,并且發出一陣陣響亮而怪異的叫聲——顯然,雄鹿們希望以自己的吼聲來震懾住對方,更希望由此博得遠處的雌鹿們的青睞。
偌大的灘涂上聚集著一頭頭雄鹿,他們站在野鹿蕩或者麋鹿野放區的縱深處,一雙雙眼睛看似瞇成了一條縫,卻是一刻不停地緊盯著那片即將成為競技場的空曠灘涂,緊盯著迎面而來的一個個對手。
一頭雄鹿開始緩步走向一頭雌鹿。即便只有短短二三十米的距離,這段旅程也幾乎需要耗盡它們全部的體力。因為,在抵達雌鹿的過程當中,幾乎每一頭身強力壯的雄鹿都要經過一場激烈角逐和生死決斗。
鹿王爭霸戰,這是麋鹿家族為了爭奪王位而進行的最壯觀的充滿血腥的戰斗。
兩頭體魄健壯的雄鹿走進了畫面,雙方是那樣的激情四射,又那么虎視眈眈。
啊,你看,它們沉默,它們不說話,它們不打招呼,就這樣猛然沖向了對方!平時的空曠地帶,瞬時成了一只只麋鹿之間爭奪鹿王的戰場。
一邊是一頭頭雄鹿為了奪取鹿王打得不可開交,一邊是大群的雌鹿站在遠處靜靜觀望。是的,那些身體里
散發著特殊氣味的雌鹿,正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這場戰斗。此時此刻,它們的眼睛里寫滿了渴望,它們希望有一頭最為健壯有力的雄鹿力克群雄,盡快脫穎而出。而那頭最終勝出的雄鹿,將是它們最偉大的“王”。
鹿王爭霸,是一群麋鹿為了奪取交配權所進行的鏖戰。事實上,雄鹿之間為了爭奪嬪妃而展開的角逐并非人們描述得這么有趣。那些攝影師們偶然捕捉到的所謂鹿王爭霸的場景,從未在直播現場的鏡頭中重現過。根據來自國外的一份資料顯示,雄鹿之間為爭奪配偶的角斗相對溫和,并無激烈的沖撞和大范圍的移動,角斗的時間一般也不超過十分鐘,失敗者只是掉頭走開,勝利者一般不再追逐,很少發生鹿與鹿之間相互傷害致殘的現象。一頭雄鹿占群之后,若遇其他雄鹿窺視母鹿,占群的雄鹿僅會用吼叫和小幅度的追逐趕走對方。
讓許多人津津樂道的麋鹿爭霸戰,說到底只是嵌入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楔子。從野放區到野鹿蕩,麋鹿家族的上千頭麋鹿似乎并不關心這些。它們或跪或臥在高高的堆堤或者淺淺的沼澤里,一邊安靜地啃食著水邊的青草,一邊抬起頭看一看透明的藍天,安然自在,氣定神閑。
那些勝利者和失敗者很快都將再次回到野鹿蕩,再次回到麋鹿野放區,回到屬于麋鹿、飛鳥和風聲的灘涂大地——那綠色無邊的草原。
對麋鹿爭霸的觀察與描述,同樣體現出東西方人精神、文化和世界觀的差異。
綠色在彌漫,一直彌漫到秋天——秋天,巨大的灘涂正被火紅的鹽蒿草覆蓋。緊接著,那血一般殷紅的鹽蒿草又將被大米草吞沒。
大米草(學名:Spartina anglica Hubb),一種多年生直立草本植物,原產于歐洲,生于潮水能經常到達的海灘沼澤中。因為耐淹、耐鹽、耐淤,可以在海灘上形成稠密的群落。
在中國東部黃海海岸地區,大米草的引進始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初只是為了擋潮消浪、保灘護堤,但是沒想到這種植物繁殖極快,幾年就能把整個灘涂上的其他植物吞噬得一干二凈,往往去年還生長在海邊的一大片鹽蒿草,今年已經被大米草吞噬了大半。在野鹿蕩附近,包括更遠一些的條子泥海灘,我們帶著滿腔希望尋找的紅灘涂,僅僅幾個月就沒有了蹤影。
但是,這片安靜的海灘還在。在一片開闊寧靜的天空下,在奔跑著成群麋鹿、留宿著無數飛鳥的野鹿蕩,今夜,我們的頭頂停留著一片世界上最黑暗也最寧靜的夜空。
剛剛被命名的“黃海野鹿蕩·中華暗夜星空保護地”,是繼黃渤海濕地作為世界自然遺產地之后,人類與大自然又一次成功建立契約。鹽城黃海野鹿蕩,這是中國繼西藏阿里、那曲之后第三個暗夜星空保護地,也是中國沿海地區從南到北第一個暗夜星空保護地。面積逾萬畝的野鹿蕩和更大范圍的麋鹿野放區,平時人跡罕至,數十萬株茵陳草迎風生長,香味撲鼻,每到夜晚,蟲鳴如潮,浩瀚的天空繁星閃爍。在野鹿蕩這片面積26 平方千米的區域內,因為沒有光污染,平均每年可觀察星空238 天,夏夜銀河、冬季獵戶星座清晰可見,仿佛伸手可觸,而白茅島上的茵陳草引來的繁星般的螢火蟲飛來飛去,閃閃爍爍,和天上的星海遙相呼應,散發著圣潔之光。“黃海西岸一古船,繁花野草滿天星。”在以條子泥為核心的黃海灘涂濕地成為世界自然遺產地之后,野鹿蕩的萬畝草原又成為無數天文愛好者追逐暗夜星空的最佳去處,于是,在追逐灘涂候鳥的隊伍之后,一群又一群人來到了這里,來到了靜靜的野鹿蕩。太陽落下,夜幕低垂,大地寧靜,星空喁喁,大家在此靜坐相依,抬頭遙望星空萬物,以手中的鏡頭記錄下頭頂的深邃星空,一起分享這獨特的、能夠看見浩瀚星空又能聽見彼此心跳的野鹿蕩之“夜”。
灘涂浩大,海生煙波。生活在大海邊,大自然賜予我們不斷生長的灘涂地,天空之鏡般的野鹿蕩。不滅的星光下,更多的志愿者加入了野鹿蕩的保護隊伍,追隨高高舉起的蘆葦穗絮,將目光一直送向頭頂的浩瀚天空。大海邊的暗夜星空,像一篇古老的神話,更是一首連著天際的大地歌謠。
自然保護主義者馬連義還徒步行走在灘涂上。他和他的團隊在野鹿蕩的田野調查工作已經進行了整整十五年,記錄下的野草種子已經達到四百八十五種,發現的鳥類也已超過了三百多種。
攝影師老宋還在灘涂上跋涉。經風歷雨,飲霜宿露,一遍一遍走向大海,走向灘涂上的野鹿蕩,他的那輛裝滿器材的車子幾乎就是一輛灘涂直通車。河流滄海,火焰灘涂,淺溝深壑,頭頂紅冠的丹頂鶴,“四不像”的麋鹿,一直都是他鏡頭中的主角。
而我,面對灘涂,面對野鹿蕩,抬頭仰望頭頂廣闊的星空,遙想著千百年前那些居住在長江口的移民部落,追憶那片灘涂大地的前世今生,以及一首詩歌的來歷和去處,我發現,身邊的野鹿蕩,那艘古舊的船頭上,不知何時,多了幾架天文望遠鏡。
“暗夜”洶涌,我們在這里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