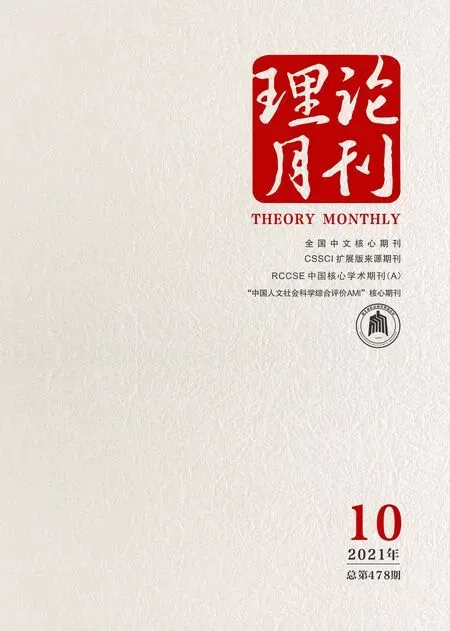鄉村振興背景下老年人福祉治理的責任分擔研究
——基于CHARLS數據的實證分析
□秦永超
(洛陽師范學院 法學與社會學院,河南 洛陽471934)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中央深刻把握鄉村現代化建設規律,順應億萬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三農”工作做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農村老年人是亟待關注和照顧的一個弱勢群體。農村老年人面臨的福祉困境較為突出,其在經濟狀況、勞動負擔、健康醫療、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存在諸多的困難。他們自身的健康狀況日益下滑,子女外出務工不在身邊,加之撫養孫輩的負擔,他們面臨著物質層面的贍養匱乏和精神層面的孤獨寂寞,這極大影響著他們的福祉水平。隨著農村勞動力不斷外流,農村日趨衰落和空心化,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弱化,是否還能承擔起基礎性的養老責任?“生于斯長于斯”的熟人社會不斷異化,還能否給農村老人們提供“葉落歸根”的安全感?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還相對滯后,能否承擔起兜底責任?如何整合家庭支持、熟人社會和國家保障的各自功能和責任分擔,進行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更是關系著鄉村振興戰略成功與否的核心問題。因此,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探討各個社會支持主體對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的責任分擔問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福祉是一個多維度的綜合概念,主要包括健康福祉和心理福祉[1](p1-15)。福祉是與幸福感、生活質量和社會福利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福祉包含幸福感,是好的生活質量;福祉是社會福利制度安排的終極目標。總的來說,福祉是一種健康的、滿意的、幸福的生活狀態[2](p73-79)。福祉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積極思考,即有效地提出制度安排規劃;積極行動,即通過福利提供行動實現福祉目標;美好擁有,即人民共享發展成果;成功避免風險,即成功避免生活中的風險;共享和獲得幸福感。福祉治理的最終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3](p310-547)。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是人們對自己生活狀態是否滿意的較為穩定的認知評價和情感體驗,是概括性的、結果導向的主觀心理反應。而獲得感反映了個體需求滿足與否的客觀現實與生活滿意度和終極幸福體驗的中間狀態[4](p195-217)。福祉治理正是通過提升人們的健康水平和獲得感,而提升其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
社會支持是老年人福祉治理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社會支持來自社會網絡成員的情感支持、工具支持和經濟幫助形成的互動過程[5](p116-134)。家庭成員之間提供的支持,熟人之間社會交往活動的支持以及國家層面提供的社會保障都屬于社會支持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已有文獻對農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6](p186-212)、彼此相互信任的熟人社會[7](p74-78)、享有國家層面的社會保障及福利[8](p54-63)進行了較為充分的探討,關于家庭支持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和生活滿意度的影響[9](p157-180),社會交往活動對農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響[10](p78-89)以及國家層面的社會保險與農村老年人福祉之間的關系[11](p68-80)也有比較充足的研究,然而已有研究明顯的不足之處在于,主要從家庭、社會和國家等單方面社會支持主體進行探討,籠統或者整體性地分析養老責任認知,缺乏系統的多元治理理論視角,未能將各個社會支持主體與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的關系放在多元框架中分析,鮮有探討各個社會支持主體在老年人福祉治理中的責任分擔問題。因而家庭支持、熟人社會和國家保障在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中的責任共擔的相關研究較為匱乏,亟待進行深入的實證分析和理論探討。
本研究以農村老年人為研究對象,采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數據,對不同社會支持主體與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的關系進行分析。通過驗證家庭支持、熟人社會和國家保障的作用差異,力圖揭示不同社會支持主體對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的責任共擔,并希望這一研究可在鄉村振興戰略的現實政策層面作出一定貢獻。具體研究問題是:第一,在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方面,家庭支持能否承擔基礎性的責任,熟人社會能否承擔補充性的責任,國家保障能否承擔兜底性的責任。第二,各個社會支持主體對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的責任分擔如何,是否均衡。通過回答以上問題,以了解不同社會支持主體對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的責任分擔情況,探索農村養老福利多元治理體系的構建路徑。
二、社會支持與福祉治理:社會學的定量檢驗
定性研究或根據定性研究發展出的理論,在方法論上不可避免地帶有小樣本和外部性的問題。基于特定地區和特定案例所得出的研究結論,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定性研究受到質疑的核心問題[12](p139-150)。而定量研究方法能夠通過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大型調查樣本來推論總體,以彌補定性研究樣本代表性不足的缺陷[13](p65-67)。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組織的“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數據。具有全國代表性,采用多階段(縣/區—村/社區—家戶)、分層(依據區縣的人均GDP),按照人口規模分配比例的隨機概率抽樣方法(PPS),覆蓋了除西藏、寧夏和海南以外的中國大陸28個省級行政區的所有縣級單位,樣本包括150個縣級單位,450個村級單位,約1萬戶適齡家庭中的1.7萬人。該數據的調查樣本基本上覆蓋了全國各個地區,其代表性較強,能夠避免小樣本和外部性問題,完全可以推論出全國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的總體狀況,進而實現本研究選擇定量研究的最終研究目的。
已有定量研究關于老年人福祉治理的測量文獻主要包括自評健康、生活滿意度兩個維度。其中,自評健康不僅是老年人對自身健康狀況的主觀評價,而且也是老年人客觀健康狀況的總體反映;生活滿意度是老年人對自身生活質量的整體認知和較為穩定的評價,是老年人對生活態度的認知層面的指標[14](p180-181)。已有的家庭支持、熟人社會、國家保障與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之間關系的定量研究文獻為本研究提出相應的研究假設奠定了理論基礎。而研究假設是社會學定量研究的基礎和核心。提出一個好的研究假設,不僅需要扎實的理論功底,需要對社會現實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力,還需要很好的想象力[15](p10-13)。社會學研究就是要充分發揮社會學理論的想象力,提出好的研究假設,用經驗數據來檢驗研究假設,從而豐富和發展社會學理論。
(一)家庭支持與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
家庭代際互惠理論認為,作為社會支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代際互惠是指家庭內部的父母與其子女之間的利益交換關系,即兩代人之間在金錢、時間、生活照顧等資源的給予和獲取方面的交換關系,通過代際之間的交換和互惠達到代際之間的平衡[6](p186-212)。根據家庭代際互惠理論,當父母步入晚年時期,理所應當得到子女的孝敬和贍養,因為這是父母一生都在為子女操勞和付出的回報[16](p13-19)。中國自古至今所謂的養兒防老、兒孫滿堂、天倫之樂等俗語蘊含了依靠家庭代際互惠關系進行家庭養老的某種假設:子女是老人物質生活的基本保障,同時也是老人精神世界的快樂之源[17](p79-80)。也就是說,家庭代際互惠關系是農村老年人晚年生活得以保障的根本之所在,是農村老年人福祉提升的基礎和源泉。
已有研究表明,子女提供的代際支持對老年人經濟狀況和生活水平的影響尤為重要,尤其是在養兒防老這一傳統觀念更為強烈的廣大農村地區。子女是一種長期的“戰略性投資”,是農村弱勢老年群體最可以依賴的養老支持資源[18](p52-60)。還有研究發現,由于農村地區缺乏正式的社會養老資源和體系,成年子女提供的經濟支持、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滿足了農村老年人養老的缺失性需求,能夠顯著改善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從而顯著地提升了農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滿意度[9](p157-180)。由此筆者認為,在當前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傳統的家庭支持還能否承擔起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的基礎性責任,亟待定量研究的經驗數據來進行檢驗。故提出本研究的假設1:家庭支持對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承擔基礎性的責任。
假設1a:家庭支持對提升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水平承擔基礎性的責任。
假設1b:家庭支持對提升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承擔基礎性的責任。
(二)熟人社會與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
熟人社會是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傳統中國鄉土社會人際關系的結構特征。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要由血緣、地緣和姻緣關系構成,人們相互間從熟悉到信任,并長期維系這種關系。熟人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19](p6-11)。作為文化和意義共同體,熟人社會給人們以守望相助、溫情脈脈的形象。在這個傳統的熟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禮尚往來,互幫互助,共度時艱,構建起了一個相互信任和高度依賴的命運共同體。以社區為基礎的熟人社會能夠滿足人們本體性安全的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社會交往的需要,以及合作應對社會風險的需要[7](p74-78)。因此,熟人社會理應在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中承擔著相應的責任。
另有一些研究表明,由熟人社會構成的社會力量作為國家和家庭在農村養老保障體系中的重要補充主體,通過一些公益性、互助性、服務性工作的開展,將成為我國今后建設農村老年人養老保障網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20](p35-41)。通過相關文獻梳理發現,來自社會主體提供的社區養老設施及服務,如休閑健身及娛樂活動、社區老年活動中心、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站、農村養老院等也都會對老年人福祉產生一定影響[21](p46-56)。然而,在當今的中國,隨著農村地區的日益衰落和空心化,鄉情原則也在衰落,村莊越來越只是村民暫時的聚居地而喪失了魂之所寄的重要意義[22](p99-102),熟人社會也在日益變異和邊緣化,正在逐步走向“半熟人社會”[23](p61-69)或“無主體熟人社會”[24](p19-25)。在當前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熟人社會還能否為理解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提供學術闡釋,將是一個有待檢驗的理論命題和研究視域。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熟人社會對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承擔補充性的責任。
假設2a:熟人社會對提升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水平承擔補充性的責任。
假設2b:熟人社會對提升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承擔補充性的責任。
(三)國家保障與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
當子女經濟支持不足以支撐農村老年人養老需求時,國家層面的社會保障應該能一定程度上緩解其經濟壓力。國家所提供的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雖然不能根本解決農村老年人的生計問題,但是能一定程度上緩解其生活壓力,從而有利于提升其福祉水平[25](p3-14)。國家作為農村老年人養老體系中的兜底性主體,一直以來都是養老保障事業的主導者和規劃者,承擔著兜底的責任。國家理應是社會福利最主要的責任主體,是社會支持主體中唯一具有總決策權的政治力量,是社會福利資源的擁有者和支配者[26](p133-138)。因此,國家主體在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中理應承擔起相應的兜底性責任。
通過梳理相關文獻發現,來自國家主體提供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都會對老年人自評健康產生一定影響[27](p21-29)。還有研究認為,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均能顯著降低農村老年人的抑郁癥狀,養老保險能顯著提升農村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28](p26-34)。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國家保障在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中的兜底性責任發揮得如何?這也是一個有待定量研究中經驗數據檢驗的命題。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設3:國家保障對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承擔兜底性的責任。
假設3a:國家保障對提升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水平承擔兜底性的責任。
假設3b:國家保障對提升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承擔兜底性的責任。
如果假設1、假設2和假設3全部成立,則表明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各個社會支持主體在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中的責任分擔處于均衡狀態。目前對養老多元化的定量研究僅僅停留在養老責任應該由家庭、政府、社會等多個主體承擔層面,而對不同主體應該承擔何種責任以及責任分擔是否均衡的研究并不明晰[29](p68-76),鮮有研究在微觀層面檢驗社會支持主體對個體老年人福祉治理的影響效應和責任分擔。由此可見,檢驗各個社會支持主體對個體老年人福祉治理的影響,探討各個社會支持主體應有的責任分擔,可以為評估和反思當前的社會支持政策后果提供更直接的經驗依據。因此,本研究使用CHARLS這一全國代表性的數據來驗證社會支持對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的責任分擔狀況。
三、數據來源與變量測量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是“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數據。該調查每兩年進行一次,全國基線調查于2011年進行,2013年進行了首次追蹤調查,2015年進行了第二次追蹤調查。其調查對象為中國45歲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個人。CHARLS調查收集了被調查老年人的個人基本信息、家庭信息、家庭交往與經濟幫助、健康狀況與功能、醫療保健與保險、退休與養老金、個人與家庭收入、社區相關信息八個部分的相關數據。本研究把2011年基線數據、2013年追蹤數據和2015年追蹤數據進行合并整理,從中篩選了戶口類型為農村、年齡在6O周歲及以上的農村老年人樣本,共篩選出6784個農村老年人樣本。
(二)變量測量
1.因變量。因變量是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本研究將從自評健康和生活滿意度兩個維度去測量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1)自評健康變量的測量。自評健康既能從客觀上又能從主觀上有效地測量被調查對象的健康狀況。該變量的測量來自CHARLS問卷中的一個問題:您覺得您的健康狀況怎么樣?經過歸類處理后,回答歸為三類,即差、一般、好;分別賦值1、2、3,得分越高表明自評健康水平越好,從而形成一個定序變量。(2)生活滿意度變量的測量。生活滿意度能夠有效測量研究對象主觀福祉的總體狀況。該變量的測量來自CHARLS問卷中的一個問題:總體來看,您對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滿意?該問題有五個答案:一點也不滿意、不太滿意、比較滿意、非常滿意、極其滿意;分別賦值1、2、3、4、5,得分越高則表明生活滿意度越高,從而形成一個定序變量。
2.自變量。核心自變量是家庭支持、熟人社會、國家保障。其中,使用三個維度來測量家庭支持變量,分別是過去一年是否得到子女的經濟支持、子女數量、有無子女經常看望。熟人社會變量的三個測量維度為近一個月是否參加休閑社交活動、生活需要時有無親戚朋友照顧、村里有無老年活動中心。國家保障變量的三個測量維度為是否參加新農合、是否參加新農保、過去一年是否得到低保。以上變量回答為“有”的編碼為1;“沒有”的編碼為0,并作為參照變量。
3.控制變量。控制變量包含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年限、個人儲蓄、家庭收入水平、患慢性病數量、生活自理能力、地區類型九個變量。其中,年齡、受教育程度、個人儲蓄、患慢性病數量四個變量為連續變量,其他五個變量操作為二分類的虛擬變量,每個變量編碼為1或0,其中編碼為0的變量為參照變量。表1是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1 :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研究結果分析
(一)各個社會支持主體與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
本研究使用序次Logistic回歸模型,并采用嵌套模型的建模策略,以分別估計家庭支持、熟人社會和國家保障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的影響效應。表2報告了家庭支持、熟人社會和國家保障三個自變量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影響的模型估計結果。

表2 :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影響的序次Logistic回歸模型
1.家庭支持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的影響。從模型2可以發現,過去一年是否得到子女的經濟支持和有無子女經常看望兩個變量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具有顯著性影響,子女數量變量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沒有顯著性影響。具體而言,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過去一年得到子女經濟支持的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更好的概率比沒有得到的要低11%左右(1-e-0.120≈0.113,p<0.1)。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子女的經濟支持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具有顯著性影響,但其概率系數是負的,也就是說,過去一年得到子女經濟支持的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水平反而更低。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那些身體不健康的老年人群體,其醫療費用花銷更大,更需要子女經濟上的支持。有子女經常看望的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更好的概率比沒有的要高出20%左右(e0.184-1≈0.202,p<0.01)。這里的結果部分驗證了研究假設1a。這說明,子女的經濟支持和子女經常看望對提升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具有積極作用。也就是說,家庭支持僅在一定程度上對提升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水平承擔基礎性責任。
2.熟人社會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的影響。模型3增加熟人社會變量是為了檢驗熟人社會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的影響。結果顯示,近一個月是否參加休閑社交活動、生活需要時有無親戚朋友照顧和村里有無老年活動中心三個變量均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具有顯著性影響。具體而言,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近一個月參加休閑社交活動的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更好的概率比沒有參加的要高出24%左右(e0.217-1≈0.242,p<0.001);生活需要時有親戚朋友照顧的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更好的概率比無親人的要高出17%左右(e0.156-1≈0.169,p<0.05);有老年活動中心的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更好的概率比沒有的要高出18%左右(e0.165-1≈0.179,p<0.05)。這里的研究結果充分證實了研究假設2a,即熟人社會對提升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水平承擔補充性的責任。
3.國家保障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的影響。模型4增加國家保障變量是為了檢驗國家保障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的影響。結果顯示,只有過去一年是否得到低保變量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具有顯著性影響,而是否參加新農保和是否參加新農合兩個變量并沒有顯著性影響。具體而言,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過去一年得到低保的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更好的概率比沒有得到的要低22%左右(1-e-0.243≈0.216,p<0.01)。這表明相對于未得到低保的農村老年人來說,得到低保的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反而更差,換句話說,低保福利供給僅對得到低保的部分老年人自評健康有一定作用。這里的結果無法證實研究假設3a。也就是說,國家保障對提升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水平不能真正承擔兜底性責任。
從表2關于社會支持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影響的研究結果發現,模型2中在0.01水平上顯著的子女經常看望變量,到了模型3中卻變成了0.05的顯著性水平,而且回歸系數也由模型2的0.184降低為模型3的0.171。這說明,子女經常看望變量的部分功能被熟人社會中的參與休閑社交活動、親戚朋友生活照顧和老年活動中心所解釋。模型3中在0.1水平上顯著的子女經濟支持變量卻在模型4中不顯著了,而且回歸系數是負的,這說明它影響的僅僅是享受低保的農村老年人這一小眾群體的自評健康水平,也就是說,低保福利供給屬于補缺型的社會救助范疇,并不是面向全體農村老年人的普惠型福利供給。綜上所述,子女經濟支持的部分功能被農村低保所替代,而子女情感支持的部分功能被熟人社會中的休閑社交活動、親戚朋友照顧和老年活動中心所替代。這意味著家庭支持功能在日益衰落,并逐漸被熟人社會的情感功能所代替。
總體來說,表2嵌套模型中偽決定系數(Pseu?do R2)的變化顯示,加入了家庭支持變量之后,偽決定系數從模型1的0.113提高到模型2的0.115,提高了0.002;加入了熟人社會變量之后,偽決定系數從模型2的0.115提高到模型3的0.118,提高了0.003;而加入了國家保障變量之后,偽決定系數從模型3的0.118提高到模型4的0.119,僅僅提高了0.001。這一結果表明,熟人社會變量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的解釋力最強,家庭支持變量的解釋力其次,國家保障的解釋力最弱。也就是說,各個社會支持主體在提升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的責任分擔方面,熟人社會承擔著最為重要的補充性責任,家庭支持承擔著一定的基礎性責任,而國家保障承擔的兜底性責任較為有限。因此,各個社會支持主體在提升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水平的責任分擔方面并不均衡。
(二)各個社會支持主體與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
本研究使用序次Logistic回歸模型,并采用嵌套模型的建模策略,以分別估計家庭支持、熟人社會和國家保障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效應。表3報告了家庭支持、熟人社會和國家保障三個自變量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影響的模型估計結果。

表3 :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序次Logistic回歸模型
1.家庭支持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從模型2可以發現,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子女數量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沒有顯著影響,而過去一年是否得到子女的經濟支持和有無子女經常看望兩個變量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性影響。具體而言,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過去一年得到子女經濟支持的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更高的概率比沒有的要高出18%左右(e0.161-1≈0.175,p<0.05);有子女經常看望的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更高的概率比沒有的要高出13%左右(e0.124-1≈0.132,p<0.1)。這里的結果部分驗證了研究假設1b。這說明,子女的經濟支持和子女經常看望對提升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具有積極作用。也就是說,家庭支持僅在一定程度上對提升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承擔基礎性責任。
2.熟人社會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模型3增加熟人社會變量是為了檢驗熟人社會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結果顯示,近一個月是否參加休閑社交活動和生活需要時有無親戚朋友照顧兩個變量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有顯著性影響,而有無老年活動中心變量沒有顯著性影響。具體而言,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近一個月參加休閑社交活動的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更高的概率比沒有的要高18%左右(e0.169-1≈0.184,p<0.01);生活需要時有親戚朋友照顧的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更高的幾率比沒有的要高出63%左右(e0.489-1≈0.631,p<0.001)。這里的結果部分驗證了研究假設2b。這說明熟人社會提供的社會支持對提升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承擔補充性責任。
3.國家保障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模型4增加國家保障變量是為了檢驗國家保障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結果顯示,只有是否參加新農保變量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有顯著性影響,而是否參加新農合和是否得到低保變量都沒有顯著性影響。具體而言,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參加新農保的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更高的概率比沒參加的要高出17%左右(e0.154-1≈0.166,p<0.05)。這里的結果部分驗證了研究假設3b。也就是說,國家保障對提升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不能真正承擔兜底性責任。
從表3關于社會支持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影響的研究結果發現,模型2中在0.1水平上顯著的子女經常看望變量,到模型3中卻不顯著了,而且回歸系數也由模型2的0.124降低為模型3的0.037。這說明,子女經常看望變量的部分功能被熟人社會中參與的休閑社交活動和親戚朋友生活照顧所解釋。即子女情感支持的部分功能被熟人社會中的休閑社交活動和親戚朋友照顧所替代,這意味著家庭支持功能在日益衰落,并逐漸被熟人社會的情感功能所代替。
總體來說,表3嵌套模型中偽決定系數(Pseu?do R2)的變化顯示,加入了家庭支持變量之后,偽決定系數從模型1的0.032提高到模型2的0.035,提高了0.003;加入了熟人社會變量之后,偽決定系數從模型2的0.035提高到模型3的0.040,提高了0.005;而加入了國家保障變量之后,偽決定系數從模型3的0.040提高到模型4的0.042,僅僅提高了0.002。這一結果表明,熟人社會變量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解釋力最強,家庭支持變量的解釋力其次,國家保障的解釋力最弱。也就是說,各個社會支持主體在提升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責任分擔方面,熟人社會承擔著最為重要的補充性責任,家庭支持承擔著一定的基礎性責任,而國家保障承擔的兜底性責任比較有限。也就是說,各個社會支持主體在提升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責任分擔方面并不均衡。
五、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家庭支持、熟人社會和國家保障對農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影響效應,以及三者之間的責任分擔。通過對“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數據的定量分析,發現家庭支持、熟人社會和國家保障在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中的責任分擔并不均衡,具體表現為:
首先,家庭支持承擔的基礎性責任在衰弱。子女數量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和生活滿意度均沒有顯著性影響。農村老年人子女大多長期在外務工,不能提供日常生活上的關心和照顧,導致其對父母的代際支持局限于經濟上的贍養功能,而其生活照顧功能較為弱化。低保戶老人的子女經濟支持的部分功能被低保救助所替代。子女經常看望這一情感支持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熟人社會所替代,這充分說明農村家庭養老功能在日益衰弱。
其次,熟人社會承擔著重要的補充性責任。積極參與休閑社交活動讓農村老年人能在熟人社會里增強自身的存在感和安全感,從而替代了子女看望這一情感支持的部分功能。親戚朋友的生活照顧解決了留守老人晚年生活上的后顧之憂,增強了其對未來生活的信心,從而彌補了子女生活照顧的缺位。老年活動中心這一為老服務也增強了農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總體來說,熟人社會里親朋之間的照顧和互助部分替代了子女的情感支持功能。
最后,國家保障承擔的兜底性責任較為有限。其中,參加新農合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和生活滿意度均沒有顯著性影響,參加新農保能夠顯著提升農村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而得到低保卻對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具有顯著性的負向作用,說明低保屬于補缺型福利,而不是面向全體老年人的普惠型福利,它影響的只是極少數生活極度困難的農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而不是所有農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因此,國家保障承擔的責任仍然較為不足,無論是在新農保資金上,還是在低保救助上都存在著群體的不均衡。
本研究的貢獻在于揭示了家庭支持、熟人社會與國家保障對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的責任分擔狀況,以此回應家庭支持、熟人社會和國家保障之間關系的理論分歧。家庭支持和熟人社會承載著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孝文化和互助文化。然而,本研究發現,傳統“差序格局”中家庭支持的資源隨著子女外遷而越來越弱化,而由親戚、鄰里以及村莊構成的熟人社會的支持資源會日益重要。這種中華優秀傳統鄉土文化的繼承和振興正是鄉村振興戰略中的核心政策議題。由于家庭支持和熟人社會的非制度性和非正式性局限,決定著其支持功能的發揮必須有國家保障的制度性扶持和兜底,因而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離不開國家保障的制度性支持。
(二)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要推進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家庭支持、熟人社會和國家保障應共同承擔起責任,鄉村振興的相關制度建設應從以下三個方面開展:
第一,增強制度化的國家保障,提升老年人福利水平。國家鄉村振興戰略需要加大農村地區國家保障的力度,如提高新農合的報銷比例,實施農村大病保險和救助制度,提高新農保的基礎養老金發放水平,健全農村低保標準動態調整機制,全面實施特困人員救助供養制度。提升新農保、新農合和低保在防范農村老年人健康、養老和貧困等社會風險中的作用。通過制度化的國家保障,旨在扭轉家庭養老功能弱化導致的留守老人福利獲得縮減的局面,讓新農保、新農合和農村低保等組成的國家保障在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中發揮真正的緩沖效應和兜底性責任。
第二,弘揚傳統孝文化,注重家庭支持和家庭建設。家庭自古就是中國傳統社會治理的基礎和重要力量,治理國家及天下其實就是齊家,因而家庭就構成了傳統基層社會治理的重心,在生活照顧、養老慈幼和婚喪嫁娶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福利功能。在家庭政策上,要變家庭支持為支持家庭,探索向低收入家庭照料者提供收入補貼。倡導子女經常探望和照料老年父母,實施帶薪探親假和帶薪照顧重病失能老人的休假制度。因而,在當前國家不能完全接力養老責任的狀況下,在農村地區還應該大力倡導孝文化,鼓勵子女盡到本分,不僅養父母之身,還要養父母之心。
第三,倡導傳統互助精神,構建鄉村互助型養老模式。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應加強鄉村公共文化建設,如倡導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方式,建設老年人文化娛樂組織,豐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以彌補由于子女外出導致的老年人情感支持上的缺失。在鄉村振興建設過程中,還要鞏固農村思想文化陣地建設,開展文明家庭等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做好家庭教育,倡導良好家風家訓,弘揚中華孝文化,強化孝敬父母的良好社會風尚。通過基層志愿服務活動,或者專業社會工作服務等方式,為農村老年人提供關愛服務,給予其更多情感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慰藉。倡導鄉村互助養老模式,可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支持社區助老為老組織和鄰里互助組織發展,推進農村幸福院等互助型養老服務發展,進而真正提升農村老年人福祉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