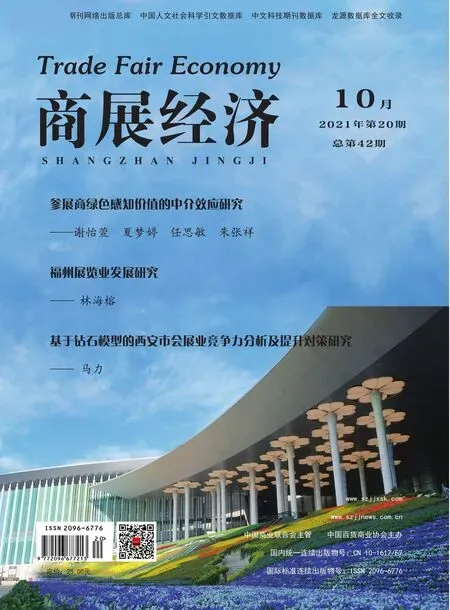金融科技創新對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的影響
——文獻計量與模型設計
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經濟管理學院 王希泉
中國人民銀行玉溪中心支行 馬福春
就金融體系而言,金融體系的完善程度決定著金融與科技融合的成功概率,對于完善的金融體系能提高金融與科技融合概率,加大金融創新,能在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做出改善。近年來,大量的學者雖然從金融體系或科技發展單一視角研究其與企業經濟之間的關系(Khoutem等,2014;劉文麗等,2014),但為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結合相關研究,將金融與科技融合起來,分析對企業經濟的影響,并進一步考慮經濟變量的空間相關性與空間依賴性,使得研究結論更具解釋力和說服力(Anselin,1988;Gilly and Torre,2000;Boschma,2005)(為了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取的省份是除西藏、寧夏、青海以外的28個省份)。
1 影響機理分析:基于文獻的視角
1.1 金融與企業經濟
大量的經濟學家對金融與企業經濟之間的關系做了廣泛研究,并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金融與企業經濟之間的相關關系。張亦春等(2015)研究表明金融發展與企業經濟增長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正相關,而是呈現出非均衡性,鑒于金融發展與企業經濟之間的關系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梳理,一方面是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金融發展理論表明,金融市場的發展可以通過產業結構傳導到企業經濟,提高資本配置效率,實現經濟增長,金融發展可以通過風險分擔來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經濟的波動,促進企業經濟增長,并且金融業在空間上的聚集也能顯著地促進企業經濟增長(劉軍等,2007;李青原等,2010、2013)。另一方面具有抑制作用。有學者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存在信息不對稱等因素,可能抑制企業經濟的發展(Patrick,1966)。李強等(2013)研究表明金融發展阻礙了企業經濟的發展,并對西部阻礙作用最大。金融抑制和金融過度都會損害經濟增長,外部金融生態環境影響會改變金融發展對企業經濟的影響,并且金融發展的滯后會對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造成障礙性效應,進而起到抑制企業經濟發展的作用(周曉艷等,2015)。
1.2 金融創新與企業經濟
對于金融創新,目前還無統一的定義,而多數定義是根據熊彼特的觀點衍生而來。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1912)中闡述創新是對生產要素進行重新組合。希克斯和尼漢斯(1969)認為金融創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目前學者和相關組織對于金融創新的內容和作用主要歸并起來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創新內容包括制度、機構、技術、產品以及市場創新等。二是創新作用包括轉移風險、增強流動性、提供資金等(龔明華,2005;陳文夏,2009)。對于金融創新與企業經濟的關系,一方面有學者研究發現,提高資金配置效率、風險分擔,加快資本積累速度,間接對企業的技術創新起到促進作用,進而提高經濟生產效率,推動經濟增長,但在不同地區可能存在異質性(Tadesse,2007;Greenwood等,1990、2010;劉文麗等,2014;李媛媛等2015),衛平等(2015)研究得出金融創新對工業增長具有正向作用,且正向作用時效長于負向作用時效,但工業增長也對金融創新呈現波動性沖擊。另一方面也有學者研究發現,金融創新對經濟增長具有差異性,單獨的金融創新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向是不確定的,有促進也有抑制,需要協同技術創新才能對經濟促進作用顯著(孫浦陽等,2012;李叢文,2014)。
1.3 金融發展、金融創新與企業經濟
金融發展可以促進技術和專利產品的產生,從而提高效率,可將金融資源更好地配置到企業經濟,促進經濟增長(Solow,1957;Schwartz,2000;Amore等,2013;劉文麗等,2014)。 另外,金融發展與金融創新兩者在融合過程中,潛在的風險會抑制企業經濟的增長。金融發展和金融創新在金融一體化背景下有著重要作用,但由于兩者融合發展復雜性和風險性的存在,可能會制約創新的效應,未能使兩者融合取得較好的效益(鮑丹,2008;曹顥等,2011)。
2 研究方法與指標選取
2.1 研究方法
2.1.1 資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
為了較為直觀地分析近幾年企業經濟的資本配置效率,資本配置效率模型屬Wurgler(2000)設置的模型,被學者廣泛運用。因此,本文基于Wurgler(2000)模型(Beck 和Levine,2002;韓立巖等,2005;李青原等,2013;張雪芳等,2016;陳創練等,2016)利用28個省份18個工業行業面板數據從微觀層面測算了地區企業經濟資本配置效率,同時用2003—2016年我國28個省份的相關宏觀數據,從整體、地區、省份三個維度測算宏觀企業經濟資本配置效率。因此,將企業經濟資本效率估算模型設置如下:

上式中,Iic,t為行業i省份c內第t年固定資產凈值(固定資本形成總額);Vic,t為行業i省份c內第t年工業總產值(總產值),η為資本配置效率,ε為干擾項。
2.1.2 空間計量模型
首先,本文采用“莫蘭指數I”(Moran’s I)(Moran,1950)檢驗經濟變量的空間相關性,指數如下:

其次,本文根據相關理論(陳強,2010)建立空間面板模型,具體如下:

公式(3)為空間面板自回歸模型,其中,Wi'為空間權重

其中,yi,t?1為被解釋變量yit的一階滯后項,τ≠0則模型為動態面板,di'Xtδ表示解釋變量的空間滯后項,模型(4)是一般模型,對參數處理將會建立不同的特殊模型,如下:

對空間模型分析,本文將具體模型設置如下:

其中,Yit為被解釋變量,FD和KJ分別為金融發展和金融科技創新,x為控制變量:gov(地方財政支出)、 inv(固定資產投資)、fdi(外商直接投資)、open(對外開放程度)、urban(城鎮化水平)、 hum(人力資本)。W 為空間權重矩陣,ε、v為隨機誤差向量,ρ為空間回歸系數,λ為空間誤差系數。對于模型的選擇主要通過拉格朗日乘子和模型的穩健性來判斷。
最后,為了模型分析本文將構建空間權重矩陣,分別從地理區位特征、社會經濟特征兩個方面設定空間權重,具體如下:

公式(9)是以地理區位特征設定空間權重矩陣,沒有反映地區間經濟社會之間的相關性及影響。介于此本文利用各省GDP構建經濟特征空間權重矩陣進行分析(張林,2016),如下:

其中,ε為隨機誤差項,s t d表示標準差,為第i省生產總值的平均值,為考察期內生產總值的均值,t為不同的時期。如果兩個地區生產總值相關關系越強,則方程的擬合效果越好,殘差波動范圍越小,空間權重系數越大,反之則作用相反。
2.2 指標選取
(1)企業經濟的代理指標:①直接拿GDP進行衡量(劉金全,2004;蘭日旭等2011)。②用工業增加值來衡量(曹源芳,2008)。③用資本配置效率模型估計工業企業的資本配置效率來衡量(李青原等,2013)。本文對企業經濟的衡量主要采取張林(2014)的做法:GDP -(金融業+房地產業)。
(2)主要解釋變量:金融發展指標(FD)和金融科技創新指標(KJ),本文主要采取因子分析法構建金融發展和金融科技創新指標。
(3)控制變量。本文以參考相關文獻的方法(李青原等,2013;張林等,2014),將控制變量選取如下:地方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對外開放程度、城鎮化水平、人力資本作為控制變量。
2.3 變量統計描述
(1)對于資本配置效率而言,本文選取樣本區間為2003—2016年,28個省份18個工業行業來測算企業經濟的資本配置效率,數據主要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宏觀經濟變量:企業經濟、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對外開放程度、城鎮化水平、人力資本指標,樣本區間同樣為2003—2016年,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3)金融發展指標和金融科技創新指標,數據來自《中國金融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金融發展和金融科技創新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較大,表明不同省份金融發展程度不一且金融科技創新程度差異大,而外商直接投資、人力資本地方財政支出標準差較小表明該指標相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