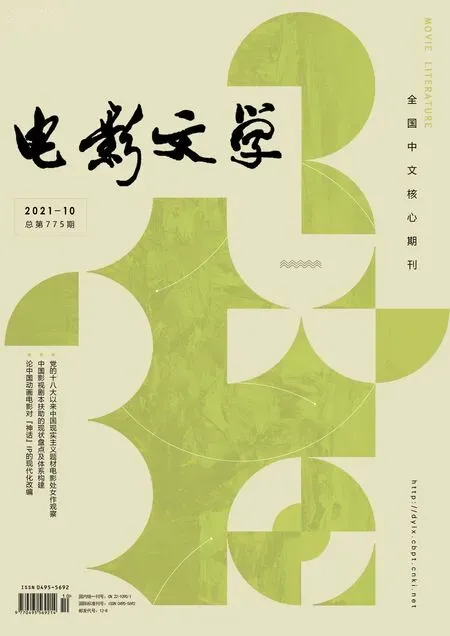論中國動畫電影對“神話”IP的現代化改編
張明浩 滿勝寵 郭培振
(1.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北京 100871;2.中央戲劇學院,北京 100710;3.東明縣廣播電視臺,山東 菏澤 274500)
2020年國慶檔,取材自“封神演義”的《姜子牙》成為一部飽受爭議、話題性很高的現象級電影。“影片劇作層面的問題是導致其‘口碑兩極分化’‘票房滑鐵盧’的重要原因。”具體而言,就是指《姜子牙》的“神話”改編并沒有符合受眾的審美期待,并沒有抓住“動畫電影吸引人的核心(人物與故事)”進行現代化改編。
《姜子牙》雖然只是個例,但是它也具有代表性:當下,我國動畫電影大多都是改編或取材自廣義的“神話”故事(此處的“神話”為廣義的神話,不僅包括上古神話,還包括仙話、傳說、志怪小說等),正確把握改編的“度”與方法,吸引受眾,滿足受眾“想象力消費”與審美期待心理,應該才是動畫電影“出圈”、制勝的關鍵。另外,“國漫崛起”顯然離不開“國家文化資源”尤其是傳統神話資源的支撐。
故此,筆者將以《西游記之大圣歸來》(以下簡稱《大圣歸來》)、《大魚海棠》《白蛇:緣起》《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影響力較大的動畫電影為案例,基于接受美學等理論,從“神話”文本重構與現代化改編的視角下,探索、總結出動畫電影“神話”IP改編的一條可持續發展“工業美學”道路。
一、優秀動畫電影的“魅力”:對受眾“互文記憶”與“期待視野”的滿足與挑戰
(一)“互文記憶”與“期待視野”
所謂“互文性”,是指“每個文本都處于已經存在的其他文本中,并且始終與這些文本有關系”。多數取材于神話故事的動畫電影必然可以觸及受眾的“互文記憶”。
所謂“期待視野”,是指“文學接受活動中,讀者原先各種經驗、趣味、素養、理想等綜合形成的對文學作品的一種欣賞要求和欣賞水平,在具體閱讀中,表現為一種潛在的審美期待”。
觀眾對于影片的“期待視野”大體會受以下幾方面影響:一是類型樣式;二是宣發;三是故事;四是受眾本身的文化素養及審美趣味。具體到動畫電影尤其是改編自神話IP的作品,受眾顯然會更期待看到自己想象的內容變為影像內容,又期待影像呈現超越自己的想象。
(二)優秀動畫電影的神話IP改編魅力:“滿足”又“挑戰”“受眾接受”
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強調主體已有的認識結構與客體刺激的交互作用。觀眾的觀影活動實則就是自身審美趣味所形成的對影片的“期待視野”與電影本體價值傳達的相互交流、融合的過程,達到某種審美“順應”狀態。
具體到動畫電影而言,它的魅力則是滿足甚至是挑戰了受眾的“互文記憶”與“期待視野”:
1.“神話”故事對受眾互文記憶的“滿足”
取材神話故事的動畫電影本身便與受眾有著“親密性”關系。神話故事中的人物或故事可以引起受眾互文記憶,拉近受眾距離。在我國傳統文化之中,有一股一直力量很大、不容小覷的“民間亞文化”,一直流傳,被諸多人“津津樂道”。《哪吒之魔童降世》取材自《封神演義》,其中,大家對哪吒“大戰龍王”“削肉還親”“蓮花重生”的故事,耳熟能詳,可以使諸多受眾回到“童年”;《白蛇:緣起》改編自民間傳說“白蛇傳”,白蛇水漫金山寺、懸壺濟世的故事家喻戶曉,白蛇與許仙的愛情故事更是唯美動人,可以勾起無數受眾的“影像記憶”;《大圣歸來》取材自《西游記》,取經、打妖、普度眾生的故事眾所周知,而影片借此“IP”,可以再度勾起受眾對師徒四人的情愫,拉近距離。
2.“神話”故事本身的“奇觀性”及對受眾的“吸引”
取材神話IP的動畫電影中的“神話”故事本身便具有奇觀色彩,可以促使受眾產生“前期待”等審美心理,滿足受眾對于神話的想象。無論是哪吒再生,還是《西游記》中的師徒關系、取經道路,抑或是白蛇傳中的唯美愛情等,取材神話故事的動畫電影,往往其故事本身便具有奇觀、夢幻屬性,而動畫電影作為這一奇觀故事的“再展現者”與影像轉化者,無疑更會激起受眾的審美期待。
3.在“改編”之中“挑戰”甚至“顛覆”受眾審美期待
取材神話IP的動畫電影不僅改編了神話,而且部分動畫電影還挑戰甚至是顛覆、沖擊了受眾的“期待視野”,以至于促使受眾體會到驚喜、“震驚”的美學體驗。在形象方面,《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丑哪吒”,《大圣歸來》中的“麻臉大圣”,《白蛇:緣起》中的“妖怪阿宣”,都一反“常態”,挑戰了受眾的審美。不止于視覺挑戰,這些作品之中的故事,也都是新穎、獨特的,甚至是具有現代感與“話題性”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將“神話”故事之中的“削肉還親”等情節刪除了,反而以“魔丸靈丸”轉世作為故事起點,雖然人物結構(家庭關系、對立關系)依舊,但故事進程已然變化:由之前的“哪吒大鬧龍宮,龍王發怒傷害百姓,哪吒為不讓父母為難而自刎”變為“哪吒因轉世靈珠問題而備受歧視,父母、師父協助其成長,哪吒最終知道身份后成魔,并在自己覺醒后‘回歸’”。這種變化,對于受眾原有的“互文記憶”來講,都在挑戰著、顛覆著受眾已有認知。
姚斯曾言:“在這個作者、作品和大眾的三角形之中,大眾并不是被動的部分,并不僅作為一種反應;相反,它自身就是歷史的一個能動的構成。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經驗視野。”
綜上所述,優秀動畫電影的魅力,便是尊重了“受眾接受”需求,在滿足受眾“互文記憶”與“期待視野”中,創新、挑戰甚至是顛覆了受眾的“記憶”與“期待”,以“相對新異性”的文本重構滿足了觀眾的新異心理和想象力消費需求,帶給了受眾相對新奇、獨特、新穎的審美體驗與審美感受。
二、優秀動畫電影“神話”IP改編的外在策略:“顛覆”式人物重構與“陌生化”敘事
如前文所述,多數取材于神話故事的動畫電影必然可以觸及受眾的“歷史記憶”,并使受眾產生“期待視野”。所以,如何基于受眾“互文”記憶又超越受眾“期待視野”,成為當下中國動畫電影改編的重中之重。
縱觀較為成功的動畫電影(如《哪吒之魔童降世》《大圣歸來》《姜子牙》《白蛇:緣起》等),它們似乎有一個共同之處——大膽改編甚至是重構了神話人物,匯入了當下想象力美學精神,并且進行了“游戲化敘事”、陌生化敘事等敘事方式的嘗試。
(一)神話人物的“重構”與“顛覆”:“丑”化的神話人物造型與“邊緣化”的人物境遇
人物是動畫電影吸引受眾的關鍵,清晰、明了、新穎的人物會促使動畫作品加快“出圈”。
當下較為優秀的動畫電影都在人物方面下了功夫。具體表現在人物造型的顛覆式重構與人物性格的重構兩個大方面。
1.人物造型的“顛覆式重構”:新奇、獨特的“丑”人物
當下引人注目的動畫電影都較為精巧地對神話人物的造型進行了現代化轉化,塑造了一個個讓人過目難忘的人物造型。人物造型的顛覆必然會引起話題,增加熱度,也正因如此,我們看到了“麻臉大圣”“丑哪吒”“中年帥大叔姜子牙”。
以《大圣歸來》中的孫悟空為例,“齊天大圣”孫悟空的人物形象出自中國四大名著《西游記》。讓中國幾代觀眾記憶猶深的當屬1983年版六小齡童飾演的孫悟空形象——尖嘴猴腮、火眼金睛、黃發金箍、手持如意金箍棒,斬妖除魔,神通廣大。之后《西游記》的翻拍中,孫悟空的形象設計也大都萬變不離其宗。在動畫作品中,被人熟記的“孫悟空造型”是20世紀60年代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制作的《大鬧天宮》,其外貌肖像、動作設計借助戲曲與剪紙等傳統文化符號進行設置,符合觀眾對孫悟空正義英雄形象的想象與“審美期待”。但《大圣歸來》中的孫悟空,變成了一個“長臉”“消瘦”“麻子”的人物,眼睛由炯炯有神的圓變為有點沮喪的扁平樣,服裝的顏色也由金黃色變為暗色,身材更是變為弓腰的形狀。這種前后的對比、差異,無疑會挑戰受眾已有記憶中的“互文記憶”,達到一種沖擊、顛覆、震驚的美學效果。
再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為例,《哪吒之魔童降世》大膽突破人物傳統造型,以奇特、大膽的想象構思了“黑眼圈”“鯊魚齒”“手插褲兜”,有點暴戾的“魔童”哪吒。“喪喪”的哪吒形象似乎是“熬夜冠軍”,這種“丑”化的人物設置直接挑戰了受眾互文記憶中那個靈巧、秀氣、漂亮的哪吒。在高度反差下,會產生一種震驚與沖擊的美學效果,讓人耳目一新。
2.人物性格與境遇的“重構”與“重塑”:平民英雄與“英雄成長”
當下較為成功的動畫電影都對以往神話人物的性格進行了重構、重塑,在其人物性格中添加了當下色彩,并對其人物境遇進行了現代化處理——如今動畫電影之中的人物,大多是有點“郁郁不得志”的平民人物甚至是邊緣人,他們代表的是一群想進行“象征性權力表達”的青年人,更映射著當下社會問題,反思著“偏見”等社會現實。
以《大圣歸來》為例,關于孫悟空的人物性格特征,在文本傳承發展中早有預設——勇敢好斗,神通廣大,正義感十足,有著大無畏的奉獻精神,對待邪惡勢力斗爭、叛逆、反抗。在以往,大圣是較為典型的東方式英雄形象。這就要求,《大圣歸來》的創作既要挑戰在觀眾思維中相對全面化的孫悟空形象,又要正確把握有關文本形象創新性的尺度,避免“絕對新異性”帶給受眾的不適。顯然,《大圣歸來》很好地權衡了創新與傳統的比例——影片中的孫悟空形象變為“年輕”模樣,畫風比例新穎,法力被禁,甚至淪為逃兵,失意,更有幾分落魄;性格上也失去以往的勇猛沖動,變得有些搖擺不定,喜歡逃避,這也是當代社會部分大眾文化心理的象征表達。之后,孫悟空“成長”“覺醒”,給江流兒復仇,決戰魔頭,實現了自我救贖。別出心裁的孫悟空形象設計一改觀眾的固化思維,在孫悟空逐漸擺脫惰性、魔性,不斷回歸神性、復蘇人性的過程中,觀眾產生共情。受眾于此在與電影文本的交流“具體化”活動中,得到了某種平民視角的代指性滿足。
再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為例,這里的魔童哪吒已經不同于《哪吒鬧海》中那個自出生便備受人民喜愛的哪吒了,他因為“出身”上的不足而飽受偏見,以至于在性格上都略微表現出缺陷。哪吒的叛逆式成長貫穿整部影片,受眾見證了“魔丸”的成長、轉變與回歸,并且極易代入哪吒的故事。《白蛇:緣起》將“書呆子”許仙改編為勇敢灑脫、敢愛敢恨的新式人物,相對以往許仙的懦弱、不堅定,此次的許宣,更能促使受眾代入“愛情”中。此外《白蛇:緣起》中的寶青坊坊主,其嫵媚與神秘也能夠滿足觀眾對于妖界的魔幻想象。
綜上所述,本土神話IP形象的創新,突破了觀眾定向“期待視野”;形象重構設計,引發了受眾思考共識;在壓迫危殆的環境下,人物的不斷成長,使觀眾產生共鳴,達到共情,完成指認。
(二)“陌生化”的敘事方式:情節的“陌生化”與場景的想象力美學
關于“陌生化”,周憲教授曾言:“藝術的本質在于通過形式的陌生化,使人們習而不察的事物變得新奇而富有魅力,因而喚起人們對事物敏銳的感受。”
美國敘事學家西摩·查特曼在《故事與話語:小說和電影的敘事結構》一書中認為敘事主要包含故事和話語兩個部分,故事可以分為情節、角色與場景。借如上理論進一步思考,我們也可以從情節與場景兩個方面對動畫電影的陌生化敘事進行探討,探析其成功的內在奧秘。
具體而言,較為優秀的動畫電影都對中國本土傳奇故事進行了適度創新,重構了文本,進行了“陌生化”處理,使受眾產生新奇的觀影體驗——文本的深層意蘊和時代主題相結合,并通過形式的陌生化呈現想象力美學。
其實,與其說是一種“陌生化”處理,不如說是一種當下性轉化。因為這種“陌生”是使受眾在回想起以往情節或場景時感到陌生,但其實卻可以從中感受到一種現實的親近性。
1.情節的“陌生化”
情節的“陌生”即是指情節與以往故事情節不同,卻具有當下時代特色。
《哪吒之魔童降世》相對以往《哪吒鬧海》,增添了諸多“陌生化”情節——靈丸、魔丸“錯轉世”,哪吒、敖丙成朋友,哪吒大鬧生日宴等。如今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幾乎除了故事人物關系與結構與之前受眾記憶之中的關系相似之外,整個情節結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并且,這一新的變化、陌生化的處理,恰恰又指向了民眾集體無意識——無論是哪吒自身的成長救贖、敖丙的家族背景,抑或是申公豹的偏見抗爭,都在極大程度上能夠引發觀眾共情,并促使受眾反思命運、身份、不公等現實問題;哪吒與敖丙的認同情誼,李靖夫婦對于“魔童”哪吒的呵護,世俗偏見所帶來的傷害等,這些具有現實感的情節設置都與觀眾心理貫通,陌生又熟悉。
《白蛇:緣起》的故事來源于“白蛇傳”。多年前,電視劇《新白娘子傳奇》將此故事推向高峰,很多受眾對于白蛇許仙故事的“互文記憶”便是于此形成的,盜取仙草、水漫金山等經典橋段都是觀眾耳熟能詳的情節。但《白蛇:緣起》講述前世“結緣”,將時空結構建構在官吏橫行、妖魔欺世的晚唐末年,并且“報恩原因”“相識”等各個情節點上都有創新。盡管情節發生變化,但白蛇與許仙這種相知相愛、為了彼此大膽犧牲的愛情精神,是具有歷史性與普世性的,也能夠滿足受眾的心理訴求,由此,情節雖陌生,但內核依舊。
2.場景的“陌生化”與想象力美學
場景的“陌生”即是指場景相對以往受眾記憶的奇觀化與夢幻化。《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場景既具有現實質感,又承載著諸多東方美學精神,如意境、寫意、樂舞等。電影中《山河社稷圖》的山水詩意畫卷帶給受眾一種過山車式的美學意境體驗;虛實相間、情景交融、融于天際的總體特質,又指向一種意境美學與寫意精神。而虛擬場景與現實場景的不斷轉變、結合,又表達了一種“陰陽相生”的傳統美學思維。這種具有中國傳統美學精神的場景,不僅能夠加強受眾認同,更具有想象力美學特質,可以滿足受眾奇觀、夢幻、震驚式的想象力消費需求。
《白蛇:緣起》詩意地還原了當時的人物風姿與民族風尚。神秘的朝堂、靜謐的白蛇棲居地等場景,既陌生,又熟悉,并使得觀眾在觀影過程中體會到傳統文化的韻味。影片以桂林山水、廣東洞天仙境等優美風光為自然基調,運用傳統水墨詩意意象,營造了一個個別樣的意境空間與場景。再如《大魚海棠》之中的水下“異世界”,《姜子牙》中的“狐族世界”,《大圣歸來》中的“妖魔異世界”,這些里面也都呈現了諸多相對新穎的場景,滿足了受眾對于“亞文化”的空間化想象,既“陌生”,又熟悉。
三、優秀動畫電影“神話”IP改編的內在邏輯:“弧度性人物”設置與溫情世界呈現
將《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大圣歸來》等較為出名、比較成功的作品放到一起討論后,我們似乎能夠發現它們的一個共性:它們都在以“動畫”“魔幻”的外殼承載現實社會的問題,并最終給受眾呈現一個溫情世界;它們在依靠主人公“弧度性變化”使受眾共鳴、共情的基礎上,滿足了中國受眾社會文化深層的“合家歡”“大團圓”的情感需求。
(一)“弧度性人物”設置滿足受眾“同情式認同”
漢斯·羅伯特·姚斯認為,“所謂同情式認同,是指將自己投入一個陌生自我的審美情感”。觀影過程中,在影院封閉環境下,受眾心理會產生某種沉浸式審美活動——觀眾會“去身份式”地主動接受賞析影片,影片也會“去身份式”地只展示它被觀看的客體屬性,進而促使觀眾與主人公產生休戚與共的情感“共鳴”。
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為代表的優秀動畫電影的魅力便在于此——在觀看此類作品時,觀眾或讀者可以在一種不完美的、較為“尋常”的主人公身上找到自身的“身影”,進而把主人公視為與自己同樣“素質”的“普通人”,從而與他休戚與共,共同成長。
具體而言,觀眾會被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為代表的動畫電影中所傳達的主題意蘊觸動心弦,被主人公戲劇式的命運起伏所打動,以此映射到自己現實生活。觀眾可以從此類作品中得到某種“超越現實”式的“成長”體驗,對照主人公的境遇(令人欽慕或招人唾棄)來實現自我慰藉,進而達到內心情緒的發泄,滿足自己成為英雄的情感消費訴求與想象力消費訴求。
《大圣歸來》便是依靠“弧度化”的人物設置在引發受眾“同情”“共鳴”“共情”的基礎上,促使受眾在“英雄成長”過程中產生了“榮譽感”與“滿足感”。
一方面,影片中“齊天大圣”孫悟空以一種全新姿態(低姿態)走向觀眾——失意落魄,做事猶豫不決趨向逃避。這里的大圣與以往受眾記憶中那個全能、沒有短板的孫悟空形成較大反差。這里的“失意大圣”似乎是當下諸多受眾的映射,具有較大的真實性與代入感——工作、生活、成長都面臨各種壓力,想讓別人“認同”自己,但奈何找不到能夠證明自己的地方。大圣口中的“管不了,我管不了”,體現了大圣內心的漠然,映射著很多觀眾對迷離生活的生活態度,極易引起受眾共鳴;大圣常常提及的“不許再提金箍棒的事”,也在表現大圣對現實的無助,觸及觀眾心懷夢想而“郁郁不得志”“無能為力”的創痛。大圣如今的境遇不禁讓人“同情”,使人共鳴。而這,也是這一作品的精巧之處——它將“神話人物”平民化,以此促使受眾代入角色,完成指認。
另一方面,影片中的大圣還依靠自身成長成為英雄,滿足了受眾(代入角色后的受眾)成為英雄的想象與期待。伴隨江流兒的犧牲,大圣的“神性”也得以復蘇,大圣進行了“重生”。經過大圣不斷的自我認知和成長,他看清楚了生命的意義,并最終“回歸社會”,成為英雄。這一過程,對當下在社會壓力下生存近乎麻木、自我指認近乎盲目的部分受眾來說,無疑具有宣泄作用。
《哪吒之魔童降世》也是依靠“成長”“抗爭”“救贖”“反對偏見”等主題與觀眾達到共情融合。影片中哪吒的成長道路頗為坎坷,“魔童”不公的出身、暴戾的魔性創傷以及“被社會邊緣”的無處傾訴,指代著一群如哪吒的青少年。而哪吒與命運不斷抗爭,“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行為,無疑會觸動如今社會人們“不信命”“自我抗爭”的內心,促使觀眾與哪吒感同身受。哪吒完成自我神性回歸、人性復蘇的過程,無不牽動著觀眾的內心,撫慰著觀眾的創痛。由此,伴隨著哪吒的成長與“走出陰霾”,受眾也相應在觀看中獲得了類似于“重生”的審美體驗。不僅如此,影片對申公豹、敖丙等人物的背景重塑,也貼合現實,代表人物生活的不易,更能夠引起受眾的同情、共鳴與共情。
(二)社會反思與溫情世界呈現滿足受眾“情感共鳴式”想象力消費需求
“想象力消費”是一種與藝術鑒賞、欣賞等心理活動有關的美學呈現,要求作品應該訴諸受眾內在心理,在滿足受眾想象力的同時使受眾產生認同,進而表現出獨特的人文價值與社會意義。
縱觀近年來中國動畫電影,無論是訴諸愛情的《白蛇:緣起》《大魚海棠》,還是主要表達成長、彰顯個性、反對偏見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大圣歸來》,抑或是“追尋自我”“叩問本心”的《姜子牙》,等等,它們都在表達妖鬼文化、風俗信仰、呈現儒道精神、影像轉化“民間亞文化”“神秘次文化”的同時,承載著受眾對真善美、溫馨家庭、溫情社會、個人成長、反對偏見的人文情感消費訴求。至此,我們不妨說,對于動畫電影神話IP改編而言,在想象力的鏈接與轉化下,溫情世界的呈現、泛情化敘事的運用、人文情感的表達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轉化應該是其滿足受眾內在“情感想象”的關鍵因素,也是其持久青春生命活力的源泉。無疑,想象力消費是離不開現實的,也是強調現實的。
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為例,影片不僅關注到了社會邊緣人物的生存境況,而且通過哪吒等主人公的具體行為,傳達出仁、義、孝等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并頌揚了親情、友情、師生情,呈現了一個溫情世界。影片中,無論是李靖替哪吒承受天劫,還是李夫人被打數次依然陪孩子踢球的情節,抑或是屢屢被捉弄的太乙一如既往地感化、教育哪吒,都在營造一種頗具東方意味的、充滿家庭溫馨之感的擬像世界,也都在頌揚著親情、友情與師生情。此種溫馨式家庭的呈現,充滿想象式浪漫主義色彩,是頗為滿足受眾期許美好家庭之想象的。此外,影片中敖丙為“友情”而選擇與哪吒一同經受天雷的行為,表現出他的“義氣”;哪吒為家庭、為拯救百姓而選擇抵御危機、回歸家庭、回歸社會的行為,表現出他的仁、義與孝;百姓因自己過失而深刻檢討并且給哪吒道歉,表現出他們的禮節與智辯;等等實例中,我們都可以窺見影片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傳承與頌揚,也可以從中有所感悟,凈化自己的內心。
再以《白蛇:緣起》為例,影片也在表現“反對偏見”等頗具現實感、話題性主題的同時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內核。為愛化身為妖的阿宣被村民驅趕、孤立,但他卻依然舍生取義,并且以“妖”的身份保證了村落安全,拯救了對妖有偏見的村民。以實際行動堅守道義、仁義、禮節并因此化解偏見的阿宣,似乎是受眾想象的能指,也仿佛給現實生活中處于被孤立、被邊緣的受眾一絲溫意,滿足了受眾內在情感、身份想象之需,這也是一種想象力的轉化與鏈接。
《白蛇:緣起》最后村民紛涌而上自發解救阿宣、白蛇的情節設置,暗示了村民對作為妖的阿宣的認同與感激,也呈現了人間之溫情。當眾人拼盡全氣打開結界看到阿宣早已消逝時,全景鏡頭下神色慌張、疲憊不堪的村民與身后昏暗幽深的山色形成強烈對比,表達出一種“冷景無情人有情”之意味,更于蕭涼悲瑟之境中呈現出溫暖、溫馨。
結 語
時代需要神話,神話不分年代。動畫電影似乎可以稱為“現代神話”,它們既可以滿足受眾奇觀化審美、想象力美學的消費訴求,又可以滿足受眾情感宣泄、情感共鳴的內在消費需求。
《哪吒之魔童降世》《大圣歸來》等作品對于“神話”IP的成功改編邏輯可為今后國內動畫電影的神話IP改編之路提供許多參考、借鑒:在人物造型上,可以將人物造型進行“現代化”改編處理,甚至是新穎的“丑”化處理;在人物身份上,要盡量將人物改編為“接地氣”的普通人甚至是“邊緣人”,以此促使受眾產生“同情”“共情”“共鳴”;在情節改編上,要進行一種“陌生”化處理——與原有情節不同,使受眾“陌生”,但又貼合時代,使受眾“共鳴”;在場景呈現上,改編中要盡量呈現具有想象力美學的場景,以此滿足受眾奇觀化審美訴求;在主題表達上,要在改編過程中注入當下時代血液,在反思社會的同時呈現溫情世界,滿足受眾大團圓、合家歡的心理消費訴求;在人物成長上,要設置有“弧度”的平民英雄,進而使其在成長過程中滿足受眾“成為英雄”的情感訴求。
在后疫情時代,基于受眾對想象、夢幻的審美/接受訴求,我們相信,作為想象力消費的重要類型,動畫電影將會持續發力,為后疫情時代的中國電影市場發展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