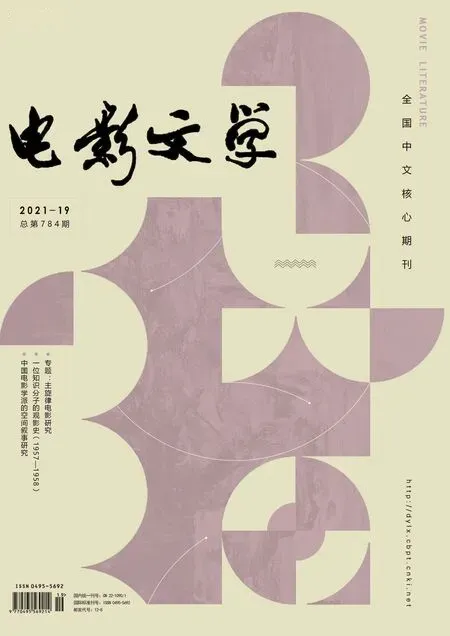扶貧劇創(chuàng)作中情感敘事的得與失
蘇也菲 竇 興(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xué),內(nèi)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圍繞國家精準(zhǔn)扶貧政策實施而創(chuàng)作的扶貧劇陸續(xù)進(jìn)入大眾視野,開始接受市場和觀眾的考驗。借政策紅利的扶貧劇創(chuàng)作是反映現(xiàn)實、重塑農(nóng)村劇經(jīng)典的一次機會,但除了《山海情》《江山如此多嬌》的豆瓣評分在7.5分以上,《歡喜盈門》《一諾無悔》《在我們夢開始的地方》《花開時節(jié)》等劇在收視率與網(wǎng)絡(luò)評價間形成了巨大落差。以2020年4月在央視一套播出的《一諾無悔》為例,“該劇每集平均收視率1.627%,隨著劇情展開收視熱度不斷上漲,結(jié)局周的收視份額達(dá)到7.043%。”但是豆瓣電影中只有868人標(biāo)記看過,且給出5.6分這一沒有及格的分?jǐn)?shù),同樣收視反響不錯的《我們在夢開始的地方》《花開時節(jié)》《歡喜盈門》暫無評分,寥寥無幾且矛盾割裂的短評說明扶貧劇的創(chuàng)作和接受還存在一定問題。為何會出現(xiàn)如此落差?這種落差的深層原因何在?扶貧劇的高收視與情感認(rèn)同是否能夠一致?對于當(dāng)前包括扶貧劇在內(nèi)的新主旋律創(chuàng)作又有哪些啟示?這些問題正是本文試圖解答的。
一、情感敘事突出:農(nóng)村劇創(chuàng)作的雙刃劍
蘇珊·朗格曾提出“藝術(shù)是人類情感的符號形式的創(chuàng)造”這一論斷。任何有意味的形式都是創(chuàng)作者情感的外化,我國古典美學(xué)更強調(diào)情感中飽含內(nèi)在精神的意象之美和情景交融的意境之妙。尤其是深植于人情社會、鄉(xiāng)土中國的農(nóng)村題材影視作品深諳情感敘事的邏輯,即以真實可信的情感推動人物行為的發(fā)展,在動人心魄的情感中置換一定的意識形態(tài),在藝術(shù)鑒賞過程中型塑主體。但是,時代背景下的個人情感是否繼續(xù)引發(fā)唯物主義歷史觀下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在變化的情感結(jié)構(gòu)中是否能保持民族特有的精氣神都關(guān)系到情感敘事的成敗。
從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不流俗的鄉(xiāng)情書寫到反映新世紀(jì)城鄉(xiāng)發(fā)展中農(nóng)民的喜怒哀樂,從史詩性悲劇色彩到地域味濃重的輕喜劇風(fēng)格,農(nóng)村題材電視劇有過幾次創(chuàng)作高峰。但隨著社會文化語境的不斷發(fā)展,農(nóng)村劇也在苦情套路與想象的誤讀中逐漸式微。靠“賣慘”來吸引觀眾、用農(nóng)村家長里短的聒噪來審丑的敘事模式已然失效。扶貧劇的創(chuàng)作要深入農(nóng)村生活,反映社會變革,展現(xiàn)時代風(fēng)貌。廣義扶貧劇的內(nèi)容不局限于本次脫貧攻堅戰(zhàn),也包括我國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具有內(nèi)在延續(xù)性的農(nóng)村致富故事。面臨主題先行的創(chuàng)作形態(tài),如何在人物情節(jié)上做到可親可信,在情感敘事上創(chuàng)新求變以吸引更大的受眾群體,在思想性、娛樂性、藝術(shù)性中實現(xiàn)平衡是創(chuàng)作者應(yīng)該重視的,也是本文所要重點探討的問題。
二、現(xiàn)實觀照不足:戲劇性與真實性失調(diào)
戲劇性的表層是具體環(huán)境中的矛盾事件,深層則是時代中個人內(nèi)心的沖突。如何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藝術(shù)真實中完成人物的矛盾沖突設(shè)置,是反映現(xiàn)實、回應(yīng)現(xiàn)實、觀照現(xiàn)實的關(guān)鍵。
(一)強沖突、弱情節(jié)的敘事模式
扶貧劇本是農(nóng)村題材的一種,它不以流行時尚為標(biāo)簽,也不以懸疑刺激見長,更不能“高大全”“假大空”地示人。身處時代變革中的農(nóng)村生活一定有著鮮活的故事,但是在把真實的扶貧故事轉(zhuǎn)化為易于觀眾接受的文藝作品的過程中,既有敘事優(yōu)勢也暴露出相應(yīng)短板。有些扶貧劇一味追求戲劇性卻懸浮于真實生活環(huán)境,刻意制造矛盾,為了沖突而沖突不僅損壞了真實性也無益于戲劇性的搭建。電視劇是敘事的藝術(shù),一般而言敘事由情節(jié)組成,且在敘事中實現(xiàn)創(chuàng)作者的抒情和表意。矛盾沖突是情節(jié)推動鋪陳敘事的前提,而當(dāng)下眾多扶貧劇中只有高強度的外部矛盾,缺乏真正的敘事情節(jié)。比如《花開時節(jié)》利用小黑羊死亡、網(wǎng)絡(luò)賭博案件、照片謠言、補貼圈套、撞牛、賠錢、棉田起火等一連串情節(jié)來給鄉(xiāng)干部藍(lán)文明設(shè)置障礙,但問題是一個接一個的矛盾走馬燈似的出現(xiàn),每個戲劇性事件內(nèi)沒有進(jìn)一步的一波三折,主人公內(nèi)心深處的矛盾也沒有展現(xiàn),困難就輕松得以解決。《歡喜盈門》第一集便以車向前與岳父共同競爭村主任、違背妻子進(jìn)城生活意愿等激烈矛盾開始,全劇始終以岳丈、夫妻間的情感矛盾為一條敘事線索。劇中又設(shè)置了村民劉桂花和趙彩霞的矛盾,整部劇在嬉笑怒罵的輕松氛圍中完成情感敘事。但在展現(xiàn)扶貧的同時終究還是陷入了“鄉(xiāng)村愛情”的程式中,劉貴祥、田茂山愛慕杜玉珍,志杰、孟珊、曉菲、滿倉的四角戀……家長里短和瑣碎吵鬧的度把握不好也會舍本逐末。
同樣,根據(jù)廖俊波先進(jìn)事跡創(chuàng)作的電視劇《一諾無悔》講述了時任政和縣縣委書記的廖俊波帶領(lǐng)百姓脫貧、造福人民的真實故事。廖俊波為百姓解決難題,與反面角色即童氏家族及其黑惡勢力展開斗爭。在劇中,縣委書記廖俊波一上任就開始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從解決人民群眾的吃水難、垃圾處理到支持小胳美食的發(fā)展,整部劇在主人公與困難的二元對立中展開。電視劇作為一種敘事形式與新聞報道、事跡報告等的差異就在于在真實性的基礎(chǔ)上賦予起承轉(zhuǎn)合的戲劇性。一方面,要從真實生活本身中提取戲劇性,既不能回避矛盾也不能生搬硬套,對矛盾的選取也要具有代表性而不嘩眾取寵。在整體現(xiàn)實主義風(fēng)格中突然出現(xiàn)“喜劇化”設(shè)置就顯得更為唐突,廖俊波的司機曹明宇為了給外商尋找正宗咖啡,偷偷潛入女朋友古語琴的家中被古父發(fā)現(xiàn)的情節(jié)、受童半壁指使的閆佳文暴力強拆時的情節(jié)和表演都過于游戲化和低幼化,缺乏合情合理的解釋,整體風(fēng)格出現(xiàn)違和感。另一方面,對矛盾沖突的展開要講求情真意切。就事論事、對故事不加以深入把握就容易流于表面而缺乏張力。觀眾想看到的是劇中的領(lǐng)導(dǎo)干部如何用智慧和謀略去解決問題,以更大的篇幅去呈現(xiàn)解決矛盾的過程,這才能真正實現(xiàn)突轉(zhuǎn)、發(fā)現(xiàn)等戲劇化敘事。其敘事主線看似是主人公廖俊波一集一集的“升級打怪”,但缺乏情感升華就會導(dǎo)致劇情寡淡無味。敘事的有效性與情感的連貫性不足,就無法滿足觀眾的心理期待。
(二)扁平人物的二元對立關(guān)系
電視劇的情節(jié)與人物是展開敘事的兩個密不可分的要素。情節(jié)的沖突性要依靠行動來實現(xiàn),而行動的內(nèi)在動力則是人物的性格所決定的。不同類型的電視劇會采用不同的情節(jié)模式和人物塑造手段,扶貧劇因其關(guān)涉現(xiàn)實農(nóng)村發(fā)展,應(yīng)在現(xiàn)實題材范疇內(nèi)進(jìn)行審視。扶貧劇雖以真實性、戲劇性、傾向性的情節(jié)構(gòu)成事件發(fā)展,但其成功的關(guān)鍵卻在于典型人物是否引發(fā)觀眾的共情。因為,對農(nóng)村生活的展示容易引發(fā)具有相似生活經(jīng)驗或情感結(jié)構(gòu)的觀眾的認(rèn)同與懷舊,但對于生長在城市中的年輕人而言,塑造真實可感的人物才能引發(fā)更大范圍的情感認(rèn)同。
扶貧劇的主角基本以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干部和年輕的扶貧干部為主,呈現(xiàn)出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化人物。“典型化”是一個老生常談卻又常談常新的話題。典型最初有模型、范式之意,后引申為文藝創(chuàng)作中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tǒng)一,且基于典型環(huán)境而言。但典型人物不一定是圓形人物,圓形人物也未必是典型人物。圓形人物是E.M.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提出的:“檢驗一個人物是否圓形的標(biāo)準(zhǔn),是看它能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讓我們感到意外。如果它從不讓我們感到意外,它就是扁的。假使它讓我們感到了意外卻不令人信服,它就是扁的想冒充圓的。”在扶貧劇的主要人物塑造上我們更傾向于既有豐富的性格又有社會概括性,即典型人物與圓形人物相結(jié)合。
當(dāng)下的扶貧劇已逐漸告別模式化、概念化、符號化的人物形象,但還存在扁平化傾向。比如原本的真人真事在劇中卻沒有感染力,或是現(xiàn)實主義典型人物的創(chuàng)作原則缺乏真實性,又或是敘事視角、細(xì)節(jié)過于單一單薄等。對扶貧劇的主角塑造絕不能是沒有缺點的圣人化,也不應(yīng)千篇一律地強調(diào)家庭與事業(yè)的對立。
有些作品仍舊缺乏對人物豐富性的開掘,而豐富性體現(xiàn)在橫向上人物性格的復(fù)雜性和個性化、縱向上人物心路歷程的變化成長。比如《一諾無悔》《歡喜盈門》以正劇和輕喜劇的風(fēng)格呈現(xiàn)出一緊一松的敘事情境,在展現(xiàn)扶貧工作的同時也加入了家庭關(guān)系的敘事線索,但二者還是少了那么一點氣韻生動的“人情味”。這里所說的“人情味”不僅是接地氣,而更要展示出人物身上的普遍情感。塑造出成功的扶貧人形象有一定難度,主要原因在于其表現(xiàn)對象通常是國家干部和公務(wù)人員,創(chuàng)作者容易把握生活與藝術(shù)的尺度。但其實扶貧工作過程本身就充滿戲劇性,為可看性增添了更大的創(chuàng)作空間。關(guān)鍵在于在典型環(huán)境中塑造出共性與個性共存的“熟悉的陌生人”,實現(xiàn)藝術(shù)形象典型化過程中要注重人物的真實性,這體現(xiàn)在對生活真實的大膽開掘萃取、對藝術(shù)真實的強有力表現(xiàn)、對心理真實的深度挖掘。
三、共情傳播微弱:藝術(shù)性與思想性失衡
(一)題材風(fēng)格的刻板化
脫貧攻堅的故事發(fā)生在我國廣袤的田野鄉(xiāng)間,近年來《青戀》《我的金山銀山》《我們在夢開始的地方》《花繁葉茂》等劇都在劇中展示出區(qū)別于北方的農(nóng)村景象,拓展了建設(shè)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的鏡像。整體上看,敘事角度也不拘一格,有以第一書記的視角來展現(xiàn)脫貧進(jìn)程的真實切面,也有以大學(xué)生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助力鄉(xiāng)村振興的新向度。具體到作品仍舊集中在“生態(tài)布局”“產(chǎn)業(yè)發(fā)展”等幾個方面,除了《遍地書香》以文化扶貧為切入點,《最美的鄉(xiāng)村》以單元劇形式出現(xiàn)清晰聚焦,其余扶貧劇還是呈現(xiàn)出主題先行帶來的視角同質(zhì)化、人物形象缺乏個性化特征等問題。
除了題材內(nèi)容較為雷同,農(nóng)村電視劇一直以相對穩(wěn)定的“影戲觀”為形式風(fēng)格,形成家庭-村落、家國一體的鄉(xiāng)土中國的表征。“影戲美學(xué)觀就是重視電影的社會倫理道德力量和章回小說式的敘事風(fēng)格。”通過中國戲曲與好萊塢經(jīng)典敘事模式的融合調(diào)動觀眾的情緒體驗,善惡分明的程式化、寓教于樂的通俗化奠定了影戲在我國文以載道的美學(xué)慣例。在我國電影發(fā)展初期,帶有影戲觀的市民電影以家庭倫理、社會道德為主要內(nèi)容構(gòu)建普通百姓的思維方式和民族意識。當(dāng)前,大部分扶貧劇還是在傳統(tǒng)的影戲觀的框架下,在通俗易懂的情節(jié)設(shè)置、較為明顯的二元對立模式中深植人類普遍的共同情感,以此引發(fā)對真?zhèn)蔚墓缠Q、善惡的辨識、美丑的判斷。
扶貧劇在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輕型化視角、輕喜劇風(fēng)格中呈現(xiàn)豐富的農(nóng)村故事和豐滿的扶貧人物,在情感敘事和細(xì)節(jié)真實中進(jìn)行情感敘事。但在題材內(nèi)容和形式風(fēng)格上也存在相似的套路模式,造成觀眾的審美疲勞。扶貧劇在內(nèi)容上還有很多表現(xiàn)空間,比如女童失學(xué)、留守問題以及鄉(xiāng)村中人的全面發(fā)展;同時,創(chuàng)作者也要更敢于直面更多的鄉(xiāng)村現(xiàn)實問題,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加大諷刺力度和批判視角。
(二)戲劇情境的懸浮化
引起觀眾共情的另一重要層面是劇中的戲劇情境是否建立起真實感。戲劇情境涉及特定的環(huán)境與特定的人物關(guān)系,而戲劇情境的真實感要通過視聽語言的造型來實現(xiàn)。不同風(fēng)格的作品有不同要求,扶貧劇應(yīng)該遵循現(xiàn)實主義原則對農(nóng)村生活情境盡可能地還原。有些作品采用高、亮、平的視覺風(fēng)格導(dǎo)致生活質(zhì)感的缺失,沒有“毛邊”感的鄉(xiāng)村圖景引發(fā)審美趣味的保守單一。又或者在人聲語言方面失去現(xiàn)實生活的多種層次,使人物對話未能形成有效敘事和情感共鳴。
電視劇敘事強調(diào)通過人物之間的對話來交待前情、人物關(guān)系,實現(xiàn)信息交流、抒情表意。無論強調(diào)農(nóng)村題材還是主旋律屬性,扶貧劇的臺詞都更應(yīng)該貼近生活,樸實無華,尤其是劇中人物對國家政策方針的形象化介紹、對精神信念的具體化表達(dá)都應(yīng)擺脫喊口號、懸空化。首先,人物的對話要形成一定的交流感。扶貧劇所要傳達(dá)的理想境界說出來不如演出來,我們可以站在角色的立場上感受一來一回對話中的深意。其次,劇中人物的臺詞要符合其性格身份和所處的規(guī)定情境。語音語調(diào)、語言習(xí)慣都是人物性格的外化,有利于塑造出個性化的人物形象。富有感染力的話語會提升整部劇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在很多扶貧劇中,不注意人物對應(yīng)的方言或語言風(fēng)格,哪怕一個小小的配角也會對整體真實感起到破壞作用。《山海情》《花開時節(jié)》中出現(xiàn)的方言版普通話,這無疑讓對話活了起來,人物立得住。在扶貧等現(xiàn)實題材的創(chuàng)作中,影像敘事是否貼近生活、還原鄉(xiāng)村本來的面貌對引起情感波動就顯得十分重要。
(三)價值格局的單一化
與近年來部分主旋律電影的口碑票房雙贏相比,主旋律電視劇總是叫好不叫座,其中也存在著極端化的評價。主流意識形態(tài)在大眾文藝作品中如何完成外化于行、內(nèi)化于心,扶貧劇的創(chuàng)作和傳播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如果拿捏不好理想與現(xiàn)實的度,疏于對人物的理想觀念、精神信仰的形成進(jìn)行深層闡釋,就容易失去觀眾與劇中人的心理同構(gòu)。觀眾只能看到作為共產(chǎn)黨員的扶貧干部一直是這樣做的,至于他在什么觸動下和思想斗爭后如此堅定,并沒有給出答案,所以影響到人物形象的豐滿度和感染力。
主旋律電視劇也承擔(dān)著傳播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社會功能,在后疫情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更加堅信人與人之間是可以共情、共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下的人類主旋律隨著社會的進(jìn)步不斷發(fā)展。觀眾以一種藝術(shù)性的方式來建構(gòu)自己和真實世界的關(guān)系,并在這個過程中完成質(zhì)詢,確立主體性。與“‘歌頌黨、歌頌祖國、歌頌英雄模范’成為題材導(dǎo)向,‘社會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成為主題導(dǎo)向”的狹義主旋律電視劇不同,廣義主旋律作品的優(yōu)勢在于與日常生活的關(guān)系密切,它更善于運用人類普遍存在的情感去推動“想象的共同體”的形成。
四、情感結(jié)構(gòu)更迭:崇高感的日常化言說
說到底,扶貧劇是新時期國家主流話語的通俗化表達(dá),通過來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扶貧故事實現(xiàn)情感共同體的建構(gòu)。無論是在傳統(tǒng)的影戲觀影響下的強情節(jié)、重倫理的敘事模式,還是隨著情感結(jié)構(gòu)不斷發(fā)生變化的新主旋律創(chuàng)作,情感敘事終究是實現(xiàn)主旋律電視劇傳播效果的有力策略之一。情感結(jié)構(gòu)是一種“作為感受的思想觀念與作為思想觀念的感受”之間所形成的特定關(guān)系的結(jié)構(gòu),即一個時代中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情感狀態(tài),而且這一過程是不斷變化發(fā)展的,具有時代性、在場性和多樣性。“情感結(jié)構(gòu)”是英國的文化研究學(xué)者雷蒙德·威廉斯所進(jìn)行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的關(guān)鍵詞,他反對精英式的文化觀念,致力于在不同的物質(zhì)生活中創(chuàng)造生產(chǎn)性的文化經(jīng)驗。那么,如何以特定的扶貧故事吸引更廣泛的觀眾,找出扶貧劇所對應(yīng)的且穩(wěn)中有變的大眾情感結(jié)構(gòu)及其情節(jié)模式就顯得十分重要。
“長期以來,鄉(xiāng)村和農(nóng)民作為‘吾土吾民’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國家與國民的形象符碼。”但是,近年來大眾媒體所塑造的農(nóng)村景觀與農(nóng)民形象有脫離真實生活之勢,甚至被遮蔽與被誤讀;黨員干部的黨性也要以人性為基礎(chǔ),既要有具有傾向性的價值判斷,又要注意避免落入窠臼。扶貧劇主流話語建構(gòu)的關(guān)鍵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采用何種英雄史觀的問題。既然脫貧攻堅的價值追求和文藝作品的目標(biāo)都是以人民為中心,扶貧故事的創(chuàng)新就應(yīng)深入廣泛基層,既要情感飽滿,又要邏輯自洽。在集體記憶和情感共鳴中把情感結(jié)構(gòu)轉(zhuǎn)變?yōu)榫窠Y(jié)構(gòu),緊扣時代脈搏、反映社會變遷。
總之,扶貧劇要真正做到從農(nóng)村生活出發(fā),從風(fēng)土人情的細(xì)微處著手,通過日常工作生活中人與人的關(guān)系凸顯扶貧人的事業(yè)初心和精神超越。在大眾文化語境中實現(xiàn)主流話語的意義生成,最終運用情感敘事策略將個人發(fā)展與社會進(jìn)步相結(jié)合。在消費主義、圈層文化中重建大眾文化的公共性與社會性,在日常生活中發(fā)掘理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