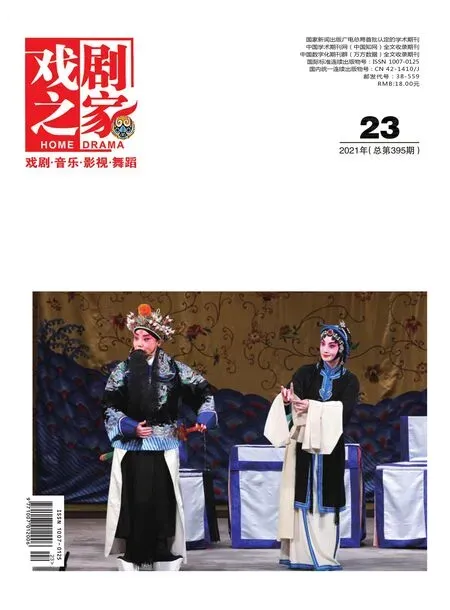從婦女主義視角解讀《紫顏色》
王柏琪
(吉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00)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美國有色文學出現了嶄新的局面,其中黑人女作家異軍突起,蜚聲文壇。長篇小說《紫顏色》是艾麗絲·沃克(Alice Walker)大膽探索產生的成功之作,其以新穎的構思和獨特的手法引起了文學評論界廣泛的關注。它的問世標志著作者在文學創作上達到了新的高度。《紫顏色》這部小說主要探討的是黑人女性問題,它探討了黑人之間的內部關系,即黑人男女之間、黑人社區內部如何和諧相處的問題,揭示了黑人自身存在的弊病并提出了克服弊病的途徑。這部小說不同于其他反復揭示白人與黑人之間不平等關系的作品,具有非凡的現實意義和開拓性的指導意義。
一、雙重意識
“雙重意識”或“雙重恥辱”這一短語描述了作為婦女和少數族裔成員的個人受到的壓迫。對此,格洛麗亞·安扎爾杜提出了穿上保護色的需要,這對于許多有色女性來說是一種生存策略:女性應該像變色龍一樣,在危險重重、選擇很少的情況下改變顏色。她把這種偽裝描述為種族主義文化滋生的一種面具,一種浸透著自我仇恨和被內化的壓迫的面具。小說中的茜莉已經把自己受到壓迫當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小時候受繼父性侵后懷孕,但是生出來的孩子都是“下落不明”。“后來,那小家伙就生出來了。他把她弄走了。我睡著的時候,他把她弄走了,在森林那兒把她殺了。假如他辦得到,把這個也給殺了吧。”從茜莉描述自己孩子的下落時的語言可以看出,她完全把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給內化了。她作為母親,對自己的孩子被“殺死”這件事情也可以無動于衷。結婚后,她面對丈夫的壓迫也不反抗。即使當X 先生的妹妹告訴茜莉要反抗:“我不能代替你斗,你得自己跟他們斗!”茜莉的反應卻是沉默。“我什么也不說,我想起聶蒂,她死了,她斗過,她逃跑。這有啥好處?我不斗,人家叫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可是我還活著。”而聶蒂的教名正是忍耐(Patient),這個名字象征著對一切都逆來順受,沒有反抗意識。
這不僅描述了女性的經歷,也描述了黑人的經歷。黑人女性在與白人女權主義者打交道時,描述了同樣的運作機制。她們被居住地的種族主義文化置于從屬地位,白人婦女則把自己置于對有色人種婦女的支配地位,她們談論自己的處境,仿佛種族和階級的問題是看不見的。索菲婭只因拒絕白人市長的太太要她當傭人的要求,就被投放到監獄里去了。文中有這樣一段描寫索菲婭入獄后的情況:“我見到索菲婭時,我不明白她怎么還能活著,他們砸破了她的腦袋,他們打斷她的肋骨。她不能說話,她渾身發紫,像茄子一樣。”可見一位具有反叛意識的黑人女性在白人強權文化下的下場有多悲慘。因此一向從不低頭的索菲婭,遭受了暴行之后也被馴服了。所以說,即使是具有反叛意識的女性,在白人文化的壓迫下也只會淪為附庸,無法伸張自我。
二、婦女主義
沃克用“婦女主義”而不是“女權主義”這個詞,來形容她致力于結束對女性的壓迫的理想。因為美國的女權主義與種族主義的聯系過于緊密,以至于許多黑人女性無法從中得到慰藉。用沃克的話來說,婦女主義者熱愛女性和女性文化;婦女主義者關注的是以她們自己的方式維護女性的身份和獨立性;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她需要“想知道更多和更深入的知識,而不是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婦女主義者把婦女描繪成一個復雜而完整的人。小說《紫顏色》中的女性群體為自己的性別和自己的“女性氣質”感到驕傲從而獲得解放。
茜莉的脆弱和勇氣,她的謙卑和悲愴代表了她和廣大正在受壓迫的婦女們一樣平凡。而莎格是堅強的,自信的,是女性一直想成為的榜樣。實際上,婦女主義就是姐妹情誼,是婦女聯合起來的觀念和實踐。女性情誼把黑人女性團結起來反抗男性主導的社會。這些黑人婦女之間已經形成一張龐大的關系網,互相聯系,互相幫助。小說中黑人社區內部黑人女性的友好關系力證了沃克的婦女主義。當自己的丈夫X 先生把自己的情婦帶回家養病,茜莉并沒有與之為敵,心地善良的她對莎格百般照顧,終于感動了莎格,得到了莎格的同情和關懷。茜莉日夜思念著為了逃避X 先生的糾纏而離家出走的妹妹聶蒂。莎格不斷給予茜莉安慰和關懷,并幫她找到被X 先生藏起來的來自聶蒂的信。在茜莉對心中的上帝失望時,莎格不斷給予她安慰和啟導,幫助她了解上帝的真正含義。正如莎格所說:“你必須把男人的影子從你眼珠里抹掉,你才能看清一切東西。男人使一切墮落,他坐在你的玉米粉箱上,留在你的腦袋里,在收音機四周。他試圖使你相信他無處不在,你就以為他是上帝了。可他不是上帝。叫他滾開。”莎格得知茜莉被X 先生虐待后,鼓勵茜莉抵制丈夫的大男子主義,要茜莉跟她一起離家。雖然遭到X 先生的反對,但是茜莉不再像以前那樣逆來順受、唯唯諾諾的了。茜莉說:“你是個卑鄙的家伙,是離開你,走出去創造新天地的時候了。”X 先生說她們那樣看起來是無家可歸的樣子,而莎格卻說:“女人為什么會在乎別人怎么想呢?”最后小說中的女性群體相視一笑。“莎格望著我。我們咯咯地笑了。接著,我們縱情地笑了個夠。”到了另一所新的城市之后,在莎格的幫助下,茜莉開始自力更生,逐漸有了自己的經濟來源。“女性的姐妹情誼及女性同盟力量,能夠化解黑人女性孤獨心靈的失語麻木,傳遞友情,重建信心。在愛的感召下,莎格以姐妹情誼勇敢地愛著茜莉,使之認識到軀體的美妙和人間情感的溫暖,終于能夠自信自然地大笑。”茜莉在經濟獨立后,給其他同樣被邊緣化了的女性提供工作崗位,絲毫不吝嗇自己的熱心,懂得與他人分享與感恩。茜莉與其他女主人公最大的不同在于她多了一份責任感,這是救其他女性于水火的責任,體現了女性間的情誼,鞏固了黑人女性間的友愛聯盟,為黑人女性的主權身份認知和構建貢獻了真正的力量。
三、和諧共生
婦女主義不僅主張女性之間的互相幫助,而且還強調兩性間的和諧共處。早期的X 先生道德敗壞,物化女性,依靠買賣衡量茜莉的價值,自己好吃懶做,什么都指使妻子做,甚至凌辱自己的妻子。然而茜莉與莎格一同離開使X 先生幡然醒悟。茜莉離家出走的舉動令X 先生震驚不已,因為他沒有意識到一向唯命是從的茜莉竟然敢于挑戰男性的權威。經過反思之后,X 先生對自己的過往行徑深感懊悔。他將原來私自扣下的來自聶蒂的信件轉交給了茜莉,并且一改往日養尊處優、大男子主義的作風,從之前只知道一味地靠自己的妻子和兒子辛苦勞作過活,到如今整日不辭辛苦地在田地里干活,并且還把自己的家收拾得干干凈凈。X 先生對女性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莎格走后,“X 先生倒好像是唯一能了解我情感的人了”。通過茜莉的描述“現在你跟他說話時,他認真地聽了”,可以看出X 先生放下了大男子主義的架子,表現出了對茜莉的尊重與關懷。“在X 先生自己發生了這些轉變之后,他第一次感到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在這個地球上,并為此感到很滿意。”正是由于性格中兩性氣質的和諧才使得X 先生感到正常和自然,這種正常和諧的狀態正是小說家所倡導的和諧性格的理想狀態。
小說最后的結局也是大團圓。X 先生成為了茜莉的朋友;莎格也不再公開演唱了,回到家和大家一起生活;索菲亞回到家中受雇于茜利;聶蒂也帶著一家人從非洲回來了。本部小說很少提到黑人在白人文化下所受的壓迫,也沒有著重提到黑人如何反抗,而是著重探討黑人內部之間的關系以及黑人的自我身份建構,呈現出黑人內部的弊端,并提出解決問題的途徑——黑人之間應該互相尊重、互相愛護,建立起自身的文化自信和身份自信。
四、結語
美國黑人女性作家艾麗斯·沃克一生都在致力于通過文學作品揭示黑人女性的生存狀態,探討如何進行身份構建以及建立文化自信心等問題,因此富有創造性地提出了“婦女主義”理論。小說中所塑造的女性群體弘揚了女性意識,認為黑人女性應該與黑人男性甚至白人享有相同的權力與地位。小說尋找到了女性如何擺脫父權社會下的壓迫的途徑,即把婦女改善處境的重點放在尋找自我,解放思想上。小說弘揚了黑人民族傳統,呼吁黑人自覺擯棄傳統陋習,增強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拒絕被白人霸權文化所洗腦,彼此間互尊互愛,推動家庭和諧。唯有如此,黑人婦女才可以擺脫被邊緣化、被壓迫的社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