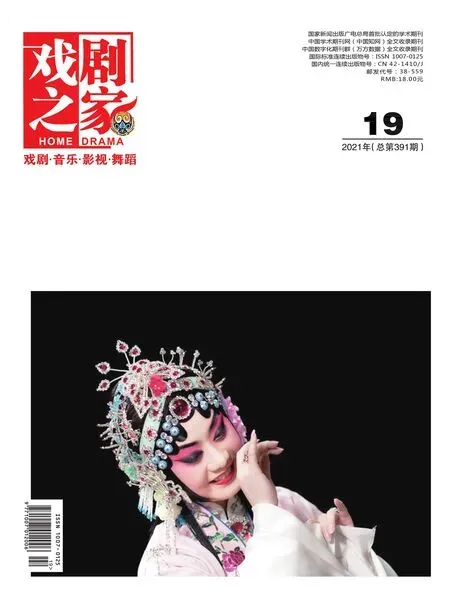從哪吒的“前世今生”看中華傳統形象影視改編中的文化傳承
魯人瑋
(遼寧師范大學 遼寧 大連 116082)
“我是小妖怪,逍遙又自在。”自《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簡稱《魔童降世》)2019年7月26日上映以來,這個離經叛道又玩世不恭、兩手插兜黑眼圈濃重的魔丸哪吒就火遍了大江南北。與以往的人物角色設定上常常以小英雄形象登場的哪吒不同,在《魔童降世》中,哪吒的形象作了顛覆性的改變——但就其本質說來,在不同影視版本的哪吒形象改編中,人性訴求表達和文化精神內核是總體一致的。
哪吒的形象最早來源于古波斯和古印度教的神話,后來傳入中國,隨著本土化的逐漸改良,在唐代末期已經開始風靡盛行。哪吒早在東晉時期就已經有了明確的記載。最初他是以佛教中軍神“那吒”演化而來,擁有三頭六臂,天賦異稟,是百邪不侵的蓮花化身。但需要明確的一點是,“那吒”和“哪吒”并不可混為一談。“那吒”是佛教毗沙門天王(也被稱作多聞天王)的兒子(或孫子),雖然他是“哪吒”的原型,但“哪吒”是中國古人在此基礎上創作出的全新形象,他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仙人,也是道教護法神。所以哪吒是地地道道的中華本土神仙。
有關哪吒的記載主要源于元代宗教神話典籍《三教搜神大全》,它在參照佛經的基礎上賦予了更多世俗化的想象,描繪出了比較完整的哪吒傳說。后來哪吒逐漸活躍于明代的神魔系列《西游記》《南游記》《封神演義》等古典文學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吳承恩在《西游記》中大膽創新,首次將一直以成年形象示人的哪吒改寫成孩童的模樣,而《封神演義》在諸多前人版本的哪吒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將哪吒刻畫得更加有血有肉。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現代哪吒形象基本上都是從《封神演義》中獲取的靈感。現代的哪吒形象經過了多種多樣的改編,但是其基本的人物設定和性格形象并未與古代的形象有太大出入。從漫畫《哪吒傳》、電影《哪吒鬧海》、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于1961年-1964年制作的彩色動畫長片《大鬧天宮》、國產動畫片《哪吒傳奇》、1974年張徹執導的電影《哪吒》、1983年陳方千導演的戲曲電影《哪吒》、電影《我是哪吒》、電視劇《蓮花童子哪吒》等一系列的影視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哪吒的形象更加多元立體化,更符合不同時期的審美需要,而且在改編過程中,賦予他的精神內核也在逐漸增加。
對于《魔童降世》這部電影的橫空出世,各路觀點褒貶不一,有的認為《魔童降世》是國漫繼《大魚海棠》《大圣歸來》《白蛇:緣起》后的又一次崛起,而有的觀點認為不論是前者還是《魔童降世》都是仿照好萊塢大片“三段式”拍攝,不論是劇情還是特效制作都毫無亮點可言。但在筆者看來,不管《魔童降世》中的哪吒相較于之前各個版本的哪吒形象做了如何改變,其依托在哪吒這個中華傳統人物形象上所做的優秀文化傳承和發揚是值得肯定的。以下便從三個方面進行簡單分析。
一、人物設計上的繼承與發展
項戴乾坤圈、身纏混天綾、手提火尖槍、足踏風火輪——如果提起哪吒,絕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就是這樣的形象。“剔筋還父,削肉救母”在最初與哪吒有關的傳說故事中也是令人唏噓不已的片段。在彩色動畫長片《大鬧天宮》和電影《哪吒鬧海》中,哪吒的膽大包天,叛逆頑皮形象達到了頂峰,在設計上濃墨重彩地描繪了哪吒的叛逆英雄史,但其本質來說還是孩童的頑劣胡鬧,雖然具有了反抗意識的覺醒,但是特征并不明顯。在后續的演變過程中,創作者們都有意識地刪減了諸如“鬧海屠龍”、“剔骨削肉”此類較為暴戾殘忍的場景情節,將哪吒聰慧機智、英勇善戰的特點做到最大程度上的強化,哪吒也從“神壇”上走下,變為和普通人一樣的小小少年。
在《魔童降世》中,哪吒形象更進一步貼近現代人的生活和理解方式。影片在保留哪吒最具符號性的人物特點的同時,根據當下觀眾的審美勇敢地打破了常規的形象塑造,變成一個兩手插兜,滿嘴打油詩,愛惡作劇捉弄人卻無比渴望得到他人認同和理解的全新“喪萌”形象。他所具有的“反叛”精神也不再僅僅是孩童的任性妄為,而是從陳塘關百姓的大視角切入,站在整體和大局觀的高度,做出以身引天雷保護大家的決定,成功從混世魔王轉型成為中國本土化的一位“反叛型超級英雄”。
二、故事情節上的延續與創新
在《魔童降世》中,哪吒被設計成混元珠魔化的一部分,而敖丙被設計成混元珠的靈化部分,這樣的兩個角色從設定上本身就相斥相吸,開場的鋪墊已經吸引了觀眾極大的觀看興趣。而且影片通過戲劇化的表現形式,將哪吒出生和成長的故事線進行創新和延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對以往哪吒有關的情節進行了調整和修改。
在《魔童降世》中增添了更多有關李靖和殷夫人之間對哪吒深沉的愛的情節,同時也真實折射出“怪胎”在生活當中由不被他人接受到最終被人認可的蛻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是哪吒的內心發生了質的轉變,陳塘關其他的百姓也從排斥抵觸變成了認可,這也是他們內心情感的蛻變。同時,在故事架構中敖丙不再是與哪吒純粹敵對的一方,他本性善良清冷,是一個背負家族希望和使命艱難成長的少年。他與哪吒與其說是仇視敵對不如說是相互救贖。
縱觀各影視改編的哪吒形象,創作者都將哪吒塑造成能獨當一面的英雄,上天入地無所不能,但似乎總歸缺少了一絲“人情味”。這種人情味不是僅僅拘泥于世俗的情愛或瑣碎紛擾,而是哪吒應該有自己獨一無二的人性表達。雖然他是先佛后道的神祇,但正如佛家語曰,四種慈悲心的第一重境界是“愛緣慈悲”。雖然“慈悲”是轉識成智的、理性的、智慧的“愛”,但這種“愛”的表達也是他與其他神祇所不同的顯著標志。在一代代哪吒的故事傳承中,哪吒“神性”的部分逐漸淡化,而作為“人性”的部分則日漸突出。直到在《魔童降世》中的哪吒,呈現出一個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這種“人性”而非“神性”的概念貫穿于整部影片當中,更具有人文氣息的改編讓觀眾更加感同身受,也能更好地有代入感和理解故事情節的發展。
正如《魔童降世》的主題思想所說,“打破成見,扭轉命運”。“破”與“立”體現在故事情節中則在于:
(一)“破”在《哪吒之魔童降世》打破常規,向我們講述了一個既熟悉又新鮮、既熱血又感人的“中國故事”。他不同于美國好萊塢大片式以一己之力去拯救世界的孤膽英雄,他會因為陳塘關百姓的不理解而痛苦,為得知父母煞費苦心的真相而難過,為擁有畢生知己敖丙而興奮……而且在最后的危急關頭,哪吒并非獨自一人承擔一切,敖丙和太乙真人的舍命相助讓他不再孤單——這也是《魔童降世》與好萊塢電影最大的區別。
(二)“立”在于影片大力弘揚“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斗爭思想,同時也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之中的忠孝和友情。影片在詼諧幽默的語言中穿插了嚴肅認真的思想精神,卻不是填鴨式的灌輸,而是貫穿于影片劇情設計,從人物語言、動作、神態、形象上逐漸滲透,將擔當重任、家國情懷都融入在“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說了才算”的霸氣里。這樣的價值觀傳達,在前人版本的哪吒故事中更加遞進和深入,結合當下優秀的主流價值觀,塑造了一個從目前來看最新鮮也最多元的哪吒。
三、精神文化內核的薪火相傳
哪吒作為少年英雄的形象深受孩子們的歡迎和喜愛。但作為以孩童為主要受眾群體的文學形象塑造不易引起大眾的普遍共鳴,反而是其作為道教與民間信仰的保護神形象更為人所接受。所以如何將“哪吒”文化更加廣泛的傳播,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形象,一直是各大影視版本在塑造哪吒時的關注重點。
哪吒身上強烈的和獨特的“符號化”元素很多,在歷來的故事中也頻頻出現。作為中國本土的道教神仙,他所承載的優秀傳統文化內核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氣概,是歷代文人不斷豐富他的錚錚傲骨。他血氣方剛,無畏生死的英雄形象流傳至今,也在不同時期被賦予了更多的含義。譬如在1964年發行的彩色動畫長片《大鬧天宮》中,結合時代背景看,可以賦予影片更多的意義。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剛剛過去,舉國上下處在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蕭條時期,國內民族問題和階級斗爭問題依舊存在,在這樣內憂外患的嚴峻大環境下,《大鬧天宮》的出現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
在改編的過程中,哪吒逐漸從最初好勇斗狠、亦正亦邪的形象變成現在的熱血小英雄形象。在形象的轉化過程中,一直沒有變過的是“打破成見,扭轉命運”的內核,這也正是哪吒之所以受到人們喜愛的原因之一。《哪吒傳奇》里哪吒的形象同樣生動活潑,他反抗以石磯和商紂王、妲己為首的邪惡力量,與姬發小龍女等同伴一起,用正義戰勝邪惡。在哪吒不斷成長的過程中,他的形象更加立體和多樣,也更加“親民”,容易被人們所接受。而《魔童降世》中,哪吒的形象進一步生活化。
“哪吒”的成功崛起并非偶然。越來越多的中華傳統形象在影視改編中重回大眾視野。相比于神話傳說和文學作品中留給大眾的固有形象,在取其精華的同時糅合現代元素,電影電視中的他們實現了非常大的突破。從影片《大圣歸來》到《白蛇:緣起》,創作者們將目光投向逐漸被淡化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傳統形象,通過結合當下優秀價值觀向國人乃至世界講述最新鮮的中國故事。這些熱血又感人的故事背后離不開人文精神內核的支撐。他們脫胎于歷史,汲取中華文化特有的古典意蘊和神秘美感,在中國電影乃至世界電影的發展中爭得了一席之地。“哪吒”們的成功也證明了這一點:作為流傳至今的中華傳統人物形象,他們不僅沒有淹沒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反而憑借自身特有的文化價值與時俱進,吸收了時代的特點,蛻變成如今的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