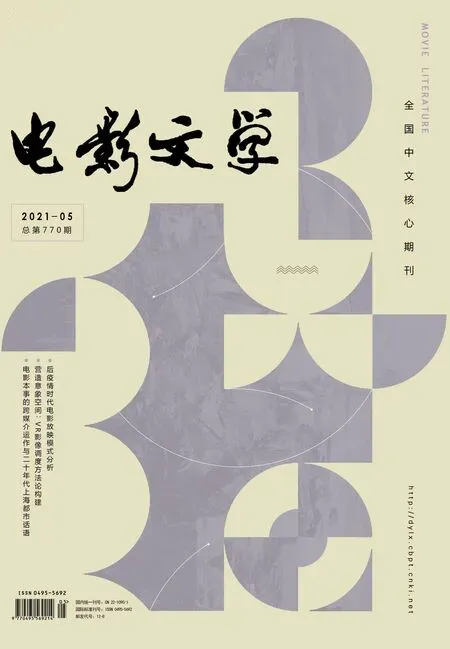觀念與思維:當代神話電影敘事倫理研究
婁欣星(1.浙江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8;2.臺州學院 人文學院,浙江 臨海 317000)
伴隨著工業生產和后現代文化的影響,觀眾對電影的審美準則一變再變,不同時代的文化對電影的敘事情節都有著自己獨特的準則,生產者對于大眾文化敘事做出了選擇,文化傳統的繼承與文化視野的開闊,成為當下文化對電影審美敘事性接受的另一個判斷。當下觀眾處于快速文化發展期,價值觀多元的敘事角度呈現給觀眾視野,電影的敘事審美如何與當下的社會觀眾所契合,是當下電影所思考的問題,神話類電影尤其關鍵。文化敘事的多元,信息量的爆炸和碎片化,導致一方面觀眾在審美接受的同時具有更加多元性的選擇;另一方面公眾在對電影敘事欣賞的同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雖然這一要求是來源于科技的進步與信息的多元,但從電影敘事的本質來看,觀眾的思維與觀念都已經發生了轉換。當代視野下的公眾已經不能簡單地用IP劇改編和傳統文本進行改編的方式來對電影的敘事多元化進行創作,而是對不同題材的神話類電影進行分別解讀,探索出在這一片文化當中不能為當下大眾視野中所熟知的,然后通過一系列劇情和敘事對其按照當下文化進行解讀,與觀眾的審美相一致,在觀眾的視野中留下內心的審美情懷,以此形成情感性的視覺印象。
一、當代神話電影敘事過程中的“戲劇性”結構
何為“神話劇”,有學者對其這樣定義:以神話文本傳說為結構特征的故事片。總體上劇情中應該出現現實生活中看似的“戲劇性”結構,主要藝術手段是挖掘現實生活中能夠有教化性的神話故事,對其進行夸張和變形,以此來形成對廣大觀眾的教化作用。判斷“神話”類型的第一要素就是看其是否具有“人”之外的角色和形象出現,在生活中,大眾文化往往都是集中于群體效應,熱衷于普世價值和社會契約的作用。
“戲劇性”結構是神話故事題材中最常見的表達方式和敘事類別。如影片《三千鴉殺》中就采用了上神傅九云與覃川之間的故事來展開,整個故事情節充滿了戲劇性,主要有以下四點:其一,上神九云的形象并沒有之前其他神仙那樣高高在上,而是我們生活中非常常見的人的形象,相反的香曲山的山主倒是顯現出了原型,這在法力的排行上是不符合的,這種劇情安排就顯得很戲劇了;其二,女主覃川見了九云,知道他是上神,但還是能夠表現出什么都不知道的表情,并對神仙這種身份沒有任何的吃驚,這顯然是和這種角色不符合的,與大眾的審美文化相背離;其三,戲劇性還表現在主人公覃川是一個香餑餑,無論是上官達貴還是神仙九云都對其神魂顛倒,但我們觀看女主人公覃川的形象設置,實在是從她的這些行為當中找不到什么優點,這就將觀眾的視覺審美排外了;其四,還表現在神燈這個角色的安排上,我們能夠看到特別多的人與神仙都做不到的事情,區區一把燈就可以完成,而整個敘事性情節將神燈這條線索完全作為整個敘事性的副線出現,但這條線本身就具有極其戲劇化的色彩。從這些戲劇性情節上就可以看出,將中國傳統文化加入神話劇當中,雖然一方面給觀眾的視覺帶來了新的色彩,引起觀眾在面對新事物中所產生的樂趣,但是從這兩條敘事性線索上來看,這種神話劇在當代觀眾的審美結構中并不符合人們的審美情懷,是因為這些導演從文本敘事到現代性神話都采用一條完整的敘事情節,而現代觀眾在審美上又是多元化的,從這種審美趨向到文化審美認同都有著不同的觀點和看法,因此,現代神話的“戲劇性”結構需要轉換。
從電影敘事性的矛盾方面來看,電影在情節安排上都是以主線與副線配合完成的,主線一般將視覺焦點集中在情節形象角色的行為上,通過其肢體語言將故事情節表達呈獻給觀眾,而副線則不同,是觀眾通過自己的審美文化對其進行解讀之后,對現代性中的文化角色和行為進行理解,由此將其正確地表現出來。“戲劇性”結構正是在這一情況下發生作用的,文本敘事原型已經對主線進行清理了,人物形象與角色的設定沒有留下太多創建的可能性,而是將其進行設定之后,副線主要發揮作用,對其進行變革,增加其視覺化的“陌生化”效果,引起觀眾視覺上的陌生感,從而調動其觀看的興趣。當代神話電影在近年來一直從事改革方面的工作,但很遺憾,所取得的效果甚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沒有進行創新,雖然在市場上出現了國產神話劇改編的電影,但就其根本性的審美沒有什么創新,以至于成為爛片,很少能調動起觀眾觀看的興趣。在后現代影片敘事的娛樂化中,很明顯地知道什么樣的情節是可以娛樂的,什么樣的情節是不行的,每一次敘事情節的改編都是導演對文本敘事的情節化處理,“戲劇性”的創作并不是對整個結構的大力改革,而是對整個藝術審美文化的辯證認識。例如2016年上映的電影《喜氣洋洋潘金蓮》里對電影文本敘事進行了改編,在故事的敘事上采用真假虛實結合的手法,對其中的一些偽劣產品和現實的新聞進行很清楚的編寫,雖然“潘金蓮”這種角色在大眾文化中已經家喻戶曉,但是這個“潘金蓮”卻從側面出發,通過這些荒唐行為對現實中的問題進行揭示,導演將“潘金蓮”這種角兒放在現代進行書寫,某種程度上,文人導演在時代黑暗的角落里對丑惡的現象進行了反叛,其本身就是一種“戲劇性”結構的表達。
二、敘事性神話結構對傳統文本的驅離
“神本文化”的語境傳統給觀眾帶來了一種文化傾向,這種文化一直對廣大觀眾產生影響,無論是政治性文化還是戲劇性的產品介紹,都給當下的觀眾觀看“神話”類電影提供了優良的語境,不會給觀眾帶來一種強制性的情感。國產神話類電影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大力生產,工業化文明和機械化生產都能夠給觀眾帶來許多共振的情感,促進生產的進步從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工業化的持續生產,在經濟方面已經能夠給廣大基層人民提供許多機會和情感,以此來恢復家庭的生活水平,因為很多時候,經濟的發展一直都是社會人民所關注的重點。正是20世紀90年代經濟的飛速發展,造就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極大提高,人們對精神的需求逐漸增大,“神話劇”在當代的創作就借用了這一契機。
任何一種類型電影在敘事性結構上都有著其自己本身獨有的敘事模式,“神話劇”也不例外。從面對人群上主要有兩點:面對底層勞動人民來說,生活的窘迫讓他們面對現實的殘酷借以虛幻的憧憬,神話劇對虛幻未來的構想正好引起了底層觀眾的向往;對于上層人士來說,神話劇題材電影正好能夠引起其未來的消遣,通過這種消遣來排擠對現實生活中的情感壓抑,是一種宣泄的方式。觀眾的消費逐漸將電影觀看的類型進行分類,通過一種政治化的審美進行消解之后,多次的社會改動電影敘事類型已經不是政治的載體,而是文化的一種審美影響,現實當中的觀眾已經不是“消費的市民”,而是對文化的監督者和觀看者,“神話劇”的審美創作要得到觀眾的認可,方可在電影市場中得到證明。
敘事性的神本文化在當代同樣也能夠受用。傳統類型的敘事文本中,對神話故事題材的敘事性已經有了明確的規定,無論是導演還是演員都對其文本進行了解讀,只能對其文本的敘事性更好地呈現,而不能對文本的敘事結構進行改編。而進行后現代神話電影創作時,后現代的觀眾相比之前觀眾有了明顯的不同,他們不需要通過電影的美好敘事來寄托自我情感,也不會對文化敘事的內涵進行延伸,而是將其認定為一種文化的消費,每一個當代觀眾面對神話電影都只是一個消費者,因此,當代神話電影在敘事性上就大膽創新,對傳統文本敘事既定結構進行驅離。神話的政治性與唯一性瓦解,電影在敘事性中對單一的價值導向不再設定,而是以觀眾的審美為中心,不同觀眾對電影的敘事性進行解讀,形成不同的價值審美判斷,形成新的價值訴求。
三、敘事結構色彩中的娛樂化消退
在電影敘事畫面的情感表達上一直都是五顏六色的,每一種顏色相比觀眾都有著不同的情感表達,如紅色多給人“暖”的感覺,在情感表現上多呈現火爆、機械之美,綠色則給人們呈現出一種生機之感。當萬象的東西在被情感的表達吸引之后,情感中的一系列物象都會變成自然界當中的黑白色,那么這幅作品就可能被孕育、升華為世界表達當中的一種。從有彩到無彩是人們在認知過程中的一種方式,吳道子的白描與中國的水墨畫都采用極其簡潔的方式,通過線條的柔軟和力度感進行創作,給人一種力量之感,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了黑白畫面的魅力。如周思聰在《人間地獄》中有幾張更加具有表現力的草圖,畫面完全忽略人物具體的形象,多用粗獷的線條表達,人物扭曲地交織在一起,或許是由于這兩幅作品沒有太明確的主題場景,使得電影文本在創作的過程中可以更加自由地傾瀉內心的悲憤之感。通過藝術的形式表現現實社會中的傾向,讓他們在進行自我創作的過程中不斷地思考,在作品中具有自己獨特的敘事性和自律性,一旦超越了事件和物體本身的自律性,那么這種自信心也會被其所干擾。同樣作為電影文化題材重要的表現形式,黑白繪畫的形式呈現出現象秩序和解構關系,具有其物體本身解構的特征,不僅能夠反映出畫家的生命特點,還包括了整個畫面中的藝術本質,人與自然之間的交合還能夠體現出藝術創作的魅力,而周思聰大膽采用這種黑白關系表現人物的形象,并不是說周思聰在技術處理方面的欠缺,沒有色彩表達的強烈,而是這種方式能夠拉近觀眾與畫面之間的關系。電影鏡頭畫面中采用強烈的黑白對比,形成一種視覺焦點,那么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也能夠親身體驗,置身于畫面中,感受當時戰爭的殘酷和人民的悲哀,從中反映出人性在社會中的演變,以此折射出更多的情感基調。
當代“神話”電影在文本敘事上就借用這些非常巧妙的故事,對其內在情感因素進行闡釋,觀眾在面對這些敘事時,電影畫面中采用的敘事結構和顏色都能夠給觀眾表達不同的審美準則。在后現代文化視域下,電影在敘事性的表現上由于受到審美準則的影響,反“英雄主義”和“無中心主義”都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電影敘事的“娛樂化”,引起后現代神話劇的娛樂化消退。而存在于電影中的文本敘事則逐漸凸顯出來,每一個角色在當下電影中都出現不同的審美觀點,敘事性的典型性得到增強和豐富。因此,后現代“神話劇”的內容敘事性隨著色彩娛樂化的消退,其精神內涵和文本性解構則更加豐富。
關于中國神話劇電影創作的敘事觀念轉變,一方面是來源于其經濟高速發展之后信息量的擴大,觀眾對信息的接收和獲取的便捷性,引發了審美準則的轉向;另一方面,傳統神話劇及其文本敘事的準則在觀眾視野中形不成“陌生感”。對于今天多元化的敘事審美格調,信息的解讀是實現文化共通的捷徑。后現代“神話劇”要對這一現象實現文化共通,就必須在其“戲劇性”結構中尋找能夠讓觀眾產生視覺化陌生感效果的文本,在審美上與傳統文本相分離,從而在娛樂化消退之時豐富敘述性的內涵和文化多元,為觀眾提供更多解讀的可能性,滿足當下公眾的視覺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