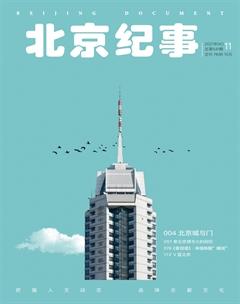東單王府井商脈何處尋?

袁家方
世上從來沒有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追本溯源,王府井的商脈是從何而生,又是怎么綿延而最終形成北京城的商業名街?是偶然還是必然?
元代的“樞密院角市”
清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王府大街”條中稱:“元名丁字街,見析津志。”
從《北京歷史地圖集》中“元大都城內主要商業區”一圖可見,元代的這個丁字街,“丁”字的一豎,直抵大都城的南城墻(大體位置在今王府井南口略南);“丁”字的一橫,則在街北端的“樞密院角市”。圖中注釋說,這個角市的位置,在今燈市口一帶(《北京歷史地圖集·人文社會卷》,侯仁之主編,北京出版集團文津出版社2013年9月,第48頁)。這是元代大都城里距今王府井最近的商業街區。或者可以認為是王府井商業街區有史以來最早的商業生發點。
另外,《析津志輯佚》一書還記載,“哈達門丁字街”有菜市。按照一般理解,這菜市不會在丁字街的南城墻根,當在“丁”字的橫豎相交處,是近樞密院角市,或者,就是角市的組成部分。
明代的“燈市”
明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記載有“十王府”(《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 京師坊巷志稿》,(明)張爵 、(清)朱一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第5頁)清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王府大街”稱:“明建十王邸于此,稱王府街”(《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 京師坊巷志稿》,(明)張爵 、(清)朱一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第75頁)。這時的“王府街”南口,距南城墻已經有二里之遙了。

一條大街的北京商業史

燈市口小胡同
王府街,一定嚴肅、清靜,不會有閑雜人等熙來攘往,更不會有商攤鋪號云集。但明代北京的燈市,在王府街北出現,似乎是在元代樞密院角市的基礎上向東延展。
明時的燈市,有“晝市夜燈”之分。明崇禎八年(1635年)刊印的《帝京景物略》的“燈市”條,用880字記述了明代北京燈市盛況。當時,白天的“市”,商品的豐富多彩,“所稱九市開場,貨隨隊分,人不得顧,車不能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即全國各地的珍異、古董和百貨用物不單是在燈市匯聚,還“旁流”至京城各處的商街店鋪;而夜晚的“燈”,則不只是彩燈的爭奇斗艷,還有煙花的施放和街頭的音樂、歌舞和雜技的巡游表演。
從文中可見,明代的燈市,其地在東華門東,綿亙二里許。在燈市期間,“市樓南北相向,朱扉,繡棟,素壁,綠綺疏,其設氍毹簾幙者,勛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屬也。”豪門貴胄爭相租賃下街市南北的市樓,以為觀燈和聚飲,盡管市樓的租金十分昂貴。這也告訴我們,燈市的所在,已經有著商業街的格局與氣勢。
明嘉靖年間,為了皇宮的安全等考慮,燈市移到南城正陽門外。內城由此沒了年節燈市的熱鬧。今天的“燈市口大街”,在地名上留存了明代燈市的痕跡。
清初的燈市,“懸燈勝處,則正陽門之東月城下、打磨廠、西河沿、廊房巷、大柵欄為最”(《帝京歲時紀勝》“上元”條);而“市”則在琉璃廠興旺起來,所謂“歲朝之游,改集于廠甸”(《天咫偶聞》,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第170頁)。
燈市移走了,但不等于說原來街上的商鋪也隨之而去。在《北京歷史地圖集》中“明北京城內主要商業區”一圖中,可見王府街北年節燈市的位置;還能看到明代北京城從燈市向東,與今東單北大街的商業已經聯系成一個“T”字形。
清代的東單
誰能想到,科舉考試,在北京的鄉試(順天府)和會試,居然影響了東單商業的發展。
夏仁虎先生在所撰《舊京瑣記》中說:“舉子應考,則場前之籌備,場后之候榜,中式之應官謁師,落第之留京過夏,遠省士子以省行李之勞,往往住京多年,至于釋褐。故其時各省會館以及寺廟客店莫不坑谷皆滿,而市肆各鋪,凡以應朝夕之求饋遺之品者,值考舉之年,莫不利市三倍”(《枝巢四述 舊京瑣記》,夏仁虎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08頁)。依夏先生所說,就全市的商業而言,市肆店鋪,值科考之年,無不“利市三倍”。東單商業街上的買賣,自然也不會例外。
除了各地會館及寺廟、客店“莫不坑谷皆滿”外,還有些舉子則是住進了“狀元吉寓”。
據清《天咫偶聞》卷三記載:“每春秋二試之年,去棘闈最近諸巷,西則觀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營、頂銀胡同,南則裱褙胡同,東則牌坊胡同,北則總捕胡同,家家出賃考寓,謂之‘狀元吉寓,每房三五金或十金,輒遣妻子歸寧以避之。東單牌樓左近,百貨麕集,其直則昂于平日十之三。負戴往來者,至夜不息。當此時,人數驟增至數萬。市儈行商,欣欣喜色。或有終年冷落,藉此數日補苴者。”(《天咫偶聞》(清)震鈞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第53頁)
這是說,每逢春秋二試之年,貢院附近的胡同,家家都把妻子兒女送回娘家,騰空房屋,出租給舉子們,美其名為“狀元吉寓”。這種離考場近在咫尺的“民宿”,自然租金也一定很是可觀。這或可說是老年間京城里依托科舉考試而生的“瓦片經濟”了。
因為舉子們租住貢院左近的房屋,他們的日常消費,也促使東單牌樓一帶百貨麕集,物價比平日則要貴上三成。從早到晚,在街上都能看到肩挑手提匆忙往來的人們。那段時候,貢院左近,人數驟增至數萬。市儈行商,欣欣喜色。有的店鋪或攤販生意冷清,就靠這兩三個月的進項,就掙夠一年的挑費。東單商業街的形成與興旺,科舉考試居然是一個重要的促成因素。這倒是寫北京商業空間變遷的書中,或者講述東單商業緣起的書中,都未見提到的。
《天咫偶聞》作者震鈞 (1857年—1920年)“世居京師十二世”,他的一生經歷了清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四朝。其書中記述的“狀元吉寓”,至少是清同治、光緒年間的事。由此推想,地近貢院考場的“狀元吉寓”,其存在或可上溯更早的時候。
東安市場拉開的帷幕
1903年東安市場的問世,一般認為是現代王府井商業街形成的標志。
關于東安市場的選址,朱啟鈐先生在《王府井大街之今昔》一文中寫道:“緣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在肅王領導內城工巡局時,改良交通,修東安門至王府井一帶馬路,首先鏟平御道,安插沿街魚攤菜市。此等攤販自明代向提督衙門租得方丈數尺地畝,搭棚營業,父子相傳,師徒相繼,每月對于地面,向官廳繳納租費。遇有皇上‘出蹕,傳統辦法,一律停市,撤出棚障,挪移魚桶,暫避一時。‘大差一過,仍然蜂擁復來,即小有損失,亦所自愿。忽聞新政,御道需鏟平,另行擴寬,棚攤全行解散。那時不僅攤販反抗,而兩街飯館及一應貴戚官庖亦以鮮魚蔬菜朝夕供應不便,群起恐慌,哄動言官、內監,浸潤上聞。遂有中旨:妥議安排,無任小民失業……步軍統領那桐家住金魚胡同,于地理民情較為明白,因建議以帥府園神機營操場劃出若干畝,收容此項拆除攤販,依次安排。于是輿論歙然,修馬路工程亦如期進展。”(《王府井》,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北京市工商業聯合會、東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北京出版社1993年12月,第46—47頁 )
從朱先生這段話可以看出,東安門至王府井一帶,自明代就有沿街的魚攤菜市,而且是經官方認可,并發有“執照”。即使從明末算起,這攤棚市場也有二百六七十年的歷史了,只是還未見史料揭示其名稱。
御道擴建,攤棚解散,引起商販及各界恐慌,以致“遂有中旨”要求“妥議安排,無任小民失業”。地方上采納了步軍統領那桐的建議,市場攤販遷移至神機營操場安排,東安市場由此問世。正是這一“安排”,使王府井商業的發展,有了一個大核心,拉動了王府井商業街的形成。那些菜市魚攤的商販也由此轉型升級。
東安門大街的沿街市場東移到了王府井北口,仿佛終于找到了自己的生發點,終于拉拽出了王府井金街。
東單王府井
現在人們說到王府井商業街,所指就是王府井大街。其實,早年間一說到王府井,前面不時地要加上“東單”二字,稱“東單王府井”,就像說到前門,總要說“前門大柵欄”。在老北京人的語義中,這是在強調王府井是個商業街區,而不僅僅是一條街。它的范圍大體包括:東單牌樓(東單北大街)、東單二條胡同(東單至王府井的東長安街北側)、金魚胡同、東安門大街東段,王府井大街是這街區的中心。《圖說北京近代建筑史》一書也說:王府井“作為商業區,還包括東安門大街、金魚胡同和燈市口一帶”。(《圖說北京近代建筑史》,張復合編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81頁)
在2021年第4期《北京紀事》刊載的拙文《老商街:一個“六邊形”的述說》中,曾提到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20世紀80年代北京一項課題研究得出結論,認為北京傳統商業街區的空間布局,切合克氏1933年創立的“中心地理論”。那項課題組的學者們繪制了“北京市商業服務業中心地模擬圖”,正是一個猶如蜂窩狀的圖形。由此想到王府井商業街區:
王府井商業街區從元代最初的萌生,即從樞密院角市起步,先是在明代東移到燈市口大街一帶,并在東安門外一帶生長;清代又在東單應“狀元吉寓”生發出興旺點;逮至清末,科舉罷停,“狀元吉寓”消失,但東單商業街已成氣候,始建于1902年的東單菜市場,成了聞名京城的一個新興涉外購物中心;1903年東安門大街攤棚市場撤銷,東安市場問世,王府井商業街形成,并與東單北大街的商業發展“近”相呼應,又有燈市口大街與東長安街北側的商業襄助,再加上東安門大街與金魚胡同的穿插其中,構造出今天東單王府井商業街區的基本格局。
從元代至清末民初,東單王府井商業街區歷經600余年,終于在兜了若干個彎兒之后,繼鼓樓、東四、西四、前門大柵欄,填補了京城商業空間布局基準六邊形的第五個點位。這六邊形的第六個點位則在西單出現,那是其后二十來年的事了。
作者說
總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境寫北京的歷史文化。
北京的文章不好寫。有根有據、扎扎實實,就是努力的目標,也是基準。
竭盡努力就是。還請各界橫挑鼻子豎挑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