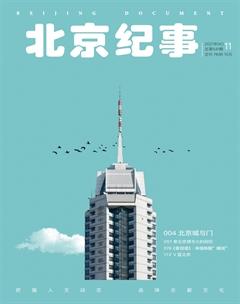老北京煤與火的回憶

燒煤
北京的冬天很長,也很冷——現在仿佛沒過去那么冷了,十冬臘月常看見年輕女子蹬著長筒或短筒單靴很瀟灑地走在街上,有的還光著腿,我們當初穿著棉鞋腳還生凍瘡呢,后來有段時間女人腳上也是鼓鼓囊囊的棉靴。反正那會兒的冬天很難過。公家規定的采暖期有4個月之久,若是生火取暖頭尾總要各延長一段時間,一家人小半年都在圍著煤爐過日子,那種生活迄今難忘。我的長篇小說《受命》以1980年代的北京為背景,其中有些相關描寫,說來均系真實情景。
“這時屋里已經該生爐子了,但上星期天冰鋒忙,還沒來得及裝上。春天拆了爐子,把煙筒、拐脖洗刷干凈,口用報紙包上,吊在房檐底下。得去胡同里找人幫忙,連搪爐子帶安煙筒”“家里已經裝好爐子,是新搪的,生了火,就擺在進門不遠。為了多留下一點熱氣,煙筒一直伸到盡南頭的窗戶才拐出去。葉生說,怪不得窗臺上碼了那么多煤呢。她要冰鋒打開爐蓋,爐火燒得正旺,她烤了烤手,又指著爐臺上擺的一圈烤得焦黃的饅頭片說,看著很香啊,我能吃一塊嗎?”(摘自《受命》第二部第四章)
那時候家里用的都是鑄鐵爐子,新的噴為灰色,久用就成鐵銹色的了。下有爐門,上有爐臺,一大一小兩個爐圈,中置爐蓋。爐臺與爐門相反的一端伸出一個向上的口以連接煙筒,還有個風門。煙筒是鐵皮的,有黑色與本色兩種,后者稍貴,但更經用。煙筒有整截的,有半截的,還有拐脖。


最早燒的是煤球,搪爐子是個技術活。蜂窩煤爐有配套爐瓦,但爐瓦燒裂了,或結砟子太多,更換時也得搪一下,上下爐瓦的縫隙,爐瓦與爐口的連接處,均需用耐火泥抹好。煙筒和拐脖都是一頭稍粗一頭稍細,安裝時細頭朝前,插進下一截煙筒,還要用紙條把接縫糊住,自墻上橫拉鐵絲將其固定,從窗戶高處所裝鐵皮中的圓孔伸出,直達房檐外,稍稍里高外低,口上安個拐脖,以免倒煙。燒煤球時還要掛個鐵盒接煙油子。
家里常備幾件工具:火鉗子、火筷子、火鏟子、火鉤子,都是鑄鐵的。蜂窩煤用火鉗子夾來,添上后用火筷子通一通煤上的火眼。最底下那塊煤燒完,用火鉤子擻一下就變成爐灰,掉進下面的爐膛,用火鏟子鏟走。要是蜂窩煤質量差,多半是黃土摻多了,燒完還是整個的,須將燃著的煤依次夾開,自上面取出。
爐臺上可烤(北京話叫“炕”)饅頭、白薯等。平時火上總是坐壺開水,隨時可喝。爐子圍個鐵皮擋板,烘晾洗的衣物等。春天拆了爐子,煙筒洗刷前須輕輕敲打或在地上磕幾下,以除去里面所積煙灰、鐵銹。煙筒若有沙眼即不能再用,可擇尚完好部分鉸成半截,壞的拐脖安在屋外,廢物利用。
“他身上原本有股戾氣,雖然讓人不太舒服,卻很有精氣神兒,可是那回我見他,已經一點都不見了,整個人看上去——怎么形容呢,就像過去咱們北京冬天家里生的爐子,煤還燒著,底下的鐵箅子給撤掉了。”(摘自《受命》尾聲)
大概20世紀70年代起,我家改燒蜂窩煤,之前燒煤球,這里提到鐵箅子,乃是煤球爐的一個部件。煤球在煤鋪制成,系煤末子摻少量黃土,最早是手搖的,后來改為機制。在窗根底下砌個磚池子以存放煤球,上蓋苫布,免得下雨被水浸泡。還要買劈柴引火。煤球破碎造成的煤末子,攢多了加水和泥,在地上攤成一餅,用刀橫豎劃開,干了即煤繭兒,亦可燒用。煤球比蜂窩煤火力大,還有燒煤塊的,火力更大,當時單位的澡堂子,燒的就是煤塊。
蜂窩煤分大煤、小煤,厚薄不同,另有炭,厚同小煤,煤末子摻木屑制成,生火時置于最下,爐口里塞上報紙點火,先燒著炭,再引燃上面的煤。也可借別人家的爐子燒炭夾回,叫“引塊炭”,系舊日鄰里間常有的照應之舉。20世紀70年代中期有了液化氣罐,在灶上燒炭更為方便。附帶說一句,沒使用液化氣之前,各家夏天也要生爐子,因為要做飯。一般都放在房檐下,只裝一節或半節煙筒,用來拔火。
送煤?
當時煤系定量供應,每家發一煤本,憑此按月叫煤,由煤鋪派人送到家里。煤叫少了,則須自行去煤鋪購買,以平板車或手推車拉回。我家住西頌年胡同時,煤鋪在東直門南小街上,臨近24路慧照寺車站;住紅星胡同時,煤鋪在相隔兩條胡同的干面胡同里。
《受命》初稿有段文字,修改時刪去,不妨抄在這里:
“冰鋒去乘24路汽車。上了車,最后一排盡右邊有個空座,他正需要全車廂這個最隱蔽的位置。沒開出幾站,車突然剎住,站著的乘客紛紛向前沖去。原來是一輛送煤的平板車從胡同口出來,大概因為拉的煤太多,拐彎又沒扶好把,在汽車前頭翻倒了,幸好沒有被撞上。道路很窄,汽車無法繞行,只得等著滿臉黢黑的送煤工從摔了一地的碎蜂窩煤中揀出一塊塊勉強還算完整的。只有他一個人在收拾爛攤子,過往的行人沒有停下幫忙的。”
送煤是個很苦也很臟的活。平板車只能停在院門口,進院后全靠人工搬運。送煤工拿一塊木板搬煤,約摸是一板6摞,每摞6塊。以一家買400塊計,得來回搬10趟以上,整整齊齊碼在各家指定的地方。家里的窗臺,寬窄恰好夠放一塊蜂窩煤的。
“剛才他進門時有些緊張,不小心將窗臺上碼著的一摞蜂窩煤碰倒了,有幾塊摔碎在門口。”(摘自《受命》第四部第七章)
送煤工在搬運過程中將煤摔碎,會以完整的替換,自己家的煤若摔得不太碎,往往拼在一起,對付著燒。
封火與生火
燒爐子最麻煩的是封火。煤得燒旺才能封,不然就滅了;但太旺也不行,又容易燒過頭了。需要根據當下火力大小,決定蓋火是否蓋嚴,中間的孔是否堵上,爐門是否留縫,乃至火眼是否稍稍錯開,各種奧妙簡直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但無論火封得多用心,都頂不了太長時間,所以每晚封火不能太早,亦即無法早睡,除非半夜起來添一回煤。爐子滅了,夜里凍得要命,早上還要籠火,假如趕著上班,就得等下班回來再說,常常為此吃不上晚飯。
平房生火保暖效果往往很差,因為一開門就是冰天雪地。每回來客,家里的人總隨口喊一聲“關門”,生怕把一點熱氣放跑了。屋子很臟,到處都落滿了煤灰。城市里空氣污染得也不輕,夜間,“街上能見度很差,路燈昏黃,天上迷迷蒙蒙,隱約有一彎新月的影子。霧氣比白天濃重多了,能分辨出煤煙、灰塵還有別的什么成分,吸到嗓子眼里有股辣味。”(摘自《受命》第四部第四章)
早晨,“街上零零星星有些行人,有的人家在生火,煙筒飄出縷縷白色的煤煙。”(同上)
當時規定單日倒爐灰,雙日倒臟土,可謂最早實施的垃圾分類。燒爐子最大的危險是煤氣中毒。友人散文家、小說家聞樹國君將近20年前即因此罹難。我也中過煤氣,是高考第一天晚上,次日勉強去考完了,還好不算嚴重,整日頭痛而已。
提到昔日北京胡同里的生活,有人想象得很寫意,我就記起1980年代打開電視,時常聽見一句“住進樓房多幸福”,一時特有感觸;盡管接下來是“美中不足下水堵”——那是一個管道疏通機的廣告。我直到快40歲時才搬進樓房,用上暖氣。但現在聊聊關于煤與火的回憶,滋味卻似乎在甘苦之間。
[編后] 止庵新著長篇小說《受命》(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后,頗受讀者關注。這部作品以1984年至1986年的北京為背景,針腳細密地還原了那個至今還常被人們追念的年代。正如作者所說,“在不超出人物關系與情節的前提下,希望為我生于斯長于斯亦將終老于斯的城市,為已經改變的往昔的生活,記錄下一點什么。詳細描繪那個年代的城市面貌和人們的生活細節,其實干的是類似舞臺布景師和道具師的活兒,布景與道具逼真,可以使虛構的故事與人物顯得更可信一些。也就是說,虛構之中不妨有一點非虛構的因素。”止庵是位“老北京”,他對過去生活的詳細了解,其實遠不限于《受命》中所寫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