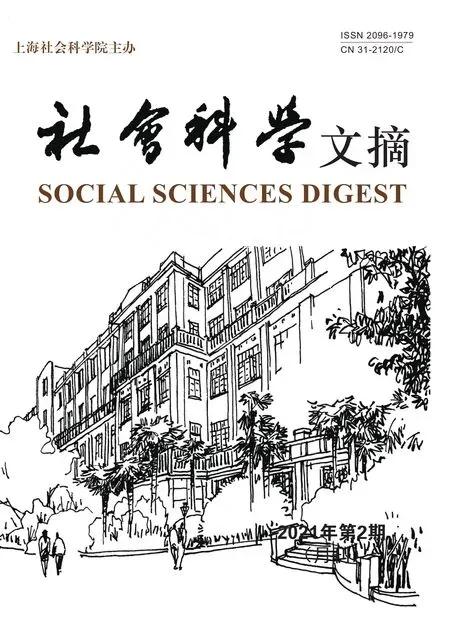論經典傳注的闡釋學意義
文/李春青
引言
在西方,闡釋學(hermeneutics)一詞來自古希臘神話中的赫爾墨斯(Hermes),他是奧林匹亞山上諸神的信使,負責把神的信息傳遞給人世間。中國古代闡釋學的最早稱謂是“傳”,而“傳”也是信使的意思。依《說文解字》,“傳”之本義就是驛使,后來引申為經典闡釋。二者不同之處是,赫爾墨斯是神與人之間的信使,而驛遞則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使。二者的共同之處在于他們都具有傳達、轉達的中介作用。這也正是闡釋的根本意義之所在。任何闡釋都是一種傳達,是在兩者之間的中介。闡釋使單個人成為群體,也使無數具有獨立性的文化因子構成一種文化傳統。因此闡釋是文化傳承的基本手段。傳注作為中國古代的經典闡釋學與西方現代闡釋學有諸多相通之處,也存在不少差異,有其獨特性。以西方闡釋學的觀念和術語為參照,在“間距與之間”的框架下對這種傳注之學予以新的認識,對于我們今天建構當代闡釋學理論來說,無疑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傳注之學的基本形態
對經典的闡釋是西方哲學史的基本言說方式,也是中國儒學史的基本言說方式。在西方闡釋學史上先是形成了文獻闡釋學和圣經闡釋學,后來產生了一般闡釋學和哲學闡釋學;在中國儒學史上則存在著源遠流長的傳注之學。從某種意義上說,傳注之學就是中國古代的經典闡釋學。
對周代典籍的傳注在孔子之前就已經大量存在。呂思勉先生嘗云:“然孔子以前,《詩》確已自有傳,《史記·伯夷列傳》引《軼詩傳》是也。以此推之,《孔子世家》稱孔子序《書傳》,書傳二字,蓋平舉之辭。孔子序《書》,蓋或取其本文,或取傳者之辭。故二十八篇,文義顯分古近也。”呂先生此說是有根據的。現存先秦典籍中有大量“傳曰”之類的引文,歷代注者大多不明其出處,皆可視為孔子前后關于經典的解讀性文字,即所謂“傳”。在中國古代經典闡釋學史上,“傳”是最早的闡釋方式。概括言之,自周公制禮作樂之后,王室史官整理制作了一批記載先王事跡與政教典章的文獻,頗有存檔備查之意,后來這些文獻便成為貴族子弟教育的基本內容,所謂“六藝”是也。可以想見,從西周中期乃至春秋后期,這四百多年中此類“千萬數”的文獻,不僅是孔門儒學之嚆矢,亦無疑是諸子百家之淵源。從寬泛的意義上說,相對于《禮》《易》《詩》《書》之類的西周典籍而言,先秦儒家的闡發性著述都可以稱之為“傳”,如此則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最早的“傳”就應該是孔子的《論語》。在西周史官整理彼時政典、記載周王政績之時,并沒有把這些文獻視為“經”,由于周代貴族秉承敬天法祖、慎終追遠之文化精神,常常把祖先的事跡、言論神圣化,予以格外的尊崇,久而久之那些記載了先王政典和事跡的文獻就成了經典。當那些關于此類文獻的解讀出現以后,便有了經、傳之分。久而久之,前輩的“傳”也漸漸獲得尊崇,被后學加以注釋解讀,從而也升格為“經”。“十三經”中的《論語》《孟子》《春秋三傳》《爾雅》《禮記》《孝經》皆屬此類。
孔子本人屢次聲稱自己一生的志向就是繼承、闡發西周典籍,最著名的提法便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述而》)這表明了他作為一個古代經典闡釋者的自覺意識。這里的“述”就是“傳”的意思。“述”和“傳”都是指對古代典籍的傳承與闡述,與“作”,即“制禮作樂”意義上的創造相區別。
然而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絕非僅僅是傳述古人的思想而已,他們在傳述中融進了新的思想觀念。用朱熹的話來說就是“夫子蓋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于作矣”。為什么孔子之“述”,其功竟“倍于作”呢?那是因為他能夠“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這“折衷之”便包含了他的創造。儒學之所以為儒學并不是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周人的禮樂文化傳統,而是因為它提出了一套新的價值觀而為后世所接受。從孔子以降,闡釋便成為儒家學說發展傳承的基本方式。經典闡釋學也就成為中國古代學術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說到作為一種文體的“傳”,現存最早的一批應該是《詩》之《毛詩故訓傳》(簡稱《毛傳》)、《春秋》之《三傳》《周易》之“十翼”、“禮”之《禮記》、“樂”之《樂記》等。這些“傳”或“記”應該都是戰國后期儒者根據古代流傳下來的各種傳注整理加工而成。比如《易傳》,即古人所謂“十翼”或《易大傳》,與《論語》《孟子》等相近,都是通過具有充分創造性的論說來闡明古代典籍所蘊含的某種道理,即所謂“道”或“大道”“先王之道”,不像漢儒的章句之學那樣逐章逐句注釋解讀,看上去似乎主觀發揮極強,雖名為“傳”,實近于“作”。然而從思想內核來看,這些“傳”的繼承性因素絕不會弱于其創造性因素。雖然孔子的“仁”的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確實具有很大的創造性,但作為儒學內核的等級觀念、官本位思想與周代貴族是一脈相承的。宋代以前儒者常常“周孔”并稱,把周公視為儒學的開山鼻祖,并不是沒有道理的。
相比之下,“傳”的其他形式與“經”的文本關系似乎更密切一些。例如與《易傳》不同,《左傳》乃是通過“屬辭比事”,即敘事來闡明經義的。《左傳》把《春秋》這個“文章提綱”擴充為文情并茂的豐滿文章,在人物與事件的描寫中蘊含了禮樂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念。雖屬于“傳注之學”,卻開了后世“史傳”傳統之先河。《公羊》《谷梁》二傳雖然開啟了為后來漢代經生所熱衷的“章句之學”的形式,但其對《春秋》之“微言大義”的挖掘卻充滿了想象力,其創造性甚至不亞于《易傳》,其“過度闡釋”之處比比皆是。唯有《毛傳》比較尊重經典字句的本義,近乎后世的訓詁之學,至今依然是欲讀懂《詩三百》所不可或缺的參考。
除“傳”之外,較早的經典闡釋方式還有“記”和“說”。《說文》:“記,疏也。”又“疏,通也”。可見“記”字原有“疏通”之義,它是一種對經典的特殊闡釋方式,并不依附經文,而是根據經義作補充性、拓展性闡述。“記”與“傳”有諸多相同之處,不同處在于在用法上諸經各有側重。觀《漢書·藝文志》所載,對《詩》《書》《易》《春秋》各經的闡釋性文字多稱為“傳”“故”“說”“微”等,唯獨對“禮”的闡釋多稱為“記”。“記事”之“記”,即“史記”之“記”,正如“史傳”的“傳”一樣,都是史學傳統的概念,不在我們的討論范圍之內。“記典禮”之“記”,我理解,應該包含對典禮儀式之意義的闡釋,而不僅僅是對禮儀的記錄。
早期另外一種闡釋性文體名曰“說”。《說文》:“說,釋也。”又“釋,解也”。可見“說”的本義并不是說話,而是解釋。其實“說”和“傳”“記”一樣,原本都是一種關于經典的闡釋性文體,但后來都沒有作為文體發展起來。“傳”和“記”都演變為敘事性文體,屬于“史傳”類而歸于“史部”或“集部”了。“說”則成為一種議論性短文文體,通過記一事或一則寓言來說明某種道理,諸如《師說》《捕蛇者說》《賣柑者說》之類,已經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闡釋功能。呂思勉先生說:“傳、說二者,實即一物;不過其出較先,久著竹帛者,則謂之傳;其出較后,猶存口耳者,則謂之說耳。”謂“傳”先而“說”后,言之有據,而謂二者“實為一物”則忽視了它們的微妙差別。
我們再來看“注”,這是一種比“傳”“記”“說”都要后起,與之密切相關又有所區別的經典闡釋方式。“注”的本義為“灌”。清儒王兆芳云:“注者,俗作“註”,灌也,傳釋若水之灌注也。賈公彥曰:‘注義于經下,如水之注物。’主于灌注經義,與傳同意。”按照賈公彥的意思,“注”乃“灌注經義”,是指經義簡而不明,需要注釋方可以解。在張舜徽先生看來似乎“傳”“注”除了出現有先后之外并無其他區別,實則不然。細加考察,二者的區別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傳”是不定型闡釋方式,“注”是比較成熟化、固定化的闡釋方式。即使孔子之前“傳”的漫長歷史忽略不計,就從孔子到戰國之末的兩百多年中,“傳”的形式也出現了多種變化。《論語》《孟子》《荀子》作為“傳”的早期形態,可以說是一種“非文本闡釋”,就是說,這種闡釋不是針對某一種具體文本展開的,而是對某種文化系統的整體性闡釋。因此這種闡釋主要是一種精神闡釋,而不是對具體觀點、概念或詞語的解讀。其二,“傳”比較注重文本整體意義,“注”比較關注字句的具體意義。在這方面,《毛傳》雖然稱為“傳”,實則是比較純粹意義上的“注”,而且是現存文獻中最早的“注”。其他稱“傳”者則大多以闡發大義為主。漢代的經典注釋多稱為“章句”,如趙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辭章句》等,也有不少直接以“注”為名者,如杜子春《周官注》《儀禮鄭氏注》、鄭玄的“五經”及《孝經》《論語》的注本等。
除了傳、說、記、注之外,中國古代傳注之學的具體方式及其稱謂尚有許多,諸如解、釋、故、微、箋、義、論、辨、評、駁、敘、引、章句、義疏、申義、講義、衍義、集義、正義、口義、疏證等,都代表著某種傳注方式,包含著闡釋學意義。但或則由于所用較少,或則因其與傳、說、記、注所含之義相近,故不再一一辨析。
中國古代經典闡釋的意義建構模式
如前所述,一部中國儒學史也就是一部經典闡釋學的歷史,闡釋在儒學思想的發展演變過程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它不僅是一種言說方式,而且是一種思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基本形態與發展方向。前述傳、說、記、注等所代表的古代傳注之學可以歸納為古代經典闡釋之意義建構的三種模式,我們分別稱之為衍義性闡釋、因循性闡釋和修正性闡釋。這三種闡釋模式在中國闡釋學史上各自占有一片領地,并且產生出不同的經學流派。下面分述之。
我們先看衍義性闡釋。呂思勉先生嘗言:“六經皆古籍,而孔子取以立教,則又自有其義。孔子之義,不必盡與古義合,而不能謂其物不本之于古。其物雖本之于古,而孔子自別有其義。儒家所重者,孔子之義,非自古相傳之典籍也。此兩義各不相妨。”這是極為精辟的見解,是對“衍義性闡釋”最準確的說明。所謂“衍義性闡釋”就是指那種以闡釋對象為基點,但具有超越于闡釋對象之上的明顯創造性的闡釋模式:看上去是闡釋已有文本,實則建構新的意義。《論語》《孟子》《荀子》作為對周代經典的“傳”,最突出地表現出了“衍義性闡釋模式”的創造性特征。這些先秦儒家學說,作為對古代典籍的闡釋,是在繼承基礎上充分發揮了其創造性的,通過他們的“衍義性闡釋”,從古代典籍中孕育出了儒學這一具有整體性、獨立性的思想系統,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
這種“衍義性闡釋”的創造性也是儒家“春秋學”的一大特征。一部《春秋》,不管是否孔子所作,其“歷史大事記”的性質是無疑的。王安石稱之為“斷爛朝報”,梁啟超稱之為“流水賬簿”,都不是沒有道理的。然而經過儒家的闡釋之后,其“微言大義”就被建構起來了。而且這種意義建構往往是“層累式”的,是通過闡釋的闡釋或闡釋的闡釋的闡釋來展開的。在今天看來,《春秋》不過是一部編年體史書,極其簡明地記載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重要事件,但在公羊學看來,這部書可是非同小可,是一部體現著“圣人之志”的“撥亂反正”之書,其意義與作用甚至可以比肩功業彪炳千秋的夏禹、商湯、周文武。而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認為:“《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后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后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這里“以《春秋》當新王”也就是“《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的意思,是說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與作用是使這部書承擔起一代“新王”的責任,就像夏禹、商湯、周文武三代圣王那樣。如此,則從文化傳承或者價值觀念體系的角度看,《春秋》接續了“三代”傳統,特別是周人的禮樂傳統,保存了評價是非善惡的基本標準,因此也就當得起一代圣王的歷史使命了。董仲舒代表的《春秋》公羊學是儒家士人意識形態的集中體現。整個“《春秋》大義”的核心——被公羊學總結出來的所謂“三科九旨”之說,都是遵循了這樣一種闡釋邏輯。
通過這一例證可知,“《春秋》三傳”及《春秋繁露》這類所謂“傳”“說”,是很有創造性的。所謂“《春秋》大義”,如“王魯,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之類并不一定是“經”的固有之義,而是那些“傳”“說”等“翼經之作”建構的產物。到了后來的宋學那里,這一“衍義性闡釋”的創造性同樣得到了充分發揮。即如“二程”代表的理學,其闡釋對象主要是《孟子》《易傳》《大學》《中庸》等幾部典籍,是先秦“思孟學派”的延續。其所討論的核心概念,如心、性、誠、敬、理、氣、情、欲等,雖然都是思孟學派曾經談論過的話題,但在理學家這里,無論是意義的深度還是廣度都是他們的前輩無法比擬的。
“因循性闡釋”是指那種更加尊重經典文本之“原義”與作者之“本意”的闡釋文字。“傳”這一文體原本大都屬于“衍義性闡釋”,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毛傳》。這里的“傳”是一種近于漢代經學之“章句訓詁”的闡釋方式,也就是“注”。《毛傳》的隨文釋義乃是因循性闡釋,《毛序》《鄭箋》的主觀評價則屬于衍義性闡釋。這里的“傳”與“箋”都是屬于對詞語的注釋,但一者按照文本呈現的樣子注釋,使難以理解的詞語明白起來,一者則除了字詞釋義之外還有明顯的意義建構。在今天看來,《毛傳》對詩歌的注釋依然是我們讀懂《詩經》作品基本意思的重要參考。《鄭箋》在闡釋詩句句義上也有一定參考意義。至于《毛序》,就詩歌文本闡釋而言,可以說參考價值最小。
“修正性闡釋”是古代經典傳注的另一種闡釋模式,其基本特征是既有章句訓詁的形式,隨文釋義,又有衍義性的闡發,表面上是挖掘文本本義和作者原意,實際上乃是對闡釋對象加以修正,從而建構一種新的意義系統。對于這種闡釋模式,最突出的代表便是朱熹的《四書集注》了。總的看來,“修正性闡釋”可以說是“衍義性闡釋”與“因循性闡釋”的結合。因此,一部《四書集注》,既有對文本固有之義比較符合實際的解讀,也有程朱理學體系的話語建構,二者并行不悖,既是對古老傳統的繼承,又是新的意義之建構,體現出中國古代經典闡釋學的高明之處。